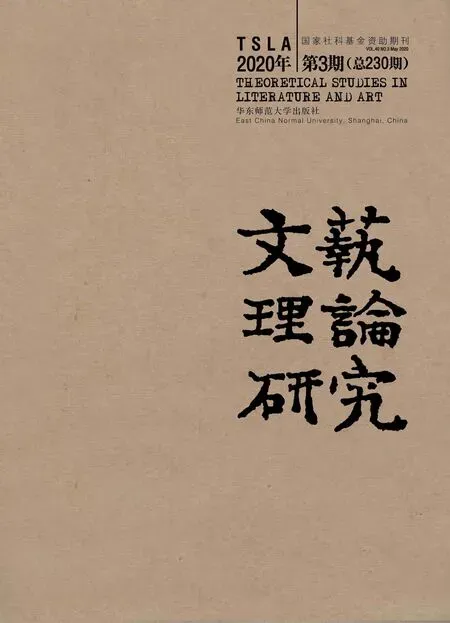“抹除”與“粉飾”
——環境話語的兩大非生態修辭功能批評分析
趙奎英
一、 生態語言學與“生態話語修辭批評”
“生態語言學”(Ecolinguistics)是在語言學與生態學等學科之間形成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它以語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存在著“作為隱喻的生態學”(ecology as metaphor)和“批評的生態語言學”(critical ecolinguistics)兩大基本研究范式。前者主張從“隱喻”的角度理解生態學,并把生態學的概念、原則和方法移用到語言學研究中。他們把語言比喻為一種“生物種”,強調語言的興衰變化存在于它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之中。后者則主張在“生物學”的意義上理解生態學;研究語言在環境(和其他社會問題)的改善和惡化中所起的作用,倡導把語言學研究作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可能途徑之一來探索(Fill43)。無論是哪一種范式的生態語言學研究都強調語言與環境、語言與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對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建構具有重要意義(趙奎英182—90)。其中“批評的生態語言學”或稱“生態語言學批評”又存在著兩個層面: 對由語法和詞匯組成的“語言系統”進行批評的“生態語言系統批評”,以及對作為“語言運用”結果的“話語”或“文本”進行批評的“生態話語批評”。
“生態話語批評”主要是從生態語言學角度對各種(包括文學與非文學)與生態環境問題有關的話語或文本(這里簡稱“環境話語”),進行生態批評分析,指出其中的生態或非生態因素,以促進環境話語的生態化,并最終達到促進生態環境問題改善或解決的目的。“環境話語”是個更具“混雜性”和“包容性”的概念,它與“生態話語”表現出一種錯綜復雜的關系,當“環境”話語意指“環境友好性”話語時,它接近“生態話語”,但大部分情況下二者是不等同的,尤其是從生態語言學批評的角度看。(趙奎英,“從生態語言學批評”11—14)在生態語言學領域,它是指所有與生態環境問題相關的話語或文本,或者說是指所有關涉生態環境主題的話語或文本。這種環境話語既可能是生態的,也可能是非生態的,既可能是文學的,也可能是非文學的。就像一部以自然環境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完全可以體現一種非生態性精神,一部非文學性的環境評估報告完全可以遮蔽環境問題一樣。生態語言學批評的對象,主要就是這種非生態性的環境話語。只是在近來,生態語言學批評的對象才有所拓展,出現了對環境話語的分類,如區分出“生態破壞性話語”“生態有益性話語”(Stibbe,216),并從主要關注原來的生態破壞性話語,拓展到也關注生態有益性話語,前者被稱作“批評話語分析”,后者被稱作“積極話語分析”(Fill and Penz440),但總的來看,目前仍是以“批評話語分析”分主。本文關注的對象也主要是非生態性環境話語,但它完全可以對生態性的環境話語進行批評分析。
生態話語批評,不僅對各種環境話語中的語法現象進行批評分析,也對環境文本運用到的各種修辭手段進行批評。實際上,在環境話語中,各種語法現象最終也是一種修辭手段。這使得生態語言學的“生態話語批評”實際上也是一種“生態話語修辭批評”。就像有學者指出的:“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環境話語及其知識體系的建構離不開特定的修辭方式。這是因為,話語一定是經由特定修辭技巧‘處理’的話語。”(劉濤12)而成為環境話語修辭手段的不只是隱喻、委婉語等通常所說的修辭格,像名詞化、被動語態、無主句等語法手段,也都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修辭功能。因此我們就把從修辭學角度將環境話語作為一種修辭現象進行批評分析的生態話語批評稱作“生態話語修辭批評”。
西方傳統修辭學把修辭看作一種“說服的藝術”。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修辭術的定義可以這樣下: 一種能在任何個別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24)亞里士多德關心的不是具體的“說服方式”,而是發現說服方式的能力。但總的來說,西方傳統的修辭學主要是把修辭看作一種“說服的藝術”。《修辭學百科全書》中說:“修辭學是西方世界最古老的學科之一。從古希臘羅馬到現代,說服的藝術已經被使用、討論和辯論了2400多年。”(Sloane1)但近年來,西方學界對修辭學的理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哲學、文學理論、傳播學等領域的學者重新關注修辭學,將其作為理解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一種方式。”(Sloane1)根據當代話語修辭理論,修辭的目的不只是說服,“盡管修辭學傳統被看作是工具性或者實用性的行為——以勸服他人為目的,但很顯然它還有第二個功能: 有目的地使用語言,塑造(或者建構)我們對世界的感知”(考克斯68—69)。根據這種理論,一切話語修辭都具有建構的功能。
在中國古代語境中,“修辭”即修飾“文辭”或“言辭”,它是與儒家的建功立業和“慎言”觀念聯系在一起的。《周易·乾·文言》中有:“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在中國現當代修辭學研究中,對于什么是修辭,人們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陳望道先生認為,修辭不只是“修飾文辭”,而是“調整語辭”。“修辭不過是調整語辭使達意傳情能夠適切的一種努力”(3)。張弓認為:“修辭是為了有效地表達意旨,交流思想而適應現實語境,利用民族語言各因素以美化語言。”(1)高名凱提出:“修辭就是使我們能夠最有效地運用語言,使語言有說服力的一種藝術或規范的科學。”(80)張志公則認為:“修辭就是在運用語言的時候,根據一定的目的精心地選擇語言材料這樣一個工作過程。”(3)除了“調整語詞”“美化語言”“語言藝術”和“選擇形式”等說法之外,當今也有學者借鑒西方言語行為理論和話語理論提出了一種“言語行為論”的修辭觀。這種修辭觀不同于傳統修辭學研究,它把修辭看成具有建構功能的言語行為。如劉大為在《言語學、修辭學還是語用學》一文中提出: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是一次修辭的建構;效果是由整個言語行為來實現的,而不是由某些個別的修辭手段造成的;語義和語法只能夠在修辭中實現,任何一次語言的使用都是在實現一次修辭行為,任何一個文本都是修辭性文本等(劉大為4)。
我們這里傾向于一種“綜合論”的言語行為修辭觀。我們認為,總體上強調修辭是一種言語行為,與傳統的“調整說”“美化說”“選擇說”等并不矛盾,因為為了達到特定的交際效果,言說者總是需要對語言材料進行選擇、進行調整的,也是需要運用一定的修辭手段、藝術技巧的。傾向于言語行為論的美國環境傳播學者羅伯特·考克斯就認為:“修辭是為有效實現效果,對一切可用的勸服方式進行有目的的選擇。”(68)根據這種新修辭觀,修辭不僅僅存在于文學、哲學或其他社會科學類的話語文本之中,而是存在于所有話語文本之中,當然它也存在于環境話語文本之中。環境話語修辭也不是局部的,而是存在于整個環境話語行為或語言運用之中的。而這里的修辭也不僅僅是為了增強表達效果或潤色詞語,而且具有建構人們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感知和看法的功能。而生態語言學的話語修辭批評,也不是對一個個孤立的修辭手段進行批評分析,而是指向對環境文本中的整個語言運用行為的分析。當我們把“生態話語批評”轉換為“生態話語修辭批評”,對環境話語運用從整體上進行批評分析時,一些環境話語文本背后隱藏的那些非生態性的東西就會被看得更加清楚。我們會發現詞匯選擇、語法手段等在環境話語運用中都在發揮一種修辭功能。鑒于目前的生態批評主要集中在對生態文學文本的生態性進行研究,①我們這里主要對更具有包容性的環境話語的非生態修辭功能進行批評分析,以拓展生態批評的對象領域并展現生態話語批評對于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和現實作用。根據筆者的考察,環境話語的非生態性修辭功能主要表現在“抹除”和“粉飾”兩大方面。發揮“抹除”和“粉飾”功能的所有修辭方式,也可分別統稱為“抹除”修辭和“粉飾”修辭。每一種修辭功能的實施都是依據一些特定的修辭規則或修辭策略的。
二、 環境話語中的“抹除”修辭: 抹除自然存在與抹除施事者
“抹除(erasure)”是環境話語最突出的非生態修辭功能。但“抹除”修辭不只是在環境話語中才使用的,相反,它首先是在其他類型的話語批評分析中被提出來的。英國生態語言學者艾倫·斯提布(Arran Stibbe)指出,“抹除”作為一個術語已經在社會科學的多種語境中被應用。弗若曼(Frohmann, 1992: 365),貝克與艾勒思(Baker and Ellece, 2011: 40),費爾克拉夫(Fairclough, 2003: 139)等人,都曾談到過“抹除”現象(159)。而斯提布則進一步揭開了抹除的使用語境,從生態語言學角度探討它在環境話語中的使用情況。他認為:“生態語言學的一個作用就是探究語言活動中的抹除,檢查什么被文本和話語抹除了,思考該抹除是否有問題。如果有問題的話,那些被抹除的東西怎樣才能恢復到意識中。”他明確將“抹除”界定為“人們心智中對那些不重要或者不值得考慮的生活領域的一種敘事”,認為“‘抹除模式’就是通過其在文本中的系統缺失、背景化或者歪曲,使這種生活領域變得不相關、邊緣化或者不重要的一種語言表達方式”(159—60)。斯提布不僅對“抹除”進行了明確界定,還提出了抹除的一些語言策略,“如被動消極、轉喻、名詞化和下位詞等”,并具體研究了一些“抹除”類型: 如“空缺”(void),“掩飾”(mask)和“淡化”(trace)(163—64)。
斯提布對“抹除”的探討無疑是富有啟發性的。斯提布雖然提到“抹除”有時需要通過語言策略來實現,但他與最初的抹除話語分析者一樣,沒有把“抹除”本身明確視作一種修辭功能。并且斯提布對“抹除”的界定,似乎主要是參照著抹除“自然世界”的環境話語來進行的,而沒有考慮到抹除施事者的情況,但環境話語中的抹除是“雙向運作”的,一個方向是對環境話語中的自然存在的抹除,另一個方向則是對環境話語中的施事者也即人的抹除。前一種抹除,壓制或剝奪了自然的主體地位,把自然存在看成不相關的、邊緣化的或不重要的,或者是為了隱藏自然正在遭受的東西,以免引起人不快的感受;后一種抹除則主要是為隱匿或模糊環境事件的主體,規避環境責任或讓人逃避于道德評價之外。而每一種路向上的抹除都是有它慣用的修辭方式或修辭策略的。總的來說,抹除施事者有兩種主要修辭方式,即“被動語態”(無主句)和“復雜名詞化”。
(一) 抹除施事者的兩種主要修辭方式:“被動語態”和“復雜名詞化”
所謂“名詞化”(nominalization),又稱“名物化”,是指從動詞或其他詞類形成名詞,或把一個包含著施事者和施事過程的及物小句(transitive clause)轉換成沒有施事者和施事過程的名詞短語的語言現象。一個完全的及物小句通常包含著“施事者”(agent)、“施事過程”(process)、“受施者”(patient)以及表示時間地點的“情境”因素(Circumstances),轉換成沒有動詞的名詞短語后,施事者和施事過程的信息就會喪失,或者說就會被“抹除”。如從及物小句“偷獵者毀滅了一些物種”到名詞短語“一些物種的毀滅”,從及物小句“探險者毀壞了熱帶雨林”到名詞短語“熱帶雨林的毀壞”,就可看出名詞化的這種抹除特征。
對于“名詞化”的抹除功能,其他學者也有談到過。但我們這里要說的是,并非任何意義上的名詞化都發揮這種抹除功能。“名詞化”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的類型。只有那種“復雜名詞化”才發揮這種強有力的抹除功能。那種最強有力的“抹除”,也即“刪除”(delete)。德國語言學家榮格(Matthias Jung),曾把語言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區分成兩種類型:“原始人類中心主義”和“意識形態人類中心主義”(275)。我們認為,除了那種出于語篇的內在要求和為了知識的有效積累而不得不使用的“描述性名詞化”外,名詞化也可以區分出“原始名詞化”和“復雜名詞化”兩種基本類型。所謂“原始名詞化”,是指那種主要由人類自然的身體或心理狀況,由原始的、內在的思維或認知模式所決定,或者由返歸原始混沌狀態的深層文化心理傾向,或由對某種非實用的詩意審美效果的追求所驅動的名詞化。在文學語言尤其是在詩歌語言中,這種類型的名詞化是會經常遇到的,但它發揮的不是非生態性抹除功能,相反,是一種生態審美功能。因為沒有人類施事者的原始名詞化,降低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程度,消解了小句的線性句法模式,更適合呈現一種動態的、整體的、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生態世界觀(趙奎英113—22)。如英國意象派詩人龐德的著名詩歌《在地鐵站》,“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人群中這些臉龐的隱現/濕漉漉、黑黝黝的樹枝上的花瓣),第一句中的“apparition”就屬于這種“原始名詞化”。
所謂“復雜名詞化”,主要是指那種出于某種更為世故復雜的實用目的而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具有明顯的意識觀念建構功能的名詞化。這類名詞化主要存在于環境、科技、商業、法律、新聞等非文學性的正式文體之中。具有“抹除”功能的正是這一類名詞化。如果依據斯提布從生態功能對三類話語的分類,我們可以說,描述性名詞化是“生態中立性”名詞化,原始名詞化是“生態有益性”名詞化,復雜名詞化則是一種“生態破壞性”名詞化。對于這類名詞化,批評話語分析的創始者弗勒(Roger Fowler)及其所領導的“東安格拉大學批評話語分析小組”,曾概括出它的四種否定性功能: (1)刪除施事者(deleting agency);(2)使過程物化(reifying);(3)假定物化的概念為施事者;(4)維護不平等的權力關系(785)。其中第二、第三種功能,都是與核心功能“刪除施事者”相關的。第四種功能則是指科學文本中那些有意讓科學語言更像科學語言的“名詞化”,有助于維護學術精英的權力地位,促使“不平等的權力關系”的再生產。
我們這里主要看一下“刪除施事者”。它是指名詞化能把一個有施事者行為的陳述轉變成一個沒有施事者行為的陳述。經過這種轉換,本來是由施事者實施的行為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自主發生的過程,主體施事方面的信息就被刪除了。如在“氣候的變化”這個名詞化短語中,人類行為對氣候改變的影響方面的信息就被過濾掉了,第一次看到或聽到這樣的短語,很容易把它看作像“季節的變化”“地球的運轉”那樣自然自發的過程,而不知主要是由人類行為所致。以至于今天有人認為“氣候變化”是騙局,除經濟利益之外,或許還與這一名詞化短語抹除人類施事者有關。盡管“空氣的污染”不像“氣候的變化”那樣隱蔽,在聽到這一短語后,可以把“人類的活動”導致空氣污染這一省略的施事者信息補充上,盡管語言學上的主語可以被指定,但社會主體仍然是模糊的。因為人們補充上的主體往往是“人類”“人們”“我們”之類抽象的、普遍的、不確定的主體,但這種向普遍主體的擴大實際上是把環境責任擴散或模糊了。因為很明顯,對于空氣污染來說,機構和個人、不同群體或個人應負的責任是不同的。但有些機構或團體,在他們的環境報告中,為了逃避環境責任,會有意識地隱藏或模糊行為主體,處心積慮地使用名詞化的手段而達到他們隱蔽的目的。
名詞化“使過程物化”,并“假定物化的概念為施事者”,是把本來由人參與實施的過程變成非人化的、客觀化的東西,讓人類的行為、事件看起來是一個自然或自動發生的客觀進程,與人類沒有關系,這實際上也是對施事者的變相刪除。韓禮德曾把名詞化看成一種“語法隱喻”,在環境文本中,它實際上也是一種修辭方式,這種修辭方式的主要功能就是抹除施事者,達到規避或模糊環境責任的目的,這是不利于環境問題解決的,因此也是非生態的。由于這種名詞化在環境文本中運用的廣泛性,對于生態話語修辭批評來說,具有典型性意義。
環境話語抹除施事者,還有一種重要的語法修辭手段,那就是“被動語態”。瑪麗·卡恩通過對《野生社會簡報》十年合集中隨機抽取出來的文章進行研究發現: 在有關動物實驗、研究和經營的科學文獻中,近乎總體上缺乏一種主動語態。通過使用被動語態,研究者讓自己的行為超越于“道德責任的王國之外”,表達出一種“生物學家的冷酷,枯燥無味的客觀性”,“對死亡和屈辱進行不受感染的凝視”。“因為在這種被動結構中,行動者(actor)已經消失了,——行為者(doer)與其行為之間的關系被切斷,——行為者被沒有行為力的、封閉的行為本身所代替,行為明顯在沒有人類投入的情況下完成了。”(Kahn242)為了更好地呈現科學文獻使用被動語態的情況,我們轉錄《野生社會簡報》中用郊狼對一種致命復合劑1080的毒性進行實驗的報告中的一段:
5只郊狼被安排服藥(dosed)(口頭話即被強行填喂),用來模擬一只郊狼可能需要接受多大劑量的田地用藥1080才能被控制。[……]等到死了之后,這些狼會被剝皮,去除內臟,并被分割。所有的肌肉組織都被聚集在一起放在一個商業用的絞肉機里磨碎。內臟,不包括腸胃,被做相似準備處理。這些被磨碎的肌肉組織被貼上標簽,分開包裝,并被冷凍起來用來喂以后被實驗的動物。(Kahn242)
這篇報告共5段。前4段都像這段一樣使用被動語態,施事者一直隱而不現,好像整個實驗活動都是在不受人操控的情況下自動進行的。但有意思的是,到了最后一段“致謝”部分,在實驗活動中一直沒有出現的施事者(“我們”)終于露面了。但他們的感謝不是給予他們正在實驗的活著的、呼吸著的、有感知的生命,而是給予為“毒死”動物和為“處理”動物提供資助的兩個人。如果說在前面,施事者——人被刪除了,在這里,受施者——動物又被刪除了。就像卡恩所說的:“科學呈現在動物研究文獻中的的確是一種被動的沒有靈魂的聲音,這種聲音可謂行進在實踐責任的道德王國之外的思維模式的完美反映。不同于在致謝中,沒有一個人,‘我’或者‘我們’——男人,女人,科學家或生物學家——作為行為的主體,作為行為的行為者出現。傳統的責任位置,句子的頭腦部分,被授權給動物來代替。”(242—43)由此可以看出,科學文本如何通過使用被動語態,進行一種雙向刪除,既在必要的地方成功地刪除人這種施事者,從而讓行為者逃避于道德責任的王國之外,又在必要的地方刪除受施者,刪除動物的存在,把它們作為不重要的或不值得尊重的東西忽略掉,以便把人作為更高的存在者突出出來。
與英語中的科學實驗報告大量使用被動語態相通有所不同,我們發現國內學界的中文動物實驗報告則經常使用“無主句”。無主句作為一種語法省略現象,雖然不同于被動語態,但在刪除人類施事者方面的功能卻是一樣的,它也讓實驗看起來是在沒有人類參與的情況下自主發生的。如我們看到的一篇《C P N顯影粘堵劑動物實驗報告》,該報告有長達7頁的篇幅,詳細記錄了實驗材料與方法、實驗過程與結果、有關實驗的討論與結論,但只是在論文摘要中,在有關實驗的“討論”和“結論”中出現了三次“我們”,其余部分基本上都是用一種無主句,或者以動物器官、部位作為主語進行描述的。試看下面的兩段話:
經解剖檢查,手術部位正常,腹腔放置粘堵劑處腐蝕嚴重,呈明顯的化學性炎癥反應;肝臟呈“檳榔肝”樣中毒性病變。心、肺、腎等則未見明顯的病理性變化。經自傘端向輸卵管內注生理鹽水試驗,證明輸卵管已完全堵塞。
79 一 01號兔死亡原因分析后,認為與氯仿中毒有關,乃以二氯甲烷代氯仿作為溶劑,得到了CPN 一 40、CPN 一 42等配方。用CPN 一 40和CPN 一 42粘堵劑實驗結果,受試家兔術后精神良好[……]。(劉詩峰31)
是誰給家兔做的手術?是誰在對手術部位進行檢查?是誰在向輸卵管注入生理鹽水?是誰分析家兔死亡的原因,又調整溶劑配方進行了新的實驗?這個施事者一直是隱匿著的。一直到實驗結果出來以后,需要對其討論并得出結論時,“我們”才出場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哪種溶劑是合適的。但整個實驗過程都好像是在沒有人類施事者參與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據我們對其他幾份中文動物實驗報告的考察,這種通過無主句抹除人類施事者的情況是具有代表性的。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無主句”也有不同的類型,無主句在不同語境中發揮的功能也是不一樣的,詩歌語言中的“無主句”,對生態審美效果的生成同樣具有重要作用,因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對物、對自然的操縱或控制,使“物之為物的本然本樣”“自然自化地興現”(葉維廉116)。
(二) 抹除自然世界的各種修辭方式: 物體化與擬人化,上位詞與下位詞
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環境話語中的抹除是雙向的,它既抹除人類施事者,也抹除動物、植物和自然世界本身。環境話語對自然世界的抹除有各種修辭方式,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對修辭方式便是“物體化”與“擬人化”。所謂“物體化”也就是通過重新命名等修辭手段,使作為生命實體的存在物成為一種沒有生命活力的抽象“物體”。生態女性主義研究者卡蘿爾·亞當斯曾經說:“在消費者參與吃掉動物之前,動物已經通過那種重新命名死尸的語言缺席了。”(Adams136)澤伯拉·伯曼把這種現象稱為“缺席的指涉物”。認為“這種缺席的指涉物允許我們去忘掉作為獨立實體的動物;也允許我們抵制使動物出場的努力”。從豬,到尸體,到肉,到火腿,暴力缺席了,死亡缺席了,豬作為一種生命實體也缺席了。“豬”成為了消費的對象(Berman264)。而這樣的“缺席”,讓我們在消費動物時不再有負罪感。因為通過語言轉換,死亡、暴力、動物實體都看不見了,也即被抹除了。通過這種抹除性的重新命名,那些令人不快的東西被隱藏起來了,人類對動物的暴力也在隱蔽中持續下去。
而這種重新命名,也是一種修辭方式。正是這種修辭,使動物從我們的語言中缺席或被抹除了。動物在這里缺席的原因,正是環境話語通過修辭手段使之成為一種離生命存在越來越遠的沒有生命活力的抽象“物體”。這一修辭路徑整體上可以稱作“物體化”,亦即把作為生命實體的存在物命名為沒有生命活力的抽象物體。而“物體化”正是環境話語抹除生命存在物的一種主要修辭方式。而這種“物體化”抹除,在生物科學話語、野生動物經濟貿易之類的話語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野生動物經濟貿易之類的話語中,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如我們看到的一篇相關文章,在這里,生物概念幾乎都是抽象概念,如動物、物種、動物活體、死體及衍生物等,很少提到具體的物種名稱,即便提到動物名稱時,也沒有把它看成有生命的生物,而是可交易的“物品”。如“尼羅鱷制品”“鱷魚皮制品”等。(王文霞等2—3)這正是通過“物體化”對動物進行抹除的典型例證。
環境話語對動物的抹除,不僅通過把動物“物體化”,讓它不再作為生命實體在話語中出場的方式實現,而且還通過把動物“擬人化”,不讓動物作為動物,而是讓動物按照人類世界的文化來活動的方式實現。而環境話語中的這種“擬人化”修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在文學話語中,更是比比皆是。在這里“動物世界被表現為高度戲劇性的領域,充斥著緊密關系的家庭、外部的沖突和緊張的競爭”,“就絕大部分而言,對動物世界的表現,傾向于強化人類世界中社會等級的社會概念和文化概念的主導地位”(Pierson710)。但無論是把動物命名為沒有生命的物體,對之進行“物體化”,還是為動物賦予人格,把動物“擬人化”,實際上都不讓動物作為它所是的動物存在,嚴格說來,都是對動物存在本身的抹除,都具有某種非生態性。因為最原初的生態倫理學原則即海德格爾所說的“讓存在者作為它所是的存在者存在”。而“語言的使命是在作品中揭示和保存存在者之為存在者”(海德格爾40)。而那種“揭示和保存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語言,正是一種詩意的語言、本質的語言,也是真正的“生態的語言”。阿倫·奈斯的“深層生態學”也正是受到海德格爾的“讓存在者存在”(let things be)的觀念影響(Zimmerman260)。由此來看,不能讓動物作為它所是的動物存在,也即不能讓存在者作為它所是的存在者存在,是違背深層生態倫理學原則的。但無論是“物體化”還是“擬人化”都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都是抹除動物本身、抹除自然本身的修辭形式,都不能讓動物、讓自然如其所是地顯現出來。只是由于把自然比擬化為人,有助于提升自然的主體性,并且有助于從人的角度理解自然與人之間的連續性,所以對其生態意義不能完全否定。但擬人化中所隱含的人類中心主義特征,以及它對自然存在本身、動物存在本身的抹除也是不容忽視的。只不過這種抹除屬于“弱抹除”罷了。但弱抹除也是一種抹除,它也是不讓動物、不讓自然按它自身所是的方式而是按人的方式去存在。這就像“以己養養鳥”而不是“以鳥養養鳥”那樣,看起來人給動物像人一樣高的待遇,但實際上是把人的東西強加到動物身上,并沒有給予動物那種“任物自然”的存在論意義上的最高尊重,仍然是不利于動物、不利于自然本身的存在的。
抹除動物、植物等自然生命存在的修辭方式有很多,除了把作為生命實體的動物“物體化”和“擬人化”外,另一個重要的修辭方式就是使用“上位詞”和“下位詞”。所謂“上位詞”(hypernym)又稱“上義詞”(superordinates),是指概念上外延更廣的主題詞。例如:“生物”是“植物”的上位詞,“植物”是“花”的上位詞,花是“牡丹花”的上位詞等。當一種生命事物不是用它本身的名稱,而是用外延更廣的上位詞來加以表達時,它就會變得更加抽象,就會離它本身的生命存在更遠,也可以說它自身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被“抹除”了。這種情況在生態系統評估報告之類的環境話語中是很普遍的。因為生態系統評估報告經常用上義詞來代替物種名字,如:“鳥類”“哺乳動物”“兩棲動物”“動物”“物種”“動物群”“生物”等。這種逐步增進的上義詞使得關于自然的話語越來越抽象。如“獾”這一名稱可以帶給人們這一類動物的很多特征,但到“生物”時就抹除了這一類動物特征而只保留了生命體特征。而“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要素”“物種的組合”“生態復雜性”“生態系統”則是更高級別的抹除性抽象詞語。“這些詞語代表了各種各樣的動物、植物的集合,但卻將可想象的個體深埋于抽象之中。”(Stibbe170-71)我們知道,生態系統評估報告總結生態系統的狀態,目的是為決策者保護這些生態系統提供有用的信息。生態系統評估報告的話語當然是關于動物、植物和自然環境的,如果報告的話語能讓人比較真切地認識到自然世界的價值,并且強烈地感受到一些具體的物種,如松鼠、麋鹿、橡樹等,那么人們則更傾向于尊重自然世界并努力去保護自然世界。因此就需要報告的話語不僅使用抽象的上位詞,還能命名具體的物種,以吸引人的想象的方式栩栩如生地展現植物和動物,激發人們的倫理反應,以促進人們對自然世界的熱愛和尊重。
使用具體生命存在物的上位詞可以抹除具體生命物的存在,當“將活著的生命設定為無生命物體的并列下位詞(hyponym)”時,也可以起到這種抹除的作用(Stibbe171)。當我們這樣來談論“鯨”時,如“鯨”“哺乳動物”“生物”,“鯨”的表述雖然越來越抽象,但依然停留在活著的生命體的語義范圍之內;但當我們說“鯨”“水”“石油”和其他“資源”時,“鯨”與“石油”這種無生命體共同作為“資源”的并列下位詞,“鯨”作為一種活著的生命體特征就傾向于被抹除了。“鯨”這時只是一種可資利用的原材料而已。當“人”作“資源”的下位詞時也是如此。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抹除是環境話語最重要的非生態修辭功能,為了實現這種抹除功能,環境話語是有一些可尋的修辭規則和修辭策略的。復雜名詞化和被動語態(無主句)、物體化和擬人化、上位詞和下位詞等,都是實施抹除的重要修辭方式。但除了上述修辭方式之外,其實還有一種修辭方式,也有抹除的作用,那就是“委婉語”。只是名詞化和被動語態都是強抹除性修辭,委婉語則屬于一種弱抹除性修辭。并且委婉語發揮抹除功能,主要是通過“粉飾”來遮掩那些令人不悅的東西,因此我們這里主要把它作為“粉飾”修辭來談論。
三、 環境話語中的“粉飾”修辭:“洗白”“洗淺”與“洗綠”

特蘭珀的這段話可以說比較全面深入地揭示了委婉語的粉飾功能,以及粉飾功能發揮作用的內在機制和更深的目的。但就像有學者所說的,國內語言學界以往有關委婉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正面功能,如禮貌功能、幽默功能、避諱功能等。對其負面功能的研究只是近年來才有所體現,如新聞報道中某些委婉語的使用可以掩蓋事實真相等。“而環境話語中委婉語的負面功能迄今仍未得到重視。”(朱長河96)而我們正是要從生態話語修辭批評角度,揭示環境文本中的委婉語修辭的非生態的負面粉飾功能。
委婉語的非生態負面功能總的來看都屬于“粉飾”功能,但如果細分起來又可以分為三種情形:“洗白”(whitewashing),也即狹義的“粉飾”,是指把壞的說成好的,或把不怎么好的說成很好的;“洗淺”(shallowwashing),或稱“弱化”,即把很壞的說成不怎么壞的,把很危險的說成不怎么危險的,把很令人不快的變成不那么令人不快的;“洗綠”(greenwashing,又譯“漂綠”),即把非生態的或與生態無關的說成生態的,把不怎么生態的說成很生態的等。而這樣做的深層目的是規避環境或道德責任,弱化環境風險或令人不快的感受,宣揚對環境進行商業利用,以獲取經濟利益等。
粉飾功能的這三種情形有時各有側重地發揮作用,有時也可能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如英語中的“greenhouse effect”(“溫室效應”)這一術語,主要是在“洗白”事實,但也可以“洗淺”不快感受,弱化環境風險。因為“溫室效應”本來要說的是由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會導致一種災難性的氣候變化,但就像貝思·舒爾茨(Beth Schultz)所說的,對許多人來說,“溫室”一詞有令人愉悅的寓意,它傾向于讓人想到那些可愛的受到精心照料的植物,或高品質的花朵、水果和蔬菜之類。將這個短語應用到預測的災難性氣候變化上,其效果就像把戰爭稱為“游戲”或“種族清洗”那樣。而關于這一現象的另一種說法“全球變暖”(global warming)也同樣存在著誤導性。第一,如果我們有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天,人們可能會認為這個預測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第二,這個詞有一種令人向往的詩意。我們向朋友送上“溫暖”的問候,并談論一段充滿關愛關系的“溫暖”話語(112)。總的來說,它是一個溫和友善的詞,有著令人愉悅的內涵。不理解這一現象的真實所指的人,是根本想不到所謂的“溫室效應”會帶來什么環境災難的。但事實上,這個聽起來令人愉悅的“溫室效應”,是可以導致一系列的災難性的氣候變化的。近年來頻發的洪水、干旱、高溫和高強度颶風等極端天氣情況,也都與這種由于人類向大氣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導致的氣候變化或稱“氣候錯亂”(climatic dislocation)有關。但通過“溫室效應”這種委婉語,是看不到也想不到這些危險的,因此可以說它具有“洗白”兼“洗淺”的功能。
在具有典型“洗淺”功能的委婉語中,美國石油公司使用的“足跡”一詞值得一提。美國石油公司使用這個委婉語的目的是通過它“來影響關于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向石油鉆探開放的新聞報道”。2001年,臨近美國國會表決時,石油公司的官員借這個形象來表明鉆井對環境的影響不大。借助先進的吹捧技術,產業發言人堅持說“通過使用側身鉆與其他先進技術,150萬畝沿海平原之下的石油可以在地球表面只留下不超過2 000畝的‘足跡’”(Spiess & Ruskin, 2001, para.1)。《安克雷奇每日新聞》報道說,石油行業使用的“足跡”的隱喻“被證明是一個有力的修辭”,它暗示鉆井只會影響不到1℅的沿海平原(考克斯69—70)。“足跡”之所以“是一個有力的修辭”,不只因為它是一個“隱喻”,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可以“洗淺”事實的“委婉語”。石油公司通過使用這個詞語,弱化石油開發給北極沿海造成的環境風險,以達到對其進行商業利用的目的。
在環境話語中,這種“洗白”事實、“洗淺”風險或不快感受的委婉語是很常見的,它可以讓表達效果變得柔和,讓令人不愉快的變成令人愉快的。不僅商人使用,政客使用,科學家也使用。瑪麗·卡恩曾分析科學家是如何通過創造性地使用委婉語,以使自己從自身行為的道德責任中擺脫出來的。她說:“現代語言學家為此已經創造了一個詞,‘玄虛之詞’(doublespeak),一種為拒絕或轉移責任而設的語言迷團。”“玄虛之談中的委婉語的使用,使否定的以肯定的面貌出現,不愉快的以愉快的面貌出現,不道德的以道德的面貌出現。”“通過這樣的措辭手法,故弄玄虛者能夠避免甚至隱藏某種情形的不和諧的、令人不安的真相,避免批評的思想和爭議。”因此,在生物學領域的語言中,“郊狼和其他野生動物不是被關在籠中的,不是被囚禁、被操縱并有可能被殺戮的科學研究的犧牲品”,而是被“安置”(housed)、被“給養”、被“處理”的“實驗動物”。在同樣的語境中,郊狼“控制”代替了令人不快的(和更精確)的郊狼“殺戮”,并且那些“令人討厭的動物”是被“重新安置”(relocated),被“改變位置”(translocated),而不是被從它們的領地或社會組織中殘忍地驅逐出去(Kahn243)。科學家對語言的這種處心積慮的使用,目的正在于對環境話語進行“洗白”和“洗淺”,隱藏或弱化令人不快的東西,使自己逃避于生態倫理責任之外。
環境話語的委婉語修辭,不僅對危害動物、植物、自然環境的事實進行洗白、洗淺,還可以對這類事實進行“洗綠”,把危害環境的反而說成是有利于環境的,起到宣揚對環境進行剝削或商業利用的目的。“洗綠”(greenwashing)這個詞是美國環保主義者韋斯特伍德(Jay Westerveld)于1986年在一篇關于旅館工業的文章中提出來的。韋斯特伍德發現,許多旅店在每個房間中都放有提示牌,鼓勵旅客對毛巾進行重復使用而不是每天更換,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但他認為,這些旅店實際上并不是真正地關心環境,而只是以環保的名義來降低成本。這些旅店在很多情況下都不肯都花力氣或很少花氣力去循環利用垃圾,因為這樣做成本太高,經濟收益太少。因此,韋斯特伍德將這一行為和其他表面上的環保行為稱為“洗綠”,認為他們的潛在目的是增加商業利潤(Orange30)。
在當今的環境話語中,尤其是在公司企業的宣傳話語、廣告話語中,這種“洗綠”的委婉語是很常見的。“當面臨環境問題時,公司要么配合解決它,要么只給人管理它的表象。后一種情況經常發生”(Nakajima),而“綠色廣告和公共關系是制造這種錯覺的常用工具”。“例如,裝有催化轉換器的汽車可以凈化大氣,使用無鉛汽油的汽車是綠色的”(Rowell, 1996年),“除草劑可以拯救瀕危物種,全球變暖對人類有益”等(334)。資源開發行業的語言中也充滿了這類委婉語。這類委婉語把自然本身說成“壞”的,把他們的開發活動描繪成“良性”的,是對自然環境有益的,如“改善自然”(improving on nature)、“完全改善的農場”(fully improved farms)等,而不顧這些改變所導致的生態系統方面的變化。這即是把本來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說成是有益于自然環境的了,這也就把他們的非生態行為“洗綠”了。這種“洗綠”行為同樣廣泛地存在于林業之中,如“clearfelling”(為陽光充足而進行的“清伐”)、“prescribed burning”(“有計劃的燒除”)等。但最能說明林業委婉語特征的應該是“收獲(harvest)森林”這類說法。它通過把伐木與園藝或農業相類比傳達出一種信息,讓人感覺砍伐森林就像農民一年一度地收獲莊稼那樣,是在收獲自己經過勞動得到的正當回報,“而不管森林自己已經在那里存在幾百年了”(Schultz111)。
本來,“委婉語”作為一種修辭方式,其“洗白”“洗淺”與“洗綠”的粉飾功能是比較隱蔽的,但隨著“洗白”“洗綠”這些術語的出現,人們對于公司企業的這類商業行為越來越警覺,因此它也時常被識破。然而,由于人們向往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綠色生活,如果再加上缺乏對這類環境話語修辭的批評意識,一看到“生態”“綠色”“環保”這樣的字眼,還是很容易被這類粉飾修辭所迷惑。這也正說明生態話語修辭批評是重要而必需的。生態話語修辭批評,不僅指向非文學性環境話語的粉飾、抹除等非生態功能,也致力于對各種與生態環境問題有關的話語文本進行生態批評分析,指出其生態或非生態性,并揭示其相應的話語構成規律或策略,以促進語言運用的“深生態化進程”,并最終促進生態環境問題的改善或解決,從而對當今的生態文化、生態文明建設發揮某種切實的作用。
注釋[Notes]
① 生態批評的發起者之一格羅特費爾蒂在界定生態批評時說:“生態批評是對文學與物理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Glotfeltyxviii)目前生態批評的對象文本仍然主要為與自然、環境、生態問題相關的文學文本,生態批評因此仍然主要是“生態文學批評”。“生態文學批評”雖然一開始就被一些學者視作“生態文化批評”,但這里的“文化批評”,主要是從“文學的文化屬性”(如認為文學屬于文化系統),或者是從“自然的文化建構屬性”方面來談的(如海倫娜·菲德爾在《生態批評與文化觀念》一書中說:“在過去的15年里,當生態批評著作討論文化這樣的問題時,它往往是在質疑自然作為一種文化建構的觀點。”Feder1),而不是從生態批評的文化文本對象這個角度來說的。它也不關心或不主張把生態批評的對象文本從文學文本拓展到一般的文化文本領域。我們這里的“生態話語修辭批評”,則是一種更寬泛的“生態語言文化批評”,它對各種(包括文學與非文學)與生態環境問題有關的(生態性或非生態性)話語或文本,從生態話語修辭角度進行批評分析,從而打破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嚴格界限,使被生態文學批評或一般大眾文化研究忽視的對象領域獲得關注,同時也使只專注于文學文本的生態批評的對象領域得到某種擴充或補充。生態話語修辭批評的目標是通過促進各領域語言運用的生態化,以達到促進生態環境問題改善或解決的更為實用的目的。在這里,“生態批評所面臨的任務將是提請注意——從而促進能夠追溯真正生態觀點的語言使用”(Ponton2),而不只是關注生態文學性或藝術性問題,盡管這一點對生態文學研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dams, Carol. “Ecofeminism and the Eating of Animals.”Hypatia6.1(1991): 125-45.
亞里士多德: 《修辭學》,羅念生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
[Aristotle.Rhetoric. Trans. Luo Nianshe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Berman, Tzeporah. “The Rape of Mother Nature? Women in the Language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TheEcolinguisticsReader:Language,EcologyandEnvironment. Eds. Alwin Fill and Peter Mühlh?usler.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258-69.
Billig, Michael. “The Languag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ase of Nominalization.”DiscourseSociety19(2008): 783-800.
陳望道: 《修辭學發凡》。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Chen, Wangdao.AnIntroductiontoRhetoric.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97.]
羅伯特·考克斯: 《假如自然不沉默: 環境傳播與公共領域》,紀莉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Cox, Robert.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andthePublicSphere. Trans. Ji L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Feder, Helena.EcocriticismandtheIdeaofCulture.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Fill, Alwin. “Ecolinguistics: State of the Art 1998.”TheEcolinguisticsReader:Language,EcologyandEnvironment. Eds. Alwin Fill and Peter Mühlh?usler.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43-56.
Fill, Alwin, and Peter Mühlh?usler, eds.TheEcolinguisticsReader:Language,Ecologyand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高名凱: 《普通語言學》。上海: 東方書店,1954年。
[Gao, Mingkai.GeneralLinguistics. Shanghai: Oriental Bookstores, 1954.]
Glotfelty, Cheryll and Harold Fromm, eds.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 Athens and London: Georg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馬丁·海德格爾: 《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0年。
[Heidegger, Martin.TheInterpretationofH?lderlin’sPoetry. Trans. Sun Zhoux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Jung, Matthias. “Ecological Criticism of Language.”TheEcolinguisticsReader:Language,EcologyandEnvironment. Eds. Alwin Fill and Peter Mühlh?usler.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270-85.
Kahn, Mary. “Passive Voice of Science: Language Abuse in Wildlife Profession.”TheEcolinguisticsReader:Language,EcologyandEnvironment. Eds. Alwin Fill and Peter Mühlh?usler.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241-44.
劉大為:“言語學、修辭學還是語用學”,《修辭學習》3(2003): 1—5。
[Liu, Dawei. “Linguistics, Rhetoric, or Pragmatics.”RhetoricLearning3(2003): 1-5.]
劉詩峰:“C P N顯影粘堵劑動物實驗報告”,《西北大學學報》4(1982): 31—38。
[Liu, Shifeng. “Report of C P N Development Adhesives in Animal Experiment.”JournalofNorthwestUniversity4(1982): 30-37.]
劉濤: 《環境傳播: 話語、修辭與政治》。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Liu, Tao.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Discourse,RhetoricandPoli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Nakajima, Nina. “Green Advertising and Green Public Relations as Integration Propaganda.”BulletinofScience,Technology&Society21.5(2001): 334-48.
Orange, Erica. “From Eco-Friendly to Eco-Intelligent.”Futurist44.5(2010): 28-42.
Pierson, D. “‘Hey, They’re Just Like u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Discovery Channel’s Nature Programming.”JournalofPopularCulture38.4(2005): 698-712.
Ponton, Douglas Mark. “Review ofEcocriticismontheEdge:TheAnthropoceneasaThresholdConcept.”Language&Ecology(2017): 1-3.
Schultz, Beth. “Languag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TheEcolinguisticsReader:Language,EcologyandEnvironment. Eds. Alwin Fill and Peter Mühlh?usler.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109-114.
Sloane, Thomas O., ed. “Description.”EncyclopediaofRhetor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tibbe, Arran.Ecolinguistics:Language,EcologyandtheStoriesWeLiveb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Trampe, Wilhelm. “Euphemisms for Killing Animals and for Other Forms of Their Use.”TheRoutledgeHandbookofEcolinguistics. Eds. Alwin Fill and Hermine Penz. New York: Routledge, 2018.325-41.
王文霞等:“全球野生動物資源可持續利用與貿易現狀和啟示”,《世界林業研究》3(2017): 1—5。
[Wang, Wenxia, et al. “Current Situ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Global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Trade of Wildlife.”ResourcesWorldForestryResearch3(2017): 1-5.]
葉維廉: 《中國詩學》。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Yip, Wai-Lim.ChinesePoetic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張弓: 《現代漢語修辭學》。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
[Zhang, Gong.RhetoricofModernChinese.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3.]
張志公:“修辭是一個選擇過程”,《當代修辭學》1(1982): 3—4。
[Zhang, Zhigong. “Rhetoric Is a Process of Selection.”ContemporaryRhetoric2(1982): 3-4.]
趙奎英:“生態語言學與當代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建構”,《文藝理論研究》4(2014): 182—90。
[Zhao, Kuiying. “Ecolinguis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Theory Founda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4(2014): 182-90.]
——:“從生態語言學批評看‘生態’與‘環境’之辨”,《廈門大學學報》5(2013): 9—19。
[- - -. “The Debate Between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rom the Ecolinguistic Criticism Perspective.”JournalofXiamenUniversity(Arts&SocialSciences) 5(2013): 9-19.]
——:“‘意識形態的欺騙’還是‘綠色語法的資源’?——‘名詞化’論爭及其生態詩學意義的生態語言學再考察”,《文學理論前沿》第11輯。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103—22。
[- - -. “‘Ideological Deception’ or ‘Green Grammar Resource’?: The Debate on ‘Nominalization’ and Its Ecolinguistics in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Poetics.”FrontiersofLiteraryTheory. Vol.11.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4.103-22.]
朱長河:“環境話語中委婉修辭法的生態批評”,《安徽教育學院學報》5(2006): 95—97。
[Zhu, Changhe. “An Ecological Criticism on Euphemism i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JournalofAnhuiInstituteofEducation5(2006): 95-97.]
Zimmerman, Michael. E. “Heidegger, Buddhism, and Deep Ecology.”TheCambridgeCompaniontoHeidegger. Ed. Charles B. Guign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24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