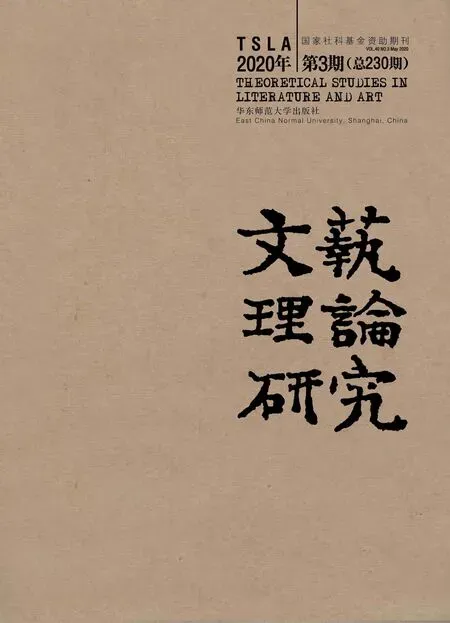“距離”與藝術實踐: 阿爾都塞文藝批評中“群眾”概念的展開
霍 炬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第12卷743)這個著名的論斷里最值得關注的是“如何創造”的問題,馬克思似乎將文學生產與其他商品生產畫上了等號。但恩格斯在1893年則進行了補充說明,“這方面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過錯”,“我們最初是把重點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第39卷93)。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對藝術生產的特殊認識就存在于這樣的論述縫隙當中。藝術不等于意識形態,它比政治、經濟、法律和宗教等理論更為復雜和晦澀,純粹的意識形態要“同現有的材料相結合而發展起來”,“不然它就不是意識形態了”(《馬克思恩格斯》第21卷348)。而對藝術則顯然不能作這樣的簡單概括,因為藝術發揮著完全不同的作用。怎樣界定藝術和意識形態的關系,與精確定位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整體理論有關。伊格爾頓認為阿爾都塞提出了一種關于文學與意識形態之間關系的“更為細致(雖然仍不完全)的說明”(伊格爾頓21),這個“仍不完全”,是指阿爾都塞沒有進一步從“形式”的角度對藝術作品進行分析,伊格爾頓的論點是:“文學形式的重大發展產生于意識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它們體現感知社會現實的新方式以及藝術家與讀者之間的新關系。”(伊格爾頓28—29)雖然有大量的轉折和限定,伊格爾頓“完全”的方法仍然可以被概括為一種心理學理論,即社會現實的改變造成了讀者普遍的心理需求,在新需求的壓力下,藝術家開始改變他們的創作,產生新的形式。可是這種方法仍然要面對馬克思提出的問題,即藝術對象怎樣創造出懂得藝術的大眾,而不是簡單地適應群眾的大眾。阿爾都塞在論畫家盧西奧·方迪時說道:“承載著意識形態的形象決不會讓人看到自己原本出自形象中的意識形態。”(“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下60)也就是說,藝術生產的特殊性在于它和意識形態之間的距離——“不會讓人看到”,這里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反映刺激關系,而是存在著非常復雜的理論迂回和立場定位,這里最重要的理論環節就是對“群眾”(讀者大眾)概念的知識闡釋。因此,為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理論特殊性,我們將經由阿爾都塞所使用的“群眾”概念來分析其意識形態理論在文藝批評中的位置。
一、 作為理論批判關鍵環節的“群眾”概念
“群眾”的概念史是現代社會思想發展的重要體現。16、17世紀的啟蒙話語中已經產生了表達廣泛參與政治改革方向的術語gemeinier Mann(普通人)和Volk, Folk, Masses(大眾),但這些詞在當時專指有待于改造的受教育對象,是落后、蒙昧的代表,必須用精英階級的理性之光來照亮他們沉睡的精神。①群眾——絕大多數的人民——作為一個正面的理論命題,在18世紀也并未出現,如18世紀60年代在法國出現并得到普遍認同的“人權”(droits de l’homme)概念則通常只被賦予有產者的道德-利益共同體。②19世紀,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哲學上第一次確立了“群眾”的位置,在阿爾都塞看來這是貢獻了“某種新的、決定性的東西”(《哲學與政治》167)。列寧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贊揚集中在“研究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列寧全集》60)之上,“群眾”不是一個“抽象”,也不是一個個“個體”的結合,“群眾”或“人民”定義直接決定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特點。③
馬克思主義形成了真正的正面意義上的群眾概念,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話語卻帶來了一系列理論問題。20世紀中葉以后,西方左翼理論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學理知識層面的豐富性,但也形成了“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傾向。這種傾向在“超越教條主義”的口號下提出很多改良路線,如將文化與理論生產問題轉變為對藝術與文學創作的普世主義與自由主義態度,將黨定位成民族文化中最具進步性的“繼承人”。④“人道主義”的前提是有一種理想型的人。這種態度進而演變成對“保守的大眾”的認定,即大眾是“普遍異化”的后工業社會制造出來的,表現為扭曲的“輿論”或“民意”。這樣的大眾不值得依靠,只能依靠“被遺棄者和被排斥在外者”的“亞階層”——“其他種族和有色人種,失業者和不能就業者”——的“敵對行為”來攻擊社會制度(馬爾庫塞216)。阿爾都塞在與這種傾向的論爭中形成了他特有的“群眾”理論概念。
阿爾都塞首先尊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主張,他在《答劉易斯》中強調,“是群眾創造了歷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群眾不是指大量‘知識分子’貴族或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專家;它是指那批被剝削的階級、階層和類型,他們聚集在那個在大規模生產中被剝削的階級周圍[……]: 無產階級。”(《自我批評論文集》59)阿爾都塞的這個論點是很多攻擊的主要對象,人們驚呼:“作為能動的主體的人不見了!”“這將是沒有人的歷史,人被貶低為只不過是承擔社會關系模式的媒介,而不是它的創造者。”(《自我批評論文集》(補卷)35—36)阿爾都塞在“理論的反人道主義”主題下強調意識形態是物質性的,既不是“虛假意識”(或對虛假意識在觀念上的批判),也不是由精英們憑其對真理的把握、對理性的洞察而灌輸給群眾的革命意識形態。
由此,阿爾都塞形成了對當代哲學話語本身的深刻質疑,這種質疑建立在對意識形態的理解上,“我們可以把哲學看作[……]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理論形式。通過其理論形式,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保證了自己對科學知識‘控制’”(Karsz323)。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本人以不清晰的方式指出了這一質疑,甚至是借助“表述中的沉默,某些概念的空缺,它的論證的嚴格性的空白”(《讀〈資本論〉》2)。阿爾都塞說列寧給了我們一些針對這種“空白”的,馬克思主義“新的哲學實踐”的指引,它新在和其他以“否認”為實踐的哲學劃清了界限,同時也和“人道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劃清了界限。“否認”的哲學實踐威脅真正科學的誕生,或者把“粗野的”科學精致化,作無害化處理,⑤而“馬克思面對的是形成他思想的條件,[……]在他的時代中通過對概念的歷史限制而明確地指向一種‘粗野的’狀態”(Althusser149);那些幻想著去“解釋世界”的哲學都號稱“以科學的方式”干預政治,對階級斗爭、無產階級的斗爭進行否定,同時又極其頑固地否認自己從未作過這種干預。只要這些哲學家認為自己有“理性”“人性”的普遍價值作為后臺來撐腰,只要他們認為哲學家能夠改變世界,能扮演一個美麗新世界的良心,他們就一定要否認下去,當然,這種“否認”發揮著非常明確的客觀的上層建筑的功能。
對“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第3卷8)這句名言的曲解就代表了“否認”哲學的特點: 齊格蒙·鮑曼說這句話“不過是啟蒙哲學運動對哲學及其使命的普遍看法的遲來的重新表達而已”,這句話的前半句在孔多塞、特拉西之后“顯然是不合適的”,哲學家就是要擺弄他們的社會改造藍圖,后半句“只是表達了這些哲學家的觀點”,這觀點對他們來說“太顯而易見”,以至于沒必要進行解釋(鮑曼135)。鮑曼將馬克思理解為一個典型的“哲學家”,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從中看到了“發現真理”“從異化中解放”。⑥阿爾都塞在列寧那里看到了“新的”解釋,馬克思的這段話不是說“哲學家”要改變世界,⑦“改變世界”的主語并沒有指定是哲學,它的后半句整個針對的是前半句,即要用“改造世界”的實踐去代替“哲學家解釋世界”的實踐。因此,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新的實踐哲學,由那些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真理的人操控,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頭腦當中,而應說它是“有助于改造世界”的哲學實踐,“僅僅有助于而已,因為創造歷史的不是理論家、科學家或哲學家,也不是‘人們’,而是‘群眾’,即在同一場階級斗爭中被聯合起來的各階級”(《哲學與政治》169)。
“群眾”對阿爾都塞而言不是一個“哲學概念”,即只在思辨活動中存在的話語符號。經過了從二戰的抵抗運動到20世紀60年代的群眾運動,在阿爾都塞個人的生活史中,“群眾”是政治斗爭的核心,是作為一個法共黨員的阿爾都塞時刻不能忘懷的“確鑿的事實”。二戰中,法國共產黨拘泥于“帝國主義戰爭”理論,迷戀公開集會宣傳,使黨組織受到了嚴重破壞,這時只有那些與黨失去聯系的戰士積極組織民眾進行抵抗,在危急時刻,只有這種在正統官方的“黨的意識形態機器”(《來日方長》214)看來純屬冒險主義、機會主義和流寇路線的斗爭才真正在法蘭西打擊了法西斯侵略者。阿爾都塞引用莫里亞克的話說,“只有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是對受屈辱的祖國忠誠不渝的”,“因為歷史不是由這樣的個人的立場所決定的,而是由那些階級的對抗和階級的立場所決定的”(209)。阿爾都塞對法共在1968年民眾運動中的所作所為同樣進行了深刻的批評,黨在斗爭最激烈的關頭千方百計地阻撓大學生和工人群眾的隊伍團結在一起,竟然強迫總工會和資產階級政府進行經濟談判,黨“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以黨的組織力量、黨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調動干部的力量,要破壞民眾運動”(246),法共的政黨機器在群眾的自發性面前表現出保守的本性。
同時,“群眾”又是一個“理論”上的概念,正是通過這個概念,阿爾都塞才與那些以“對象、開端、歷史”的名義建立起來的“哲學”“劃清了界限”,這是他“理論實踐”的重要組成。與人民同在,阿爾都塞說這是“消失在那支黑壓壓的部隊伍里”,像福柯一樣,“與被監禁者并肩戰斗”(《來日方長》225)。要想理解這種以“群眾”為基礎的“哲學實踐”,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難題”,有必要進行一些說明上的“迂回”。阿爾都塞作為一個哲學家去談論藝術,這本身是一個迂回的例子,如同哲學研究“需要每一種哲學取道其他的哲學兜一個圈子,目的是要根據它跟別的哲學有的差異、它的區分來說明自己和理解自己”(《自我批評論文集》151),哲學也需要取道其他知識,對其中的差異和區分進行說明。⑧
二、 “匿名作者”與讀者群眾
從文藝批評的角度講,讀者大眾-觀眾-受眾-群眾的存在是核心問題,而與此相關的,首先則是“作者”的存在。在《來日方長》里,阿爾都塞提到他喜歡福柯對“作家”概念的批評,這啟發我們在藝術問題上根據意識形態理論思考“群眾”概念的理論功能,如果“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那么“作家創作了作品”這樣的話就沒有意義,但畢竟有作品的存在,有歷史的存在,如何理解沒有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的歷史,如何理解沒有作家的“天才”所組成的作品,以及歷史能帶給我們的教益,作品能獲得的影響呢?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最核心的論點是在保留作者概念的前提下,“抓住它的作用,它對話語的介入,以及它的從屬系統”,中止那些諸如“自由主體的意義”“主體的內部構思”等問題,進而“揭示根據社會關系表達話語的方式”,“簡言之,必須取消主體(及其替代)的創造作用,把它作為一種復雜多變的話語作用來分析”(福柯548)。“作者”自有其“作用”,這作用是在介入的物質活動中進行,是在作家和他的時代起決定作用的上層建筑系統中產生客觀功能。不存在純粹的“創造”,但必須有一個“開局”。阿爾都塞認為任何思想都是非個人的,因為那是多種智力因素作用的結果,但“任何思想都是由一個‘有智能者’思想出來的,因此,它就必須通過某一單個的‘有智能者’來重現這個非個人的思想”(《來日方長》224—25)。而在藝術領域中,也發生著相同的情況。
正是“作者之名”確保了藝術的客觀物質功能的實現,確保了文藝和其所存在的世界之間的有機聯系,和那種流行的“文學的非個人化法則”拉開了距離,這也是阿爾都塞與結構主義拉開距離的關鍵。他的批評可以說是對主流的“結構主義”文藝理論的深刻批判。對羅蘭·巴爾特而言,“作家是唯一在言語的結構中失去自己的結構和世界的結構的人,[……]真實對于它從來就僅僅是一種借口。結論便是,言語從來就不能闡釋世界,或者至少,當它假裝闡釋世界的時候,它從來就只是為了更好地推移世界的含混性”(羅蘭·巴爾特174)。且不論這種“作家之死”的理論有何種正面意義(相對于浪漫主義陳詞濫調的批判意義,相對于精致的“文學性”研究的正面意義),以巴爾特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歸根到底是從形式主義的角度來看待藝術的,將“作家”這個詞劃掉,是為了將“作品”理解為一種單純的言語結構,作家沒有自己的結構和世界的結構,留下來的只是空洞抽象的文本形式,假裝解釋世界的言語只是對世界的復雜含混、不可理解的現狀的說明。這是典型的“商品拜物教”在藝術觀念上的體現,對形式的抽象觀察就如同拜物教一般,將“人腦的產物表現為富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并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的存在的東西”,文本獨立于人,文本之間發生著神秘的聯系。馬克思說:“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資本論》90)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把價值看作物本身所具有的屬性,形式主義者將藝術形式這個“完成的結果”當作“藝術性”“文學性”的核心,而這個物的形式掩蓋了真正發揮作用的社會關系,甚至會將這種形式研究從藝術作品中擴散開去,所有的文本都可以作為形式來推移這個世界的含混性。作為浪漫主義“創造者”意義上的作家的確早已死亡,而這并不意味著藝術就借此擁有了一種“先驗”的地位,它必然在某時某地和某人發生關系,一種非常明確的與意識形態有關的社會生產關系。
當阿爾都塞說“不把真正的藝術列入意識形態之中”時,他表達了一種關于藝術生產的唯物主義理論。阿爾都塞強調這里是“真正的藝術”,不是指“平常一般的、平庸或低俗的作品”(《列寧和哲學》242),所謂“真正的藝術”,相當于列寧所說的,“藝術家如果真是一個大藝術家”,用來標示出藝術發揮其功能的那些因素,在著作中“反映了革命的若干重要方面”(《列寧論托爾斯泰》1),阿爾都塞說這“并不給予我們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因此不能代替知識(現代意義上的,即科學知識),但是它所給予我們的,卻與知識有某種特殊的關系。這個關系不是同一的關系,而是差異的關系”。藝術的功能就在于“以‘看到’‘覺察到’和‘感覺到’的形式(不是以認識的形式)所給予我們的,乃是它從中誕生出來、沉浸在其中、作為藝術與之分離開來并且間接提到著的那種意識形態”(《列寧和哲學》242)。作家,像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或索爾仁尼琴那樣的作家,并不會提供一種對社會的判斷,一種和科學知識一樣的認識,他們讓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作品所間接提到的,并且經常給他們的作品供給養料的意識形態,作家存在著,他們的作品具有現實的功能,這功能來自他們所處的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而“看到”這一點,“需要的是從產生他們小說的意識形態向后退一退,在內部挪開一點距離”,“從內部,通過內部的距離,使我們‘覺察到’(但不是認識)他們所保持的那種意識形態”(242)。
三、 “認出自己”的群眾藝術實踐
“向后退一退”的“距離”就是作家本人的意識形態立場與其作品的矛盾,這種矛盾現象是文藝批評的重要分析內容。托爾斯泰開明地主的立場和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敏銳觀察是矛盾的,巴爾扎克極端保守的政治傾向和他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描述是矛盾的,在常見的文學批評中,這種矛盾一般都被描述為作家的個人情感受到了藝術結構的限制,藝術本身的邏輯使作家放棄了他本人的觀念。如羅曼·羅蘭認為寫作《復活》的托爾斯泰“注視著世界,他的生活,他的過去的錯誤,他的信仰,他的圣潔的忿怒。他從高處注視一切。[……]但藝術家的精神,如在《戰爭與和平》中一樣,統制著作品”。羅曼·羅蘭同時確信托爾斯泰“的藝術家底真理與他的信仰者底真理決沒有完滿的調和”(446—448,451)。對于一個作者而言,他不可能形成一種“認識”,這是“作者之死”這個命題合理的一方面,但作者會讓我們在矛盾中,在他的意識形態立場和作品之間的距離中看到“意識形態現實”,哪怕是索爾仁尼琴那些炮火猛烈的社會譴責小說,也頂多只是讓人看到問題的存在,其中絕對不能“確定說出能夠補救這些”問題(比如“個人崇拜”這樣的問題)的手段(《列寧和哲學》244)。流行的作者崇拜或作家中心論制造出一套通過作家本人的意志來宣泄情感、改造社會的說辭,究其實,是想用一種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話語來達到既定目的,讓作者的思考去替代讀者群眾的思考。作者的存在,“真正的藝術”的存在恰恰一直在躲避這種“意圖謬誤”。
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經典著作對這種矛盾有深刻的觀察,列寧指出:“托爾斯泰觀念中的這些矛盾不只是他自己思想中的矛盾而已;它們是改革以后革命以前的階段中鑄造俄國社會不同階級各不同階層的心理狀態的那些極端復雜矛盾的條件、社會影響和歷史傳統的一個反映。”(《列寧論托爾斯泰》13)托爾斯泰的矛盾不是理解上的障礙,正因為“真正的藝術”保留了,而且是無意識地保留了一個空間,作者的意識形態立場越是頑固不化,作品中保留的這個空間就越大,就越能促使人們看到意識形態現實。馬舍雷將阿爾都塞的論點引申為:“作家不會和知識與歷史統一起來[……]他只向我們提供一種想象,一種獨一無二和特殊的觀察[……],作家的角色就是用敘述的方式將歷史結構戲劇化。”(Macherey113)真正的藝術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使人“看到”意識形態的物質存在的前提,使人看到那些極端復雜的矛盾所產生的條件。作者正是以這種在場的方式“匿名”,他們不是在以主體、個體的身份發言,毋寧說,他們的發言是對那種想象出來的作者主體的取消,作者“匿名的在場”正是藝術批評中讀者-觀眾-群眾真實存在的位置。
阿爾都塞對他所處的時代中最新的藝術實踐有著敏銳的觀察和分析,從中得出了他關于文藝批評的正面命題。他看到,布萊希特的戲劇是一種與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現實主義傳統”不同的藝術實踐,一種積極的“介入”。布萊希特說:“當大膽媽媽什么也沒學到的時候,我認為觀眾卻能夠從她身上學到一點東西。”(布萊希特139)阿爾都塞看到,布萊希特“在戲劇中建立一種新的實踐,使得戲劇不再是神秘化”,讓它也有助于對世界的改造[“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上)26]。這種改造不是“寓教于樂”“情感共鳴”的沉醉陶冶,也不是直接“革命宣傳”,即宣教工具意義上的改造。以布萊希特為代表的戲劇實踐建立在與傳統戲劇整體所拉開的距離之上,要讓群眾自己去“學到一點東西”,而非告訴他們一些道理。傳統戲劇要求有統一性,要有一個整體的意識、整體的含義,這種內容就是戲劇本身,但傳統戲劇的題材恰恰正是意識形態的題材,并且這些題材的意識形態性質從沒有受到批判或非議。具體地說,這種未經批判的意識形態無非是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可以從中認出自己(不是認識自己)的那些家喻戶曉和眾所周知的神話。認出自己不等于認識自己,要想認識自己,必須打破這種未經批判的意識形態,布萊希特的戲劇做到了這一點,“他要在舞臺上表現的東西,正是對自發意識形態環境的批判”(《保衛馬克思》136)。布萊希特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特點在于賦予觀眾對錯綜復雜的社會結構的判斷力和產生社會主義的推動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產生的娛樂性主要在于通過社會掌握人類命運的可能性的喜悅”(布萊希特115)。
群眾的判斷力來自他們在戲劇表演中與戲劇活動的距離,拉開距離才能看到戲劇本身所昭示的東西,沒有距離,完全將戲劇等同于自己的生活,將自己等同于角色,戲劇的空間就封閉成了一個自足的、以先驗的意志為核心的領域,將假想的存在等同于真實的東西。群眾必須意識到“戲劇就是戲劇,僅僅是戲劇,而非生活。必須讓人看到舞臺就是舞臺,它人為地搭在觀看者面前,而不是大廳的延伸”[“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上)47]。對于傳統的戲劇,觀眾頭腦里的“關于戲劇的意識形態”是想在劇場看到生活,看到舞臺和生活的一致,通過角色和情節,讓自己認出自己。這個“認出”的過程是戲劇的效果之一,所認出的東西即“戲劇的材料,就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意識形態的東西,不僅僅是一些觀念,或觀念的體系,[……]戲劇就像一面鏡子,觀看者在那里想要看到的,是他們在頭腦里和身體上具有的東西,他們在那里是要認出自己(se reconnatre)。這是至關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意識形態的功能在于承認(reconnaissance)(而非認識)”(49)。這是使戲劇交流成為可能的前提,也即是群眾在革命運動中獲得真實的自我認知,使人民成為人民,而不是從外部得到關于革命的真理。而布萊希特“為了使觀眾產生出一種新的、真實的和能動的意識,[……]必定要打消任何想以自我意識的形式充分地發現自己和表現自己的念頭”(《保衛馬克思》135)。傳統戲劇中觀眾與演出之間的“情感交融”或“共鳴”被打破了,雖然戲劇有主角,但“劇本本身使主角不能存在,劇本把主角連同主角的意識以及這種意識的虛假辯證法統統消滅了”(139—40)。
四、 哲學與藝術實踐的共同結構:“拉開距離”
阿爾都塞是一位哲學工作者,應該說他的藝術批評是哲學理論的一場實驗,哲學和藝術實踐的內在有機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主要特征之一。我們看到,馬克思與恩格斯在《神圣家族》里對《巴黎的秘密》的討論,已經顯露出對類似于戲劇中主角和主角意識的“意識的虛假辯證法”的批判。“歐仁·蘇書中的人物必須把他這個作家本人的意圖[……]充作他們自己思考的結果,充作他們行動的自覺動機。[……]因為他們不是過著真正有內容的生活,所以他們就只得在自己的言談中竭力強調一些微不足道的行為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第2卷233)這“虛假辯證法”就像那種認為蘋果、梨、桃的背后有一個叫作“果實”的本質的“思辨”,在不同的“表象”背后看出共同的東西,“巴黎的秘密”總是躲藏在事物的外殼當中,藝術就是對這秘密的揭示,而這思辨的秘密總歸是作家意圖的直接反映,馬克思本人的工作則是“拋棄意識世界的虛假辯證法,轉而去體驗和研究另一個世界,即資本的世界”(《保衛馬克思》135),就是與這虛假的東西的徹底決裂。馬克思不是向我們宣布,而是(通過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讓我們看到”資本的秘密。文學作家、戲劇角色神秘價值的消失,不借助“引導”“宣傳”,真正的藝術促使群眾自覺地經過思考而獲得對現實世界的體驗和研究。
在《克勒莫尼尼,抽象的畫家》中,阿爾都塞指出:“現代的藝術評論家常常在畫家的主體性的奧秘中來思考這些關系,說是畫家把他的‘創作意圖’畫在由他‘創造’的理想物質性中。”這種“創造美學”和“消費美學”是同樣的東西,都建立在“主體的范疇”(主體的自由意志)和“客體的范疇”(以供消費的作品)之上(《保衛馬克思》132)。觀眾在藝術中所體驗到的“情感交融”和“共鳴”,將被消費的作品和創作主體統一起來的東西是“美的意識形態本身”(《列寧和哲學》250)。在藝術世界中,或更廣泛地說,在審美世界中,意識形態本質上始終是個戰場,它隱秘地或赤裸裸地反映著人類的政治斗爭和社會斗爭,但永遠不可能在畫布上,在戲劇舞臺上畫出、演出社會關系和階級斗爭的形式,不可能將這個戰場上的所有對抗雙方、策略謀劃、后勤補給指示清楚,就像將軍和士兵,甚至統帥也不可能了解戰爭的一切細節和來龍去脈。但藝術家可以描述出那些控制著人們的具體存在,每個癥狀都有曲折的原理,只有以“拉開一段距離”的方式,才能使觀眾-群眾去自覺主動地分析支配著人的那些抽象關系,與關于創造和消費的主體劃清界限。
阿爾都塞有限的藝術討論是在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限度內展開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藝術問題是附帶一提的邊角領域,他特別強調“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在各方面都與布萊希特的戲劇革命相像: 這是一場哲學實踐中的革命。[……]正是在馬克思和列寧的哲學實踐中,正是在布萊希特的戲劇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對各自的對象——哲學或戲劇——的性質和機制的、多少有所明確的認識”[“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上)47]。在哲學中和在藝術中一樣,都需要拉開一段距離,才能發現哲學和藝術的性質和機制。布萊希特、貝爾多拉西、克勒莫尼尼、維弗雷多·林、阿爾瓦雷茲-里奧斯、盧西奧·方迪等藝術家正是通過他們的“技術”制造出了鮮明的形象,而承載著意識形態的形象決不會讓人看到自己原本出自形象中的意識形態。必須對它加工,以便在其中制造出這種細微的、內在的距離,使它失去平衡,得到識別和揭露。而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在做著同樣的事,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就在于引起哲學中的移置,這些移置具有雙重的目標: 在實踐上廢除哲學神秘化的作用,以及讓那些受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影響的人在了解事實的情況下作決定。哲學的移置和戲劇上的“間離效果”(阿爾都塞說他更愿意把布萊希特的這個著名概念翻譯成“移置效果”)是一樣的,哲學和戲劇都是要通過移置去占據一個政治的位置,而這個位置不是代替政治去講話,去宣傳,作為“喉舌”發聲,而是“必須把言語還給政治,因而必須對哲學的聲音和戲劇的聲音進行移置,以便人們聽到的聲音是從政治的位置上發出的聲音。這就是列寧所說的哲學中的黨派立場”[“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上)47]。讓人們聽到、看到、覺察到,一切哲學和藝術都是在政治的位置上發聲,人們之所以看不到這一點,是因為哲學和藝術總是在否認它們和政治有關,這否認或明或隱,或有意或無意,阿爾都塞說這類似于弗洛伊德所說的“否拒”(dénégation),⑨聲言否定的企圖往往只是肯定的特殊表現形式。必須要廢除和暴露那種思辨的哲學、消費主義戲劇的神秘化,清晰地指出它們的位置,它們在替誰講話,說出了什么政治的話語,但這揭示的過程決不是法庭宣判式的,群眾會經由參與分析、檢覽證據、通盤考慮達到自己的判斷。“任何哲學都在于劃清一條主要的界限,它要用這條界限來抵制那些表述相反傾向的哲學的意識形態概念;[……]一條界限其實就是無所發生的;它甚至不是線,也不是劃,只是被劃分這個簡單的事實,即被拉開距離而出現的空白。”(《哲學和政治》164)阿爾都塞批評理論中的群眾功能就在這空白里顯現。
結 語
阿爾都塞在列寧的啟發下看到了馬克思主義新的“哲學實踐”,也看到了新的藝術實踐。用他更簡略的表述來說,在這里分析“不把真正的藝術列入意識形態之中”意味著,文化藝術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IE)“所實現的意識形態扎根在各種實踐中,但那些實踐,無論是審美的(戲劇、電影、文學)還是身體的(體育運動),雖然是那種意識形態的支撐物,卻不能化約為那種意識形態。[……]它們所實現的意識形態都‘扎根’一種現實,但這種現實不能化約為那種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就是階級斗爭”(《論再生產》176—77)。藝術實踐支持了一定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扎根于(深深植根于)群眾的實踐,但它本身不是意識形態,無法化約為(或直接表現為)意識形態本身。用比喻的方式來說,在樓上的人無法看到、無法了解他所處的建筑的地基,但借助客觀情形的描摹、科學細致的分析、對具體環境的遠觀近察,群眾總能得到自己的結論。因此,對藝術的全部分析應該基于這個理論基礎,既不能幻想藝術與意識形態的脫離,也不能聲稱在藝術中可以直接接觸到意識形態。正是這個距離(哲學或藝術與群眾的距離),決定了與藝術有關的意識形態理論的政治價值。
注釋[Notes]
① 參見喬納森·B.克努森: 《論大眾啟蒙》,《啟蒙運動與現代性: 18世紀與20世紀的對話》,詹姆斯·施密特編,徐向東、盧華萍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1—85頁。另參見雷蒙·威廉斯: 《關鍵詞: 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北京: 三聯書店,2005年)中“Folk(人們、百姓、民族)”和“Masses(民眾、大眾)”詞條。
② 參見林·亨特: 《人權的發明》,沈占春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9—13頁。
③ “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并沒有用它來抹煞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來概括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兩方面結合了起來: 既以完全科學的冷靜態度去分析客觀形勢和演進的客觀過程,又非常堅決地承認群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革命首創精神的意義。”參見《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頁,第747頁。
④ M.迪馬喬:“‘對領導權的誤讀’: 法共對葛蘭西思想的接受”,《馬克思主義與現實》3(2019): 130。不僅法共在政策層面有這種思想表現,如盧卡契的文藝批評也充滿了對人的價值的抽象想象:“(對無意義的反抗要)深入到資本主義制度下使人的生活變得沒有意義的人的基礎。”參見《盧卡契文學論文集﹝一﹞》(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77頁。文學的反抗仍然建立在對“人的意義”的指認上。需要指出的是,葛蘭西代表了與這種人道主義傾向劃清界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方向,阿爾都塞從中汲取了理論營養。
⑤ 阿爾都塞在《列寧與哲學》中說列寧的哲學實踐是一種“粗野的實踐”,就像弗洛伊德所說的“粗野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認為那種“企圖在第一次診療中就將醫生所猜測到的秘密突然丟給病人”的做法是“粗野的”,但弗洛伊德并不是譴責這種行為,而是要指出將這種行為視為“粗野”的看法才是真正的野蠻和自以為是,是自認為能避免粗暴、尊重科學的遁詞。弗洛伊德引用《哈姆雷特》里的臺詞來諷刺這種自以為是:“混賬!難道你覺得我比一根木管還容易玩弄嗎?”參見尚·拉普朗虛等《精神分析辭匯》,沈志中等譯(臺北: 行人出版社,2000年)第378頁,此書譯為“野蠻精神分析”。
⑥ 詹明信說馬克思的偉大發現“正在于認識到發現真理、完善真理是與行動分不開的”,爭取解放就是從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從異化中解放出來,比如我們時代的很多“與主流文化相對抗的運動”。參見弗·杰姆遜: 《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西安: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204頁。
⑦ “實際上任何哲學都不只是解釋世界: 任何哲學在政治上都是主動的,但大多數哲學把時間都用來否認自己在政治上是主動的。它們說: 我們在政治上無黨無派,我們只是解釋世界,只說事情是什么。”參見“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上),陳越等譯,《文藝理論與批評》(6)2011: 46。
⑧ 阿爾都塞藝術問題的評論相當有限,這可以理解為一種“哲學的迂回”,是建立在哲學的標準之上的,他跟藝術的關系“主要是哲學的和政治的關系”,只“是從外部,作為哲學家和政治人、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來談論藝術。參見“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上),陳越等譯,《文藝理論與批評》6(2011): 43。
⑨ 弗洛伊德說:“沒有什么比被分析者以‘我沒這么想過’或‘我(從來)沒這么想過’這些話來反應,更能證明我們成功地發現了無意識。”參見尚·拉普朗虛等: 《精神分析辭匯》,沈志中等譯(臺北: 行人出版社,2000年)第378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路易·阿爾都塞:“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上),陳越等譯。《文藝理論與批評》6(2011): 43—52。
[Althusser, Louis Pierre. “Althusser’s Five Comments on Art (Part I).” Trans. Chen Yue, et al.TheoryandCriticismofLiteratureandArt6(2011): 43-52.]
——:“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下),陳越譯。《文藝理論與批評》1(2013): 58—61。
[- - -. “Althusser’s Five Comments on Art (Part Ⅱ).” Trans. Chen Yue, et al.TheoryandCriticismofLiteratureandArt1(2013): 58-61.]
——: 《自我批評論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譯。臺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 -.EssaysinSelf-Criticism. Trans. Du Zhangzhi and Shen Qiyu. Taipei: Yuanliu Publishing Co. Ltd., 1990.]
——: 《自我批評論文集》(補卷),林泣明、許俊遠譯。臺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 - -.EssaysinSelf-Criticism(SupplementaryEssays). Trans. Lin Qiming and Xu Junyuan. Taipei: Yuanliu Publishing Co. Ltd., 1991.]
——: 《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6年。
[- - -.ForMarx. Trans. Gu 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 《來日方長: 阿爾都塞自傳》,蔡鴻濱譯,陳越校。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 - -. ‘TheFutureLastsForever. Trans. Cai Hongbin. Ed. Chen Yu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列寧和哲學》,杜章智譯。臺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 -.LeninandPhilosophy. Trans. Du Zhangzhi. Taipei: Yuanliu Publishing Co. Ltd., 1990.]
——: 《論再生產》,吳子楓譯。西安: 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
[- - -.OnReproduction. Trans. Wu Zifeng.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2019.]
——: 《哲學與政治: 阿爾都塞讀本》,陳越譯,何懷宏編。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 -.PhilosophyandPolitics:AnAlthusserReader. Trans. Chen Yue. Ed. He Huaihong.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讀〈資本論〉》,李其慶譯。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 - -.ReadingCapital. Trans. Li Qiqi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
- - -.WritingsonPsychoanalysis:FreudandLacan. Eds.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Jeffrey Mehl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齊格蒙特·鮑曼: 《立法者與闡釋者》,洪濤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Bauman, Zygmunt.LegislatorsandInterpreters. Trans. Hong Ta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羅蘭·巴爾特: 《文藝批評文集》,懷宇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Barthes, Roland.AnthologyofLiteraryCriticism. Trans. Huai Yu.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貝托爾·布萊希特: 《布萊希特論戲劇》,丁揚忠等譯。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
[Brecht, Bertolt.BrechtonDrama. Trans. Ding Yangzhong. Beijing: China Drama Press, 1990.]
特里·伊格爾頓: 《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寶譯。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Eagleton, Terry.MarxismandLiteraryCriticism. Trans. Wen Ba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米歇爾·福柯:“什么是作者”,《最新西方文論選》,王逢振等編。桂林: 漓江出版社,1991年。
[Foucault, Michel. “What Is an Author.”SelectedWorksonLatestWesternLiteraryTheory. Eds. Wang Fengzhen, et al.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1.]
Karsz, Saül.Théorieetpolitique:LouisAlthusser. Paris: Fayard, 1974.
列寧: 《列寧論托爾斯泰》,林華譯。北京: 中外出版社,1952年。
[Lenin.LeninonTolstoy. Trans. Lin Hua. Beijing: Sino-Foreign Press, 1952.]
——: 《列寧全集》第26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年。
[- - -.TheCompleteWorksofLenin. Vol.26.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Macherey, Pierre.TheoryofLiteraryProduction.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R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赫伯特·馬爾庫塞: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張峰、呂世平譯。重慶: 重慶出版社,1988年。
Marcuse, Herbert.One-DimensionalMan:AStudyoftheIdeologyofaDevelopedIndustrialSociety. Trans. Zhang Feng and Lv Shiping.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1988.]
卡爾·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
[Marx, Karl.Capital. Vol.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卡爾·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年。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TheCompleteWorksofMarxandEngels. 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0年。
[- - -.TheCompleteWorksofMarxandEngels. 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年。
[- - -.TheCompleteWorksofMarxandEngels. Vol.12 and 2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5.]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年。
[- - -.TheCompleteWorksofMarxandEngels. Vol.39.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4.]
羅曼·羅蘭: 《托爾斯泰傳》,《傅雷譯文集》第11卷。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Rolland, Romain.Tolstoy.TranslatedWorksofFuLei. Vol.11. Hefei: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