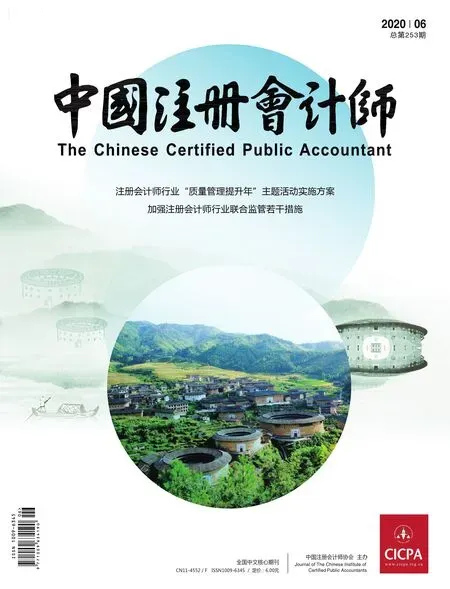審計質量代理變量的適當性與應用策略
薛文艷
一、引言
近期,我國資本市場頻頻爆發上市公司違法違規事件,如康得新、康美藥業、獐子島、輔仁藥業財務舞弊案件,給投資者等利益相關方帶來巨大損失,財務報表的真實性以及審計報告的恰當性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然而,由于受到審計收費、審計時間、審計成本、審計人員執業能力與職業道德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審計質量無法通過直接觀察得出結論,更難以獲取量化結果,因此,學者們通常會選用代理變量對審計質量進行實證研究。
在目前國內外已有的審計質量研究中,選用的代理變量主要有:審計 收 費(Lobo and Zhao,2013;Chakrabarty 等,2015)、事務所規 模 或 品 牌(Fang and Wong,2005)、可操控性應計利潤(Booner等,2008;楊明增等,2018;張金丹等,2019)、非標審計意見(Lim and Tan,2008;陳運森等,2018)、財務報告重述(馬晨等,2014;張宏亮等,2018)等。上述研究中,大多直接選用某個或某幾個代理變量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較少解釋選用的依據與理由。那么,這些代理變量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審計質量?選用是否適當?針對這些問題,學者們對選用上述代理變量的依據和局限性進行了分析,并對有效性進行了檢驗。如DeFond和Zhang(2014)對現有研究中關于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進行了綜述,并分析了各個代理變量在度量審計質量方面的優勢和缺陷。張宏亮、文挺(2016)選用權益資本成本效應、違規可能性和財務報表重述概率作為過濾檢驗變量,逐一檢驗了各個審計質量替代指標的有效性。趙艷秉、張龍平(2017)以2001—2014 年深滬兩市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檢驗了審計質量替代變量在我國的適用性。然而,上述研究并未從替代指標與審計質量相關性的角度研究各代理變量的適當性,因此本文從審計質量測度指標入手,對事務所規模、企業盈余質量、非標審計意見、財務報告重述替代指標的適當性逐一進行評析,并提出審計質量代理變量的應用策略。
二、審計質量測度指標及選取要求
要想厘清審計質量代理變量是否適當,首先應明確與審計質量相關的測度指標以及審計質量代理變量的選取要求。
(一)審計質量的測度指標
審計質量指的是審計最終產品的質量,即審計報告實現審計目標的程度。審計質量的高低最終需要通過審計結果反映,而審計結果又受到審計投入、審計過程與審計環境等綜合因素的影響。審計質量的衡量,從被研究對象的角度區分,分為對單項審計業務質量的度量和對會計師事務所總體審計執業質量的度量。對單項審計業務質量而言,審計投入、審計過程、審計環境及審計結果均與其高度相關,都構成了度量單項審計業務質量的替代指標。而會計師事務所總體執業審計質量取決于一定時期內單項審計業務質量的總和,因此,其替代指標在度量單項審計業務質量指標的基礎上增加了反映會計師事務所總體執業質量的規模及聲譽。本文借鑒了Knechel等(2013)提出的審計質量特征的一般框架,從審計投入、審計過程、審計結果、審計環境四個方面提出了測度審計質量的分級指標,如表1所示。
Deangelo(1981)將審計質量定義為審計人員發現和披露錯報漏報情況的聯合概率。審計投入與審計過程決定了審計人員是否能發現錯報,而審計結果與審計環境又決定了審計人員報告財務報表重大錯報的概率。因此,理論上,上述因素都與單個審計項目的質量密切相關,都可以作為代理變量衡量審計質量,但從實證研究的可行性上,只有上述可以直接觀測、容易判斷與計量的因素滿足審計質量代理變量的前提條件。
(二)審計質量代理變量的選取要求
按照審計準則的規定計劃和執行審計工作是衡量審計質量的技術標準,審計計劃與執行過程需要通過審計工作底稿呈現。依據保密性原則,審計工作底稿涉及委托方非公開的商業機密,其所有權歸屬于會計師事務所。因此,反映審計項目質量的整個審計程序、審計證據的收集、審計決策、審計復核信息都是不可觀測的,即使可以觀測也難以客觀衡量,并作為變量數據加以獲取。因此,在實證研究中,需要選取可直接觀測的度量指標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以研究與審計質量相關的問題。
代理變量的基本特征需要符合:(1)代理變量與被代理變量高度相關,與隨機誤差項不相關;(2)代理變量容易判斷與計量;(3)代理變量與其他解釋變量無多重共線性;(4)如果審計質量為因變量,則其代理變量不宜使用外生變量。例如,外部監管與處罰力度,公眾訴訟的便利性與訴訟成本。表1中所列示的影響審計質量的因素均與審計質量相關,但不可直接觀測的因素不滿足上述第(2)項特征。在進行審計質量實證研究時,如果審計質量為解釋變量,則應檢測與其他被解釋變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如果審計質量為被解釋變量,表1可直接觀測的因素中,審計收費、行政處罰、收入依賴(客戶重要性)及審計訴訟率均是受審計環境影響的因素,與審計活動本身無關,不受審計活動過程及結果控制,因此也不滿足替代因變量的選取要求。

表1 審計質量的測度指標

表2 不同情形下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代理變量的適當性

表3 不同情形下財務報告重述代理變量的適當性
三、審計質量代理變量適當性的評價
此處的適當性是指審計質量替代指標是否符合代理變量的選取要求,是否與審計質量高度相關且容易判斷與計量,并能滿足上述其他兩項基本特征。由于本文并不研究計量模型中審計質量與其他變量的關系,因此,在評價審計質量替代指標適當性時,并不涉及上述第(3)項與第(4)項特征的分析。
表1反映審計投入的可直接觀測指標中,審計人數、審計時間、審計范圍、簽字注冊會計師年度審計項目數量只有在獲得會計師事務所報備系統中的相關數據時,才可作為觀測指標。但這些可觀測指標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是否適當呢?以審計人數為例,由于不同企業所處行業與業務性質存在差異,同等資產規模企業的交易量與審計范圍并不相同,所需的審計人數也就不同。因此,審計人數的多寡并不能反映審計質量的高低,即使以審計人數除以總資產作為測度指標,也并不客觀。同理,采用審計時間、審計范圍、簽字注冊會計師年度審計項目數量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也存在上述問題,均不滿足與審計質量高度相關的要求。在實證研究中,不宜采用其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
表1中反映審計過程的因素屬于不能直接觀測因素,即使有機會查閱審計工作底稿,審計程序、證據、結論等也難以量化。即使較全面地將其構建為審計質量指標,分值、權重也難以科學地加以確定。因此,在可直接觀測的因素中,排除表1中審計投入、審計過程以及受審計環境影響的變量,本文只對會計師事務所規模或聲譽、企業盈余質量、審計意見和財務報告重述作進一步評價。
(一)以事務所規模或聲譽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
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越大,越具有品牌效應,越注重維護其聲譽價值。大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更加注重審計風險的控制,比如,通過招聘素質更高的審計人員,投入更多的人員薪酬、風險控制成本、培訓成本與審計時間來保證審計質量。早期研究發現,大型事務所花費更多的審計時間和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故認為大型事務所提供更高的審計質量(Palmrose,1986)。此外,大所對客戶的經濟依賴性低,獨立性高,審計質量也越高。事務所規模越大,在股東與經理層的代理關系中越中立,審計質量就越高(Fang和 Wong,2005)。
我國學者也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正相關。例如,大所更能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王良成和韓洪靈,2009);“四大”更可能出具非標審計意見(曾亞敏,2014;龍小海和張媛媛,2016)。但也有部分學者研究發現,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原紅旗,2003;郭照蕊,2011)。可見,我國關于會計師事務所與審計質量相關性的實證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因此,我國關于審計質量的實證研究文獻中,通常將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解釋變量來研究與被解釋變量的關系,極少運用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作為被解釋變量來替代審計質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如采用事務所規模作為因變量的代理變量,無法解釋與研究問題中自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即使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相關,但由于決定事務所規模的因素與影響審計質量的因素并不一致,因此,事務所規模并非是各解釋變量的結果。例如,事務所合并與規模正相關,但事務所合并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并不確定,運用事務所規模作為審計質量因變量的代理變量,會弱化與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甚至喪失研究的經濟意義。
(二)以企業盈余質量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
通常,在無保留意見情形下,被審計單位對外公布的財務報告已經做了審計調整,調整后的財務報告盈余質量越高,表明審計質量越高。因此,在實證研究中,大量學者運用盈余質量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最常用的盈余質量測度指標有盈余反應系數、盈余穩健性與盈余管理程度。
其中,盈余反應系數常被學者作為投資者感知的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加以使用,但由于影響股票回報的因素很多,模型存在的變量遺漏問題會影響盈余反應系數的準確度,此外,計算未預期盈余以及累計股票回報過程中的測量誤差均會影響回歸結果(Dechow等,2010)。更重要的是,我國資本市場尚處于弱式有效階段,會計信息質量令人堪憂,會計信息的可信度影響利益相關方對股票投資的反應程度。因此,用盈余反應系數指標測度盈余質量存在局限性。
學者大多以Basu模型的回歸系數衡量會計盈余的穩健性,回歸系數越大,盈余越穩健,盈余質量越高。但確認壞消息期間的盈余持續性低于確認好消息期間的盈余持續性,雖然當年度盈余更穩健,但未來期間好消息的盈余持續性更強,盈余穩健性與持續性均會影響盈余的決策效用(Basu,1997)。此外,Dechow等(2010)指出,模型的回歸系數主要基于長時窗的股票回報指標,而影響該指標的因素較多,因此,應用巴蘇模型測度盈余質量同樣存在較大的局限性。
企業盈余管理分為真實盈余管理與應計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雖涉及管理層操縱真實的交易活動,但財務信息如實反映了這種實質性交易活動的后果,會計處理也遵循了會計準則,因此,CPA無理由要求被審計單位調整該類交易的會計處理,更無法要求被審計單位逆轉相關活動。鑒于此,CPA對真實盈余管理不作審計調整,真實盈余管理也就不能作為反映審計質量的度量指標。如果發現并證實存在此類操縱行為,一般認定為內部控制的重大缺陷。應計盈余管理是企業通過會計政策與會計估計變更等手段改變盈利水平,以此操縱利潤的行為。應計盈余管理將總應計利潤分為正常性的不可操縱應計利潤和可操縱應計利潤兩部分,其值等于凈利潤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應計盈余管理的估計模型主要有業績匹配的應計盈余管理估計,基本的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DD模型和修正的DD模型三種。
其中,業績匹配的應計盈余管理估計方法是通過控制與不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相關的會計業績因素,以業績配對的控制組公司在隨機或非隨機樣本中得出對超額經營業績的無偏估計。國外關于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實證研究大多采用業績匹配樣本。然而,在審計質量研究中,實驗樣本與配對樣本的選擇依據并未得到有效論證。例如,用非標意見的審計報告與標準意見的審計報告分別作為實驗樣本與配對樣本進行配比研究,這是基于非標意見審計報告質量低于標準意見審計報告質量的假設,然而非標意見作為審計質量代理變量在以往文獻中并未得到有效論證,因此,在此假設下計算出的可操縱性利潤之差更不適宜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
鑒于上述模型存在的缺陷,大多學者采用Jones模型或DD模型計算出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盈余質量的衡量指標。但運用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是否適當呢?本文首先根據審計前與審計后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大小,分析企業盈余質量,再依據被審計單位是否接受調整以及CPA出具審計意見的類型,分析審計質量,進而揭示不同情形下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與審計質量的相關性。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代理變量的適當性如表2所示。
表2將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代理變量的適當性分為四種情形:(1)如果審計前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較高,而審計后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較低,則意味著審計調整較大,即錯報更正較多,這意味著未審盈余質量較低,審后的盈余質量較高,審計質量較高,此時二者呈負相關;(2)如果審計前與審計后的可操縱性利潤都較高,此時,分兩種情況,一是CPA未建議較多的審計調整,審計調整較少,審后的盈余質量較低,審計質量也較低,此時二者仍呈負相關;(3)如果被審計單位拒不接受審計調整,CPA出具了保留或否定意見,雖然審后的盈余質量也較低,但審計質量較高。這是由于CPA發現了重大錯報,并提出了調整建議,而并非是由于審計后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較高指示了審計質量較高,因此二者不具有相關性;(4)如果審計前財務報表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較低,表明未審盈余質量本身較高,CPA無須實施更多的審計程序,收集更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降低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審計調整也較少,審計后的可操縱性利潤自然也低,但并不意味著CPA提供了高質量的審計。此時可操縱性利潤不能指示審計質量,二者并不相關。因此,第3、4種情形下,選用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明顯是不適當的。
其次,即使在表2的第2種情形下,也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即可操縱性應計利潤所涉及會計政策或會計估計未受到準則的嚴格限制,CPA未獲得確鑿證據證明該操縱行為的不合法與不公允,因而未能提出調整建議,此時,較高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并不意味著較低的盈余質量,也不代表較低的審計質量。故而,嚴格地講,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對審計質量的指示意義進一步弱化了。綜上,表2中的第1種情形下,審計前的可操縱性利潤高,審計后的可操縱性利潤低,意味著審計質量較高,此時,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最為適當。但在實踐中,由于財務報表未審數不公開披露,審計前可操縱性應計利潤數據不易獲取,只能從行業協會或相關監管部門數據庫中觀測,限制了樣本的采集與研究。
最后,相較于真實盈余管理與交易型舞弊,可操縱性應計利潤操縱了應計利潤在不同期間的分布,長期來看,應計利潤總額不變。而真實盈余管理卻實質性地損害了相關方的長期利益,降低或平滑了未來期間盈余質量,但真實盈余管理活動并不影響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不違反會計準則,且難以逆轉,CPA不能提出審計調整,這種情形下,可操縱性應計利潤指標不能測度企業全部盈余質量,也不適合作為代理變量度量審計質量,只能作為企業應計盈余質量的代理變量;交易型舞弊是企業通過與供貨商、銷售商或隱蔽的第三方等關聯交易方偽造采購、生產、銷售等資金流,進行系統化規模化的一條龍舞弊。該類舞弊手段以制造真實資金流為主,較少使用調節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手段進行會計造假。此時,即使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較低,也不代表有較高的盈余質量和審計質量。因此,實施交易型舞弊的情形下,以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便不適宜了。
(三)使用非標意見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
衡量審計質量的好壞,最直觀的是通過審計報告能否為信息使用者提供可供其進行正確決策的信息來進行甄別。對比標準意見的審計報告,非標意見報告中陳述了導致非標意見的事由,為利益相關者提供了明確的信息甄別價值,且保留意見與否定意見本身也表明CPA發現并報告了重大錯報,意味著較高的審計質量,故有學者使用該指標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進行實證研究,但運用該指標存在著如下重要缺陷:
首先,非標意見審計報告的質量未必一定高。如,CPA與被審計單位合謀,對本應發表否定意見的審計報告,以無法取證為由,發表無法表示意見報告;又如,對本應是否定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的,發表保留意見;再如,對本應是保留意見的,發表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雖然均為非標意見,但卻是審計意見的折衷與妥協,意味著較低的審計質量。
還有一種例外情形是由于細節抽樣帶來的誤拒風險和控制抽樣帶來的信賴不足風險的影響,當推斷誤差不能代表總體特征時,可能會使推斷的總體誤差超過報表重要性水平。而真實錯報可能小于根據樣本推斷的總體誤差,低于報表重要性水平。此時,如果被審計單位拒絕調整,審計師可能會出具非標意見,而真實審計意見可能是無保留意見,這也是審計質量較低的一種情形,雖然這種情形比較少見,但也真實存在。
其次,標準意見審計報告的質量未必一定低。當被審計單位依據CPA建議對審計差異進行調整后,財務報表所有重大方面都符合報表的兩性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較低,盈余質量較高,事務所出具了標準審計意見,其審計質量也是較高的(譚楚月、段宏,2014)。
最后,統一用非標意見作為與審計質量正相關的代理變量不能客觀反映審計質量的層級。哪種審計意見質量更高?如果用非標意見代表審計的高質量,那么,最嚴重的否定意見是否代表最高審計質量?保留意見代表較高的審計質量?標準審計意見審計質量最低?尤其是在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情形下,CPA并不承擔出具該意見的審計責任,也就不應以此種意見來代理CPA的審計質量,反映審計質量的高低。
綜上,無論是非標意見還是標準意見,只能代表被審計單位對外公布的財務報告的會計信息質量,并不能客觀反映CPA的審計質量。衡量審計質量的標準是CPA是否對被審計單位財務報表發表了恰當審計意見,而不是對財務報表發表的審計意見類型。此外,由于我國被出具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較少,如果以此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會影響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四)選擇財務報告重述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
1971年7月,《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第20號意見書——會計變更》中提出,財務報告重述是指被審計單位在發現并糾正前期財務報告的差錯時,重新表述以前公布的財務報告。可見,財務報告重述意味著先前的會計信息質量較低,同時也可能表明CPA未發現前期財務報告存在的錯報。因此,通常情況下,財務報告重述意味著較低的審計質量。故而有部分學者選用年度財務報告重述(因中期報告未經審計)作為與審計質量負相關的代理變量。
會計差錯更正表明前期財務報告所提供的信息有誤,會計信息質量低下。那么,財務報告重述前的審計報告質量究竟如何?還應根據下列三種不同的情形加以判斷,具體如表3所示。
一是如果CPA未發現前期財務報告的重大錯報,發表不恰當審計意見(如標準意見),之后管理層自愿或在監管部門敦促下重述了財務報告,此時,審計師雖根據重述后的財務報告,重述了恰當意見的審計報告,但前期審計報告質量仍較低。這種情形下,財務報告重述與審計質量負相關。
二是如果前期財務報告不存在重大錯報,CPA發現的錯報未超過重要性水平且性質也不重要,因此出具了標準意見審計報告,但之后管理層自愿對低于重要性水平的錯報進行重述,此時,CPA雖對前期財務報告出具的是標準意見,但審計質量也較高。該情形下,財務報告重述與審計質量不相關。
三是如果CPA發現了前期財務報告的重大錯報,被審計單位不同意調整,因此發表了非標意見的審計報告,期后由于媒體曝光,監管層迫于壓力或考慮非標意見后果而自愿重述了財務報告,此時,由于CPA對前期財務報告發表的是恰當的非標意見,故審計質量較高。此情形下,財務報告重述與審計質量也不相關。
可見,財務報告重述不一定與審計質量負相關,只有前期財務報告存在重大錯報且未被CPA發現或報告,進而出具了標準意見審計報告時,財務報告重述作為與審計質量負相關的代理變量才是適當的。
由于因審計質量受到行政處罰的會計師事務所較少,以行政處罰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限制了指標的應用范圍,少量的研究數據會影響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因此本文不對行政處罰作進一步分析。
四、審計質量代理變量的應用策略
(一)會計師事務所聲譽的應用
鑒于會計師事務所聲譽與審計質量相關性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且其影響因素寬泛于審計質量的影響因素,因此,當審計質量為被解釋變量時,不應選用事務所聲譽作為其代理變量。此外,實證研究往往采用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作為事務所聲譽的代理變量,較大規模的事務所,如國際“四大或“本土“八大”,是否一定具有良好聲譽?從2019年瑞華事務所被罰事件來看,事實并非如此。因此,本文建議用會計師事務所與簽字注冊會計師的誠信等級作為事務所聲譽的替代指標,并以此作為審計質量充當解釋變量時的代理變量。
(二)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應用
前述表2所提及4種情形中,只有披露后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大幅低于披露前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時,表明CPA發現并建議調整了重大錯報,審計質量較高。應注意的是,使用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代理變量,應剔除審計差異調整小于報表層重要性水平(非重大錯報,無需建議調整)、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大,但CPA發現并對外報告了重大錯報,審計質量較高,非負相關)、運用真實盈余管理以及被處罰的交易舞弊型(均與可操縱性利潤無關)上市公司樣本。
(三)非標意見的應用
由于非標意見中可能存在意見錯配與級差過大的問題,以此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會影響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如將否定意見出具為保留意見或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雖均為非標意見,但意見并不恰當,不能指示高水平的審計質量。再如,無法表示意見并不能代表CPA實施了恰當的審計程序,提供了高水平的審計質量,因此,其不能作為審計質量的指示變量;加之,被出具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較少,少量樣本限制了該變量的指示效力。綜上,應謹慎使用非標意見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一是應剔除被處罰且被出具了保留意見和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的公司樣本(因被處罰的事務所應出具的是否定意見的審計報告);二是剔除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公司樣本。
(四)財務報告重述的應用
如前述表3所示,只有被審計單位前期年度財務報告存在重大錯報,且CPA對其出具了標準審計意見時,財務報告重述指標與審計質量呈負相關,因此,選用財務報告重述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時,應剔除非標意見和對重述財務報告未重述審計意見(因前期報告不存在重大錯報,CPA無需對重述的年報重新出具審計意見)的公司樣本。
為增強研究結論的有效性,有部分學者分別采用幾個審計質量代理變量來驗證與解釋變量的相關關系。如果檢驗結果一致,會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但檢驗結果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且以往研究表明,即使只選用單個代理變量,不同學者的研究結論也并不一致。因此,在利用多變量進行分項或聯合檢驗時,進一步加劇了研究結論的不穩定性,縮窄了研究結論的適用范圍。
綜上,不同指標作為審計質量代理變量的適當性不同,其應用范圍也不盡相同。進行審計質量相關的實證研究,應在明確研究問題的前提下,界定所研究的對象與范圍。為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需合理評估各代理變量的局限性,對不同的代理變量謹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