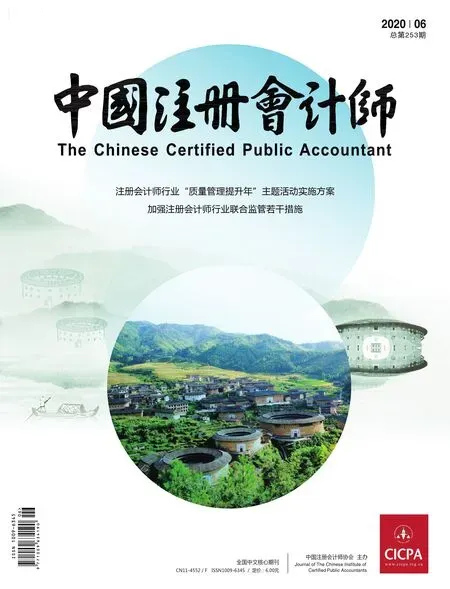銀行承兌匯票在新金融工具準則執行下會計確認的若干問題探討
魯 立
銀行承兌匯票是由在承兌銀行開立存款賬戶的存款人簽發,向開戶銀行申請并經銀行審查同意承兌的,保證在指定日期無條件支付確定的金額給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據。由于其具備銀行信用擔保,同時又可實際延期支付款項,故我國各類單位將其廣泛應用于向供應商支付貨款。在使用過程中,收到銀行承兌匯票的單位即可能將其持有至到期,向承兌銀行進行兌付,也可能將其繼續背書至下一級單位供應商單位用以支付,從而將銀行承兌匯票進行流通。
財政部于2017年發布了修訂后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與計量》(以下簡稱新CAS 22準則),要求境內上市企業,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關會計準則。新CAS 22準則中關于金融工具確認進行了較大修訂,對銀行承兌匯票這種在國內普遍應用的結算方式產生了較大的沖擊。按照原有的金融工具準則,購買方收到匯票后,會減少應收賬款,增加應收票據,規定明確,沒有疑義。新金融工具準則的實施和現實過程企業具體使用銀行承兌匯票的方式,使得業界對于銀行承兌匯票的相關會計處理產生了疑惑和爭議。
一、銀行承兌匯票會計確認的總體原則
銀行承兌匯票屬于金融資產中的非權益工具,根據新CAS22準則,對于非權益性工具而言,其分類與業務模式測試及現金流量測試的具體關系如下:(1)假設企業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且金融資產的合同現金流量特征為對本金和未償付本金金額為基礎的利息償付,該金融資產劃分為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AMC);(2)假設企業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又以出售該金融資產為目標,且金融資產的合同現金流量特征為對本金和未償付本金金額為基礎的利息償付,該金融資產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FVTOCI);(3)無法劃分為上述兩類金融資產的,則列入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FVTPL)。
據此,對于銀行承兌匯票這種金融資產來講,企業對其的業務管理模式決定了它在金融資產中的具體分類:若企業將其持有到期進行托收承付的話,該企業應該將銀行承兌匯票作為AMC進行會計確認,列入“應收票據”會計處理;若企業業務管理模式是既可能將相關票據持有至到期,進行銀行托收,也可能將票據背書轉讓給相關供應商進行支付結算(在資金缺乏時),獲取將票據貼現(特別缺乏現金時),從而獲取相關現金以滿足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那么該企業中銀行承兌匯票應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FVTOCI),列入“應收款項融資”進行會計處理。
二、銀行承兌匯票的不同信用等級對于會計確認的影響
現實中,銀行承兌匯票在出票人出票后,可交由各種銀行機構進行承兌,既可以由工、農、中、建、郵儲等國有銀行進行承兌,也可由各商業銀行、城商行、農商行、信用社等中小銀行機構進行承兌,不同的承兌銀行機構給予銀行承兌匯票不同的信用等級,在現實支付結算以及貼現過程中接受程度有所不同。
諸多公司在背書轉讓銀行承兌匯票時,未考慮對應銀行承兌匯票的信用等級對于會計終止確認的影響程度,一律進行了終止確認,但根據票據法及企業會計準則相關規定,在轉讓合同中未明確約定不附追索權的情況下,公司管理層需對已背書未到期銀行承兌匯票所有權上幾乎所有風險和報酬是否發生轉移進行分析和判斷,從而確定背書行為是否可以終止應收票據確認。2019年科創板企業發行審核時的一般做法明確了這一點,監管部門不認可低信用等級銀行承兌匯票在背書轉讓時即可進行票據終止確認,要求所有涉及的科創板申報企業就此進行了會計差錯更正,要求企業對銀行承兌匯票進行信用等級分類,認可信用等級高的銀行承兌匯票(一般指6+9銀行承兌的匯票,6 家大型商業銀行分別為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交通銀行, 9 家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分別為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中國民生銀行、平安銀行、興業銀行、浙商銀行) 背書轉讓時可終止確認應收票據; 對于信用等級較低的銀行承兌的匯票在背書時則不予終止確認,繼續在應收票據確認。這樣的審核和監管要求帶來一個問題,如果企業對于銀行承兌匯票的管理模式為既以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又以出售該金融資產為目標,同時金融資產的合同現金流量特征為對本金和未償付本金金額為基礎的利息償付,但企業收取的銀行承兌匯票即包括信用等級高的銀行承兌匯票,也包括信用等級一般的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在此情況下,又該如何進行會計確認呢?
根據前述,原則上,根據新金融工具準則的規定,企業對銀行承兌匯票的業務管理模式會決定其在金融資產中的具體分類,如果企業一般將銀行承兌匯票持有至到期,進行托收,獲取相關現金流量,應該將其劃分為AMC,列入“應收票據”會計處理;如果企業根據其現流流量管理的需求,對結算收取的相關票據進行管理,當企業現金流量充足時,將相關票據持有至到期,進行銀行托收,從而獲取相關合同現金流量,當企業現金流量不足時,優先將票據背書轉讓給相關供應商進行支付結算,在特別缺乏現金時,則以承受銀行貼現息為代價,進行票據貼現,從而獲取相關現金以滿足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假設歷史數據表明,企業出售金融資產(包括票據背書轉讓也包括票據貼現)對于實現業務模式目標是不可或缺的,而非僅僅是附帶性質的活動,那么這樣的企業管理模式符合既以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又以出售該金融資產為目標,且金融資產的合同現金流量特征為對本金和未償付本金金額為基礎的利息償付,該金融資產應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FVTOCI),列入“應收款項融資”進行會計處理。
票據法、企業會計準則相關規定及2019年科創板企業發行審核的具體做法明確,企業對于信用等級較低的銀行承兌匯票在背書時不予終止確認,需要繼續在應收票據保留。這樣明確的要求,造成企業管理模式哪怕符合既以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又以出售該金融資產為目標,但若涉及的銀行承兌匯票信用等級較低,那么企業出售金融資產(包括票據背書轉讓也包括票據貼現)時還是不可以終止確認,低信用等級銀行承兌匯票終止確認情況只有一種,就是票據到期,會計上造成企業對于信用等級較低的銀行承兌匯票實質上只有一種“業務管理模式”,那就是“持有至到期”。
綜上所述,企業持有的低信用等級銀行承兌匯票只可以劃分為AMC,在應收票據進行核算。
三、銀行承兌匯票質押對于銀行承兌匯票會計確認的影響
現實中,不少企業和銀行之間實施了票據池業務,將一部分銀行承兌匯票質押給銀行,從而根據需要開具出新面值和到期時間的銀行承兌匯票以便與供應商進行結算,這樣的業務,事實上造成該等質押的銀行承兌匯票一直保持銀行承兌匯票狀態直至其到期,可以認為是“持有至到期”,若企業歷史管理模式上對于銀行承兌匯票符合既以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又以出售該金融資產為目標,那么在出現這種業務情況下,是否要對這些質押的銀行承兌匯票單獨劃分為AMC,在應收票據核算呢?
關于這一點,應該從如何確定企業管理金融資產模式的角度來談論。事實上,準則要求,企業應當在金融資產組合的層次上確定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而不必按照單個金融資產逐項確定業務模式。企業在收到單個應收票據時,無法確定未來是否用于背書、貼現或質押,因此對于應收票據應依據其整體主要的業務模式是收取合同現金流、出售或兼有,而不應根據期末單個應收票據的所處狀態來劃分其業務模式,但對于劃分為不同組合的應收票據,可以分別確認其業務模式。故對于劃分為 FVOCI 列報于“應收款項融資”項目的應收票據組合,只要原先的分類合理,不需要將其中的期末處于質押狀態的票據以業務模式為“僅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為由重分類為“應收票據”列報。
如果企業票據管理中存在較多票據質押至到期收款的情況,應將預期質押因素放到各組合層面總體判斷其業務模式,具體思路如下:將銀行承兌匯票分為兩大類。一是信用等級較低的銀行承兌匯票,這一類在貼現或背書時不滿足終止確認的條件,因此無論未來是否貼現、背書或質押都不影響其業務模式,都應當分類為AMC,列報于應收票據項目;另一類是信用等級較高的銀行承兌匯票,此類票據的貼現或背書滿足終止確認條件,可根據企業規劃的貼現或背書、到期收款(包括質押)的比例分類為AMC 或 FVOCI,列報于應收票據或應收款項融資。比如預期貼現或背書占 40%,到期收款(包括質押)占60%,可認為總體符合“既以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又以出售為目標”的業務模式,將此類票據列報為“應收款項融資”;又比如,預期到期收款(包括質押)占絕大多數,可認為業務模式總體符合“以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將此類票據列報于“應收票據”。
四、小結
新金融工具準則下,原則上,企業對于銀行承兌匯票的具體管理模式決定了其如何進行會計分類和確認,但銀行承兌匯票的信用等級及具體使用情況,會影響其分類和確認,信用等級較低的銀行承兌匯票背書轉讓或貼現時,在會計確認上無法作為會計終止,只能成為會計上“持有至到期”,故不論企業管理模式上意圖轉讓還是貼現與否,都只能劃分為AMC,在應收票據進行核算; 對應的,銀行承兌匯票質押造成的事實上的“持有至到期”,不影響其分類,對于劃分為FVOCI 列報于“應收款項融資”項目的應收票據組合,只要原先的分類合理,不需要將其中的期末處于質押狀態的票據以業務模式為“僅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為由重分類為“應收票據”列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