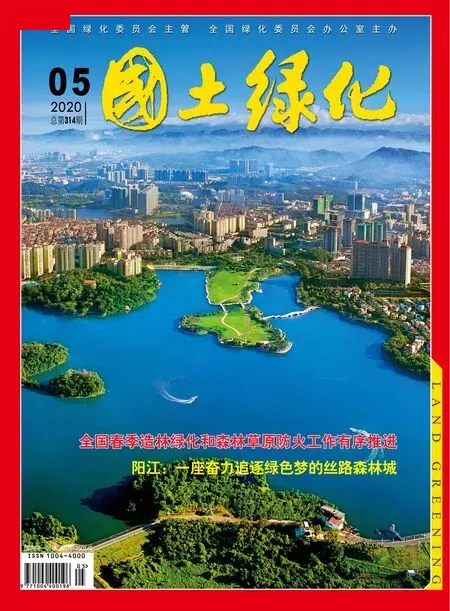吳賢蘭 一家三代堅守深山奉獻林業
◎ 鐘南清 余書福 黃長生
在江西贛南有這么一家人,祖孫三代堅守在大山的深處,把青春歲月奉獻給了他們鐘情的青山綠水。
四月初的于都縣祁祿山生態林場,林海蒼茫,翠綠浩瀚,瀑布飛瀉,溪水淙淙。筆者來到祁祿山生態林場,見到了36年扎根深山的護林員吳賢蘭,聽他講述一家三代人奉獻林業的感人故事。
爺爺是林場的打鐵匠
從祁祿山圩鎮前往吳賢蘭守護的大壩工區有近15公里,其中很長一段為坑洼崎嶇的山路。車行約40 分鐘,終于顛簸到了吳賢蘭的“家”。正巧遇到巡山回來的吳賢蘭,得知我們的來意,他連忙擺手:“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護林員,沒什么可采訪的。”邊說邊熱情地將我們迎進了“客廳”。
所謂的客廳,就是一處簡陋的木棚,一張木桌子,幾條木凳子。在吳賢蘭的屋里轉了一圈,沒有看到一件家用電器。見筆者納悶,吳賢蘭解釋道:“我這里是用小型發電機自行發電,功率小,能保障照明就不錯了。”長年居住在這個幾近與世隔絕的深山里,吳賢蘭沒有半句怨言,“跟我父親當年比,現在條件好多了。”
今年57 歲的吳賢蘭,老家在于都嶺背,其父親吳林舍在祁祿山林場(現為生態林場)干了幾十年,直到1984年退休。吳賢蘭說,父親留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滿手的老繭,而且一年難得回幾次家。直到懂事后自己才知道,父親原來在幾十公里外的祁祿山林場當鐵匠,鍛鑄鋤頭、砍刀、斧頭等采伐和護林工具。別看是掄大錘,在當年可是一項技術活。因為是在國有林場上班,每月領工資,鄉親們都很羨慕父親端上“鐵飯碗”。

吳賢蘭(右)帶著兒子在山上認識樹種

吳小紅(右)與父親手牽著手一起蹚水過河
吳賢蘭說,在他10 歲那年的秋天,父親帶著他來到林場。在山腳下一處簡易的工棚里,他看到父親和兩名工友輪番掄錘打鐵,每天為上百號工人趕制斧頭、砍刀,掙的是辛苦錢。當年林場經濟收入全靠木材銷售,而秋天又是一年最佳的采伐季節,工人們采伐的木頭越多,收入就越高。所以,為工友們鍛鑄、磨修一把鋒利的斧頭、砍刀,是父親的職責使命。吳賢蘭看到鐵匠鋪里堆滿了鍛鑄好的斧頭、砍刀等工具。一天中午,他趁父親打盹之機,偷偷拿了兩把砍刀藏在衣服里,準備帶回家里用,不巧被父親發現了,“你從哪里拿的,給我放回哪里去!小小年紀,好大的膽子,長大了還得了。”父親這番怒斥,仿如昨日。說起這事,吳賢蘭至今難掩慚愧。
在吳賢蘭眼中,父親是一個公私分明的人。記得16歲那年,家中的大門門框被蟲蛀空后需重修,母親讓父親回家時從林場捎兩根杉木回來,不料遭到父親的嚴厲拒絕:“林場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國家的,哪能隨便說拿就拿。”
吳賢蘭說,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看到父親腰彎了,頭發白了,干活也越來越吃力,便心疼地說:“老爸,我來替你干吧!”沒想到這句玩笑話便真成了“長大后我就成了你”。
“賢蘭,干一行就要愛一行,你一定要記住,公家的東西千萬不能動!”2009年冬,父親臨終前的這句囑咐,吳賢蘭一直銘記在心。
父親是林場護林員
1984年,吳賢蘭頂替父親成了“林二代”,先后在祁祿山生態林場溪井、羅江、大壩等工隊擔任護林員,負責守護4000 多畝山林,一干就是36年。無論在哪個工隊,吳賢蘭都繼承了父親鐵面無私的性格,不管是誰,都別想打他管區林木的歪主意。
俗話說,靠山吃山。上世紀80、90年代,木材緊俏,林區盜伐現象十分嚴重。護林員縱使每天上山巡邏,由于山高林密,點多線長,仍難以遏制。吳賢蘭清楚地記得,1992年秋,在一次巡山時,他隱隱聽見山谷里傳來鋸木頭的聲響,便循聲悄悄摸了過去,赫然看見兩名男子正在盜鋸一棵粗大的杉樹,而他們身邊已有兩棵杉木被鋸倒。
“住手!”吳賢蘭大聲喊道。兩名男子發現只有吳賢蘭一人,便兇惡地說道:“又不是你家的,你管得著嗎?”“我是護林員,當然管得著。”對于吳賢蘭的話,兩男子根本不當回事,準備繼續鋸樹。吳賢蘭不顧危險沖了上去,用身體護住杉樹:“來吧,那就把我一起鋸了吧!”兩男子被吳賢蘭的凜然正氣所震懾,拿起鋸子灰溜溜地跑了。吳賢蘭想,盜伐者白天跑了,可能晚上還會再來。于是,他獨自在山谷里守了兩夜。不巧半夜下雨,吳賢蘭全身被淋透了,最后生病住進了醫院。
事后,有朋友笑他:“滿山的樹木,多幾根少幾根有什么關系,何必這么賣命?”護林多年,吳賢蘭深愛山上的一草一木,誰想進山砍一兩根木料都會被拒絕,哪怕親朋好友也不行。久而久之,吳賢蘭得了個“黑臉包公”的外號。
護林工作除了要與盜伐者作斗爭,長年在深山里穿梭,還得時刻提防蟲獸。吳賢蘭說,2019年夏天的一次巡山中,他走在茂密的樹林里,一條粗大的眼鏡蛇就臥在路邊草叢里,幸虧及時發覺,否則后果不堪設想。還有一次,他巡山走在密林中,一頭一百多斤重的野豬從身邊躥過,嚇了他一身冷汗。
出門一把刀,手持一根棍,沒有路,用柴刀劈一劈;餓了吃口干糧,渴了喝口山泉水,困了就在樹底下打個盹。吳賢蘭認為,條件艱苦還可忍受,最難熬的是孤獨與寂寞。
早些年,山上連手機信號都沒有,電也沒通,逢年過節一人獨守工區很孤寂。由于工作原因,加上離圩鎮遠,通常一周外出買一次菜。遇上連續大雨無法出行,所購的肉菜吃光了,就只好連吃幾天的腌菜。為此,吳賢蘭不僅在工棚外開荒種菜,還飼養了幾只雞和鴨,屋里也儲備了好幾壇酸菜,以備不時之需。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轉眼,吳賢蘭已扎根深山36年。巡山護林一次,來回步行近20公里,磨破的膠鞋已不計其數。這期間,不少工友因為忍受不了孤寂和危險,紛紛離開了林場。吳賢蘭早年學過廚藝,炒得一手好菜。曾有飯店老板請他去當廚師,工資是當護林員的兩三倍,他卻不為所動。一些親戚朋友知道后說他傻,吳賢蘭卻一笑了之。在吳賢蘭眼里,那茫茫林海便是對自己最好的饋贈。也因為工作出色,他先后被縣林業局、林場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護林員。
兒子是森林資源監管員
受爺爺、父親的影響,去年冬,吳賢蘭曾在部隊服役兩年的兒子吳小紅,放棄在沿海城市工作的高薪待遇,一頭扎進了深山,成為“林三代”,在林場擔任“森林資源監管員”。
連續多天降雨,吳小紅放心不下父親。4月7日一早,就來到大壩工區,陪父親一起巡山,以便有個照應。
4月8日,吃罷午飯,父子倆結伴去巡山,筆者也跟隨前往。雨后初晴,走在茂林里,山路異常濕滑,遇到陡坡,吳小紅總會伸手拉父親一把,父親也不時停下腳步,指著路邊一棵棵粗大的樹木,向兒子介紹樹種及防治病蟲害的辦法。翻過一道山,山谷里的小溪流因為前幾天的持續降雨水位上升,湍急的水流擋住了去路。
“爸,水冷,我背您過去吧。”“不用背,我哪有這么嬌氣,你自己小心點。”隨即父子倆脫掉了鞋襪,手牽著手一起趟水過河。看著父子倆巡山有說有笑的,筆者不解:早幾年不少護林員都“逃離”林場,而今年只有31 歲的吳小紅為何甘守寂寞,選擇加入林業隊伍?
“吳小紅是2019年冬通過考核聘用到林場工作的。”對于吳小紅的到來,隨行巡山的祁祿山生態林場黨支部書記、場長肖來龍也覺得意外。他告訴筆者,林場現有職工60 多人,平均年齡52 歲。林場改制后,近幾年想招護林員非常困難。年輕的吳小紅之所以投身林業,是因為他與他的爺爺、父親一樣,對綠水青山充滿了愛。更讓肖來龍感動的是,吳小紅的妻子獨自帶著出生不久的孩子居住在縣城里,夫妻倆聚少離多,吳小紅卻毫無怨言,工作認真踏實。年輕人有這股干勁,難能可貴。“再過兩年我就要退休了,我希望兒子接好我的班。”吳賢蘭說,“基層林業工作確實辛苦,以前收入低,這幾年林場改制后工資福利待遇提高了很多。我退休后有退休工資,生活有保障,我看好林業事業。”
吳小紅坦言,當初選擇來林場,許多親戚朋友都想不通,因為自己在外務工每月有六七千元的收入。“其實,務工工資除去租房和日常開支外,每月所剩無幾。”在林場工作,每月有穩定的收入,還有“五險一金”,日后退休了生活有保障,總的待遇不會比在外務工差。加上自己從小在農村長大,對大山獨有情懷。正因為有爺爺和父親這樣一代又一代林業人的堅守,才成就了今天的這片綠洲。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自己愿意接力去守護。
入職半年來,善于鉆研學習的吳小紅沒有辜負領導的期望,他已熟練掌握了數據統計、網絡定位、“林長通APP”及引種育種、營林造林、病蟲害防治等技術,已然成為一名新時代的林業人。
用腳步兌現無聲的誓言,用生命澆筑綠色的豐碑。祖孫三代,以山為家,兢兢業業守護林海,付出了常人難以承受的辛苦與寂寞,在綠海松濤間,書寫了一家三代人奉獻林業的感人故事。

吳賢蘭(前)帶著兒子去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