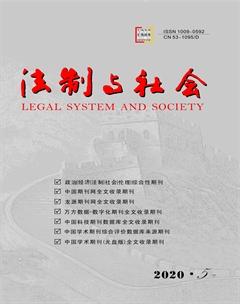我國民事訴訟單位證人資格探討
關鍵詞 單位 證人證言 書證 證明力
作者簡介:黃玥,河北政法職業(yè)學院法律系,講師,研究方向:民事訴訟法。
中圖分類號:D9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5.165
證人證言作為我國法定的證據(jù)種類之一,在司法實踐中運用非常廣泛。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的規(guī)定,凡是知道案情的單位和個人,都應當作為證人。筆者認為,該條文中單位可以作為證人的規(guī)定并不妥當,故通過本文對該問題提出一點自己淺薄的看法。
一、現(xiàn)有法律規(guī)范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規(guī)范民事訴訟證人證言的法律及司法解釋主要包括《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訴解釋》)、最高人民人民法院新修改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稱《新證據(jù)規(guī)定》)。除了《民事訴訟法》明確肯定了單位可以成為證人之外,《民訴解釋》和《新證據(jù)規(guī)定》均未對單位作為證人進行進一步規(guī)定。筆者認為,現(xiàn)有關于單位擔任證人的規(guī)范中,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單位內(nèi)涵和外延不明確
無論是《民事訴訟法》,還是《民訴解釋》或《新證據(jù)規(guī)定》均未對“單位”的內(nèi)涵和外延進行明確界定。《民事訴訟法》對訴訟參加人的規(guī)定主要集中在第五章。但是,第五章只對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進行了規(guī)定,而未對證人等其他訴訟參與人的主體資格進行規(guī)定,對“單位”更沒有明確的概念界定,比如它是僅指依法成立的合法組織,還是也包括某些實際存在的非法組織。筆者認為這是立法上的疏漏。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guī)定“當事人所在社區(qū)、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可以擔任訴訟代理人。此處出現(xiàn)的“單位”與“社區(qū)”“社會團體”并列。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的規(guī)定,民事主體劃分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社團法人屬于法人其中一種類型。因此似乎可以得出這一結(jié)論,立法者心目中對“單位”外延之理解是不包括社團法人的,是否包括非法人組織則并無定論。但這一外延界定似乎又與第七十二條的立法本意并不相符。筆者認為,立法者第七十二條中所規(guī)定的“單位”,應當是指除了擁有自然生命體之外的一切法律擬制主體,立法者無意排除社團法人作為證人提供證言的資格。總而言之,“單位”內(nèi)涵和外延的不確定性,將導致其難以真正在司法實踐中被加以運用。
(二)單位作證的程序未予規(guī)定
《民事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民訴解釋》對證人出庭作證進行了更細化的指引,要求證人必須簽署保證書,還可以主張出庭費用。《新證據(jù)規(guī)定》則在二者基礎之上對證人作證的程序進行了更細致的規(guī)范。然而,這些規(guī)定都只是針對個人作證的。單位作為一個不具備自然生命特征的法律擬制主體,其作證過程必定不同于自然人。比如,單位作為擬制主體,該如何出庭?其作證費用又應當如何支付?再則,單位的證言應當以何為準?是以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所言還是其工作人員或是單位內(nèi)部形成的決議為準?若單位內(nèi)部工作人員認識不一致時,誰能代表單位的意思表示?由此可見,無論是從立法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單位這一法律擬制主體作證都有一定障礙,而這些障礙并未通過法律或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得到有效解決。
二、單位不應作為證人證言的主體
證人證言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定的證據(jù)種類之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證人在民事爭議案件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曾對其中部分事實有過親身感知。證人以其感知系統(tǒng)接收并存儲這些事實所釋放的各種信息,并在爭議發(fā)生后,通過自己的表達系統(tǒng)將這些信息陳述出來,使得這些事實得以再現(xiàn)。鑒于此,證人的感知系統(tǒng)和表達系統(tǒng)是否正常運行,就決定著其能否有資格作為證人。《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第三款也明確規(guī)定“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
按照前述證人基本屬性,我們可以得出這一結(jié)論,證人應當具備感知能力和表達能力,但是單位屬于法律擬制主體,并不具備自然人才擁有的感知和表達能力。單位即使能夠成為證人,實際上也是“借助特定的自然人的生理本能對案件事實進行感知,從而得出有關事實的印象和感受①”,并通過該自然人的記憶能力儲存其體驗。
那么,證人為何應當出庭作證呢?究其原因則在于,證人對案件事實的感知能力依據(jù)其自身生理、心理素質(zhì)的差異也會有所差別。因而,即使對于同一個事實,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感知。比如,一個人若患有紅綠色盲癥,則無法區(qū)分這兩種顏色。此外,現(xiàn)場環(huán)境也會影響證人的感知能力,比如天氣的冷熱、時間的早晚、距離的遠近等等。所以,證人證言的認定“需要通過特殊的詢問規(guī)則來完成,單位只是虛擬的人格,無法出庭作證,也無法接受法官、當事人的詢問、質(zhì)證,最后仍需要自然人代表單位參與訴訟②”,由個人運用其表達系統(tǒng)完成作證義務。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法律擬制主體的單位既然無法出庭,那么其作為證人實際上也就并無必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規(guī)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由此可知,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能夠作為證人的只能是感知系統(tǒng)和表達系統(tǒng)沒有缺陷,能夠正常運作的自然人,排除了單位作為證人。筆者認為該條規(guī)定是合理的。雖然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在證明標準上有差異,但在證據(jù)資格的判斷上應該具有一致性。因此,我國民事訴訟法應當進行修改,刪除單位作證的規(guī)定。
三、單位在民事訴訟中的角色應如何定位
(一)明確單位的內(nèi)涵和外延
如前所述,單位不具備證人的基本資格,不能作為證人提供證人證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單位就無法參與民事訴訟。單位作為法律上的虛擬人格,廣泛參與著各類民事活動。如果完全排除單位參與民事訴訟的可能,大量的民事案件無法查清。因此,首先必須肯定單位能夠參與民事訴訟。緊接著就需要對單位進行概念界定,確定其內(nèi)涵和外延。筆者認為,單位是指自然人以外的一切法律擬制主體,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組織。這就明確排除了非法組織參與民事訴訟的可能。因為“組織”之所以能成為法律擬制主體,前提條件就在于其必須依法成立,所以現(xiàn)實生活中雖然存在一些非法組織,但它們卻不可以參與民事訴訟。比如,某一傳銷組織不能對內(nèi)部工作人員之間的經(jīng)濟往來進行證明,只能由該組織內(nèi)部的自然人以個人的方式就其了解的情況向人民法院作證。而且,明確單位的外延包含所有法人與非法人組織,也能夠與我國實體法上的規(guī)定在邏輯上保持一致。
(二)單位應當以提供書證的方式參與民事訴訟
《民事訴訟法》所規(guī)定的法定證據(jù)種類一共有八種,除了證人證言外,單位還可以通過其他形式向法官提供其所了解的案情。筆者認為,最符合單位作證這種方式的證據(jù)種類就是書證。《民訴解釋》第一百一十五條規(guī)定“單位向人民人民法院提出的證明材料,應當由單位負責人及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簽名或者蓋章,并加蓋單位印章。人民人民法院就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可以向單位及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進行調(diào)查核實。必要時,可以要求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出庭作證。”由這條規(guī)定可知,單位雖然無法作為證人出庭作證,但是它可以通過書面證明材料的方式向人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為待證事實提供證據(jù)材料。雖然該條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外觀形式上對“證明材料”進行規(guī)范,但這條規(guī)定卻給了我們一條單位作證的指引路徑。
首先,單位以自己的名義提供書證,避免了單位作為證人的資格缺陷,繞開法律對證人具備感知和表達能力的要求,同時又以單位的意思表示提供證據(jù)材料。此時,只需要單位負責人和書面材料制作者簽名并加蓋單位公章,即可在形式上推定該書面材料為單位的真實意思表示,符合書證的原件規(guī)則。其次,當單位內(nèi)部個別人員所掌握的情況與單位不一致時,他仍然可以個人身份提供證人證言。這樣就可以避免單位內(nèi)部為追求認識的一致性而相互協(xié)商、作出妥協(xié),反而導致該證言的真實性受到影響,最終不利于人民法院查清案情。最后,單位提供書證作證,在必要時也可以要求制作該書證的工作人員出庭作證。這一做法延續(xù)了“證人詢問規(guī)則”,既可以幫助人民法院掌握單位了解案情的經(jīng)過,也有利于雙方當事人對該書證進行質(zhì)證。
(三)單位提供證明材料的證明力問題
在民事訴訟司法實踐中,單位了解某一民事糾紛待證事實的主要原因通常是因為其曾參與過該待證事實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或者是其掌握了糾紛主體在該待證事實中的相關信息。因此,對單位而言,它提供證明材料的基礎就是這些客觀的碎片化信息。這與單位內(nèi)部工作人員親身感知過該待證事實有所不同。單位工作人員對該待證事實的感知因自身差異而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直觀性、整體性卻很強,所以人民法院在認定單位內(nèi)部工作人員所做的證人證言的證明力時應當結(jié)合該工作人員自身的作證能力以及其與糾紛主體之間的厲害關系綜合認定。在某些情況下,單位內(nèi)部工作人員的證人證言可以單獨作為認定待證事實的根據(jù)。而單位則有所不同,單位因只掌握著該待證事實的各種客觀碎片化信息,所以要對該待證事實形成單位的意思表示時,只能通過拼湊這些碎片化信息來進行。因而單位意思表示雖更具客觀性,但直觀性、整體性欠佳。通過上述比較可知,單位雖然能夠通過書面證明材料的方式提供證據(jù)材料,但這一證明材料與待證事實的關聯(lián)程度不夠緊密,往往只有在與單位所保留的碎片化信息證據(jù)相互印證時才能起到證明作用,因而該證明材料的作用僅僅是輔助性的。所以筆者認為,單位提供的書面證明材料雖為原始書證,但因其證明力較小,在民事訴訟中作為補強證據(jù)更為合適,不建議糾紛主體過分依賴此種證據(jù)形式。
綜上所述,雖然《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單位可以作為證人提供證人證言,但其配套司法解釋均未對單位作證進行體系規(guī)范。單位作為證人不僅缺乏理論支撐,在司法實踐中也有操作障礙。因此,筆者認為,我國三大訴訟法應當達成否定單位可以作為證人的理論共識,并在法律條文中刪除單位作證的規(guī)定。但是,單位仍然可以通過提供書證的方式參與民事訴訟。只要該書證滿足形式真實,就具備證據(jù)資格,而是否實質(zhì)真實,則需要人民法院結(jié)合案件其他證據(jù)綜合審核認定。
注釋:
①畢玉謙.民事證據(jù)法及其程序功能[M].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頁.
②常怡,王建華.民事證據(jù)判例與理論分析(上)[M].人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