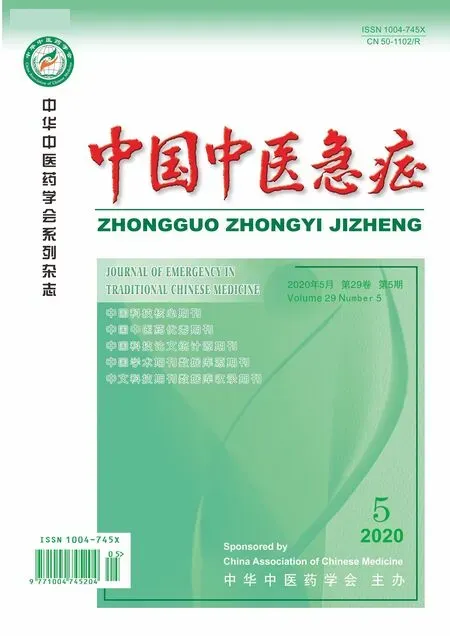清熱化濕調氣通絡法治療急性潰瘍性結腸炎的臨床研究?
魏永輝 單海燕 戚丹鳳 劉 鈺 陳 偉 李春耕 李松柱 趙宇琦 朱葉珊 張 茹
(河北省唐山市中醫醫院,河北 唐山 063000)
潰瘍性結腸炎是累及大腸黏膜及黏膜下層的非特異性炎癥性腸病,病因與發病機制尚不明確,臨床以腹痛、腹瀉、膿血便及里急后重為主要表現,臨床尚缺乏特異性治療藥物,多應用氨基水楊酸類和皮質類固醇藥物[1-4]。中醫學認為其屬于“泄瀉”范疇。本文采用清熱化濕調氣通絡法治療急性潰瘍性結腸炎取得了較滿意的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診斷標準:依據《潰瘍性結腸炎中西醫結合診療指南(草案)》[5]確定急性潰瘍性結腸炎診斷標準;依據《潰瘍性結腸炎中醫診療共識意見》[6]確定泄瀉及濕熱瘀滯證診斷標準。納入標準:符合急性潰瘍性結腸炎、泄瀉及濕熱瘀滯證診斷標準;年齡≥18歲;患者或家屬知情同意。排除標準:細菌性痢疾、克羅恩病、腸結核等其他腸道炎癥性疾病;合并腸梗阻、腸穿孔等腸道嚴重并發癥;合并其他臟器嚴重性疾病;合并精神及語言障礙性疾病;妊娠或哺乳期女性;對試驗藥物過敏;正在參加其他臨床試驗。
1.2 臨床資料 選取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在唐山市中醫醫院就診的急性潰瘍性結腸炎患者90例,按照1∶1原則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與治療組。對照組45例,男性27例,女性18例;年齡29~67歲,平均(41.39±8.25)歲;病程 2~10 d,平均(6.05±2.41)d。治療組45例,男性24例,女性21例;年齡25~69歲,平均(41.75±7.90)歲;病程 3~12 d,平均(6.22±2.37)d。兩組患者性別、年齡及病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采用柳氮磺吡啶腸溶片(華潤雙鶴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1020818,0.25 g/片)治療,每次1 g,每日3次。治療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采用清熱化濕調氣通絡法,組方:黃連12 g,黃芩12 g,焦檳榔10 g,葛根10 g,生薏苡仁15 g,川芎6 g,地榆12 g,木香10 g,炒白芍20 g,三七粉3 g(沖服),延胡索9 g,砂仁9 g(后下),仙鶴草15 g,炒白術12 g。每日1劑,水濃煎至200 mL,早晚各服100 mL。兩組均治療2周。
1.4 觀察指標 1)癥狀與體征評分: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7]按照癥狀、體征權重及無、輕、中、重程度進行評分,腹痛、腹瀉、膿血便評分均包括0分、2分、4分、6分,里急后重評為0分、1分、2分、3分。2)炎癥相關性指標:治療前后分別采集空腹靜脈血3 mL置于采血管中,靜置20 min后離心取上清液,采用ELISA法檢測超敏C反應蛋白(hs-CRP)、白介素-6(IL-6)、白介素-10(IL-10)、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3)綜合評價性指標:依據《潰瘍性結腸炎中醫診療共識意見》[6]評價黏膜組織評分、結腸鏡評分、Mayo指數評分、IBDQ評分。
1.5 療效標準 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7]確定療效標準,其中癥狀與體征消失,療效指數≥95.0%為痊愈;癥狀與體征明顯改善,療效指數≥70.0%為顯效;癥狀與體征有所改善,療效指數≥30.0%為有效;癥狀或體征變化不明顯,療效指數<30.0%為無效。
1.6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9.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 χ2檢驗,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兩組癥狀與體征評分比較 見表1。兩組治療后癥狀與體征評分較治療前均降低(P<0.05),且治療組低于對照組(P<0.05)。
2.2 兩組炎癥相關性指標比較 見表2。兩組治療后hs-CRP、IL-6、TNF-α較治療前降低(P<0.05),且治療組低于對照組(P<0.05);兩組治療后IL-10較治療前升高(P<0.05),且治療組高于對照組(P<0.05)。
表1 兩組癥狀與體征評分比較(分,±s)

表1 兩組癥狀與體征評分比較(分,±s)
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P<0.05。下同
組 別 時間 腹瀉 腹痛 膿血便 里急后重治療組(n=45)對照組(n=45)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5.26±0.71 0.85±0.40*△5.30±0.68 1.72±0.47*5.15±0.77 0.79±0.36*△5.09±0.72 1.64±0.39*4.97±0.60 0.73±0.44*△5.02±0.65 1.46±0.51*2.47±0.53 0.59±0.38*△2.51±0.57 1.13±0.40*
表2 兩組炎癥相關性指標比較(±s)

表2 兩組炎癥相關性指標比較(±s)
組別治療組(n=45)對照組(n=45)時間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hs-CRP(mg/L)96.36±10.12 12.56±4.77*△97.20±11.49 28.71±6.63*IL-6(μg/L)85.36±8.84 19.67±3.20*△84.92±8.33 36.05±5.57*IL-10(μg/L)29.41±4.35 63.80±7.73*△30.23±3.91 47.55±7.28*TNF-α(μg/L)72.49±9.36 28.60±5.07*△73.10±9.85 45.33±4.92*
2.3 兩組綜合評價性指標比較 見表3。兩組治療后黏膜組織評分、結腸鏡評分、Mayo指數評分較治療前降低(P<0.05),且治療組低于對照組(P<0.05);兩組治療后IBDQ評分較治療前升高(P<0.05),且治療組高于對照組(P<0.05)。
表3 兩組綜合評價性指標比較(分,±s)

表3 兩組綜合評價性指標比較(分,±s)
組別治療組(n=45)對照組(n=45)時間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黏膜組織評分4.25±1.32 1.31±0.75*△4.20±1.29 2.27±0.88*結腸鏡評分2.12±0.78 0.45±0.34*△2.17±0.81 0.92±0.37*Mayo指數評分8.96±2.24 2.20±0.96*△8.92±2.31 3.86±1.02*IBDQ評分106.27±15.44 174.69±21.30*△109.42±17.85 145.56±24.62*
2.4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4。治療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

表4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
3 討論
目前,潰瘍性結腸炎的發病率呈升高趨勢,其發病原因及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但有研究表明可能與遺傳因素、免疫因素、環境因素及感染等有關,臨床尚缺乏特異性治療手段[1]。中醫學將潰瘍性結腸炎歸屬于“泄瀉”范疇,病因可見于外感六淫、內傷七情、飲食失宜、稟賦不足等,基本病機為脾虛濕蘊[8-9]。但不同醫家對潰瘍性結腸炎的治療各具特色,豐富了中醫藥對潰瘍性結腸炎的認識,如張聲生從內癰論治[10];楊強善于將清熱活血灌腸方與補益活血口服方結合論治[11];王愛華認為潰瘍性結腸炎發病以脾虛為本,濕熱為標,日久夾瘀,脾腎虧虛[12]。
筆者結合歷代先賢論述及自身臨床經驗認為,潰瘍性結腸炎基本病機為濕熱蘊腸,氣滯絡瘀,誠如《沈氏尊生書》云“大抵痢之瘍根,皆由濕蒸熱壅,以至氣血凝滯,漸至腸胃之病”。濕熱瘀滯的形成多與脾腎密切相關,脾為后天之本,腎為先天之本,先后天相互影響,脾氣虧虛,日久及腎,水液運化失常,濕濁內蘊,久蘊化熱,濕熱自成,耗損陰津,阻礙氣機,血行遲緩,日久損及絡脈,形成濕熱瘀滯之證。因此,針對急性潰瘍性結腸炎,應遵“急則治其標”,以清熱化濕調氣通絡為主要治法。方中黃芩、黃連為苦寒燥濕之佳品,長于清熱燥濕止利。焦檳榔行氣導滯,以緩解泄瀉之里急后重感,配以行氣消脹之木香,調氣之功顯著增強。葛根善于升發脾胃清陽之氣而發揮止瀉之功。生薏苡仁清熱利濕,兼能消癰腫,促進創面愈合。川芎長于行氣活血,為血中之氣藥,配以活血止痛之延胡索,能夠發揮二者活血、行氣、通絡、止痛的協同作用。地榆清熱涼血止血,有改善便膿血作用,同時配以仙鶴草,其治療作用顯著增強。炒白芍柔肝緩急止痛,兼能養陰生津,以防久泄傷陰。三七粉具有“化瘀不傷正,止血不留瘀”的特點,取其活血止血之功。炒白術配合砂仁健脾化濕以兼顧脾虛之本。藥理研究表明:黃芩、黃連能夠調節機體炎癥因子水平,緩解機體炎癥反應,發揮抗炎作用,減輕腸道組織損傷[13-14]。木香、地榆對潰瘍性結腸炎等腸道炎性細胞因子具有抑制作用[15-16]。砂仁能夠降低炎癥性腸病TNF-α水平,上調抗炎因子IL-10、TGF-β水平,促進腸道免疫平衡,增強機體免疫功能,調節腸道菌群,改善受損腸黏膜組織病變[17]。仙鶴草具有顯著的抗炎鎮痛及雙向調節出凝血功能的作用,能夠促進受損腸黏膜修復[18]。全方協同配伍,發揮清熱化濕調氣通絡之功,改善機體炎癥狀態,促進腸道組織修復。研究結果顯示,采用清熱化濕調氣通絡法治療急性潰瘍性結腸炎,能夠降低腹痛、腹瀉、里急后重等癥狀及體征評分,調控IL-6、IL-10、TNF-α等炎癥相關因子水平,減輕疾病嚴重程度,促進腸黏膜組織修復,改善內鏡評分,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且臨床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
綜上所述,采用清熱化濕調氣通絡法治療急性潰瘍性結腸炎能夠改善臨床癥狀,調控炎癥因子表達,促進腸黏膜組織修復,提高生活質量及臨床療效,值得臨床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