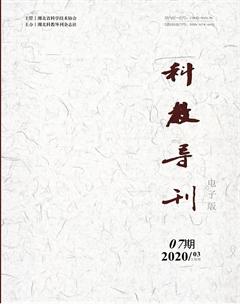“以心體之”而求未發(fā)之中
王曉樸 殷雅輝
摘 要 楊時(shí)作為兩宋之間重要的理學(xué)家和承繼者,自宋南渡后,以理學(xué)中的天理論、人性論、誠(chéng)論為思想體系,把洛學(xué)傳承到了閩地,發(fā)揮了北宋二程時(shí)期的理學(xué)思想。本文以楊時(shí)的“中”論思想為基礎(chǔ),簡(jiǎn)要概述一下其理學(xué)思想及脈絡(luò)。
關(guān)鍵詞 楊時(shí) 理學(xué) 未發(fā)之中
中圖分類號(hào):R473.6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1人物簡(jiǎn)介
楊時(shí)(公元1053-1135年),字中立,號(hào)龜山,祖籍弘農(nóng)華陰(今陜西省華陰市東),南劍西鏞州龍池團(tuán)(今福建省三明市明溪縣)人。北宋時(shí)期的著名哲學(xué)家、文學(xué)家、思想家和學(xué)者。北宋熙寧九年中進(jìn)士,歷任官職瀏陽(yáng)、余杭、蕭山知縣,至荊州教授、工部侍郎、以龍圖閣直學(xué)士專事著述講學(xué)。曾先后從學(xué)于程顥、程頤二師,與游酢、呂大臨、謝良佐并稱為“程門四大弟子”。后又與羅仲素、李延平并稱為“南劍三先生”。 因晚年世居南劍西鏞州北龜山,自號(hào)龜山,后世學(xué)者尊稱其為龜山先生。
正是楊時(shí)以傳播和弘揚(yáng)洛學(xué)為己任,才得以把二程的理學(xué)思想傳播到了南方地區(qū)尤其是閩地,并為南宋理學(xué)的發(fā)展和弘揚(yáng)起到了非常積極的推動(dòng)作用和承上啟下的作用。
2求“已發(fā)未發(fā)”之“中”
2.1緣起
“已發(fā)未發(fā)”出自《中庸》第一章的第三句:“喜怒哀樂(lè)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dá)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àn)物育焉。”
關(guān)于“已發(fā)未發(fā)”的問(wèn)題,早已成為宋代理學(xué)家和學(xué)者討論最多的問(wèn)題之一。在北宋時(shí)期,二程曾對(duì)于“已發(fā)未發(fā)”問(wèn)題進(jìn)行過(guò)數(shù)次的討論。二程認(rèn)為,“天下之大本”為“中”, 并把求得“已發(fā)未發(fā)”之“中和”學(xué)說(shuō)融入到了其洛學(xué)心性論體系當(dāng)中,作為一個(gè)重要的理論支撐依據(jù)。而對(duì)于“天理”之道的認(rèn)知,則需要通過(guò)人的主觀意識(shí)來(lái)認(rèn)識(shí)。而如何保持“天理”層面上的“純一”、和“無(wú)雜”,就需要每時(shí)每刻守住內(nèi)心上的“中和”之氣。
二程說(shuō)論述的“已發(fā)未發(fā)”、“中和”之說(shuō),為楊時(shí)的“已發(fā)未發(fā)”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dǎo)和借鑒。楊時(shí)正是憑借著二程的理學(xué)思路,對(duì)《中庸》所言之“中”的問(wèn)題有了自己的見解。
2.2楊時(shí)的“中”論
楊時(shí)曾提出說(shuō):“道止于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guò),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微,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
楊時(shí)認(rèn)為,“中”作為“天下之大本”,“無(wú)過(guò)”且“無(wú)不及”,如果超出了預(yù)知范圍則“過(guò)”,如果未達(dá)到目的要求則“不及”,而“中”就是“道之至極”之意。
楊時(shí)以“中”為“極”,進(jìn)而對(duì)“中”與“權(quán)”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闡釋和說(shuō)明。
(學(xué)生)或問(wèn):“有謂‘中立常,權(quán)盡變。不知權(quán)則不足以應(yīng)物,知權(quán)則中有時(shí)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時(shí))曰:“知中則知權(quán),不知權(quán)則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quán)焉。是中與權(quán)固異矣?”(楊時(shí))曰:“猶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quán),豈非不知中乎?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zhí)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大小之體殊,則所執(zhí)者,長(zhǎng)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quán)以中行,中因權(quán)立。《中庸》之書不言權(quán),其曰‘君子而時(shí)中,蓋為權(quán)也。”
“中”與“權(quán)”是協(xié)調(diào)和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知中而知權(quán),執(zhí)中而知權(quán),權(quán)以中行,中以權(quán)立。權(quán)衡利弊各種關(guān)系和問(wèn)題,需要以“中”作為標(biāo)準(zhǔn)來(lái)進(jìn)行判斷。楊時(shí)認(rèn)為,“執(zhí)中”之義,比如用一尺長(zhǎng)的物體先找到其五寸作為“中點(diǎn)”,即便是一尺長(zhǎng)的物品長(zhǎng)度均等,然而其厚度和寬度因物體的大小、外形、重量等情況而不相同。同樣如此,雖然只是看到了物體的“中”,然而卻忽略了物體的其他特征屬性,這就等于是無(wú) “權(quán)”而衡之。所以說(shuō),認(rèn)識(shí)或者觀察物體時(shí),一方面要看到物體的“中”,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物體的“權(quán)”,只有做到了這樣,才能真正的做到“權(quán)衡而取中”。《中庸》一書既言之“中”,同時(shí)又言之“權(quán)”,就是這個(gè)道理。
楊時(shí)又說(shuō):“事各有中,故執(zhí)中必有權(quán),權(quán)猶權(quán)衡之權(quán),稱物之重輕,而取中也。中無(wú)常主,惟其時(shí)焉耳。時(shí)者,當(dāng)其可之謂也。仲尼不為己甚者,而孟子曰圣人時(shí),以其仕止久速,各當(dāng)其可也。君子之趨變無(wú)常,蓋用權(quán)以取中也。小人不知時(shí)中之義,反常亂德,以欺世其為中庸也,乃為無(wú)忌憚也。”
“權(quán)”,其書面意義為“秤錘”,后又引申為“權(quán)衡”。先秦時(shí)期的孟子曾在《盡心上》篇提到說(shuō):“執(zhí)中無(wú)權(quán),猶執(zhí)一也。所惡執(zhí)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選擇了“中”而忽略了“權(quán)衡”,這就等于是偏執(zhí)一隅而為。這正是如同先秦時(shí)期的墨家之言,以“兼愛(ài)”、“非攻”之學(xué)說(shuō)“以利天下之道”,楊、朱以“為我”之意拔一毛利于天下而不為,這兩種學(xué)術(shù)之論在儒家看來(lái)都是屬于“偏執(zhí)無(wú)中”,最終導(dǎo)致的后果就是“為其賊道”、“舉一而廢百”。而儒家提倡的君子應(yīng)當(dāng)“用權(quán)而取中”,但小人因?yàn)椴欢脵?quán)衡利弊的“時(shí)中”之義,就會(huì)導(dǎo)致其“欺世盜名”而“反言亂德”,最終變得“肆無(wú)忌憚”。
楊時(shí)時(shí)任龍圖閣直學(xué)士期間,曾經(jīng)在給皇帝提交的諫言對(duì)策中,也提及到了“用中”的方法和措施。
他說(shuō):“堯舜曰‘允執(zhí)厥中,孟子曰‘湯執(zhí)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極,歷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fù)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圣、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愿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dāng)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wèn),一趨于中而已。”①
在南宋初期,因朝廷上的“朋黨之爭(zhēng)”,使得皇權(quán)陷于機(jī)會(huì)主義,當(dāng)時(shí)的朝廷局勢(shì)混亂而無(wú)法穩(wěn)定,作為龍圖閣直學(xué)士的楊時(shí)便向皇帝奏請(qǐng)上書,請(qǐng)執(zhí)政者以“允執(zhí)厥中”、“執(zhí)中”、“趨中的“中道”精神來(lái)重建混亂的朝綱,并期望以重審的視角來(lái)思考儒家思想在“體用一源”的重要作用。
楊時(shí)對(duì)于“中”進(jìn)行的論述、闡發(fā)和思考,并重新發(fā)揮了《中庸》所蘊(yùn)含“已發(fā)未發(fā)“的理論意義。
楊時(shí)說(shuō):“喜怒哀樂(lè)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學(xué)者當(dāng)于喜怒哀樂(lè)未發(fā)之際,以心驗(yàn)之,則中之義自見。執(zhí)而勿失,無(wú)人欲之私焉,發(fā)必中節(jié)矣。發(fā)而中節(jié),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也,于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鑒之茹物,因物而異形,而鑒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出為無(wú)為,則為出于不為,亦此意也。若圣人而無(wú)喜怒哀樂(lè),則天下之達(dá)道廢矣。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于是四者,當(dāng)論其中節(jié)不中節(jié),不當(dāng)論其有無(wú)也。”
楊時(shí)認(rèn)為,人們情感的表達(dá)、外露和釋放,主要就是喜、怒、哀、樂(lè)的“已發(fā)未發(fā)”之情。從孔子的悲慟之心、孟子的喜悅之情等的喜、怒、哀、樂(lè),其所流露出來(lái)的各種不同形態(tài)皆是對(duì)人或物的有感而發(fā),這些都符合在未發(fā)之時(shí)和未發(fā)之中。用一個(gè)比方來(lái)說(shuō),就好像人拿著一面鏡子照在物體上,鏡子里面所反射出的影像和人眼所看到的影像可能不盡相同,但是對(duì)于鏡子本身,它所反射出來(lái)的光線和其自身的照射功能還是存在的,并不會(huì)因外界環(huán)境的改變而產(chǎn)生任何的變化。鏡子終究還是鏡子,只是它所照見的物體本身因顏色、形狀的差異而不同。
3結(jié)語(yǔ)
楊時(shí)通過(guò)用“喜怒哀樂(lè)未發(fā)之際以心體之”的論述,把作為認(rèn)知主體的人,通過(guò)尋求精神層面的道德修養(yǎng)進(jìn)行感知,從而達(dá)到內(nèi)心的修煉過(guò)程。這種方法論是對(duì)二程“求中”之法的一個(gè)提升和凝練。正是由于楊時(shí)所提出的這種理論和方法,并把此法傳于后學(xué)者羅從彥和李侗,李侗又傳授給了南宋理學(xué)大家朱熹,為朱熹在南宋理學(xué)上的理論建構(gòu)和方法論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理論基礎(chǔ)。
基金項(xiàng)目:本課題為2018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項(xiàng)目課題“宋代理學(xué)語(yǔ)境下的《中庸》思想研究”(項(xiàng)目批準(zhǔn)號(hào):HB18ZX012)的成果之一。
注釋
① 脫脫:《宋史》卷第四百二十八,《列傳》第一百八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39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M].王孝魚點(diǎn)校.北京:中華書局, 2004.
[2] (宋)朱熹.二程外書(諸子百家叢書)(影印四庫(kù)全書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2.
[3] (宋)楊時(shí).龜山集[M].四庫(kù)全書影印版,1736:310+315+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