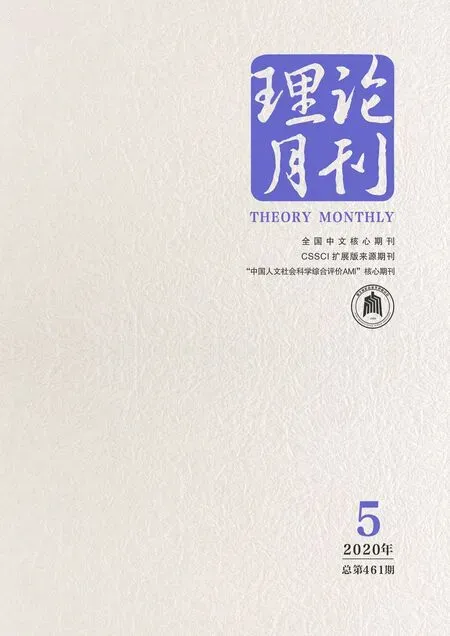政治風險的生成機理與系統(tǒng)規(guī)避
——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
□胡洪彬
(浙江財經(jīng)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進治黨治國的過程中,把防范政治風險、維護政治穩(wěn)定擺在了突出位置上,早在2013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就告誡“全黨同志要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以增強工作的前瞻性、進取性、創(chuàng)造性,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1](p155)。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一中全會上,則明確提出了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著力“強化政治責任”,不斷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勢、把握全局的能力”和“駕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風險的能力”的執(zhí)政理念,以確保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堅持正確政治方向”[2](p227)。2019年6月,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則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高度,再次強調(diào)了“凈化政治生態(tài)”和“防范和化解政治風險”[3](p1-3)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更是基于完善國家安全體系的角度,明確要求堅持“以政治安全為根本”“提高防范抵御國家安全風險能力,高度警惕、堅決防范和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動”[4](p8-19)。黨中央對防范化解政治風險的高度重視,既為深化黨的政治建設(shè)指明了方向,同時也對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出了新的現(xiàn)實要求。那么,當前該如何科學認識政治風險?其到底從何而來?抑或又該如何才能形成長遠規(guī)避效應(yīng)?顯然,解答這一問題,既需要在實踐中總結(jié)經(jīng)驗,也離不開理論層面的深刻剖析。本文基于政治學視野,對政治風險的要素來源進行了歸納,明確了政治風險的內(nèi)在演化機理,進而提出了政治風險的系統(tǒng)規(guī)避路徑,以期為新時代黨和國家政治風險防范能力的不斷提升提供學理借鑒。
一、邏輯架構(gòu):政治風險的因素來源
概念分析是科學研究的邏輯起點,要科學把握“政治風險”,首先就必須對“風險”的概念及其因素來源作出厘定。從詞源上看,風險(Risk)一詞最早始于法文的“risque”,最初屬于航海術(shù)語,意指船在航行中遭遇到的可能性危險。此后,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尤其是機器大工業(yè)的崛起,使人類更加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人類社會面臨的不確定性和復(fù)雜性因素也不斷增多,風險作為“人為的”和“可能性的危機”[5](p21)亦不斷得到人們的重視,并誕生出了諸如經(jīng)濟風險、社會風險、生態(tài)風險等多個相關(guān)概念。所謂政治風險(Political Risk),顧名思義就是國家政治系統(tǒng)出現(xiàn)的可能性危機。同國家內(nèi)部其他領(lǐng)域的風險一致,政治風險既有著偶發(fā)性、現(xiàn)實性和不確定性等基本特性,同時又有著更為致命的毀滅性和破壞性,其不僅構(gòu)成了對政治穩(wěn)定、政治秩序的威脅和破壞,而且從根本上關(guān)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因而歷來受到各國統(tǒng)治者的普遍重視。政治風險雖爆發(fā)于政治系統(tǒng)內(nèi)部,但其產(chǎn)生因素則是多元性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和外部環(huán)境因素等都可能構(gòu)成政治風險產(chǎn)生的重要根源。從政治發(fā)展的系統(tǒng)性而言,我們認為,政治風險的因素來源可劃分為有形、無形二大層面:
(一)政治風險的有形因素來源,主要涵蓋經(jīng)濟基礎(chǔ)因素和國家機構(gòu)因素兩大類
其中經(jīng)濟基礎(chǔ)因素是確保政治系統(tǒng)穩(wěn)定的前提性要件,對國家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能起到根本性影響。馬克思主義認為,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政治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就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政治上層建筑。隨著經(jīng)濟基礎(chǔ)的改變,政治上層建筑也必然發(fā)生或慢或快的變革。正如列寧所言:“政治是經(jīng)濟的集中表現(xiàn)”[6](p407)。因此,考察國家政治風險的因素來源,首先必然是從經(jīng)濟基礎(chǔ)展開的。概言之,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對經(jīng)濟運行的掌控力狀況。一般而言,國家對經(jīng)濟運行的掌控能力越強,國家內(nèi)部的政治風險就越低,反之則越強。譬如,20世紀90年代,拉美、俄羅斯等地區(qū)和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政策,其結(jié)果就不僅造成經(jīng)濟增長的衰退和大量失業(yè)問題,而且亦帶來了國有資產(chǎn)的流失和國家經(jīng)濟主權(quán)的削弱,這一歷史事實已充分表明,國家對經(jīng)濟運行掌控能力的強弱,實質(zhì)上構(gòu)成了國家政治風險的重要變量。二是國家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推動力狀況。經(jīng)濟增長既是社會穩(wěn)定的“孵化器”,也是確保國家政治穩(wěn)定的現(xiàn)實根基。國家政策既可為經(jīng)濟發(fā)展注入推動力,而決策失誤則又不可避免地帶來經(jīng)濟發(fā)展的制約,由此必然削弱國家政策的合法性根基,進而給國家政治發(fā)展帶來不可忽視的反噬效應(yīng)。正因為此,一些學者亦將經(jīng)濟發(fā)展與政治穩(wěn)定界定為相輔相成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性[7](p26-30)。
國家機構(gòu)因素是確保政治系統(tǒng)穩(wěn)定的本體性要件,對國家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能起到直接性影響。作為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國家本身是由特定的領(lǐng)土、一定的人口和主權(quán)等構(gòu)成的有機整體,其中,國家機構(gòu)設(shè)置是國家運行的根本依托。國家內(nèi)部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亦同國家機構(gòu)的發(fā)展和運行狀況緊密相關(guān)。具體而言,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國家機構(gòu)內(nèi)部的制度體系完善度。制度是帶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因素,誠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8](p333)。換言之,制度的滯后性和殘缺性,構(gòu)成了政治風險和危機產(chǎn)生的直接內(nèi)因。(2)國家機構(gòu)內(nèi)部的政治生態(tài)的潔凈度。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有過極為深刻地闡釋:“政治生態(tài)好,人心就順、正氣就足;政治生態(tài)不好,就會人心渙散、弊病叢生”[9](p167)。也即,政治生態(tài)與政治風險呈現(xiàn)出反比例的內(nèi)在關(guān)系,政治生態(tài)的惡化,為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提供了環(huán)境和誘因。(3)國家機構(gòu)內(nèi)部的具體個體的能力狀況。人是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也是各級國家機構(gòu)有效運行的主體,更是推進國家政治發(fā)展的根本主體,無論是政治制度的發(fā)展還是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態(tài)的維護,都離不開作為政治主體的人的參與和支撐。國家機構(gòu)內(nèi)部人的發(fā)展狀況,包括領(lǐng)導(dǎo)能力、認識水平、素質(zhì)能力等等,是實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政治穩(wěn)定的基本要件,因此其較低的發(fā)展水平,必然構(gòu)成政治風險產(chǎn)生的微觀基因。
(二)政治風險的無形因素來源,主要涵蓋意識形態(tài)因素、社會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三大類
其中,意識形態(tài)因素關(guān)乎國家發(fā)展的前途命運,對其進行把握的狀況決定了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方向。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quán),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10](p194)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亦多次強調(diào),“意識形態(tài)工作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面對“社會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媒體格局深刻變化”的主客觀環(huán)境,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tài)建設(shè),“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11](p86)。也即,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同意識形態(tài)主導(dǎo)權(quán)的掌握程度緊密關(guān)聯(lián)。意識形態(tài)作為同一定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觀點和概念的總和,本質(zhì)上是對社會經(jīng)濟基礎(chǔ)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國家領(lǐng)導(dǎo)主體掌握意識形態(tài)工作主導(dǎo)權(quán),意味著政治系統(tǒng)在開放環(huán)境和多元價值體系中,在指導(dǎo)理念、基本原則等方面的鞏固,意識形態(tài)工作主導(dǎo)權(quán)的喪失,則政治系統(tǒng)必然因為失去價值根基而導(dǎo)致風險因素的產(chǎn)生。可見,能否做好意識形態(tài)工作,事關(guān)國家長治久安,意識形態(tài)風險構(gòu)成了國家政治風險的核心要件。
社會心理因素是政治系統(tǒng)穩(wěn)序運行的社會根基,其內(nèi)在的性質(zhì)、特征及發(fā)展狀況,是構(gòu)成政治系統(tǒng)風險因素產(chǎn)生的不可忽視的心理變量。社會心理作為特定時期內(nèi)社會群體的心理狀態(tài),是包含社會整體的情緒基調(diào)、社會共識以及價值取向的總和性體系。國家作為管理社會的工具,絕非“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12](p258),而是建立在社會系統(tǒng)之上的組織架構(gòu),國家的權(quán)力本質(zhì)上源于社會,正如馬克思所言,“國家是從家庭和市民社會之中無意識地偶然地產(chǎn)生出來的”“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13](p82)。市民社會對國家的決定性,必然通過社會心理狀況得以體現(xiàn)出來。對于國家的政治發(fā)展而言,社會心理層面的風險性因素包括社會個體對政治系統(tǒng)的心理認同狀況、國家政治系統(tǒng)的社會公信力狀況、國家對社會情緒的引導(dǎo)力狀況等多個重要方面。其中,社會個體的心理認同與政治風險產(chǎn)生呈內(nèi)在的反向關(guān)聯(lián)性,國家政治系統(tǒng)的社會公信力狀況和國家對社會情緒的引導(dǎo)力狀況,則同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呈現(xiàn)內(nèi)在的正向關(guān)聯(lián)性。社會個體對政治系統(tǒng)認同度越高、政治系統(tǒng)的社會公信力,及其對社會情緒的引導(dǎo)力越強,則政治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就有更加堅實的社會根基,政治系統(tǒng)產(chǎn)生風險危機可能性就越低。反之,政治系統(tǒng)必將缺乏社會支撐而失去穩(wěn)定性,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可能性亦得到提升。
政治文化因素是政治系統(tǒng)穩(wěn)序運行的理念根基,其內(nèi)在存量、發(fā)展模式及其適應(yīng)性狀況,是構(gòu)成政治系統(tǒng)風險因素產(chǎn)生的柔性根源。政治系統(tǒng)的發(fā)展既需要經(jīng)濟基礎(chǔ)和各級國家機構(gòu)的客觀保障,也離不開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堅實支撐。阿爾蒙德(Almond Gabrial)等就認為,“政治文化影響著政治體系中每一個政治角色的行動”,包括“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nèi)容和對法律的反應(yīng)”等[14](p26)。可見,政治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力量,實質(zhì)上構(gòu)成了政治系統(tǒng)實現(xiàn)穩(wěn)序發(fā)展的內(nèi)在靈魂。一般而言,政治文化一經(jīng)形成,就會貫穿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發(fā)揮出持久性的影響作用。因此,對于政治系統(tǒng)穩(wěn)序發(fā)展而言,選擇和建構(gòu)契合自身訴求的政治文化至關(guān)重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選擇,決定了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必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dǎo)而構(gòu)成的有機體系,就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而言,這一層面的風險性因素包括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狀況、革命文化的繼承狀況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fā)展狀況等方面。推進當代中國政治系統(tǒng)的穩(wěn)序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科學傳承是理念基礎(chǔ),革命文化的堅定繼承是內(nèi)在源頭,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則構(gòu)成了其中的核心主體,缺失了其中任何一方面,政治系統(tǒng)亦必然因為文化根基的不足而失去穩(wěn)定性,政治發(fā)展亦將無從談起。
二、生成機理:政治風險的系統(tǒng)演化
上述對政治風險的因素分析,表明政治風險在產(chǎn)生根源上的多元性,事實上,作為人類社會風險的主要組成部分,政治風險同其他各領(lǐng)域的風險一致,本身亦是一個有機體系,除了上文闡釋的風險因素(Risk factors)外,還包括風險事故(Risk Accidents)、風險損失(Risk Loss)等一系列要件。政治風險的這一特性決定了要全面對其做出把握,就必須從系統(tǒng)論的角度對其內(nèi)在運行機理做出科學分析。在人類歷史上,系統(tǒng)作為由要素構(gòu)成的整體性概念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出現(xiàn),古希臘的先哲包括泰勒斯、德謨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亞里士多德等的論述中都曾有過相關(guān)性的闡釋。如赫拉克利的“世界整體觀”、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觀等皆為其中代表。這些系統(tǒng)觀為現(xiàn)代系統(tǒng)科學誕生提供了文化根基。進入20世紀后,以奧地利學者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一般系統(tǒng)論”的建立為起點,標志著現(xiàn)代系統(tǒng)科學的真正誕生,進而推進了系統(tǒng)分析方法在各領(lǐng)域的廣泛應(yīng)用,尤其在自然科學領(lǐng)域,《一般系統(tǒng)論》《系統(tǒng)工程》等的面世極大促進了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發(fā)展。
在社會科學領(lǐng)域,1950年代以后,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系統(tǒng)論研究也是方興未艾。如在社會學領(lǐng)域,一些社會學家積極借鑒一般系統(tǒng)論的原理來分析社會的層級結(jié)構(gòu)和組織架構(gòu),由此誕生了如帕森斯(T.Parsons)、霍曼斯(George C.Homans)等為代表社會系統(tǒng)論專家,在政治學研究領(lǐng)域,隨著社會系統(tǒng)理論研究的逐步壯大,一些學者繼而對政治行為及其組織結(jié)構(gòu)和功能做出了系統(tǒng)分析,推進了政治系統(tǒng)理論研究的應(yīng)運而生,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on)和阿爾蒙德等即為其中的代表,為推進現(xiàn)代政治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從方法論的角度看,社會科學領(lǐng)域的系統(tǒng)分析主要是基于內(nèi)在動因、運作過程等角度對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功能做出探討,如帕森斯就認為,社會大系統(tǒng)包含了適應(yīng)(A)、達鵠(G)、整合(I)和維模(L)四個基本系統(tǒng),并指出這四個要素性系統(tǒng)之功能的滿足,是保持社會大系統(tǒng)穩(wěn)態(tài)性的前提。阿爾蒙德則直接將政治體系視為社會“有意識地制定和追求集體目標的工具”,政治體系作為一套制度和機構(gòu),關(guān)系到社會群體“共同目標的制定和實現(xiàn)”,政治體系功能的發(fā)揮主要通過“體系、過程和政策”三個層次來加以實現(xiàn)[14](p38)。伊斯頓也將政治系統(tǒng)視為一個“由環(huán)境包裹著的行為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內(nèi)涵信息的輸入、輸出和反饋等環(huán)節(jié),并受到外在環(huán)境的影響和制約,同時又“反轉(zhuǎn)過來影響環(huán)境”[15](p325),這其中“輸入”環(huán)節(jié)包含了“支持”與“需求”兩部分,“輸出”環(huán)節(jié)是政治系統(tǒng)對外在環(huán)境的作用和影響,而“反饋”環(huán)節(jié)則是政治系統(tǒng)經(jīng)過信息輸出之后進一步產(chǎn)生的反效應(yīng)。
隨著國外學界對社會科學系統(tǒng)論研究的不斷深化,近年來國內(nèi)學界也展開了相關(guān)探討,并借鑒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方法來分析各類社會現(xiàn)象。在風險治理領(lǐng)域,目前亦有一系列成果面世。如有學者從風險運行角度出發(fā),對社會風險的產(chǎn)生、機理和演化過程展開系統(tǒng)性的分析,進而基于社會風險的警源指標、警兆指標和警情指標等方面,對預(yù)警和系統(tǒng)規(guī)避社會風險進行了機制設(shè)計[16](p69-76)。有的學者則基于旅游經(jīng)濟發(fā)展的角度出發(fā),闡釋了旅游安全風險系統(tǒng)的要素組成、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和運行規(guī)律,進而對旅游安全風險系統(tǒng)的評價體系、安全措施等展開了具體論證[17](p17-21)。此外,一些學者亦基于系統(tǒng)動力學的視角,對教育層面信息化項目的風險演化展開了仿真研究,進而提出了相應(yīng)的風險管控意見[18](p49-56)。遺憾的是,截至目前基于系統(tǒng)演化的視角,對國家政治風險的生成機理展開的分析,國內(nèi)理論界還缺乏足夠關(guān)注。顯然,這同當下國家對防范政治風險的高度重視是不相契合的。事實上,政治風險的內(nèi)在系統(tǒng)性,及其在當下面臨的重大風險性問題中核心性位置,都決定了要科學把握其內(nèi)涵,就決不能僅將目光聚焦于政治系統(tǒng)內(nèi)部,而應(yīng)基于社會整體發(fā)展的宏觀視野對其展開系統(tǒng)分析和檢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政治風險絕不是孤立出現(xiàn)的,也不限于政治領(lǐng)域,而是經(jīng)濟文化社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19]。
基于系統(tǒng)科學的視域來審視政治風險,可見要切實形成風險防范和規(guī)避效應(yīng),則基于政治系統(tǒng)為核心中樞,對政治風險因素的系統(tǒng)輸入、內(nèi)在演變過程做出明確是根本前提。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首先就要對政治風險因素的主體構(gòu)成做出歸納界定,由此才能把握政治風險的內(nèi)在根源,摸清其演化路線,進而從根本上形成規(guī)避效應(yīng)。由此路徑展開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政治風險因素雖內(nèi)含了有形因素和無形因素之二重架構(gòu),但這些風險因素的產(chǎn)生主體從根本上主要來自政治系統(tǒng)的“內(nèi)生”、社會系統(tǒng)的“衍生”和外部系統(tǒng)的“傳導(dǎo)”三大方面,如其中的國家機構(gòu)因素,包括各級國家機構(gòu)的制度發(fā)展狀況、政治生態(tài)狀況和個體政治能力狀況等,就是典型的“內(nèi)生”型政治風險因素,而社會心理因素包括社會個體的心理認同狀況、政治系統(tǒng)的社會公信力狀況等,則顯然是社會系統(tǒng)的“衍生”型政治風險,與此相對應(yīng),在開放環(huán)境下,意識形態(tài)因素則兼具“自生”和“傳導(dǎo)”的雙重特性,而政治文化因素、經(jīng)濟基礎(chǔ)因素等則既具由“內(nèi)生”和“衍生”的雙重特性,又具有不可忽視的“傳導(dǎo)”型特性。也即這類因素的風險源是多維度的。基于此,可厘定國家政治風險的系統(tǒng)演化模型(圖1)。
基于這一模型,可將政治風險的生成和演化概括為以下三條主要模式:
其一,政治系統(tǒng)的“自生”型生成演化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政治風險的生成主要基于以下四條路徑展開:1.國家機構(gòu)層面的“自生”型路徑,主要以制度、生態(tài)和個體為主要“病灶”,其中制度體系建設(shè)的缺失是主要根源,制度規(guī)范體系的不足不僅極易致使政治生態(tài)污染,亦阻礙個體政治能力的提升,進而通過各級國家機構(gòu)弊病和問題的產(chǎn)生和放大,在政治系統(tǒng)內(nèi)部生成政治風險。2.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自生”型路徑,主要以對社會多元思潮,尤其是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性不足,導(dǎo)致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導(dǎo)權(quán)、管理權(quán)和話語權(quán)喪失,進而通過動搖國家核心價值觀的根本指導(dǎo)地位,在政治系統(tǒng)內(nèi)部生成政治風險。3.政治文化層面的“自生”型路徑,主要以政治系統(tǒng)內(nèi)消極腐朽的政治文化,如特權(quán)意識、家長作風、潛規(guī)則思維等的叢生和缺乏治理,對國家政治紀律、政治規(guī)矩和政治生態(tài)等造成扭曲和破壞,給政治系統(tǒng)運行帶來潛移默化的惡性影響,進而在放大政治文化問題的過程中形成政治風險。4.經(jīng)濟基礎(chǔ)層面的“自生”型路徑。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對經(jīng)濟基礎(chǔ)亦具有反作用,這一層面主要基于政治上層建筑在推進經(jīng)濟發(fā)展中忽視基本規(guī)律,政府職能轉(zhuǎn)變不到位、權(quán)力過分集中和對市場資源配置缺乏足夠效率,囿于引導(dǎo)和推進經(jīng)濟發(fā)展能力的缺失,進而在上層建筑放大問題并導(dǎo)致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
其二,社會系統(tǒng)的“衍生”型生成演化模式。所謂衍生,即從母體中演變而生成新物質(zhì)。伊斯頓認為,“政治系統(tǒng)是在社會系統(tǒng)中與社會價值之權(quán)威性分配有關(guān)的互動行為”[15](p26),即政治系統(tǒng)本身包容于社會系統(tǒng)之中。社會系統(tǒng)的風險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具有在政治系統(tǒng)進行衍生的可能性。在這一層面下,政治風險的生成主要基于以下三條路徑:1.社會心理層面的“衍生”型路徑,主要以社會系統(tǒng)內(nèi)部信任體系、參與體系等的瓦解為導(dǎo)引,進而蔓延至政治系統(tǒng)內(nèi)部,引發(fā)社會成員對政治系統(tǒng)的認同危機,致使政治系統(tǒng)社會資本存量不斷流失的情況下,導(dǎo)致政治風險與危機的產(chǎn)生。2.政治文化層面的“衍生”型路徑。政治文化雖是人們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價值取向,但同社會文化亦存在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性。在這一層面下,正是基于消極社會文化向政治文化體系的蔓延,給現(xiàn)實政治生活、政治生態(tài)造成破壞,進而導(dǎo)致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對此,從近年來中央對部分地方黨政系統(tǒng)存在的“江湖習氣”“碼頭文化”和“圈子文化”的著力批判便可管窺一豹。3.經(jīng)濟基礎(chǔ)層面的“衍生”型路徑。同政治文化類似,經(jīng)濟基礎(chǔ)因素同樣關(guān)聯(lián)著政治系統(tǒng)和社會系統(tǒng)兩方面,政治系統(tǒng)內(nèi)的反作用,使其對政治風險具有“自生”效應(yīng),而其在社會系統(tǒng)的消極展開,則又構(gòu)成了“衍生”政治風險的重要外因。在這一模式下,包括經(jīng)濟動力的衰退、發(fā)展績效的低下和失業(yè)率的提升等等,都會對社會成員的政治認同帶來制約作用,并消解政治主體的合法性根基,進而在經(jīng)濟危機的基礎(chǔ)上點燃政治風險。
其三,外部系統(tǒng)的“傳導(dǎo)”型生成演化模式。外部環(huán)境因素是確保政治系統(tǒng)穩(wěn)定的拓展性要件,對國家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能起到間接性影響。現(xiàn)代國家的運行絕不是孤立自主的,而是在同其他國家的交往中得以展開的,也是在同其他國家的交往中實現(xiàn)發(fā)展的。國家所處的外部環(huán)境,包括參與國際事務(wù)治理的廣度和深度、同國際社會展開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家內(nèi)部的運作狀況,并在實踐中構(gòu)成了國內(nèi)政治風險的潛在性因素。在當前國際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中,這一層面政治風險的生成,亦主要集中于三條路徑:1.外部經(jīng)濟層面的“傳導(dǎo)”型路徑。如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為擺脫國內(nèi)產(chǎn)業(yè)效率低下和政府應(yīng)急機制失靈等的現(xiàn)實問題,通過關(guān)稅戰(zhàn)、貿(mào)易戰(zhàn)對他國進行的打壓,實質(zhì)上就是試圖將本國經(jīng)濟危機轉(zhuǎn)嫁于他國,給他國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負面影響,進而在政治系統(tǒng)產(chǎn)生風險因素。2.外部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傳導(dǎo)”型路徑,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既是政治系統(tǒng)的“內(nèi)生”型問題,也是社會系統(tǒng)“衍生”型問題,在開放環(huán)境下更是外部環(huán)境的“傳導(dǎo)”型問題,意識形態(tài)滲透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歪曲他國理論指導(dǎo)體系到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再到直接展開“顏色革命”等皆屬此類。3.外部政治文化層面的“傳導(dǎo)”型路徑。這一層面實質(zhì)上亦屬于意識形態(tài)滲透范疇,但相對要更為隱蔽和間接,如借學術(shù)研究的名頭,大肆傳播西方政治理念和大眾文化等,以達到消解他國政治文化合法性的目標,這些因素的傳導(dǎo)無不對他國構(gòu)成嚴峻的政治威脅。
三、路徑選擇:政治風險的系統(tǒng)規(guī)避
上述有關(guān)政治風險之因素來源和內(nèi)在機理的論證,表明政治風險生成和演化的系統(tǒng)性和復(fù)雜性,即政治風險本身是由多因素、多主體共同推動和作用的結(jié)果,這決定了相關(guān)的政治主體要切實防范和有效規(guī)避政治風險,就決不能僅僅將目光聚焦于政治系統(tǒng)內(nèi)部,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片面性毛病,而應(yīng)從政治風險的因素流動、主體識別等角度展開應(yīng)對,由此才能為規(guī)避政治風險,維護政治穩(wěn)定提供堅實支撐。基于上述分析,要防范和規(guī)避政治風險,可立足于政治系統(tǒng)、社會系統(tǒng)和外部系統(tǒng)之關(guān)聯(lián)性的大視野,形成具體的規(guī)避策略,具體而言,相關(guān)政治主體可重點從以下三方面展開:
其一,從政治系統(tǒng)的內(nèi)部視角看,要切實規(guī)避政治風險,就應(yīng)把積極推進各級國家機構(gòu)的有序運行擺在核心位置上,以徹底掃除政治風險的“內(nèi)生”土壤。對此,應(yīng)基于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展開應(yīng)對。從宏觀看,切實規(guī)避政治風險,就要在堅持核心領(lǐng)導(dǎo)的前提下,推進國家治理理論的不斷創(chuàng)新化。對于國家機構(gòu)的治理而言,領(lǐng)導(dǎo)即引導(dǎo),理論即指南。唯有形成強大的領(lǐng)導(dǎo)核心,才能形成國家發(fā)展的堅強動力,也唯有不斷推進國家治理理論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亦才能為規(guī)避政治風險提供主導(dǎo)性理論支撐。放在新時代我國政治體系中,就是要把堅持黨的領(lǐng)導(dǎo)和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chuàng)新發(fā)擺在首位,唯此才能在規(guī)避政治風險上形成根本性領(lǐng)導(dǎo)力量。從中觀看,切實規(guī)避政治風險,就要堅持以制度完善為驅(qū)動,推進各級國家機構(gòu)內(nèi)部政治生態(tài)的不斷廉潔化。制度是國家機構(gòu)有序運行的剛性支撐,制度作為“周期性發(fā)生的行為模式”,同“組織與程序”的運行狀況“成正比例”[20](p12)。在推進各級國家機構(gòu)有序運行的過程中,相關(guān)政治主體唯有推進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以堵塞一切可能性制度漏洞,才能在提升治理效率的過程中營造良好政治生態(tài),進而為規(guī)避政治風險提供防護保障。從微觀看,切實規(guī)避政治風險,就要堅持以政治素質(zhì)培育為本,推進干部綜合素質(zhì)的全方位提升。政治素質(zhì)是干部素質(zhì)體系的核心,決定著其他素質(zhì)的培育效用,唯有在強化政治素質(zhì)培育的前提下,推進干部各方面素質(zhì)的全方位提升,才能確保干部切實形成駕馭政治局面的主觀能力,進而才能在推進各級國家機構(gòu)有序和有效運行的過程中,真正提升防范和規(guī)避政治風險的主觀能動性。
其二,從政治系統(tǒng)與社會系統(tǒng)的關(guān)聯(lián)性角度看,要切實規(guī)避政治風險,就應(yīng)把強化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和推進政治社會化擺在核心位置上,以徹底剪除政治風險的“衍生”搖籃。社會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既是社會主體強化凝聚力和參與力的重要前提,也是政治主體提升社會公信力的現(xiàn)實根基。因此,對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保障,實質(zhì)上關(guān)涉到政治與社會兩大系統(tǒng)的發(fā)展與穩(wěn)定。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guān)”[13](p82)“政治權(quán)力不過是用來實現(xiàn)經(jīng)濟利益的手段”[21](p250)。因此,要切實防止出現(xiàn)社會風險向政治系統(tǒng)蔓延的可能性,一項最為基本的工程就是把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擺在極為突出的位置上。對此,應(yīng)著力做好兩方面:一要不斷提升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質(zhì)量,其中既要通過投資體制的深化改革來優(yōu)化資源配置,也要通過結(jié)構(gòu)優(yōu)化來提升全要素生產(chǎn)率,尤其是要不斷提升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和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以在建設(shè)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體系的過程中,更好地滿足社會主體日益增長的物質(zhì)和精神需求。二要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增進民生福祉是推進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根本目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既要堅持效率優(yōu)先,亦要著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尤其要在發(fā)展中著力補齊民生短板,如此才能在不斷強化社會主體政治認同的過程中,為規(guī)避政治風險的社會衍生提供基礎(chǔ)性支撐。
切實規(guī)避社會風險向政治系統(tǒng)蔓延的可能性,也要積極推進政治的社會化。政治社會化,簡言之即社會成員塑造其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識的過程。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政治社會化的展開包括政治主體傳遞政治文化和政治價值,以及社會主體通過學習形成正確政治態(tài)度、政治價值和政治行為兩大層面。伊斯頓等就將政治社會化界定為“人們習得政治取向和行為模式的發(fā)展過程”[22](p356)。政治社會化既是維系政治系統(tǒng)穩(wěn)定的基本條件,也是提升社會主體政治參與熱情和能力的重要保障。對此,則應(yīng)積極做好兩方面工作:一要不斷創(chuàng)新政治文化,為推進政治社會化提供內(nèi)涵支撐。政治文化是政治社會化的內(nèi)在主體,政治社會化說到底就是“政治文化形成、維持與轉(zhuǎn)變的過程”[14](p91)。維系政治穩(wěn)定,政治主體首先就要不斷推進政治文化創(chuàng)新,既要積極推進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現(xiàn)代化,也要培養(yǎng)和發(fā)展參與型政治文化,尤其是要積極做好同當代政治系統(tǒng)運作相契合的政治文化的挖掘和提煉,以在提升文化自信中不斷豐富政治社會化的理論內(nèi)涵。二要不斷疏通渠道,為推進政治社會化提供豐富載體。政治社會化的展開必然要通過一定的媒介,提升政治社會化的實效性,不僅要積極通過學校、社會政治組織和政治實踐活動等傳統(tǒng)渠道來傳播政治文化,亦要善于利用各類新式的大眾傳播工具開拓政治社會化的新途徑,由此,在不斷強化社會政治認同的過程中,為維系政治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提供文化保障。
其三,從政治系統(tǒng)與外部系統(tǒng)的關(guān)聯(lián)性角度看,要切實規(guī)避政治風險,就應(yīng)把積極推進多變合作和強化意識形態(tài)工作擺在核心位置上,以徹底斬斷政治風險的“傳導(dǎo)”渠道。多邊主義內(nèi)蘊著開放包容、平等協(xié)商與合作共贏的價值取向,既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基本前提,也是確保國內(nèi)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推行的貿(mào)易保護主義戰(zhàn)略,實質(zhì)上是對國際多邊主義發(fā)起的挑戰(zhàn)。要切實規(guī)避這一層面帶來的政治風險,就必須堅定地同世界大多數(shù)國家一道,堅持推進多邊主義,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一方面要著眼于構(gòu)建開放型世界經(jīng)濟的要求,著力推進多邊自由貿(mào)易的深化發(fā)展,既要在現(xiàn)有國際機制下不斷拓展多邊合作框架,也要積極維護多邊貿(mào)易體制及其基本原則,推進國際貿(mào)易不斷提升法治化和穩(wěn)定性,以在著力實現(xiàn)開放共贏的過程中,為推進本國社會經(jīng)濟的有序發(fā)展提供外部驅(qū)動力。另一方面,也要在堅持權(quán)責統(tǒng)一的前提下,積極推進全球治理機制的變革。對此,既要切實遵循《聯(lián)合國憲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則,也要本著積極主動的姿態(tài),積極參與到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與執(zhí)行當中去,以在國際事務(wù)中不斷提升本國的話語權(quán)和影響力,由此,在構(gòu)建和形成以合作共贏為目標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chǔ)上,為規(guī)避政治風險的外部傳導(dǎo)構(gòu)筑堅實的防火墻。
切實規(guī)避外部環(huán)境傳導(dǎo)帶來的政治風險,也要把意識形態(tài)工作擺在極為突出的位置上。政治風險的產(chǎn)生主體是人,政治風險的防范和規(guī)避主體同樣也是人,唯有著力提升人的理性認知和思想覺悟,才能確保政治風險真正做到可防可控,尤其是面對當下國際政治層面意識形態(tài)斗爭日益復(fù)雜多變的大背景,要切實規(guī)避外部意識形態(tài)滲透帶來的政治風險,則強化意識形態(tài)建設(shè)力度是必然要求。從政治系統(tǒng)與外部系統(tǒng)的關(guān)聯(lián)性角度看,對此應(yīng)著力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要不斷增強本國意識形態(tài)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意識形態(tài)工作事關(guān)國家的前途命運,要切實規(guī)避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風險,政治主體既要嚴格落實意識形態(tài)工作責任制,牢牢掌握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也要不斷創(chuàng)新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在提升意識形態(tài)工作針對性和實效性的過程中,不斷夯實政治系統(tǒng)穩(wěn)序運行的理念根基。二要堅持不懈地展開對外部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性工作。必須明確,意識形態(tài)本身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自成體系的意識形態(tài),任由外部意識形態(tài)滲透不僅動搖本國思想根基,亦是對本民族向心力的破壞。必須通過批判對意識形態(tài)滲透的危害性作出深刻揭露,闡明其在內(nèi)在的陰謀動機和真實意圖,由此才能在不斷激發(fā)愛國熱情的基礎(chǔ)上,為規(guī)避政治風險提供更加堅實的理念根基。
四、余論
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風險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標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無所不包的背景”[23](p5-11)。如何有效防范和規(guī)避風險也成為當下各國普遍關(guān)注的焦點話題。人類本身是生活在由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軍事和國防等各要素構(gòu)成的有機系統(tǒng)中,這其中政治問題因關(guān)涉到國家主權(quán)和政權(quán)問題,而更帶有權(quán)威性和根本性,這決定了在人們所面臨的眾多風險類型中,政治風險顯然是居于核心位置的,其他領(lǐng)域的風險如若不及時加以化解,最終都有可能蔓延和反映到政治領(lǐng)域,給政治系統(tǒng)的穩(wěn)定帶來破壞性,因此,對政治風險的防范和規(guī)避也必然更為系統(tǒng)和復(fù)雜。目前,學界對風險問題的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社會風險、生態(tài)風險等“邊緣”層面,對作為其中之“核心部件”的政治風險問題還缺乏學理闡釋。要切實提升防范政治風險的能力,必須對政治風險生成機理作出明確界定。文章旨在拋磚引玉,提出一個初步的系統(tǒng)性分析框架,當前,在厘清框架邏輯的基礎(chǔ)上,學界應(yīng)結(jié)合實際,進一步對政治風險的防范機制展開深度分析,為維護社會政治穩(wěn)定提供更加堅實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