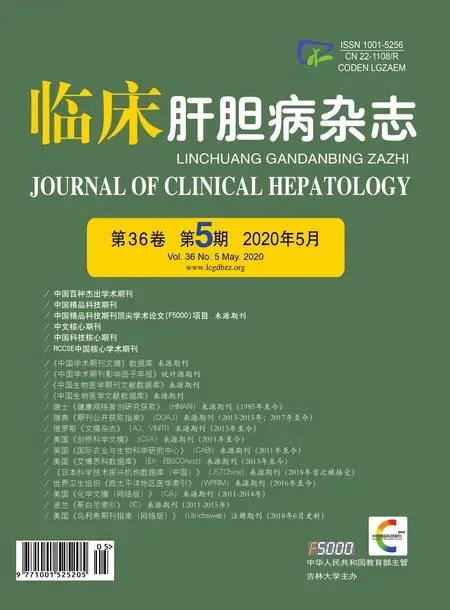男性原發(fā)性膽汁性膽管炎合并抗富亮氨酸膠質(zhì)瘤失活1蛋白抗體相關(guān)腦炎1例報告
劉 曼, 唐彤丹, 劉永華, 朱 磊
1 大連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第一醫(yī)院 消化科, 遼寧 大連 116011; 2 大連市中心醫(yī)院 急診病房, 遼寧 大連 116033
原發(fā)性膽汁性膽管炎(PBC)是一種由免疫介導(dǎo)的、抗線粒體抗體陽性的小葉間膽管炎癥性損傷的慢性膽汁淤積性疾病,是女性慢性肝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病因,極少數(shù)見于男性患者。抗富亮氨酸膠質(zhì)瘤失活1蛋白(leucine-rich glioma inactivated-1, LGI1)抗體相關(guān)腦炎是自身免疫性腦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E)的一種,多見于中老年男性,與癲癇有高度相關(guān)性,通常不伴隨腫瘤的發(fā)生,而且臨床上對免疫治療的反應(yīng)較好[1]。抗LGI1抗體相關(guān)腦炎并不常見,而同時合并男性PBC的概率更低。本文通過分析臨床診斷的1例男性PBC合并抗LGI1抗體相關(guān)腦炎的病例,對可能的發(fā)病機(jī)制復(fù)習(xí)文獻(xiàn),做初步的探討。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性,59歲,以“肢體抽搐、精神智能改變4個月加重3 d”于2018年9月4日來大連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第一醫(yī)院就診。表現(xiàn)為頭頸部串電麻木,意識欠清,少言易怒,左側(cè)肢體僵硬抖動,肌肉疼痛,頭部擺動,面色潮紅咬牙,呼吸困難,心前區(qū)緊縮感,反應(yīng)遲鈍,肢體乏力。既往否認(rèn)病毒性肝炎病史,否認(rèn)飲酒史,否認(rèn)肝損害藥物攝入史。6個月前曾查肝功能:ALT 92 U/L, AST 49 U/L,ALP 170 U/L,GGT 68 U/L,TBil 7.1 μmol/L,TBA 6.0 μmol/L。入院查體:無貧血貌,鞏膜無黃染;腹平軟,肝脾肋下未觸及;雙下肢不腫;神經(jīng)系統(tǒng)無異常。肝功能:ALT 118 U/L,AST 40 U/L,ALP 186 U/L,GGT 69 U/L,TBil 8.6 μmol/L,TBA 3.5 μmol/L。 腎功能:尿素5.26 mmol/L,血肌酐71 μmol/L。尿蛋白陰性,尿紅細(xì)胞、白細(xì)胞0個/高倍視野。血清四鐵、銅藍(lán)蛋白正常。肝炎病毒學(xué)陰性。血清免疫學(xué):抗核抗體陰性,抗線粒體抗體(AMA)陽性,AMA-M2亞型陽性,抗平滑肌抗體陰性,抗肝腎微粒體抗體陰性,IgG 16.9 g/L,SS-A抗體陽性,Ro-52抗體陽性。血清LGI1抗體陽性,滴度1∶100。視頻腦電圖示輕度異常腦電圖,背景活動偏慢,右側(cè)枕頂后顳區(qū)局限性慢波發(fā)放。頭部MRI T2FLAIR序列示右側(cè)海馬區(qū)信號改變,考慮亞急性炎性改變(圖1)。肝臟MRI示肝臟形態(tài)大小正常、肝囊腫。腦脊液檢查外觀無色透明,壓力190 mm H2O,葡萄糖3.52 mmol/L,總細(xì)胞數(shù)3×106/L,蛋白定量31.2 mg/dl,氯115 mmol/L,細(xì)菌培養(yǎng)陰性。腦脊液LGI1抗體陽性,滴度1∶32。治療方法:甲強(qiáng)龍500 mg、240 mg、120 mg各5 d,后改醋酸潑尼松口服逐漸減量至15 mg/d維持。德巴金1 g/d控制癲癇發(fā)作。口服熊去氧膽酸750 mg/d,改善膽汁淤積。治療1個月后隨訪,患者仍時有左側(cè)肢體抖動,反應(yīng)遲鈍有所好轉(zhuǎn)。復(fù)查肝功能:ALT 33 U/L,AST 26 U/L,ALP 86 U/L,GGT 35 U/L,TBil 9.2 μmol/L,TBA 4.0 μmol/L。

注:T2FLAIR序列提示右側(cè)海馬區(qū)信號增強(qiáng)(箭頭所示)。
2 討論
抗LGI1抗體相關(guān)腦炎多見于50歲以上人群,男性多見。臨床常以癲癇、認(rèn)知功能障礙、近記憶力下降、幻覺等發(fā)病。抗LGI1抗體相關(guān)腦炎的一個特征性臨床表現(xiàn)是面臂肌張力障礙,其常出現(xiàn)在意識障礙、精神行為異常發(fā)生之前[2]。抗LGI1抗體相關(guān)腦炎患者頭部MRI可見雙側(cè)顳葉高信號或一側(cè)海馬區(qū)異常信號,腦脊液檢查多正常或僅有輕中度蛋白、細(xì)胞數(shù)升高。血清及腦脊液中檢出抗LGI1抗體是特異性表現(xiàn)。抗LGI1抗體相關(guān)腦炎是僅次于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抗體腦炎的一種AE。抗LGI1抗體相關(guān)腦炎的診斷要點(diǎn)為:對表現(xiàn)為邊緣性腦炎,或者面臂肌張力障礙的患者,如頭MRI示單側(cè)或雙側(cè)的顳葉異常信號、腦電圖異常,需考慮AE的診斷,如血清和(或)腦脊液抗LGI1抗體陽性,可確診抗LGI1抗體相關(guān)性腦炎。體液免疫異常與抗體介導(dǎo)的可逆性神經(jīng)元功能障礙是AE的主要機(jī)制[3],AE的確診往往依賴特異性抗體的表達(dá),提示B淋巴細(xì)胞在AE中的作用或許更為突出。
PBC是由肝內(nèi)細(xì)小膽管非化膿性、進(jìn)行性、破壞性炎癥,導(dǎo)致長期持續(xù)性肝內(nèi)膽汁淤積,最終引起肝纖維化、肝硬化的一種慢性自身免疫性肝病[4]。好發(fā)于中年女性,男女發(fā)病比例為1∶9,男性PBC很少見。PBC病因及發(fā)病機(jī)制不清。目前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是一定的環(huán)境因素作用于具有遺傳易感性的個體,誘發(fā)機(jī)體免疫失衡,導(dǎo)致T淋巴細(xì)胞、B淋巴細(xì)胞介導(dǎo)膽管上皮的自身免疫性損傷[5]。PBC的診斷目前主要依據(jù)美國肝病學(xué)會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1)膽汁淤積的生化學(xué)表現(xiàn),如ALP的升高;(2)AMA陽性,尤其是AMA-M2亞型陽性;(3)肝臟病理學(xué)可見非化膿性小膽管破壞性炎癥、旺熾性膽管病變;以上3條符合其中的2條就可以診斷PBC。本例患者在本次住院6個月前的門診資料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ALP、GGT升高,但均未予以重視并進(jìn)一步查治。本次入院期間前后3次化驗(yàn)ALP、GGT仍升高且AMA、AMA-M2皆陽性,所以考慮診斷PBC。另外患者多次肝功能均提示ALT、AST升高,因此需要注意其他原因造成的肝細(xì)胞損傷,比如病毒性肝炎、藥物性肝損傷、脂肪性肝病等,但患者無肝炎病史、無應(yīng)用肝損傷藥物史,肝臟影像學(xué)未見脂肪肝,所以此幾種原因不考慮。但是需要注意PBC重疊自身免疫性肝炎的可能,但ALT、IgG升高不明顯,需要肝臟病理學(xué)證實(shí)。并且因其是男性患者,診斷PBC、尤其是確診有無與自身免疫性肝炎的重疊綜合征更應(yīng)慎重,曾考慮進(jìn)行肝活檢,但因?yàn)榛颊呱窠?jīng)系統(tǒng)癥狀持續(xù)而未能獲取肝臟組織學(xué)依據(jù)。PBC可以并發(fā)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常見的有合并干燥綜合征、甲狀腺炎等,但是查閱文獻(xiàn)未見有合并AE的報告。
從AE和PBC的發(fā)病機(jī)制、診斷標(biāo)準(zhǔn)以及免疫治療來看,體液免疫異常、抗體產(chǎn)生介導(dǎo)的免疫損傷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也意味著B淋巴細(xì)胞在這兩個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fā)生發(fā)展中起到關(guān)鍵作用。PBC發(fā)生的核心問題是膽汁淤積,膽汁淤積必然會導(dǎo)致脂溶性維生素吸收障礙,包括維生素D[6]。PBC患者普遍存在血清25-(OH)D3低水平狀態(tài),而且25-(OH)D3低水平與疾病嚴(yán)重程度以及是否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guān)[7]。本例患者近期出現(xiàn)了神經(jīng)系統(tǒng)問題,在此之前已經(jīng)有肝功能異常,雖然沒有檢查AMA,但是其后的AMA、AMA-M2的陽性表達(dá)提示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PBC,因此可以考慮PBC誘發(fā)了膽汁淤積,從而維生素D吸收障礙,導(dǎo)致最終有活性的骨化三醇減少。目前有研究[8]指出,維生素D在AE中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PBC導(dǎo)致的膽汁淤積、維生素D缺乏可能從一定程度上誘導(dǎo)了AE的產(chǎn)生。
維生素D是一種脂溶性類固醇激素,人體內(nèi)的維生素D僅少量來自于食物,主要是由皮膚中的7-脫氫膽固醇經(jīng)紫外線照射后生成,在腎臟和肝臟中,維生素D經(jīng)過兩次羥化形成活性的1,25(OH)2D3,又稱骨化三醇。骨化三醇在維生素D結(jié)合蛋白轉(zhuǎn)運(yùn)后與靶器官的維生素D受體結(jié)合發(fā)揮生物學(xué)效應(yīng)。B淋巴細(xì)胞可以表達(dá)維生素D受體,激活后誘導(dǎo)B淋巴細(xì)胞的低反應(yīng)性,可直接導(dǎo)致細(xì)胞凋亡,抑制B淋巴細(xì)胞的分化增殖,減少免疫球蛋白的產(chǎn)生,表明維生素D對B淋巴細(xì)胞功能紊亂性的疾病有潛在的作用[9]。但是,無論是AE還是PBC,由于T淋巴細(xì)胞介導(dǎo)的免疫耐受被打破,導(dǎo)致B淋巴細(xì)胞產(chǎn)生抗體引發(fā)的免疫反應(yīng)最終導(dǎo)致免疫損傷,都是一個極其復(fù)雜的免疫過程。維生素D對T淋巴細(xì)胞免疫也有一定的調(diào)節(jié)作用,所以一定程度上,維生素D在PBC、AE的發(fā)病、發(fā)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此,可以把維生素D作為一個重要的靶點(diǎn)進(jìn)行研究,闡述PBC、AE的發(fā)病機(jī)制,甚至可以為其他免疫性疾病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思路甚至新的治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