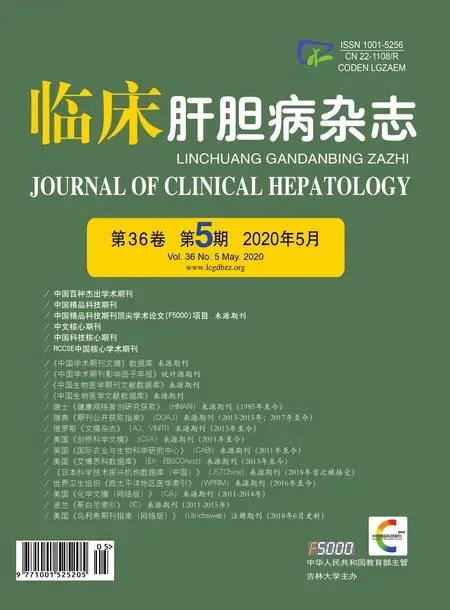肝內固有抗原遞呈細胞調控抗HBV免疫應答的作用及機制
謝曉紅, 楊東亮, 劉 嘉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 感染科, 武漢 430022
據2006年的統計資料,我國現有慢性HBV感染者9300萬人,其中慢性乙型肝炎(CHB)約2000萬例,每年約有30萬人死于CHB所導致的終末期肝病,如肝硬化和肝癌[1]。闡明HBV持續性感染的機制,探索清除HBV持續性感染的新靶點和新策略是該領域亟待解決的重大科學問題。
作為被HBV侵犯的主要器官,肝臟具有極其特殊的解剖結構和免疫微環境。肝血竇是肝臟所獨有的特殊結構,是肝臟微循環血流灌注和免疫應答的主要發生部位。血液中的各種成分(如淋巴細胞和病原體等)在肝血竇內可較長時間停留,并充分與肝血竇內的各種細胞發生相互作用,這一過程對于肝內天然免疫和適應性免疫應答的發生非常重要[2]。肝竇內皮細胞(liver sinusoidal endothelial cells,LSEC)和枯否細胞(Kupffer cells,KC)是肝血竇內最主要的固有抗原遞呈細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可從血液循環中有效攝取、加工抗原并交叉遞呈給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既往研究[3-5]認為,與成熟的專職APC遞呈誘導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活化不同,LSEC和KC交叉遞呈抗原往往誘導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形成耐受,表現為T淋巴細胞喪失細胞毒效應及產生效應性細胞因子(IFNγ和IL-2等)的能力。近年來的研究顯示,除誘導T淋巴細胞耐受外,LSEC和KC等肝內APC在特定條件下,也可促進肝內抗HBV免疫應答的發生,從而介導HBV的清除(表1)。本文就肝內固有APC調控肝內抗HBV免疫應答的作用及機制加以綜述。
1 肝竇內皮細胞(LSEC)
LSEC構成了肝血竇的血管壁,是肝內非實質細胞的主要群體,約占肝非實質細胞的50%。由于LSEC在肝血竇中所處的特殊位置,其暴露于血液中各種成分的刺激之下,并與血液中的淋巴細胞存在著密切的相互作用。LSEC是一種高效的APC,表達參與抗原遞呈過程的多種分子,如CD54、CD80、CD86、MHCⅠ/Ⅱ和CD40等,可向CD4+和CD8+T淋巴細胞遞呈抗原[6-7],從而調控肝內的T淋巴細胞應答。
1.1 LSEC介導T淋巴細胞耐受 與DC類似,來自于病毒等病原體的外源性抗原可以被LSEC攝取和加工處理,并以交叉遞呈的方式遞呈給抗原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7]。且其交叉遞呈可溶性抗原的能力相較于DC更為高效[8]。與在淋巴結內活化的T淋巴細胞不同,LSEC交叉遞呈致敏的抗原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會在肝內滯留[9]。LSEC遞呈抗原給CD8+T淋巴細胞后,在最初的24 h內T淋巴細胞表面CD25、CD44和PD-1等分子的表達升高,CD62L的表達下降,抗原特異性T淋巴細胞發生增殖[6,10],這一過程與成熟DC致敏CD8+T淋巴細胞的過程相似。但與DC致敏誘導T淋巴細胞持續增殖不同,LSEC致敏的T淋巴細胞只發生短暫地增殖[11]。LSEC表面高表達PD-L1(B7-H1)分子,抗原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被致敏后PD-1分子表達上調,二者相互作用,導致T淋巴細胞無法進一步持續活化[10,12]。LSEC表面表達的MHC-Ⅰ和CD54等分子決定了LSEC對CD8+T淋巴細胞的黏附能力[13],這兩種細胞相互作用之后,LSEC表面CD54分子進一步上調,從而穩定LSEC對T淋巴細胞的抑制作用[9]。但T淋巴細胞也不會經歷凋亡,其機制可能與LSEC致敏的CD8+T淋巴細胞表達大量的抗凋亡分子bcl-2有關[10]。未經刺激的LSEC幾乎不表達IL-12,這一關鍵共刺激信號的缺失,導致T淋巴細胞被LSEC致敏后的活化無法持續,IFNγ的產生水平低下[14]。最終被LSEC致敏的T淋巴細胞被誘導形成耐受,接受TCR再刺激后缺乏IL-2和IFNγ等效應細胞因子的產生[9],IL-2缺乏進一步抑制CD8+T淋巴細胞活化[6]。此外,LSEC可通過影響其他細胞功能調控肝內T淋巴細胞免疫應答。LSEC與肝內DC相互接觸后,可降低DC表面CD80/CD86等共刺激分子的表達,抑制DC對初始T淋巴細胞的活化功能[15]。LSEC還可以以TGFβ依賴的方式誘導Treg的生成,抑制T淋巴細胞免疫應答[5]。通過LSEC遞呈抗原,被致敏的CD4+T淋巴細胞會發生增殖,但是不能分化為促炎性的Th1[14]。相反,LSEC可以促進CD4+T淋巴細胞向Th2方向分化并分泌IL-4[4]。其機制可能為生理條件下門靜脈血中內毒素誘導LSEC產生IL-10和前列腺素E2,降低LSEC表面MHCⅡ和CD86等分子的表達,從而抑制了LSEC致敏CD4+T淋巴細胞產生IFNγ的水平,更易向Th2方向分化[16]。上述因素共同參與了LSEC介導的肝內T淋巴細胞免疫耐受形成。
1.2 LSEC介導T淋巴細胞應答 越來越多研究表明,在特定條件下,例如在病毒感染或特定天然免疫通路活化等條件下,LSEC可逆轉其耐受屬性并促進T淋巴細胞應答。加入CD28可以解除B7-H1依賴的LSEC介導的CD8+T淋巴細胞的耐受性,表明共刺激/共抑制平衡決定了免疫耐受或免疫活化狀態[17]。靜息狀態下LSEC缺乏IL-12表達,而外源性IL-12則增加了LSEC對記憶和幼稚CD4+T淋巴細胞的輔助功能。在組織損傷時單核細胞會滲透到肝臟,由肝臟的APC誘導的局部免疫反應可以通過血液來源的單核細胞產生的IL-12增強[14]。有趣的是,將脾臟細胞加入到LSEC和CD4+T淋巴細胞的共培養體系中,導致了Th1表型的誘導,這表明LSEC介導的幼稚CD4+T淋巴細胞的失活可以被其他APC細胞群所克服[14]。筆者前期的研究[12]也顯示,TLR1/2配體刺激LSEC可誘導其活化,分泌IL-12且維持PD-L1表達水平不上調,進而誘導抗原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增殖并且產生IFNγ。改變抗原濃度也會對LSEC的免疫活性產生影響。LSEC遞呈低濃度卵清白蛋白抗原時,誘導抗原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產生耐受,而當提高抗原濃度10倍,LSEC不僅不能誘導CD8+T淋巴細胞產生耐受,相反,CD8+T淋巴細胞分化為功能性效應T淋巴細胞[18]。Kern等[19]在小鼠巨細胞病毒感染模型中首次表明,病毒感染LSEC后可誘導其功能成熟,進而促進CD8+T淋巴細胞免疫。Bottcher等[20]首次提出LSEC交叉遞呈抗原致敏的抗原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還存在第三種命運,即分化為具有增殖潛能的記憶性T淋巴細胞。這些記憶性T淋巴細胞與中樞記憶性T淋巴細胞相似,可重新定位到次級淋巴組織,再次接受TCR/CD28/IL-12共同刺激時,可以快速分化為效應T淋巴細胞。這種記憶性CD8+T淋巴細胞分化伴隨著迅速而短暫的顆粒酶B(GzmB)的表達和效應功能的誘導,早期短暫的GzmB表達依賴于LSEC分泌的IL-6介導的跨信號轉導途徑[21]。在此過程中,如果存在激活的Th1,其分泌的IL-2可顯著增強LSEC致敏的CD8+T淋巴細胞GzmB的表達水平,且啟動更加迅速[22]。
LSEC的活化狀態對調控肝內抗HBV特異性T淋巴細胞應答至關重要。筆者的研究[23-24]顯示,刺激NOD1信號通路在體內體外均可誘導LSEC活化和成熟,促進肝內抗HBV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應答,進而在HBV慢性復制小鼠模型中加速HBV的清除。在HBV自然感染過程中,T淋巴細胞表面膜CD100會被剪切釋放形成可溶性CD100,這一分子可誘導LSEC活化,進而促進抗HBV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應答并介導病毒的肝內清除[25]。筆者新近研究發現,HBV感染過程中產生的HBeAg也具有誘導LSCE的免疫功能成熟進而促進CD8+T淋巴細胞免疫功能的作用。此外,LSEC表面可結合活化的血小板,進而使得活化的HBV特異性效應T淋巴細胞可以錨著于其表面,通過LSEC間的窗隙與HBV感染的肝細胞接觸,發揮殺傷作用[26]。上述機制顯示LSEC在急性HBV感染的肝內免疫清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 枯否細胞(KC)
KC是肝臟的常駐巨噬細胞,除了由肝源性前體維持[27],還可以以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依賴的方式從單核細胞衍生。它們與LSEC一起形成應對病原體入侵肝臟的第一道屏障。KC的主要功能是清除門靜脈循環中的內毒素、釋放可溶性介質和提供抗原,有效地將抗原呈遞給免疫活性細胞[28-30]。在抗原攝取或刺激下,KC可被激活并分泌一系列的細胞因子(IFNα/β、TNFα),進行T淋巴細胞的招募[31-32]。
2.1 KC介導的T淋巴細胞耐受 KC是肝內免疫應答調節的重要參與者,通常與維持肝臟免疫耐受環境相關[33]。在體外誘導分化之后,KC顯示出更快速且持續地上調抗炎細胞因子編碼基因的表達[34]。相較于脾臟DC致敏的T淋巴細胞,KC致敏的T淋巴細胞表達相當水平的CD69,但CD25表達水平及IL-2分泌水平低下,從而導致T淋巴細胞失能[35]。在脂多糖刺激下,KC同樣釋放出大量的IL-10[36],而生理條件下門靜脈血中內毒素即可誘導KC分泌IL-10[16],肝竇局部IL-10濃度較高,誘導T淋巴細胞耐受。與此一致,IL-10受體阻斷可以部分恢復CD8 T淋巴細胞功能[37]。此外,與LSEC相同,KC可以抑制DC誘導的T淋巴細胞活化[35]。在病毒性肝炎中,大多數KC被激活并表達高水平的CD80、CD40和MHC-Ⅱ分子,從而獲得專職APC的表型[38]。
HBV感染的慢性化與年齡顯著相關,KC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研究[39]顯示,HBV陽性孕鼠的HBeAg可刺激子代小鼠的KC,誘導其分化為M2型巨噬細胞并上調PD-L1的表達,從而抑制抗HBV特異性的T淋巴細胞應答。這些HBeAg暴露過的子代小鼠出生后再次接受HBV攻擊后會發展為慢性化感染。此外,接受HBV攻擊后,幼年小鼠的慢性化比例要顯著高于成年小鼠。進一步研究[40]顯示成年小鼠肝內KC較幼年小鼠顯著減少,且其細胞上的TLR4表達也較幼年小鼠低,也提示了KC在介導HBV慢性化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敲除幼年小鼠的KC可增強Ly6C+單核細胞的肝內募集,促進HBV特異性CD8 T淋巴細胞的擴增及效應功能,加速HBV的清除[40-41]。乙型肝炎核心抗原可通過激活TLR2信號通路誘導KC產生IL-10,從而誘導HBV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耐受并致感染慢性化[42]。TLR2基因敲除或敲除小鼠的KC可增強小鼠體內的HBV特異性CD8+T淋巴細胞應答并促進HBV的清除[42]。筆者近期研究[37]也發現,HBsAg也可通過TLR2信號通路誘導KC擴增以及增加IL-10的分泌,進而抑制效應T淋巴細胞的功能。另外,HBeAg通過抑制NF-κB磷酸化以及抑制活性氧生成,抑制KC的NLRP3炎癥小體活化與IL-1β產生,這可能也是HBV免疫耐受形成的機制之一[43]。
2.2 KC介導的T淋巴細胞活化 KC可以在肝臟原位激活抗原特異性CD4+T淋巴細胞[44]。KC識別HBV或HBsAg后,迅速誘導IL-6、IL-1β、TNFα產生,促進自然殺傷細胞活化[45],并且可以在感染早期控制HBV復制[46]。Poly I:C可以顯著上調KC表達MHC-Ⅱ、B7-1、B7-2和ICAM-1,增強活化T淋巴細胞的功能;另一方面,吲哚美辛可以抑制KC分泌前列腺素,抑制KC介導的T淋巴細胞耐受[35]。Poly I:C還能上調KC表達CXCL13,促進肝內免疫,加速HBV清除[47]。KC在炎癥刺激下產生的細胞因子也可影響肝竇內其他細胞的活性[36]。
3 肝內其他APC
肝竇內的低速血流有利于淋巴細胞和肝細胞之間的相互接觸。肝臟微絨毛可以通過LSEC窗隙延伸到肝竇腔[48]。T淋巴細胞胞質也會形成偽足穿過LSEC窗孔延伸到Disse腔,與肝細胞微絨毛緊密接觸[26,49]。肝細胞表面大量表達MHC-Ⅰ和ICAM-1分子,可遞呈抗原給T淋巴細胞[50]。值得注意的是,肝臟ICAM-1并非均勻分布,而是集中分布在肝竇表面。LFA-1在淋巴細胞微絨毛上表達,可能通過其配體ICAM-1與肝細胞相互作用[49]。新近研究[51]顯示,HBV感染過程中,肝細胞可遞呈抗原給CD8+T淋巴細胞并誘導其活化和增殖,但不能使其分化為效應T淋巴細胞,而是表現為功能耗竭T淋巴細胞的特征。如果給與IL-2信號刺激,可挽救這些T淋巴細胞的功能。
肝星狀細胞也能夠處理外源性抗原肽,遞呈給CD4+T淋巴細胞,并以交叉遞呈的方式致敏CD8+T淋巴細胞,誘導T淋巴細胞活化并發揮功能[52]。
4 總結與展望
肝內固有APC在調控肝臟免疫應答、維持肝臟免疫穩態中發揮重要作用。在生理條件下,肝內固有APC可以通過多種機制誘導T淋巴細胞耐受,避免肝內病理免疫損傷的發生。然而,上述機制也會被HBV利用從而幫助其建立持續性感染。隨著研究的深入,目前已發現在HBV感染過程中,多種機制參與了調控肝內固有APC的活化狀態,進而決定肝內抗HBV特異性T淋巴細胞應答的強度并影響病毒的清除。但目前對于肝內APC功能的研究多停留在單個細胞亞群的水平,仍缺乏對肝內不同細胞群體間以及肝內和肝外免疫細胞間的互作網絡的整體認識。進一步深入闡明相關機制將為探索更有效的阻斷HBV持續性感染的免疫干預策略提供理論基礎和實驗依據。

表1 肝內固有APC調控肝內抗HBV免疫應答的作用及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