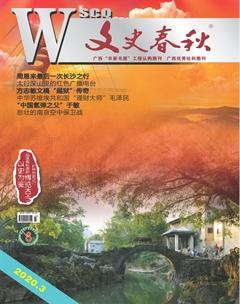古人如何防疫
鄭學富
在科技和醫學都不發達的古代,一旦有了疫情如何應對?古人也很有智慧,有很多防治的辦法,如藥酒、建隔離醫院、藥物醫治等。本文所述的只是其中幾種,
古人在春節時有喝防疫藥酒——屠蘇酒的習俗。屠蘇酒,相信是由漢末名醫華佗創制而咸,后經唐代醫藥學家孫思邈流傳開來,其《備急千金要方》中說:“飲屠蘇,歲旦辟疫氣,不染瘟疫及傷寒。”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也有關于屠蘇酒的記載:“用赤木桂心七錢五分,防風一兩,菝葜五錢,蜀椒、桔梗、大黃五錢七分,烏頭二錢五分。赤小豆十四枚,以三角絳囊盛之,除夜懸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煎數沸。”兼有滋補保健、防病療疾、驅邪避瘴等多種功能,這大概就是古人新春佳節飲屠蘇酒的原因所在。
古時雖然醫療條件差,但是為了對抗疫情擴散,當政者也采取了一些應對措施。從秦朝時就設有癘遷所。秦代竹簡《睡虎地秦墓竹簡》上記載:“城旦,鬼薪癘。何論?當遷癘遷所。”癘遷所就是當時專門收容麻風病人的隔離治療醫院,人們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染上麻風病,要立即向官府報告,醫生確診后,官府便將患者送到癘遷所強制隔離,以防止麻風病毒傳播蔓延。到了唐代,經濟科技都有了很大發展,長安城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專業醫療機構,如官辦的“養疾坊”、民辦的“病坊”。在緊急情況下,一些寺院也被開辟為“癘人坊”,名曰“悲田坊”或“福田院”,專門收容傳染病隔離治療,而且做到男女分住,給予一定的供養和照顧。
抗擊疫情,藥物治療是古今都普遍使用的辦法。大文豪蘇軾,不僅苦讀經史,于少年時也讀了不少醫學書籍,為官后更是收集了不少宮廷秘方和民間偏方,在醫藥、養生和防疫方面有很多建樹,他收集到的“圣散子方”就曾在抗疫疾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蘇軾謫居黃州的第二年,一場疾疫大爆發,迅速蔓延,民眾掙扎在死亡線上。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蘇軾手中正好有一秘方“圣散子方”可用。此方是蘇軾懇訪眉山名醫巢谷所得,對醫治瘟疫甚為有效。“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救民于倒懸。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52歲的蘇軾到杭州任太守。在他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顆粒無收,饑民哀嚎,流離失所,由于饑民食用死掉的家畜、家禽,造成疫疾大流行。蘇軾又拿出“圣散子方”,配成藥劑發給患者,并派官員帶著醫生到各街巷為患病者醫治,救活了很多人。蘇軾從長遠考慮,他深知“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于是將朝廷撥付的修繕費節約出2000緡錢。自己又捐出50兩黃金,在杭州城中心建起了一處病坊,取名“安樂坊”。據記載,“安樂坊”在3年時間里就醫好了上千個患者。蘇軾還未雨綢繆,廣蓄糧米、藥品,以備急用。
后來朝廷充分肯定了蘇軾的做法,將“安樂坊”收歸朝廷管理,更名為“安濟坊”,并撥付經費。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朝廷開始在各地設置“安濟坊”,專為窮苦人治病。
傳染病、瘟疫不僅給人們帶來巨大損失,而且還讓人擔驚受怕,談之色變。對疫情重視是必要的,但過度擔心,甚至恐懼則是沒必要的。《中國疫病史鑒》記載。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里,中國先后發生過321次疫病流行,經過有效預防和治療,在有限的地域和時間內都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由此可見,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與病毒疫情斗爭的經驗是先進的,有些好的做法也是值得我們后人借鑒與推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