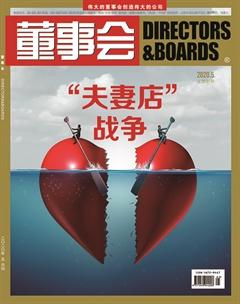上市公司面臨內控“控不住”風險
衛文省
近日,從媒體得知,中信銀行某分支機構因為未經客戶同意私自將客戶的銀行流水明細提供給第三方而被銀保監會立案調查。中信銀行作為上市公司,這樣的問題也暴露出其內部控制存在著相當大的漏洞。目前,中信銀行是否還存在其他的內部控制問題不得而知,該事件給作為上市公司的中信銀行未來帶來的影響也很難予以評估。作為上市公司,欲獲得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或者是要使本公司的基業長盛不衰,加強內部控制管理正當時。
首先,要從觀念上引起相關各方的重視。俗話說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大股東和政府主管部門不重視,上市公司就很難重視內部控制;沒有慘痛的教訓,上市公司的董監高們也不會重視內部控制;離開投資者的有效監督,上市公司同樣不會重視內部控制管理;沒有監管部門的監管高壓,上市公司更不會重視內部控制。作為曾經的上市公司監管者,筆者曾發現某上市公司董事長(兼任大股東集團公司董事長),為謀取私利,刻意繞過集團公司和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竟然命令管理公章的工作人員私自給替其他公司擔保的合同蓋上公章,該董事長潛逃國外若干年后,該筆違規擔保才被年審會計師發現,如果不是并購重組后的現任大股東幫助處理,該上市公司差點因此陷入退市邊緣。而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的總經理和董事長互相爭斗,總經理利用種種非法手段控制了公司的公章,把公司的資金好幾個億轉到海外,讓公司從盈利轉為巨額虧損,被迫被別的公司借殼;等等。這些“血淋淋”的慘痛教訓應該喚醒大家對上市公司開展內控工作的認識,而上市公司的內控工作也完全有必要實現從“要我抓”到“我要抓”的轉變。
其次,要建立對內控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制約機制。這是因為,我國上市公司治理還有很大的缺位,內部控制工作起步較晚,離開外部監督,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工作還很難做到自覺自省。這里,參加各方可以有地方政府、紀檢、司法、證券監管、新聞媒體、律師、投資者等,量化和透明上市公司執行內控制度的情況,獎優罰劣,不給“劣幣驅良幣”留下可操作的空間,不給不遵守和執行內控制度的上市公司相關人員留下可乘之機,不讓嚴格遵守和執行上市公司內控制度的老實人吃虧。這里,這個監督制約機制還應有一個牽頭負責人單位,筆者以為,對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內控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制約機制,應由地方政府、紀檢和司法機關為主,其他各方為輔;而對于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內控制度的執行情況的監督制約機制,則應由證券監管、新聞媒體、投資者為主,其他各方為輔,相互配合,共同達成。
再次,要建立和真正實施對上市公司內控制度執行情況的考核。對于內控制度不全、執行不力、管理混亂、效率低下、經營虧損、案件頻發、群體事件不斷的上市公司,要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的董監高和相關人員實行任期問責,在調查清楚的情況下,不僅要限制公司的再融資和并購重組工作,該免職的免職,該移交司法的移交司法,并附帶對董監高和相關人員的民事訴訟,維護國家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對于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的董監高和相關人員實行任期問責,在調查清楚的情況下,不僅要限制公司的再融資和并購重組工作,還要由證券監管部門對責任人實行問責,采取適當的市場禁入措施,并附帶對董監高和相關人員的民事訴訟,維護國家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和社會的穩定。
此外,要有效限制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的權力濫用,為上市公司消除內控控制不住的風險。十多年前,證監會在全國上市公司中開展的清理大股東及其關聯方占用上市公司資金專項活動,想來大家還是記憶猶新的。然而近幾年,甚至包括新上市的公司,上市公司內控失效的例子屢見不鮮,大股東和關聯方占用上市公司資金而被監管部處罰的事件時有發生。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濫用控制權掏空上市公司,損害投資者利益,擾亂證券市場正常秩序。而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的權力濫用,在現實生活中,上市公司是無能為力的,否則,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在對上市公司內控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制約機制中應該明確,凡違法違規,不按內控制度辦事,有損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利益,而上市公司高管及其相關人員又無能為力者,可以向牽頭負責監督的主要單位實名舉報,舉報查實的,舉報人可以不承擔相關責任。而對于明知違法違規,卻不舉報,甚至相互串通的,要予以嚴懲。
最后,上市公司的內控有效與否,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方勠力同心才可以達成。比如,上市公司的中層和一般員工也許不懂內控,內控制度執行中出現梗阻,也會功敗垂成;投資者維權意識不強,不知道對于上市公司內控失效可能對自己利益帶來損害進行維權,那么,內控制度執行也就缺乏了一方面的推動力;新聞媒體和律師等,如果不能主持公正,伸張正義,也會削弱上市公司內控制度的執行力;還有,就是各級上市公司協會如果能夠不斷加大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管理工作的培訓,也可以有效改善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工作的水準,避免上市公司因為內控失效給公司的發展帶來不必要的損失;當然,最重要的是,如果地方政府、紀檢、司法機關不積極發揮作用,僅靠證券監管部門和其他各方,對于上市公司、大股東、實際控制人違法違規,破壞和踐踏上市公司內控制度的行為的制約作用畢竟有限,甚至可以說相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