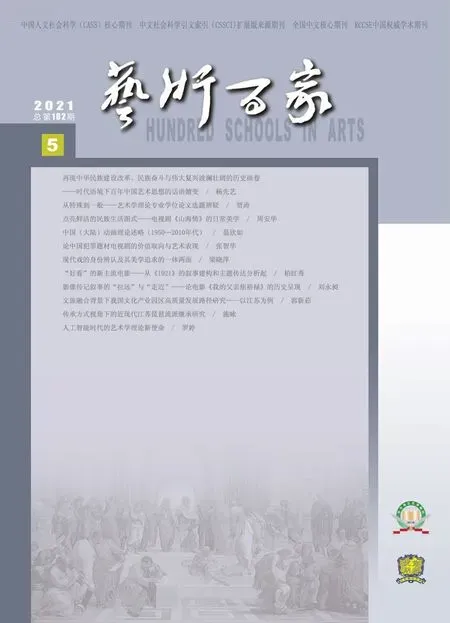論草書先于正書*
駱冬青
(南京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97)
草書先于正書,這一命題,可謂驚心動(dòng)魄,一字千金!它將藝術(shù)的自由創(chuàng)造置于一切既定秩序之前,將造字原則置于“正字”“正體”原則之前,既為漢字造字探本,又為書法藝術(shù)立法,更指向了美學(xué)的超越之境。這一命題,郭紹虞先生曾在1961年從書體、字體以及書法史角度提出:“我們既認(rèn)為草先于楷,那么也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行先于楷。”[1]1972年,晚年郭沫若從另一更為根本的角度,即造字角度,將此命題的意蘊(yùn)提到新的層面。應(yīng)當(dāng)指出,郭沫若似未曾注意到郭紹虞的論述。①這位曾經(jīng)狂飆突進(jìn)的創(chuàng)造社詩(shī)人,始終“心有天游”,即使晚年,猶在其意中生出漫天瘋長(zhǎng)的野草、春草——草書,正是那種自由的象征、創(chuàng)造的表現(xiàn)!
郭紹虞和郭沫若兩位先生的命題,其意蘊(yùn)如今需繼續(xù)深化。我以為,兩位先生所采取的文字學(xué)、書法學(xué)視角,仍然是最重要的。不過,考古學(xué)和古文字學(xué)的新發(fā)現(xiàn)、新成果,為重新論證這一命題提供了契機(jī)。更重要的是,哲學(xué)、美學(xué)上的新進(jìn)展,為我們思索這一命題貢獻(xiàn)了更多的向量。
郭沫若說:“在我看來,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劃符號(hào)應(yīng)該就是漢字的原始階段。創(chuàng)造它們的是勞動(dòng)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的。從這種觀點(diǎn)出發(fā),我認(rèn)為廣義的草書先于廣義的正書。南宋的張栻(號(hào)南軒,與朱熹同時(shí))曾經(jīng)說過:‘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以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jǐn),便成草書。’雖出以意必,是卓有見地的。”[2]又曰:“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隨意刻劃先于圖畫;從書法觀點(diǎn)來說,也就是草書先于正書。”[2]將刻劃符號(hào)的創(chuàng)造歸功于勞動(dòng)人民,姑且存疑;說刻劃符號(hào)的形式草率急就,我以為真乃意必之言。但是,其推論則允為超拔。從“指事先于象形”,竟遷想妙得,得出“草書先于正書”的結(jié)論,郭沫若畢竟是靈感激蕩的詩(shī)人!蓋從創(chuàng)造的根柢上看,造字與寫字(書法——?jiǎng)?chuàng)造性地寫字)來自一種沖動(dòng),即將內(nèi)心所具有的一切表達(dá)為符號(hào);創(chuàng)造的形式,則均為某種“造型”;而共同歸宿,則是超越感性的靈智的飛翔。
本文以“變形記”“解形記”“超形記”論之。
一、變形記
草書,郭沫若仍承傳統(tǒng)想法,以為“形式是草率急就的”。草率,與嚴(yán)謹(jǐn)相對(duì);急就,與即興相同。這一似乎最能代表漢語中那種龍飛鳳舞、大象無形、天馬行空精神的書體字體,卻沒有一個(gè)看起來具有學(xué)術(shù)嚴(yán)謹(jǐn)性的定義,使我們的論述失去了起碼的基點(diǎn)。尤其別扭的是,讓“草書先于正書”這一命題首先依賴于“正書”,方可定義“草書”,郭沫若引張栻所謂“寫得不謹(jǐn)”,其實(shí)反而挑明了自身論斷中的悖謬,因?yàn)椤爸?jǐn)”應(yīng)為原態(tài)、常態(tài)。所以,正書、草書的定義,均需首先審視。我以為,正書、草書概念,需要打破斷代概念,將其推至漢字書寫以及字體中的普遍性層面。行書介于正書、草書之間,可由此兩種定義規(guī)定。也就是說,將正書、草書規(guī)定為漢字書體、字體的普遍概念。郭紹虞認(rèn)為:“就漢字而論字體,有三種不同的含義:一指文字的形體;二指書寫的字體;三指書法家的字體。就文字的形體講,只須分為正草二體。就書寫的字體講,一般又分為正草隸篆四體,或真行草隸篆五體。就書法家的字體講,那是指各家書法的風(fēng)格,可以分得很多,最流行的如顏體、柳體、歐體、趙體之類便是。”[3]這里所說的正書、草書,既是指字的形體,又是書寫的字體,因此,從文字學(xué)角度看,可以作為漢字字體的普遍概念。至于書法家的“字體”,乃是書寫的個(gè)人特征,應(yīng)納入風(fēng)格范疇,當(dāng)從文字字體概念中區(qū)分出去。
在郭沫若論述的語境中,正書、草書,當(dāng)是指自有文字以來,任何時(shí)代通行的字體、書體與其變體。正書與楷書、真書、正楷等概念,乃后起,是始于漢末的漢字字體規(guī)范化、規(guī)正化的產(chǎn)物。研究字體常引用宋代《宣和書譜》“漢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書”之說,這里的楷書實(shí)際上是指王次仲所創(chuàng)的八分書,而不是現(xiàn)代所謂的楷書。郭紹虞先生曾作明確區(qū)分:“我們要從本質(zhì)來分別正體和草體,不要泥于舊時(shí)古籀篆隸分楷行草種種名稱。”“凡是對(duì)于字體有整理規(guī)定的作用的,如《史籀篇》《倉(cāng)頡篇》以及后世所謂《三倉(cāng)》或《石經(jīng)》等等,都可以看作是文字的正體。凡是為了書寫便利,或減省筆畫以趨約易,或隨筆轉(zhuǎn)折不求整齊,這些又都可看作是文字的草體。”[3]我以為,“正體”“正書”乃任何時(shí)代某一區(qū)域中規(guī)范化、規(guī)正化、模件化的字體,并不只是指后世的方正平直的可作楷模的楷書。而草書即“草創(chuàng)”之字體書體,《論語》有“裨諶草創(chuàng)之”語,張懷瓘《書斷》謂“因草創(chuàng)之意,謂之草書”,竊以為“草創(chuàng)”之意尤可深味:此“創(chuàng)”字有兩重含義,一是最初的草創(chuàng),是首先的創(chuàng)立;二是指后來的草書,乃是要從正書回歸到草創(chuàng)狀態(tài)。草書之“草”,常解作草率、草稿、潦草,均含一定貶義,但卻說出了它的某些特征;至于匆忙、急就、即興等表示快速之意的言辭,則描述了動(dòng)作,可是,這些卻也會(huì)遮蓋更為重要的性質(zhì)。草書,具有強(qiáng)烈的動(dòng)作性、變化性、易簡(jiǎn)性,即所謂“縱任奔逸”[4]64“示簡(jiǎn)易之旨”[5]2,因此,草書與心靈的激越狀態(tài)密切相關(guān)。藝術(shù)的草書,乃是當(dāng)文字書寫本身成為一種抒情,文字、圖象、動(dòng)作、筆墨等的遇合,構(gòu)成了一種奇跡般的姿態(tài)——書寫藝術(shù)、書寫痕跡與書寫動(dòng)作本身合一,成為一個(gè)美學(xué)事件。所以,草書的美學(xué),是靈感的形狀,是激情的成功革命,是圖象的飛翔意態(tài)。草書創(chuàng)造了新的存在符號(hào),以意向、意念、意想,創(chuàng)造出特殊的意象,抽象而姿態(tài)靈動(dòng),夭矯而不屈。最初的造字,正是來自“天雨粟,鬼夜哭”般的靈感,后世的草書創(chuàng)作,則需回歸漢字初創(chuàng)時(shí)那種“筆落驚風(fēng)雨,詩(shī)(書)成泣鬼神”的情境。以創(chuàng)造性書寫,留下的即時(shí)的動(dòng)作痕跡,將成為會(huì)意讀解和心靈溝通的符號(hào)。
最早的漢字難以尋覓。甲骨文告訴我們,什么是無羈創(chuàng)造,什么是立象盡意,什么是象外之象,什么是大象無形!人、日、月、山、水、牛、羊等,真的是所謂“象形”字嗎?沒有在先的“指事”,“象形”難以成立。“象形”即“變形”。郭沫若認(rèn)為,最初的文字,有指事與象形兩個(gè)系統(tǒng),造字則指事先于象形。我以為,只是有了指事的抽象,才使得“象形”成為造字原則有了可能。
以往許多人認(rèn)為,象形先于指事;文字是從圖畫變異而來。直到現(xiàn)在,仍有以為漢字乃象形字的意見。郭沫若重申許叔重的排列,并證之以原始刻畫的符號(hào)。我想,若象形在先,則許多民族均早已有圖畫,卻難以造出文字。其原因在于,圖畫只能非常有限地“畫”出一些具體事物,且“畫”的方式難以成為“寫”的方式。只有以抽象符號(hào)為代表的指事,方可創(chuàng)造以“寫”的方式來“畫”出事物,并且涵蓋萬有。所以,以抽象的指事符號(hào)來“象形”,才產(chǎn)生了象形“字”。單純的繪畫產(chǎn)生不了文字。西方拼音文字超越象形,只用字母表音,即證明“指事”的“象聲”性質(zhì)。超越象形,乃造字之必要環(huán)節(jié)。指事先于象形,即符號(hào)創(chuàng)造先于圖象系統(tǒng),乃文字產(chǎn)生的必然。明乎斯理,方可談文字。
由于指事先于象形,故“象形”已是“變形”,是“抽象”而“變形”。沈兼士謂漢字為“意符字”,以諸簡(jiǎn)單符號(hào)組合而成。他以象征主義(Symbolismus)概括指事字;以模型主義(Typismus)概括象形字,謂其“由記號(hào)的進(jìn)化而為象形的”;以因襲主義(Konventionalismus)指稱“借象字”——因襲實(shí)物的形狀,以代表作者的意思;個(gè)性主義(Individualismus),指稱“復(fù)象字”,或象形兼會(huì)意字,“漸漸脫離實(shí)物標(biāo)本的束縛,作者能自由拼合各象形體,以發(fā)揮其意思”;主觀主義(Subjectivismus)指稱會(huì)意字,所謂“能超乎跡象,主觀地把各個(gè)文字間的關(guān)系看做有機(jī)的,而化合之,以表現(xiàn)作者的意思”[6]4-5。沈兼士以德國(guó)歷史學(xué)家蘭普希特(Lamprecht)劃分的人類思想五時(shí)期,來框架漢字,頗有啟迪,卻也頗為機(jī)械。我以為,他以超越性的意符為文字的最高階段,固含卓識(shí),但其實(shí)卻應(yīng)顛倒——只有這種具有最高表意功能的符碼自由拼合,才是文字產(chǎn)生的因由。所以,指事之中,即含會(huì)意。自然,指事之中,即推至象形——“由記號(hào)的進(jìn)化而為象形的”。六書中所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象形”,乃是抽象出事物的某種特征,并且以抽象符號(hào)表現(xiàn)之。如“日”“月”“牛”“羊”諸字。并非“隨體詰詘”,也不可能做到“隨體詰詘”;所謂“畫成其物”之“畫”,只有成為文字筆畫,即抽象的符號(hào),才會(huì)成為構(gòu)字元素,而非任何別的繪畫形式。故六書“象形”實(shí)是以“指事”為前提。草書尚簡(jiǎn)的屬性,正與指事通。毋寧認(rèn)為,所謂“圖畫字”自非字,不過,只有出現(xiàn)“圖畫字”草書,才有了字,如“牛”字、“象”字。只有在刻畫和刻畫符號(hào)以及圖形意識(shí)中方才可能有“文字”。有圖畫無文字的民族多矣;有文字而非“圖象”文字者猶多。其實(shí),只是因?yàn)橛辛宋淖?才有所謂“圖畫字”,才有把圖畫“認(rèn)”作“字”的觀念。清代翁方綱有言:“空山獨(dú)立始大悟,世間無物非草書。”那是先有草書,才會(huì)悟到“無物非草書”。
在面對(duì)“天”和“神”的時(shí)候,漫天神靈飄舞,“無物非草書”才成為現(xiàn)實(shí)。甲骨文中,許多字,均有不同寫法,一個(gè)“人”字,就有48種字形[7]1-2,勾勒著側(cè)面“人”的形態(tài)——為什么我們可以認(rèn)出是同一“人”字?那是以草書的眼光,看殷商人的浪漫表達(dá)!那種來自生命、來自美學(xué)的不安分,讓甲骨文里的字常常變形、變幻、變換出不同的形式,其中,既有從生命本原出發(fā),勾勒人體、自然以及想象世界的不同形態(tài),又有從美學(xué)本原而生的“字”本身的不同形體。畫成其物,隨體詰詘,那個(gè)“畫”,在甲骨文特定書寫工具與書寫載體中,已經(jīng)演化為線條的“詰詘”蜿蜒,抽象造型意識(shí)隨著某種抽象線條而展現(xiàn),但是其中勃勃蛹動(dòng)的美學(xué)精神,卻變化出萬千形態(tài)。草書的意的極度擴(kuò)張,令一切抽象、變形。甲骨文中的自由表現(xiàn),無論“你”變出多少種形狀,我們還是一眼就能認(rèn)出你!“任憑你在千種形式里隱身,可是,最親愛的,我立即認(rèn)識(shí)你”,歌德著名情歌似乎最好地表現(xiàn)了甲骨文中那個(gè)自由的精靈:“我外在和內(nèi)在的感性所認(rèn)識(shí)的,你感化一切的,我認(rèn)識(shí)都由于你”!那個(gè)喜愛變形的精靈,卻總是以某種方式出人意料地打動(dòng)我們“外在和內(nèi)在的感性”,它就是漢字最初的美學(xué)。草書極度意化的拓?fù)渥冃?卻以情感力量,讓我們“認(rèn)”出“她”來!這就是精神的超越性。
即使是鐫刻固定的圖象,卻在有限中表達(dá)自由。在那個(gè)巫術(shù)時(shí)代,人內(nèi)心的神靈與天上的神靈在文字中相遇,迸發(fā)出的創(chuàng)造力只有少量留存,卻以偉大的符號(hào)固定為永恒。所以,我要說,甲骨文最具草書精神,不僅因其乃漢字草創(chuàng)未久的形態(tài),更因其夭矯多變的書寫。不過,這種存留下來的特殊書寫,恐怕仍然未能表現(xiàn)出彼時(shí)應(yīng)當(dāng)具有的別樣書寫。考古證明,甲骨文鐫刻前或已有毛筆書寫痕跡。如果暢想甲骨文時(shí)代的非甲骨文書寫,那肯定是一個(gè)何其爛漫自由的存在!在未定形與已定型之間,在未入框架與已入框架之間,正是一個(gè)草書的時(shí)代。
從西周金文到戰(zhàn)國(guó)文字,漢字經(jīng)歷的紛紜變幻,迄今猶未從“字理”上得到很好的闡釋。直到秦的規(guī)范統(tǒng)一,讓一切變得單調(diào)貧乏:即使創(chuàng)造,也只剩下一個(gè)同一的意志。篆,那個(gè)以弧形的圓滿形成的字,以彎曲消解了一切自由,卻固定了秩序。
二、解形記
解形,是對(duì)形成的固定乃至僵死秩序的解構(gòu),是對(duì)“同一”的反抗。指事先于象形,首先是對(duì)“象形”之“形”的解構(gòu)與解放。所謂圖畫文字,乃是既有文字之后,仍然有以圖像代文字者,如甲骨文已有“象”字,金文中仍有“象”字圖像,表明那種以圖像、圖形代文字,以表尊榮,顯示其藝術(shù)性,還是一種奇特的沖動(dòng)。這種沖動(dòng),在當(dāng)今電子媒介中,以“表情包”、火星文、圖片、視頻等形式與文字混排,作為某種語言形式存在。似乎具有文字功能,卻較之文字倒退回具體的感性表征,其中意味,尤當(dāng)深思。竊以為,漢字,乃是對(duì)這種本能的原始象形的反抗,卻又在很深層面依賴于這種本能。這種反抗,乃是草書。一方面,草書的易簡(jiǎn)思維,在《周易》中簡(jiǎn)化為陰陽兩爻,是最抽象的線。陰、陽兩爻抽象敘事在某種特殊層面代表了草書精神。草書對(duì)字形的簡(jiǎn)化,乃是重要特征。另一方面,草書書寫時(shí)的飛快速度必致痕跡的如線一般的特征。甲骨文在很大程度上面對(duì)的就是就兩個(gè)問題:圖像本能和書寫中“如線”本能。甲骨文特殊工具令后者成為常態(tài),而前者則是尤為本質(zhì)的改變——“字”解散了“形”。
字體改變的一個(gè)重要時(shí)刻,是所謂“隸變”。隸者,奴隸也。但是低賤往往帶來肆無忌憚,帶來弱者的特殊反抗。這種反抗,即書寫時(shí)的“草”,表現(xiàn)出一種率意和怠惰,但卻又包含著可能的創(chuàng)造。啟功先生曾從“寫字”角度指出:“古代有些字體風(fēng)格,從甲一大類型變到乙一大類型時(shí),也常是從一些細(xì)微的風(fēng)格變起的。例如篆和隸現(xiàn)在看來是兩種大類型,但在秦代,從篆初變隸時(shí)的形狀,只是藝術(shù)風(fēng)格比較潦草一些、方硬一些而已。這足見字體的演變常是由細(xì)微而至顯著的。”[8]1郭紹虞則更具學(xué)術(shù)史眼光:“籀文偏于繁體,是晚周文字的正體,而許書之古文,則是當(dāng)時(shí)的書寫體,可說是具有草體性質(zhì)的字體。因此,從籀到篆,是繁體的演變;而從古到隸,則是簡(jiǎn)體的演變。所以在當(dāng)時(shí),篆是正體,而隸則有草體的性質(zhì)。”[1]在論述草書的正體化時(shí),郭紹虞曰:“章草之正體化,發(fā)展為兩個(gè)不同的方向。一個(gè)變?yōu)闈h隸,即是有波勢(shì)之隸,已如上述。另一個(gè)方向變?yōu)榭瑫?使點(diǎn)畫俯仰之勢(shì)成為懸針垂露之形,于是又在字體上產(chǎn)生了一大變化。”[9]郭紹虞還總結(jié)說:“正體的性質(zhì)屬于靜,靜故不易變,也不要求變。草體的性質(zhì)屬于動(dòng),動(dòng)故容易變,而且也有變的要求。所以字體演變,不在正體而在草體,草體才是字體演變的關(guān)鍵。”[9]其中,最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隸書竟在一些方面向甲骨文回歸:“我們作戎字不從小篆作而同甲文作戎,塵字不從小篆作而與甲文作同意,也就可以證實(shí)這一點(diǎn)了。”[1]稍作推論,則可說,甲骨文盡管受到書寫工具限制,但仍然最為充分表現(xiàn)出草書的草創(chuàng)精神,那種蜿蜒曲折復(fù)雜多變的圖象,那種貫穿一氣的奔逸放達(dá),尤其是以指事的虛靈象征洋溢著的意向體驗(yàn),可以說,先驗(yàn)地、先在地規(guī)范了漢字的格局,卻又讓我們從三千年的暌違中認(rèn)出了那里隱藏著的精神世界。
劉熙載說“草書意多于法”,我認(rèn)為,這揭示出某種真相,草書之“意”正在于那種不羈的精神;可是,更深層次看,“法”自“意”立,那么,草書之法,來自于怎樣的“意”?若不是泛泛而論,需深入到草書創(chuàng)造的漢字圖象營(yíng)構(gòu)規(guī)律之中。通常,從易簡(jiǎn)、快捷這兩個(gè)角度勾勒草書特質(zhì),大體有道理;可是,相反命題也可成立,簡(jiǎn)化與繁化共生,“匆匆不暇草書”,“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乃書學(xué)中重要現(xiàn)象。草書,尤其是具有美學(xué)性質(zhì)的草書,恐當(dāng)從草書圖象的角度,從創(chuàng)造心態(tài)與創(chuàng)造過程等方面進(jìn)行探討。其中,關(guān)鍵在于草書建立的圖象,尤其是草書對(duì)漢字圖象的創(chuàng)造——“草創(chuàng)”。
漢字來自“象”,形成“象”,又創(chuàng)造“象”。許慎定義漢字之“文”為“象形”,“依類象形謂之文”;謂“象形”為“畫成其物,隨體詰詘”。那么,如何“依類”?如何“隨體詰詘”地“畫”成其“物”?也就是說,一旦“依類”,即需“指事”,將“物”抽象。而在“畫”的過程中,所依據(jù)的乃是內(nèi)心的圖象。草創(chuàng)之際,這一內(nèi)心圖象依據(jù)的乃是“意”——“音”與“心”構(gòu)成的“意”字,代表著的超越意味,自然超越了具體“物”象,而指向了物的“類”之“象”。西方畫家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等的非具象藝術(shù)、抽象藝術(shù),在很大程度上與漢字的創(chuàng)造相通,都指向“依類”而“象形”,這就解構(gòu)了原來的“物”形,而指向了“無形”。“形”即圖象。蓋“形”與“型”通,“型”為鑄冶以土范物,故意通于“圖”,彡者,毛飾畫文也,本指具體圖像,但漢字中強(qiáng)大的含意在抽象的“圖”的規(guī)引下,“像”遞進(jìn)為“象”,故“字形”乃字的圖象。[10]
草書草創(chuàng)圖象的創(chuàng)造性在于,它是沒有母本的摹仿。章黃學(xué)派有從初文求本義的傳統(tǒng),“初文”作為漢字圖象,可以追問其“初文”之“初文”嗎?竊以為,造字中,從“邏輯在先”來說,指事先于象形,即可推知,“相”先于“象”,“象”先于“像”。也就是作為范疇、概念的“相”(佛教謂為“名相”),是“象”的“先驗(yàn)”條件和先驗(yàn)感性結(jié)構(gòu)之本原。那么,何以有“相”或“名相”?太初無名,只有渾沌中的“草創(chuàng)”。此根本性的草書,乃創(chuàng)造世界符號(hào)之精神。從“無名”到“有名”,從“無字”到“有字”,世界這本大書上的“原字”,必自指事始,必自草書作。也就是以一種含有“幾何學(xué)”的激情和沖動(dòng),以拓?fù)渥冃蔚膱D象創(chuàng)造形成精神世界。它結(jié)構(gòu)了世界,解構(gòu)了原初世界。
所以,草書與指事的關(guān)系,是“心”凌駕于“形”。“心中有數(shù)”——“形數(shù)”成為心靈抽象而超越、靈動(dòng)而欲飛的媒介。時(shí)、空、數(shù),三者實(shí)統(tǒng)一于“數(shù)”。草書,恰在時(shí)、空上,構(gòu)造了飛動(dòng)著的審美世界,凝定、規(guī)整、規(guī)范為“正書”“楷書”。草書那種自由的表現(xiàn),是精神自由的綻放,是從“形而上”與“形而下”中,努力地從限制中顯示身手“形而放”的表現(xiàn),故能“龍飛鳳舞”,世間本無虛幻的龍鳳,卻在筆下變換莫測(cè),夭矯不群。
最初的草書,即甲骨文。那些甲骨文字中,許多表現(xiàn)“姿態(tài)”的字,或立或臥,或側(cè)或反,或長(zhǎng)發(fā)飄然,或大眼灼然……可是,它所屬的那個(gè)“本體”呢?不見!哪怕是眼、手、足等本身,也失去“本體”,唯余“姿態(tài)”乃至“神態(tài)”。這與漢字拓?fù)渥冃斡嘘P(guān),無論是拉伸旋轉(zhuǎn)還是收縮移位,其形變之規(guī)律,似難捉摸,卻自在心中;非無規(guī)律,實(shí)蘊(yùn)至理。蓋“形”之變,存乎心,存乎心中的拓?fù)洹皫缀巍币病N锵筠D(zhuǎn)化為心象(相、像、象),心象解構(gòu)著物象。草書中,因三維(時(shí)間之維)而解散二維圖象,因四維(空間三維加時(shí)間)而解散三維圖象。故后世草書欲回歸那種自由書寫,必先賦予圖型(式)以圖象(形象),而賦予“正書”“楷書”以三維乃至四維圖象。
在“正書”“楷書”中,“心象”“物象”更消失殆盡:固定的筆畫構(gòu)件,乃至?xí)鴮戫樞?讓漢字圖象拓?fù)渥冃蔚哪撤N單一形式成為典范。所謂筆畫,割裂了圖象;所謂筆順,很大程度上悖逆了書寫自由。甲骨文以刀筆為之,但仍然努力地創(chuàng)造出許多“一筆”畫出的圖象,更有曲折蜿蜒的彎線。這固然是后世草書未及見過的世界,但卻又是草書一直“夢(mèng)見”,并且表現(xiàn)出來的,加以毛筆“唯筆軟則奇怪生焉”的特質(zhì),故后世之“一筆書”乃是那種一意貫之、連綿婉延而又如音樂般既深入內(nèi)在感性,而又外在奇怪疊生,靈動(dòng)活躍的精神延續(xù)。草書的動(dòng)態(tài),乃是拓?fù)渥儞Q的圖象呈現(xiàn)。
三、超形記
漢譯西方概念中,“形式”一詞非常重要。康德美學(xué)即推崇純粹形式。“形”在漢語中,亦作動(dòng)詞用;草書也有動(dòng)詞義,草書之“形”乃是雙倍的“動(dòng)”。超“形”,乃指草書超越“變形”“解形”而指向某種更高的美學(xué)抽象之境。變形,是“指事”對(duì)那種“象形”本能的反叛,抽象的沖動(dòng)征服了低水平的感性復(fù)制,如原始符號(hào)刻劃對(duì)原始圖畫。解形,則是解散原型,解構(gòu)形狀,走向自由的姿態(tài),呈現(xiàn)自由的意態(tài)。正是在純粹形式中,草書體驗(yàn)到的積極自由,令其反觀形式自身,在形式本身尋求變化。并不自由的限定形式,卻在草書中“逼”出自由的創(chuàng)造,于是,超越某些字體的超形,在漢字歷史上,也從來不乏其例。草書的超形,最后往往被正書接納,成為形態(tài)意識(shí)的“意識(shí)形態(tài)”。這就是陸宗達(dá)所謂從筆意到筆勢(shì)。草書創(chuàng)造的“筆意”,最后必成正書、楷書的“筆勢(shì)”。陸宗達(dá)說:“什么是筆意呢?許慎認(rèn)為最古的漢字,它的字形結(jié)構(gòu),保存了造字的筆畫意義,叫‘筆意’。《說文解字·敘》說:‘(古文)厥意可得而說。’意即筆意。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xùn)》里提出,許慎分析文字是用筆意解釋字形的。他說,‘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diǎn)一畫有何意焉。’什么是‘筆勢(shì)’呢?漢字的形體是不斷變化的,筆畫日趣約易,加以書法取姿,致使原有的筆意漫漶不明,已不能分析它的點(diǎn)畫結(jié)構(gòu)有何意義了,這種字形叫‘筆勢(shì)’。”[11]70其實(shí),所謂筆勢(shì),乃是超越原來字形但似乎仍可“意會(huì)神契”的某種“個(gè)人知識(shí)”。不過,筆勢(shì)來自書寫的超越,來自草書,陸宗達(dá)卻未明言。
超越曾經(jīng)有過的形,創(chuàng)造自己的個(gè)人獨(dú)有的形,卻成為群體的“默會(huì)知識(shí)”,其中自有美學(xué)精神的重要作用。康德美學(xué)實(shí)通貫知識(shí)學(xué)與倫理學(xué),以及后世之闡釋學(xué)。草書“超形記”,乃鯤化為鵬的“怒而飛”。無窮之“意”如何向著高遠(yuǎn)處提升?“形”如何化為神韻(音樂化)?在“超形”階段,必將回歸草書的精神實(shí)質(zhì)。
其實(shí),草書拓?fù)渥冃蔚臉O致,冥冥中,一點(diǎn)一畫中的意義既未消失,反倒升華。拓?fù)滢D(zhuǎn)換中蘊(yùn)含著的自由的秩序,讓漢字圖象的意義更加自由地生成。草書中的簡(jiǎn)化、繁化,草書的速與遲,凝結(jié)為圖象后,卻在正書、楷書中獲得了安靜的位置。從筆勢(shì)反求筆意,是一種訓(xùn)詁的方法,竊以為,更當(dāng)是中國(guó)精神家園的回望、守望,也應(yīng)是從正書、楷書中,體會(huì)到沉默心音和勃勃心動(dòng)的必須。
日本假名中,以取于漢字草書的平假名居先,片假名居后。根據(jù)近年的考古文獻(xiàn),平假名和片假名其實(shí)都是唐代的音符,日本人以樂譜上的音符充作文字,來記錄他們的語言。古琴譜“減字譜”亦出于漢字,但似乎代表著不同思路。我以為,草書確似字母也。在飛揚(yáng)中凝定的抽象,乃音樂精神的象征。音樂乃時(shí)間藝術(shù),乃內(nèi)心的抽象感性。音樂中那種抽象的抒情,那種自由精神,似乎只有草書才可以表達(dá)——抽象的音與形相遇,似乎無意義的意義,在草書圖象中結(jié)合為一。
音樂(無形)的記譜符號(hào),聲音的抽象符號(hào),在平假名、片假名中表現(xiàn)出漢字的“形”“聲”合一特質(zhì),但此“形”非所謂“形聲”字之“形”,而是更為抽象、更為形式化的“形”本身。以此,才可使得符號(hào)直接表示聲音。草書似乎可以直接成為拼音文字,然而,事實(shí)并非如此。為什么?不可知。但以指事符號(hào)駕馭象形符號(hào),符號(hào)的抽象之美令其為虛數(shù)(復(fù)數(shù))符號(hào)。指事具有虛數(shù)意義,故可刻劃無形之“事”。漢字草書之“意”化,與指事先于象形,二者確有根本聯(lián)系。
數(shù)學(xué)中,數(shù)與形的糾纏,令其不斷升上新的靈境。虛數(shù)(想象的數(shù))令數(shù)學(xué)進(jìn)階,令象進(jìn)入數(shù),由此而飛翔。“萬物皆數(shù)”,數(shù)與樂一體。宇宙音樂奏響在草書中,令其超越于形。草書與音樂節(jié)律神秘地統(tǒng)一,草書作為凝固的音樂,必固定為正書,為中國(guó)精神的一種建筑!
《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書”具有的,是“在天成象”的天馬行空般的大精神,“天文”需要我們用心將其連接。“正書”則如“在地成形”,“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大地,仍然要用心靈來構(gòu)畫軌跡。天地之“象”之“形”,是否可作漢字世界隱喻?不妨以心解悟。
① 按:郭紹虞先生提供的漢字演變的許多論據(jù),較之郭沫若給出的全面且有力,顯示出醇厚大氣的學(xué)者風(fēng)度。我們說郭沫若可能未見郭紹虞之論,蓋郭紹虞所給出的一些有力論據(jù)以及論證,郭沫若若見到,必當(dāng)采納。后來,郭沫若之論為大家所知,郭紹虞論述反淹沒不彰,哀哉!但,郭沫若將此命題尤為鮮明地提到一個(gè)高度,可能是重要原因。漢字必須研究字形的幾何學(xué)問題,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拓?fù)渥冃巍4藶橹斐绮沤淌谑装l(fā)之辭。拓?fù)涫茄芯繋缀螆D形或空間在連續(xù)改變形狀后還能保持不變的一些性質(zhì)的一門學(xué)科,它只考慮物體間的位置關(guān)系而不考慮它們的形狀和大小。見駱冬青、朱崇才、董春曉《文藝美學(xué)的漢字學(xué)轉(zhuǎn)向》“前言”,商務(wù)印書館,2017年版,第3頁。
- 藝術(shù)百家的其它文章
- “力挽頹波”的華喦*
——評(píng)劉毅《華喦花鳥畫研究》 - 在道技并重中“繼絕學(xué),開太平”*
——評(píng)陳琦教授新著《中國(guó)水印木刻的觀念與技術(shù)》 - 中國(guó)文化背景下書法的歷史承載和審美價(jià)值*
——從葛承雍《書法與文化十講》論書法與人文、人性的關(guān)聯(lián)性 - 關(guān)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與利用的辯證思考*
-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非遺主題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開發(fā)策略研究*
——以無錫靈山小鎮(zhèn)·拈花灣為例 - 數(shù)字化時(shí)代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