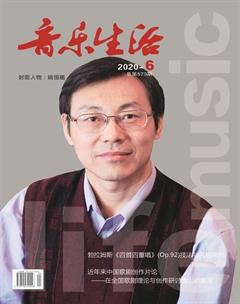我所經歷的青少年時期的音樂教育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音樂家庭,在那個以音樂為專業還不多見的年代,父母于1949那年的夏天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音樂系——當時北京唯一的一所音樂高校。伴隨著父母音樂教學中的鋼琴演奏、聲樂演唱的音響成長起來,在“耳熏目染”中感受,我最初對音樂的感情就是在這種自然的生活狀態中獲得的“生態贈品”。
在我出生時的五十年代初,全國經濟都不富裕。媽媽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任音樂教師、爸爸在匯文中學(26中)任音樂教師,兩校均為北京市重點中學,前者為公立、后者為教會學校轉為公立。他們用兩袋面粉、一把舊小提琴換回一架英國產的莫特利牌(MOTERLY)鋼琴,我學琴就是用的它,這架鋼琴一直用到20世紀90年代,其音響帶有“近彈聽音色柔和,遠處卻異常清晰”的特點。

1949 年在北京師范大學音樂系學習期間,父親指揮平漢鐵路局合唱團、母親擔任領唱的演出照。第一排左2 帶眼鏡者是我母親李晉瑗、右1 執指揮棒者為父親姚思源
我對于音樂最初的種種記憶像是一幕幕朦朧的畫面,雖已久遠,但很深刻。3、4歲的我在匯文中學教師宿舍家外的窗前,手里握著一只蝸牛,嘴里唱著:“水牛兒,水牛兒,先出犄角后出頭……”房間里父母在教鋼琴或教聲樂,音樂聲持續不斷……。那時媽媽還外出教鋼琴,記得她有一次帶我到家住東單的李立三家里,教他女兒鋼琴,我則坐在琴室外,吃著他們家人給我的糖果,聽著琴聲。
那時,父親指揮北京市匯文慕貞合唱團(匯慕合唱團),到勞動人民文化館指揮工人樂隊,我都“隨同前往、洗耳聆聽”。 4歲的某一天,我們去聽蘇聯專家杜馬舍夫的合唱排練,在排練廳門口,父親與杜馬舍夫交談時,他看到我,取出一塊糖,塞進我的嘴里!
5歲時,我和奶奶專程去中山公園音樂堂,去聽媽媽獨唱、爸爸鋼琴伴奏的一場音樂會,當時的興奮不可言狀。可是散場后,我們站在昏暗、風聲呼嘯的天安門廣場,卻找不到回家的車,奶奶摟著我用山西話說:“惜乎的俺孩”(可憐的孩子)。在7歲時,我們全家到天橋劇場觀看了蘇聯國家芭蕾舞團演出的《天鵝湖》。第一次聽到激動人心的音樂伴隨著樂隊現場演奏與臺上芭蕾舞景觀的一次大融合,在那音樂生活并不豐富的年代,這些記憶和經歷可謂彌足珍貴了。
1956年全國院系調整,我父母都調到大學工作,母親李晉瑗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講授學前音樂教育,她退休后從90年代開始,擔任北京市幼兒音樂教育研究會會長。父親姚思源在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負責全市音樂教師的培訓工作。當時北京還沒有音樂學院,初建的中央音樂學院還在天津。1954年父親參與了籌建北京師范學院音樂系的工作,而真正建院則是十年后的事了。1974年父親調回北京師范學院音樂系(現首都師大音樂學院)任教學副主任。1980年任北京市音協副主席。
我的幼兒園大班是在“二附幼”(北京市幼兒師范學校第二附屬幼兒園)度過的。幼兒園在班主任曹妙閣老師的帶領下,接觸到很多音樂游戲,小朋友們圍成一圈唱著《找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位好朋友,敬個禮,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還經常踏著《加洛普舞曲》音樂的節奏練習行進,增添了充實的“樂感和愜意”。不久前我與當時“二附幼”的竇文光老師說起那時的一些趣聞,還津津樂道、回味不覺。
1960年的春天,我進入了小學二年級下半學期,父母決定讓我學鋼琴。某個星期天我隨父親來到鮑家街的中央音樂學院二號樓,開始在一位姓黃的女老師家中學鋼琴,每周來一次。一年后,我參加了在中央音樂學院一號樓一層教室舉辦的附小招生考試,在根本不懂什么是樂理、視唱練耳的情況下,居然也能聽出、模唱各種音程、三和弦、七和弦,并且演奏了一首已經學過的曲子,在前來參加考試的一百多名孩子中,招生10名,我被錄取了。
現在看來那時的學費可真“便宜”,全學期僅付人民幣4元。但我想,對于絕大多數家庭來說,那也是一筆不小的“額外開支”。4元錢也可能是一個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呢。通知書是由蠟版打字印制的,紙很薄,看看那信封的粗制帶毛刺的草紙、再看看通知書、收費收據薄薄的透明紙,就知道當時全國正在處于“三年災害困難”時期。印刷的收據還是五十年代的,手寫將“195 -”改為 “61”。

1958年8月“二附幼”畢業照,前方第二排左二為姚恒璐,后排右4為竇文光老師、右5為曹妙閣老師。
我的主科老師先是蘇紹卿老師,后來在第二學期換成陳惠甦老師(小提琴隋克強先生的夫人,二位老師現在都已離世)。我記得那時是每周四下午去附中學鋼琴課、每周日來本院一號樓學習樂理、視唱練耳。
這種走讀式的學習方式大約是那時附小的主流辦學方式,那時只有附中學生才有住校生。我家住在西城區豐盛胡同,每次來上課,坐公交需要坐4站地,再在胡同里由東向西步行約一站地。當時中央音樂學院的地址為鮑家街21號(現在為43號),沿著高高的老圍墻走到學院唯一的正門(東門)口,拿出上課證,跟傳達室工友說一聲:“我上課來了”。
我們的鋼琴課先是在鮑家街本院一號樓上,第二個星期改到新華社后面的音樂學院附中教室內上課,那里面也有中學的住校生。直到90年代后期,附中才由現在的七號樓的位置搬到方莊芳群園的新建校舍。
那時的視唱練耳課除了被動聽音、視唱外,還有摹寫曲譜的練習,對于手寫五線譜,這種練習是很有成效的。
當時除了學鋼琴,我還考入了位于景山公園內的北京市少年宮友誼合唱團。考試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在景山大殿前報考合唱隊的孩子們轉著圈排隊,等候考試,每個人接受的都是唱歌(音準音色)、聽音(內心感覺)的考核。10歲的我進入的是合唱團的初級班,每個周末去景山公園內活動排練一次,但四聲部合唱的訓練是那么扎實地整合了自己的多聲部感覺和內心聽覺。
由鐘維國老師指揮的合唱團,在當時演唱的曲目有《國際歌》《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雪花飛》《7.26頌歌》等,我到現在都能夠記憶起每首歌四個聲部的不同旋律。這些合唱的實踐對于培養和聲多聲部的聲部感覺甚有益處,為我日后音樂創作多聲部的音樂實踐,提供了可靠的感性積累。我們友誼合唱團的高級班是由高中生為主建立的,他們參加的社會活動特別多,而我們小學的初級班,社會活動并不多,記得只有幾次到電視臺為舞蹈伴唱、到錄音棚錄音。但無論怎么說,這些藝術實踐活動也為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回憶的還有我們豐盛胡同小學的音樂生活。北京市特級音樂教師李存當時還是青年音樂教師,他同時也在北京教師進修學院隨我父親進修音樂理論課程,把小學的音樂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首先,他組織我們五年級(當時一屆只有我們一個班級、四十幾個同學),這個班我和另外三個男生組織起來排練各種重唱歌曲,從獨唱、二重唱到四重唱排練,演唱的曲目有《延安頌》《再過十年》《游擊隊歌》《黑孩子》等,這對于普通小學的學生、教師而言,在專業上都是極大的挑戰。我們的四重唱組織得非常卓越,至今都能回憶起當時演唱時的快樂、興奮與激情。后來李老師甚至想到請我父親作曲,排練演出了一場兒童歌劇,在北京市西城區文化館組織全校、外校學生前來觀看,我們穿著小動物的劇裝,唱著唱段,那場景的確令人難忘。

中央音樂學院附小上課入門證

1968年秋天練鋼琴、手風琴時的留影,時年17歲
我覺得,那時的學習環境和治學方式就是我們現在反復倡導的所謂“素質教育”。我總結為:熱愛、獨立思考與創造力三大因素。在“熱愛”教育的寬松環境中,學習與愛好結合,沒有強迫、沒有與利益相關的雜念,學習音樂當然就要“愛樂”。沒有人與人之間爭奪“起跑線”的那種與利益相關、與生存相連的競爭,不給孩子太大的壓力,完全是在自愿、愛好的生態環境中學習,等到孩子長大后其“生活方式”與“性格塑造”自然會賦予他選擇、思考的能力,而不是萬眾走一個“獨木橋”,在模式化、概念化教育方式中,培養為“成功的模仿者”或熟練工種式的 “匠人”。失去了獨立判斷的思考能力、缺乏“熱愛”的情感支撐,就不會造就創造的愿望和創造力思維,一切教學空有“分數”的外觀,留下的頂多是干巴巴的概念框架。
在豐盛胡同小學的班級內,我還擔任著文體委員,組織文體活動。學校的文化課作業在放學后的一小時內準能完成,之后就可以做自己感興趣的活動了。現在想來,可能是那時國家的教育還遠未進行“深入改革”,許多教育教學的方式都是建立在以往成功案例的實踐基礎上和時間的積淀上,因而反倒是符合自然形成的教學規律。
在我們豐盛胡同小學,四十人左右的一個班里,經過班主任沈乃斌老師的教學,考上市里重點中學四中1人、八中2人、六中和三中各1人,這在一個普通的胡同小學絕對是驕人的成績。之所以我一直反感應試教育,是因為它以固定的單一模式,來代替豐富的知識體系(以偏概全),以分數論英雄,而不是以獨立見解為光榮;但另一方面我卻也從來不畏懼應試,那是因為我的記憶力好,對于記憶性的知識,比如算數、珠算、政治這樣固定概念的課程,只要花兩天時間都能背下來去應付考試,考出好成績,可自己心里也明白,這,不值得自豪。 就是“小升初”考上重點中學北京八中,我也是以語文100分、算數98.5分的成績考上的。北京豐盛胡同小學的“素質教育”卻使我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凡事自己思考,學會了怎樣通曉新知識的各種方法,會有不止一條可選的解決方案,以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為標準,而背誦僅僅是輔助的學習手段。
在北京八中的初一、初二這兩年,我參加了學校的鼓號隊,吹號,初一時肺活量不大,學校要求能連續把隊號吹7遍者,才有資格參加國慶鼓號隊。初一那年沒有達標,沒去成,但參加了彩旗隊。初二國慶節前過關了,參加了1965年的國慶游行,衣褲、襪子、手套,一身白色服裝,號的下端配上紅色隊旗,對少年的心理而言真是“帥呆了”。除了國慶游行,我們鼓號隊還常常參加在首都機場舉辦的迎賓儀式,諸如迎接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等。這些少年時期的音樂生活經歷積累了大量的感性體驗,也鑄就了自己對音樂的熱愛。
我先后去山西插隊5年、山西大學藝術系學習作曲3年以及大學畢業后到山西雁北地區文化局工作了3年,總共在山西11年的經歷當中,父母是我繼續學習進取和精神上支柱。
父愛如山——我的作曲導師
我于1968年底到山西渾源縣插隊,大約三年后的1971年,我開始了音樂理論的學習。冬天農閑回家過年期間,父親開始教我一些作曲的科目。先是寫作旋律,以歌曲創作為主,寫好后父親修改。在學習旋律寫作時自然會說到調式調性、旋律形態等樂理問題。父親為我找到合適的歌詞,母親幫我抄寫,因我小時學過鋼琴、手風琴、基本樂理,對于音樂也有著濃厚的興趣,自然多少就有些長進。
1972年,我在農村飲食不當、營養不良,患上了十二指腸球部潰瘍、胃部粘膜脫落的病,在京治療期間,我們定了學習計劃,開始正式按部就班地學習和聲、復調等音樂理論課程。10個月以后,和聲學了兩遍、習題做了幾本。旋律寫作、復調也做了相關的練習。每天父母親前一天晚上留下作業,第二天他們上班后我就寫作和聲習題、寫好之后自己再彈奏 ,先自我修改一遍、記住和聲音響,然后拿給父親修改。
為了監督學習進度,保證學習內容的全面準確,父親還事先寫了學習規劃,對于歌曲寫作的內容進行了規范。
我最早寫歌是在北京八中上初二的時候,寫過一首歌曲,但不記得什么內容了,還被音樂老師發現,加以贊許,隨后就被張貼到學校的文化宣傳欄里,展覽了許久。從1971年開始的歌曲寫作,此后就一直堅持寫了下去,其中在專業上得到的是音樂陳述習慣的積累、詞曲結合的磨合、樂句樂段概念的鞏固,民族調式旋律的熟悉。
當時我還寫作了一批獨唱、合唱歌曲,盡管那時的歌詞都是“革命題材”,但也不妨礙我對旋律寫作的認識。為了學習如何寫出好的旋律,父親帶我數次拜訪過北京軍區文工團的作曲家唐珂、音協主席作曲家李煥之,請他們幫我指正作品。
在七十年代的十年中,寫歌的實踐始終都沒有間斷過,下面的目錄是從大量寫作中選擇出來,用一個筆記本自己手抄作為留底用的。以今天年輕人的眼光,這些或許根本沒有保留價值,題材局限、簡譜記譜、歌詞也缺乏詩意。但作為歷史,我們還是要正視,從中也可以看出那時的社會導向、藝術視野到底是什么樣子。
在學習了和聲之后,我又堅持每作一首旋律必定配上鋼琴伴奏的習慣,即使在那時單旋律流行的年代,我卻始終認為,沒有配以鋼琴伴奏的“作品”就是不完整的習作,因此每首自己覺得值得保留的歌曲都有鋼琴伴奏。

當時通過學習,我獲得的一個重要認識就是,要及時地把學到的音樂理論變成創作的初愿。比如,寫作歌曲的鋼琴伴奏,就是用以鞏固學到的和聲成果的極佳途徑。和聲等理論是“手段”,創作才是“目的”。 加上鋼琴和手風琴貝斯的和聲記憶,以后大量參與鋼琴、手風琴的即興伴奏的彈奏實踐,形成了對于音樂織體的綜合認識,也試圖嘗試不同的音型和豐富的節奏。這些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對于和聲的理解迅速提升。從那時起,腦子里就儲存了“鍵盤和聲”,手感與音感的同時訓練,尤其是對功能和聲的音響記憶,轉調與調性布局的意識,都是隨著和聲學習的進度而不斷積累、加深理解的過程(現在我把它叫做“內心聽覺的音響想象能力”)。我理解,對于多聲部的學習,如果沒有內心聽覺,等于紙上談兵。
對于我的和聲學習進度和內容的把控,父親同樣寫出了一個教學大綱,從這個大綱也可以看出,我們將和聲學習的重點放在了后半部分的“變音體系”方面,并且特別強調出以下幾點: 1.和聲半音化色彩的應用;2.旋律線的裝飾,和弦外音的及時補足;3.西方作曲家典型音樂作品譜例的視奏與音響記憶;4.西方和聲與中國民族調式的有機結合。
1973年我有幸從農村插隊的知青點上了山西大學藝術系作曲專業,在學校缺少教師的情況下,還能為下兩屆同學擔任和聲教學,就是與插隊期間這樣難得的學習機會所獲得的音樂本體理論技能分不開的。

父親為我學和聲制訂的教學規劃

2009年與我的學生們參加第一屆中國音樂分析學會
在鋼琴演奏的基礎上,我自學手風琴,每天在家不斷練習,還多次拜訪過空軍政治部文工團手風琴家任士榮老師。后來,陳志老師也多次來到我家指導我手風琴(他年輕時曾隨父親學習理論,后來在中央院教授吉他)。帶來他教過的不同的學生,演示給我觀摩、學習。那時我所能夠演奏的曲目十分有限,也就是當時流行的那幾首:《牧民新歌》《小蘋果》《單簧管波爾卡》《打虎上山》,等等。
1972年我治病結束,回到下鄉的村里,這種短期學習,就變成了“函授”。做好了題隨家信寄出,不久就會收到父親修改后的回信。因此更加激發了我的學習動力和熱情。
在山西大學藝術系的一些學習經歷?
1973年秋,我進入山西大學藝術系學習。學作曲與學繪畫一樣,除了技法的訓練,還要多聽、多見識各種音樂作品,才能開闊眼界、打開創作思路。為此我特意從北京拷貝了6盤大開盤錄音帶,錄制了柴可夫斯基、舒伯特、莫扎特、貝多芬、肖邦等作曲家們的典型作品。這些作品曲目都是由我的父親姚思源與姨父沈湘商定,姨父親自為我錄制的。帶來系里之后,這些“寶貝”備受歡迎,不僅同學們常常“借閱”,就連很多老師也借去聆聽,那時我們系里的資料室也都沒有這些東西,深知資料對于學習音樂專業的重要性,我們有幸得以一遍一遍的聆聽名作、領會音樂作品展開的要義,真是與那個難能可貴的小環境分不開。“沈湘酷愛音樂是從聽唱片開始的,他聽的第一本唱片是《藍色的多瑙河》 ……沈湘收集唱片是為了學習和研究音樂。他的許多唱片都經過他反復地聽,反復地研究……” [1]對此我也深有體會。 6盤錄音帶所容納的大約6小時的音樂,被我反反復復聽啊,聽啊,我甚至能夠做到當夜深人靜、躺在床上之時,自己“背聽”完整的交響曲之后再去入睡。這樣訓練自己去認識“音樂展開的邏輯”,對于日后的音樂創作真是大有裨益。想到現在的年輕人想要得到什么資料,很輕易地就能得到,相比之下,我更感到應當學會利用資源、學會應對不同目的而應用資料,“擇取”比單純“擁有”更加重要。
盡管我小時學過鋼琴,但5年的插隊勞動早已把手磨練得足夠僵硬。回憶起那時學琴練琴,力度不成問題,柔度、連音則差得遠;節奏不成問題,但速度、靈活度大有問題,每天練琴花去很多時間。 因為要排練鋼琴協奏曲《黃河》,我們系的樂隊還請來中央樂團的韓中杰老師客串指導、指揮。作為學生的代表,我和其他兩位同學,在于立和李濱雯兩位老師的指導下,都在練習《黃河》協奏曲,李恒林演奏第一、二樂章,閻莉恩演奏第三樂章,我演奏第四樂章《保衛黃河》。那時候練琴真“玩命”,指甲蓋都練劈了,手上還沾滿了膠布。在兩位鋼琴老師的指導演示下,終于,我們在大同69軍的駐地,迎來了由我們三位同學分擔演奏的鋼琴協奏曲《黃河》的演出,由張永聲老師指揮音樂系樂隊協奏,演出的場面熱烈、最終的演奏還算完滿,激情的時刻至今回味起來還有一種亢奮的余感,那也算是人生中的一段頗有意義的經歷吧。
1974年,在我上大二時,時任系主任的王永清老師正式安排我,為我的下屆班級的同學們上和聲課,同時還教鋼琴和手風琴。我們班那年集體去大同69軍學軍一年,僅留下我一人任教。那時我深知機會的難得,每日埋頭于琴房,練琴、寫作,不亦樂乎…… 在講授和聲課的當時,我還摸索出一套快速入門法,合并和聲教學內容的同類項,半年講完規定課程,并要求以實踐為主,不能停留在純理論的層面上,同時還增添講授了如何配鋼琴伴奏的內容。
在系里任教的日子里,我還采用山西民歌素材創作了不少歌曲、合唱作品,為系里出版印制的聲樂教材、小提琴教材配置鋼琴伴奏;特別是為京劇《海港》的唱段編創了鋼琴弦樂五重奏《一輪紅日照胸間》;為晉劇的唱段編創了鋼琴伴唱《紅燈記》《讓革命的紅旗插遍四方》。

2013年10月姚恒璐與父母
至今我還保存著一本在1975年1月由山西大學藝術系油印的教材《小提琴曲集》(第二集),因為其中選編了兩首我寫的鋼琴伴奏:《瑤家歌唱毛主席》和《豐收忙》。1974年《豐收忙》這首曲目還在省級刊物上出版了,成為我最初寫作時發表的第一首器樂作品。
這些教材中的曲目同時也是我們在藝術實踐中經常演出的曲目。當時,我也是由嚴富保老師指導的小提琴合奏小組的一位固定伴奏者。
我覺得,所有這些上學期間的教學藝術實踐,都大大激發了自己不斷進取、鉆研專業、藝術實踐的熱情,也更加明確了學習之后的專業目標。1976年畢業后,我在雁北文化局做了三年群眾文化工作,編創、教學輔導、征集編輯音樂作品等工作,能夠有序進行,也是受益于這段“藝術實踐”所帶來的感性認識。
在山西大學三年的學習期間,這種“函授”依然在進行中,學習的內容已經轉換到了配器與器樂作品的寫作方面。舉一個例子,1975年我曾經根據王銘的歌曲《海霞主題歌》做過管弦樂配器練習。
1976年山大畢業,我被分配到山西大同市雁北地區文化局任音樂干事。在這期間,“函授”也沒有中斷。我還保留自己寫的一份配器方案設計說明,采用施光南的歌曲《趕起馬兒送公糧》,作樂隊配器的練習。

1977年我在雁北文化局工作,被派到渾源縣水磨町村“學大寨工作隊”工作期間,也在寫管弦樂作品的練習,當時我沒有地方寫作,就跑到原來被廢棄了的知青住宿點,找到一間土草房,把一個水缸倒置過來,在水缸底上再鋪上一個木板,坐在土炕頭上,在那上面寫總譜。記得當時,我給寫的曲子起了名字:《展宏圖》,頗有“勵志”的色彩。針對這首配器方案中的問題,當時我用鉛筆寫出鋼琴縮譜,標上設想的音色,父親則用紅筆寫出修改意見和創作建議。
后來回到文化局,有了安定的環境之后,為了鞏固配器學習成果,我繼續寫作了另外一首完整的管弦樂小品《雁北春早》。1978年我還寫過一首鋼琴獨奏曲《‘交城山主題變奏曲》,這些都可以算作我1979年底離開山西、回到北京工作,在藝術性音樂作品學習方面的一種成果總結,同時也算是結束了我青少年時期啟蒙音樂教育階段的標志。
沒有曲折、活躍的人生經歷,也不會產生多維、綜合的想法,音樂創作也會失去“原動力”;沒有愛樂情結,就不可能去主動“鑒賞”音樂作品、主動探尋創作的種種可能性; 沒有藝術實踐,理論難以升華,很多所謂的“音樂研究”工作就只能停留在推理的層面,去做種種 “隔靴搔癢式的臆想”。 在面對博大的音樂藝術,應試、強學的效益不會長久、很難寬泛。在經歷、體驗音樂生活的同時,也在不斷品味著音樂藝術帶來的種種審美魅力。“音樂生態”不可強行獲得,體驗之余還需善于思考和聯想,因為,這些才是引發音樂審美、音樂實踐的源頭。
“沒有了歌聲,孩子們就沒有了笑臉”是母親對幼兒音樂教育工作者中肯的囑托,也從另一方面說明音樂教育植根于生命之源、培養人材素質全面發展的重要性。“幼兒的歌唱只有做到觸及情感、‘有聲有情、聲情并茂地表現音樂,感受到歌唱的美,才能達到提高綜合素質能力的教育目的” 。[2]
“要想使音樂教育有效地為實現學生全面發展的目標服務,就必須了解并把握音樂作為一種藝術學科的特殊性和自身的規律。那就是,構成音樂作品的物質材料是經過提煉、加工的音響,要通過聽覺來接受;音樂是表現人們內心情緒體驗的。施行音樂教育,就應當駕馭這些規律,以發揮它的優勢,而不能違反它的規律,要求它做自己并不擅長的事情。一句話,音樂教育主要是作為一門實施美育的課程而存在于學校的” [3]。
總結個人這段音樂教育的啟蒙過程,比較現今音樂教育的實情,我深刻地感悟到:教育的結果是應該培養獨立思考的人,而不要做跟風、人云亦云的盲從者。音樂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獨立的藝術審美能力者,要知曉音樂的美感奧妙在何處——聽覺美的審視體現了音樂培養人“情商”的涵養;音樂表演是對音樂作品的二度創作,通過演奏演唱促成和激發了自己后來的作曲愿望。通過各種基本的藝術實踐和理論總結,逐步學會以新的不同視角詮釋音樂作品、進而善于發現學術空白點、即時提出自己的新觀點并解決新問題的能力——這是音樂賦予人邏輯支持的“智商”魅力。
被音樂所感染的激情、被音響所感動的瞬間,這些體驗過后,經過反復地思考、頓悟,那距離“心智帶給我們的音樂”還能有多遠呢?!
注釋:
[1]李晉瑋:《沈湘軼事二三則》,選自《沈湘紀念文集》李晉瑋、李晉瑗編,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年7月,第156頁。
[2]李晉瑗:《小朋友心中的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第1頁。
[3]姚思源 :《學校音樂教育應努力追求審美境界》),1991年。
姚恒璐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