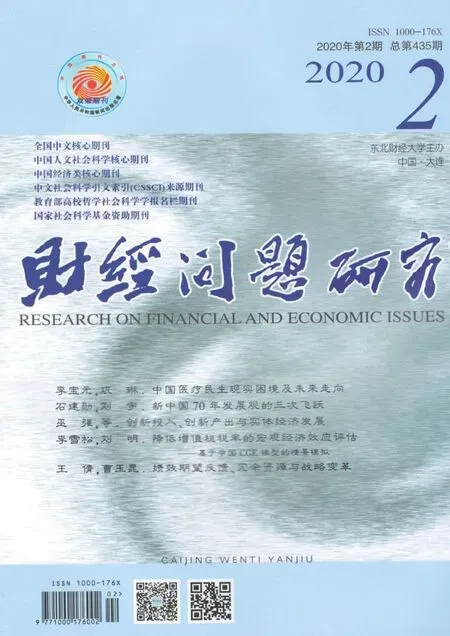不確定性、宏觀經濟波動與貨幣政策效果
熊海芳,劉天銘
(東北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一、問題的提出
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促進經濟增長等。Greenspan[1]指出,制定貨幣政策不僅應關注通脹缺口和產出缺口波動等經濟風險,還應關注沖擊發生的不確定性。已有研究表明,在部分投資不可逆時不確定性會導致企業投資下降,進而導致經濟出現衰退[2-3],因此,在貨幣政策維持物價水平、經濟增長的穩定時,需要考慮不確定性的影響。市場中的不確定性有多種,如宏觀經濟不確定性[4-5]、經濟政策不確定性[6]和金融市場不確定性[7-8]等。前兩種不確定性對應宏觀經濟波動,后一種不確定性對應金融市場波動,相關研究分別討論了不確定性與宏觀經濟、貨幣政策的關聯。在中國,一些研究主要討論宏觀不確定性與企業投資的關聯[9]-[11]、政策不確定性的作用[12-13],部分研究討論了不確定性與貨幣政策的關聯[14]-[17]。
關于不確定性對宏觀經濟的影響,Bloom[2]認為,大的不確定性沖擊會導致隨后的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無效。為了更精確量化不確定性,有學者分別構建了企業不確定性指數[4]、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指數[5]以及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6]。諸多研究證實了股票期權隱含波動率指數(VIX指數)、金融風險溢價等金融不確定性在宏觀經濟波動中的作用[8]。
關于不確定性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Bekaert等[7]采用SVAR模型證實VIX與貨幣政策態勢緊密相關,貨幣政策寬松會降低市場的不確定性及風險厭惡程度。Williams[18]研究了金融不確定性下的最優貨幣政策規則,發現金融危機時期的最優貨幣政策應該有所變化。Gnabo和Moccero[19]在考慮通脹預期風險和金融市場風險的基礎上采用區制轉移LSTAR模型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風險管理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存在高度經濟風險時貨幣政策應該比正常情況下更激進。Kilian和Manganelli[20]考察泰勒規則下利率變動與中央銀行雙目標風險之間的聯系,結果發現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是對中央銀行雙目標向上、向下風險的權衡,而不是簡單的標準泰勒規則反應。Mishkin[21]認為,標準的線性—二次框架解決不了金融市場崩潰的問題,應該采用風險管理的方法考慮金融市場中的尾部風險。因此,在貨幣政策風險管理中,中央銀行不僅面臨宏觀經濟不確定性,還要考慮金融市場波動等金融沖擊。Evans等[22]研究了存在零利率下限時不確定性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認為考慮不確定性和零利率下限時延遲加息是最優的,貨幣政策應對不確定性應該是一個長期的實踐過程。經驗研究也表明,金融市場中風險溢價是時變的,與市場不確定性、貨幣政策之間存在相互影響[23]。此外,金融危機對貨幣政策影響巨大,通常認為,金融危機時期的貨幣政策與經濟穩定時不一樣,因此,相關研究主要采用非線性方法。Martin和Milas[24]發現,2007年危機后英國的貨幣政策出現了結構變化,危機后更加關注金融穩定。Drakos和Kouretas[25]發現,危機前后歐元區的貨幣政策發生了結構變化,危機前遵循泰勒規則,危機后更關注產出而降低了對通脹的關注。在貨幣政策效果方面,Lo和Piger[26]發現,貨幣政策在衰退時比擴張時更有效。Gambacorta等[27]發現,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導致物價短暫的上升,對產出的影響與常規政策類似。
盡管關于不確定性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在諸多研究中得到了證實,但不確定性如何影響貨幣政策效果仍在討論之中。鑒于此,本文綜合考慮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基于月度和季度數據,討論貨幣政策決策是否考慮不確定性以及不確定性對貨幣政策效果的非線性影響。在中國政府和中央銀行都致力于防范金融風險背景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充分認識多種不確定性的特征,對于貨幣政策防風險決策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文的創新在于:一是將貨幣政策風險管理與多種不確定性相結合,用非線性時變參數的方法研究貨幣政策決策的偏好以及貨幣政策傳導效果;二是對比分析不同頻率以及貨幣政策的漸進性和突變性的差異;三是在不確定性衡量方面,不僅考慮政策不確定性,而且考慮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和信用利差;四是構造綜合的貨幣政策調整幅度、調整發生指數,采用排序Logit回歸討論貨幣政策調整對不確定性的反應。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一)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貨幣政策效果為被解釋變量,用調整幅度、調整發生以及短期利率來衡量。
1.調整幅度和調整發生
在2000—2005年間,中央銀行僅在2003年9月、2004年4月上調兩次存款準備金率,在2002年2月、2004年10月兩次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大量的貨幣政策操作主要在2006年以后。為了考察貨幣政策效果,本文綜合考慮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公開市場操作和2013年以來的借貸便利(SLF)、抵押補充貸款(PSL)、中期借貸便利(MLF)等措施,其中,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的具體操作日期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公開市場操作采用投放減回籠后的凈投放來衡量,常備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和中期借貸便利始于2013年和2014年,本文將這三者合并計算作為借貸便利,數據來自Wind資訊金融數據庫。對于貨幣政策操作來說,有宣告時間和執行時間,通常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宣告和執行都在同一個月內,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相差最多一天,因此,這里不考慮這種差異,僅根據宣告時間來判斷中央銀行決策的依據。
貨幣政策決策中,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幅度一般是百分數,而公開市場操作和借貸便利等操作是百億元級別以上。為了區分不同操作之間大小的差異,本文將每個貨幣政策操作調整幅度進行標準化,然后將其按月份、季度加總,這一方法記為調整幅度。在加總時,為了區分貨幣政策調整方向的差異和影響力的大小,在調整幅度中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根據標準化數值計算,而公開市場操作和常備借貸便利的調整則將標準化后的值取負號除以5再加總,這樣保證調整幅度的各組成部分在貨幣政策緊縮時都是變大、寬松時都是變小。為了作對比,本文還將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單獨分析,當向上發生調整時記為1、向下調整時記為-1,其他則為0,每個月計算它們的總和,這一方法記為調整發生。之所以沒有考慮公開市場操作的調整發生,是因為2004年后基本上每周中央銀行都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不適合用事件發生與否作為政策調整的信號。考慮到要分析貨幣政策決策對不確定性的反應,當使用月度的政策不確定性、市場不確定性和信用利差時,直接使用每個月的貨幣政策決策。調整幅度與調整發生的具體數值如圖1所示。

圖1 調整幅度(左軸)和調整發生(右軸)
從圖1可以看出,調整幅度和調整發生的調整方向基本是一致的,在2006—2007年貨幣政策主要是向上調整,即偏向于緊縮,2008年開始明顯出現寬松態勢,2011年趨于緊縮、2012年又是寬松,2014—2015年都是寬松態勢,表明調整幅度和調整發生兩者很好地區分了貨幣政策調整。
2.短期利率
對于短期利率,本文選擇常用的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7日利率來衡量,季度數據根據對應月度數據平均得到。
(二)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不確定性和宏觀經濟波動為解釋變量。
1.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主要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政策不確定性。參照王義中和宋敏[9]、金雪軍等[12]與蘇治等[17],本文使用Baker等[6]構建的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二是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參照Bloom[8]的做法,本文使用股指日收益、國債日收益、匯率等來計算,相關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在中國,考慮到債券市場有國債、企業債等,因此,本文還考慮了上證國債指數和上證企業債指數。根據股指日收益、國債日收益以及匯率計算月度的波動率,并將其標準化后進行加總得到市場不確定性。三是信用利差(SP2)。除了采用市場指數收益波動率外,金融市場中信用利差也是經常使用的指標[23]。本文計算兩年期AAA級中債企業債收益率與兩年期國債收益率的差,記為SP2,數據來自Wind資訊金融數據庫。
表1給出了各種不確定性和經濟景氣的相關性系數,其中經濟景氣是指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表1中,從經濟景氣看,政策不確定性、SP2具有明顯的逆周期性,市場不確定性具有順周期性。政策不確定性與市場不確定性和信用利差SP2是有一定的正相關性。月度數據中的相關性與季度數據中的相關性類似,只是相關程度有些下降。
2.宏觀經濟波動
本文選擇通貨膨脹、實際經濟增長等變量對宏觀經濟進行分析,所有宏觀數據都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對于通貨膨脹,本文采用月度同比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來衡量,季度數據用月度的定基數據平均得到。對于經濟增長,季度數據中使用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月度數據中使用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衡量。對于GDP,首先計算以1999年為基期的定基通貨膨脹,然后將其除以定基通貨膨脹進而得到實際經濟增長。對于宏觀經濟波動,本文選擇產出缺口和通脹缺口進行衡量,其中,季度和月度的產出缺口分別根據GDP、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的實際值進行季節性調整,然后根據HP濾波得到趨勢項進而根據實際值減去趨勢項得到,通脹缺口根據季調后通脹值減去HP濾波趨勢項得到。
在本文使用的數據中,信用利差始于2006年3月,貨幣政策操作主要也是始于2006年,因此,本文的樣本區間為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月度數據和季度數據。
三、貨幣政策工具對不確定性的反應
在貨幣政策實際操作中是否考慮了多種不確定性的影響呢?本文采用兩種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一是采用構造的調整幅度虛擬變量,將其對政策不確定性、市場不確定性和信用利差等進行回歸;二是采用構造的調整發生虛擬變量,運用排序Logit回歸模型判斷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整是否受到各種不確定性的影響。考慮到貨幣政策不僅對不確定性有反應而且對宏觀經濟波動有反應,因此,這里會控制產出缺口、通脹缺口兩個因素。
當進行線性回歸時,估計方程如下:
y1t=c+β1unindxt+β2infgapt+β3outgapt+εt
(1)
當進行排序Logit回歸時,估計方程為:
y2t=Logit(β0+β1unindxt+β2infgapt+β3outgapt)
(2)
其中,y表示貨幣政策調整,在式(1)、式(2)中,y1t、y2t分別為調整幅度、調整發生,unindx、infgap和outgap分別表示多種不確定性、通脹缺口和產出缺口,t表示時間,ε表示隨機誤差項。
(一)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在表2的單位根檢驗中,各變量至少在10%顯著性水平下平穩,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表2 變量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ADF(I,t,0)表示采用帶有截距項I、趨勢項t和都不帶的ADF單位根檢驗。***、**和*分別表示1%、5%和10%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括號中是P值。
(二)基于調整幅度的貨幣政策反應
首先,采用簡單的線性回歸分析貨幣政策調整對多種不確定性的反應,結果如表3所示。由于貨幣政策決策中可能存在前瞻反應和滯后反應,本文還選擇了前瞻1期和滯后1期進行比較。

表3 基于調整幅度的貨幣政策反應
注:括號內為t值,下同。
從表3可以看出,在同期數據中,政策不確定性和SP2兩個變量的系數都顯著為負,季度數據中分別為-0.016、-2.800,月度數據中分別為-0.003、-0.695,表明在這兩種不確定性增加時,貨幣政策是更加寬松的,這與危機時期不確定性較大需要貨幣政策寬松來應對是一致的。在季度數據中,政策不確定性的系數一直顯著為負,SP2的系數只是在前瞻1期中不顯著。在月度數據中,無論是同期數據還是前瞻1期、滯后1期的非同期數據,政策不確定性和SP2的系數一直顯著為負。這說明兩個指數具有明顯的逆周期特征進而使得貨幣政策對其有反應,也說明貨幣政策會根據同期以及歷史的數據作出調整,但對未來的數據僅限于月度的短期反應,更長期限的前瞻反應相對較弱。在季度數據中,對于市場不確定性,在滯后1期顯著正向反應,其他都不顯著,這表明貨幣政策較少關注金融市場的波動,僅在事后進行了較慢的反應。對于通脹缺口,無論是月度數據還是季度數據,在前瞻1期時貨幣政策有顯著的反應,系數都顯著為正,表明貨幣政策的調整充分考慮了未來的通脹情況,在通脹壓力較大時會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對于產出缺口,在月度數據和滯后1期的季度數據中,貨幣政策有顯著正的反應,表明貨幣政策僅對當前兩個月以及歷史的經濟增長作出了積極反應,當產出缺口較大時會采取緊縮貨幣政策,說明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前瞻性反應不強。
(三)基于調整發生的貨幣政策反應
為了充分考察貨幣政策對不確定性的反應,參照Carlson等[28],采用離散變量衡量貨幣政策調整,進而討論貨幣政策發生調整是否與不確定性有關。由于離散變量把每次發生調整看做一次事件,沒有時間刻度,因此,沒有考察前瞻或者滯后的反應。考慮到中國貨幣政策既有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又有準備金率的調整,一個月調整2—3次,一個季度發生調整的次數多達5—7次,因此,僅考慮是否有調整。為了區分貨幣政策調整的方向,把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記為上調,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記為下調,沒有發生調整記為不調整,即調整發生是取值上調、沒有調整、下調的離散變量,采用式(2)進行分析,得到的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基于調整發生的貨幣政策反應
從表4可以看出,無論是季度數據還是月度數據,政策不確定性和SP2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政策不確定性或SP2較大時,貨幣政策趨向寬松,而市場不確定性的系數都不顯著,與表3結論一致,表明貨幣政策調整對政策不確定性和SP2有積極的反應,但對金融市場波動關注較少。
四、不確定性與貨幣政策效果
(一)不確定性與貨幣政策效果:基于STAR模型的漸進性分析
參考Gnabo和Moccero[19]的做法,貨幣政策設定為帶有1階利率平滑的泰勒規則,如式(3)所示。在此基礎上,建立STAR模型,其中,政策不確定性、SP2等不確定性僅作為外生的轉換變量,如式(4)和式(5)所示:
rt=ρrt-1+(1-ρ)(α+β1infgapt+β2outgapt)+εt
(3)
rt=φ0zt+φ1ztG(γ,c,st)+μt
(4)
G(γ,c,st)={1+exp[-γ(st-c)]}-1
(5)
其中,r表示短期利率,ρ表示利率平滑系數,z=[1,rt-1,infgapt,outgapt]′,φ0表示線性部分的系數,φ1表示非線性部分的系數,G(γ,c,st)是以S為轉換變量、以c為門限、以γ為轉換斜率的轉換函數,式(5)為邏輯轉換函數的具體形式。對式(3)進行LSTAR檢驗,結果表明,式(3)存在明顯的非線性,轉換函數符合式(5)中的邏輯函數形式。
基于式(4)、式(5)的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其中,線性部分表示不確定較小時的政策反應。

表5 非線性貨幣政策規則
注:L.表示變量的滯后1期,下同。
從表5可以看出,在月度數據中,政策不確定性、SP2的線性部分中通脹缺口、產出缺口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當政策不確定性較小時貨幣政策主要積極應對通脹和產出波動,但產出缺口的系數更大,表明貨幣政策短期更關注產出波動的影響。非線性部分中產出缺口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當政策不確定性、SP2較大時貨幣政策主要積極應對經濟增長,下調利率刺激經濟,即貨幣政策穩增長的做法更明顯。在季度數據中,通脹缺口的系數不顯著,政策不確定性下線性部分利率對產出缺口有顯著正向反應,非線性部分有顯著負向反應,說明貨幣政策在不確定性較小的時期抑制經濟過快增長,在不確定性較大時期會寬松進而刺激經濟增長,進一步體現貨幣政策穩增長的意圖。考慮SP2時通脹缺口和產出缺口的系數盡管有變化但不顯著,表明在季度數據中,中央銀行較少考慮SP2的大小變化。
(二)不確定性與貨幣政策效果:基于TVAR模型的突變分析
在貨幣政策應對外生的不確定性時,其反應可能不是漸進的而是突變的,鑒于此,進一步考慮基于門限的TVAR模型考察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這里將不確定性作為門限轉換變量。多元門限向量自回歸模型的設定如下:
Xt=α0+c0(L)Xt-1+[α1+c1(L)Xt-1]I(Rt>r)+εt
(6)
其中,Xt表示各內生變量的向量,包括通脹缺口、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等變量。α0和α1表示常數。c0(L)和c1(L)表示滯后算子。Rt表示門限變量,r表示門限變量的門限值。對于門限值的選擇,本文根據使得誤差最小的搜索法來決定。I(·)是一個指示函數,當Rt>r時函數取值為1,其他則為0。εt表示隨機誤差項。通常不確定性被劃分為大不確定性和小不確定性,因此,這里采用1個門限進行分析,具體的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貨幣政策效果:基于TVAR模型
注:由于空間有限沒有報告常數項系數,括號中是標準誤。
在表6中,從非線性貨幣政策傳導的系數看,考慮月度數據時,在兩個不確定性相對較小的區制1時,短期利率對滯后的通脹缺口和產出缺口都有顯著正向反應,在不確定性較大的區制2時,這兩個系數都不顯著,而此時短期利率的一階滯后項不僅非常顯著而且比不確定較小的區制1時大很多,這說明貨幣政策在不確定性較小的正常時期主要維持通脹和經濟增長的穩定,而在不確定性較大的非正常時期并沒有對經濟有明顯反應,更多注重貨幣政策的慣性,即利率平滑,這與理論上危機時期保持政策穩定、合理引導市場預期是一致的。
根據門限值得到月度數據轉換變量的劃分區間如圖2所示。從圖2可以看出,政策不確定性的門限值較低,而SP2的門限值則較好地區分了其較大的時期,可見SP2的不確定性衡量效果較好。考慮季度數據時,在不確定性較小的區制1中,政策不確定性和SP2下的貨幣政策反應有差異:從政策不確定性看貨幣政策關注了經濟增長,從SP2看則沒有反應。從圖3可以看出,政策不確定性和SP2的門限值劃分出來的時間區間在2008年、2012年比較接近,所以,在不確定性較大的區制2中,政策不確定性和SP2下貨幣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短期利率對滯后的產出缺口都有顯著正的反應,說明在不確定性較大時貨幣政策主要是穩定經濟增長。從圖3看,政策不確定性和SP2劃分的區制2的差異主要在2014年,在2014年中國經濟形勢相對穩定,但金融市場比較動蕩,SP2較多地反映了金融市場的風險,這表明SP2中的信息會更多。


圖2 月度數據門限轉換變量


圖3 季度數據門限轉換變量
五、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文在“穩增長、防風險”背景下綜合考慮多種不確定性在貨幣政策中的作用。首先,本文度量了政策不確定性、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和SP2等多種不確定性,發現它們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其次,發現政策不確定性或SP2較大時,貨幣政策趨向寬松,表明貨幣政策調整對政策不確定性與SP2有積極的反應。最后,本文通過漸進變化的LSTAR模型分析發現,月度數據中當政策不確定性較小時貨幣政策主要積極應對產出波動。在季度數據中,貨幣政策在不確定性較小的時期抑制經濟過快增長,在不確定性較大的時期會寬松進而刺激經濟增長,SP2的大小變化對利率規則的影響不顯著。基于門限變量的TVAR模型分析表明:在月度水平上,貨幣政策在正常時期維持物價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在不確定性較大時期貨幣政策的慣性較強。在季度水平上,貨幣政策在不確定性較大時期比正常時期更加關注經濟增長的穩定。這些結果一方面體現了中國貨幣政策多目標的特征,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不同頻率信息下中央銀行政策偏好的差異,總的體現了貨幣政策更多穩增長的目標,但是對金融市場風險的關注較少。
(二)啟示
本文的結論對于貨幣政策操作有兩個重要的啟示:一是分析發現貨幣政策的前瞻性不足或貨幣政策操作相機抉擇的成分比較多,盡管貨幣政策操作受到不確定性的影響,但是不確定性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弱。因此,貨幣政策應該更加注重對宏觀信息的使用,增強前瞻性和規則性。二是貨幣政策一直較為關注經濟增長,尤其是在不確定性較大時期,這非常符合貨幣政策防范風險的要求。但各種不確定性的表現不同,政策不確定性和SP2的作用較好,SP2有較好的信號作用,因此,更好地綜合考慮各種不確定性有助于實現貨幣政策防范風險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