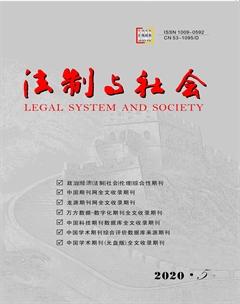以幾個實踐案例為切入點淺談權利行使與財產犯罪的界限標準
關鍵詞 公力救濟 私力救濟 權利行使 財產犯罪
作者簡介:郭庭,北京市煒衡(南通)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研究方向: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
中圖分類號:D92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5.256
一、 案例呈現與爭議焦點
(一)陳某搶劫案
史某拖欠陳某78萬元,陳某得知史某做蟲草生意,故意安排張某謊稱買主與史某交易,并在交易現場以暴力手段搶走史某55萬元。
(二)王某等人搶奪案
羅某為購置保時捷轎車,經由擔保公司擔保向銀行貸款100余萬,并以該轎車向擔保公司做抵押。后羅某又將該車質押給劉某借款42萬。因羅某停止向銀行還款,王某等人受擔保公司委托取回車輛。王某等人經周密安排,在馬路上逼停劉某駕駛的保時捷轎車,并公開搶奪車輛。
(三)丁某等人盜竊案
周某將車輛抵押某公司借款17萬余元,并辦理抵押登記手續。后周某又將該車輛質押給王某借款15萬余元。此后,王某又將對周某的債權以及附隨的擔保權轉讓至丁某。因周某違反合同約定,擔保公司周某某通過秘密手段從丁某處盜竊取得該車。丁某獲悉車輛被周某某盜走后,因與周某某無法協商一致,遂與他人合謀又從周某某處將該車秘密竊回。
(四)黃某敲詐勒索案
2006年2月黃某在商場購買了某公司的筆記本電腦一臺。在使用過程中,黃某發現該公司生產的CPU存在嚴重質量問題,遂向該公司提出索賠要求,索賠金額為500萬元人民幣。黃某聲稱,如該公司不進行索賠將向媒體曝光。該公司不承認黃某稱有質量瑕疵的CPU是自己生產的,同時向某派出所報案稱被黃某敲詐勒索。
(五)張某某盜竊案
張某某在其朋友馬某位于古玩城“唐寶齋”店內,趁無人之機用向馬某要來的店門鑰匙,將馬某店內的紀念幣、刺繡等財物盜走,財物價值經鑒定9600余元。張某某辯稱,其之所以采取不正當手段將被害人店內物品盜走,是因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經濟糾紛,主觀惡性不大。
以上前四個案例都是權利行使的典型形態,即行為人都是為維護自身利益,未借助訴訟、仲裁等公權力救濟途徑,徑行采取符合搶劫、搶奪、盜竊或者敲詐勒索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維護自身權利的情形。案例(一)和案例(四)反映的是行為人有無從對方取得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的類型,案例(二)和案例(三)反映的是行為人有無要求對方返還原物權利的類型。四個案例最大的爭議點都不約而同的涉及到行為人主觀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財產犯罪保護法益的類型以及行為人是否具有正當的權利基礎三個共通問題。如何把握權利行使出罪與入罪的標準,成為司法實踐中模棱兩可且亟待解決的尷尬和難題。
二、案例評析與界限標準的展開
根據文前對權利行使的分類,結合民法請求權基礎理論,筆者將行為人有從對方取得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的權利概括為債權權利,將行為人對無權占有者在私法上有要求返還原物的權利概括為返還原物請求權的權利。
(一)返還原物請求權權利行使與財產犯罪的界限標準
返還原物請求權包括物權返還請求權以及占有返還請求權。占有返還請求權系占有被侵奪的,占有人有權請求侵奪人及其繼受人回復其占有,返還原物的權利。物權返還請求權系物權人(所有權人、質押權人等包含占有權能的物權人,但不含抵押權人)基于物權本身享有的請求返還原物權利。根據張明楷教授的觀點,只要行為人對無權占有者在私法上有要求返還原物的權利,其采取符合盜竊、搶奪等財產犯罪手段恢復其權利的,不能構成相關財產犯罪。其次,從犯罪構成的違法性角度分析,在具有正當權利基礎的情形下,因目的具有正當性,以致手段的非法性所反映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大降低,情節顯著輕微,不構成財產犯罪。
案例(二)中,羅某將車輛抵押給擔保公司后,擔保公司與羅某之間即形成抵押合同關系,因車輛抵押權的設立不以登記為生效要件,擔保公司對抵押車輛依法享有抵押權。后羅某再次將車輛質押給劉某,羅某與劉某簽訂質押合同并交付車輛后,劉某依法取得車輛質權。羅某與擔保公司、劉某之間系存在兩個不同、獨立的法律關系。根據合同的相對性,羅某與擔保公司之間的合同權利義務只能約束羅某與擔保公司,并不能突破合同主體制約善意的劉某。其次,擔保公司對汽車享有的抵押權系沒有占有權能的物權,該擔保公司對其他合法占有人不享有物權返還原物請求權。劉某基于物權質權對車輛合法占有,擔保公司在私法上不具有要求劉某返還車輛的權利,故本案中擔保公司雇傭的王某強行奪取劉某車輛時,并不具有正當的權利基礎,因此并不能發生違法阻卻的效果。王某客觀上實施了搶奪行為,主觀上其除了具有排除劉某對車輛占有的排除意思,還有利用車輛實現抵押權的利用意思,可以評價為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案中,劉某基于質權合同負擔對車輛進行妥善保管的義務,在保管過程中因質權人過錯導致財物滅失情形的,劉某應當向羅某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此外,劉某對質物的享有的留置權、孳息收取權、優先受償權等相關權益均因質物被搶而無法實現。綜上分析,王某應當構成對劉某的搶奪罪。與案例(二)不同,案例(三)中丁某基于質權依法對車輛合法占有并負有妥善保管的義務,周某雖然系抵押權人,并且已辦理抵押登記,但在私法上并不具有要求丁某返還車輛的權利,其只能在債權實現過程中享有優于丁某受償的權利。周某侵奪丁某車輛后,對車輛進行非法占有,丁某為恢復自身合法權利,采取盜竊手段將本應自己合法占有的車輛取回,應當發生違法性阻卻的效果,不應構成犯罪。
筆者認為在財產犯罪與返還原物權利行使之間界限標準,可以這樣把握:行為人客觀上采取符合財產犯罪構成要件的手段行為獲取財物,若行為人對該財物享有返還原物請求權,財物的原持有者相對于行為人而言系現實的無權占有者,則行為人獲取財物的行為客觀上應評價為恢復權利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若行為人對該財物不享有返還原物請求權,行為人奪取財物的行為不具有正當的權利基礎,則行為人獲取財物的行為應當構成相應的財產犯罪;若行為人盡管享有返還原物請求權,但行為人的手段行為超過必要的限度,侵害了人身法益、社會法益或其他類型法益,不排除可能構成其他犯罪。
(二)債權權利行使與財產犯罪的界限標準
此處的債權并不局限于合同之債等意定之債,還包括侵權之債、不當得利之債等法定之債,但不管是何種之債,均應建立在正當的權利基礎之上,亦即合法之債。從相關裁判案例及理論學說來看,債權權利行使與財產犯罪的界限標準應當與債權數額與索取數額相關聯。
筆者認為在合法的債權范圍內,行為人行使債權,如果沒有超出權利的范圍,具有使用私力的必要性,而且其手段行為本身不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一般不宜認定為相應的財產犯罪。例如,在合法債權范圍內劫取財物,不成立搶劫罪,但如果達到故意傷害罪的立案追訴標準則成立故意傷害罪,如案例(一)的陳某搶劫案;再如在合法債權范圍內盜竊、騙取、敲詐勒索財物的,也并不能成立相應的盜竊罪和詐騙罪。但是,針對根本不存在的債權或者已經結清的債權,或者債務人一方具有期限的利益、清算的利益等值的保護的利益,或者債權的內容未確定,債務人在民事訴訟中存在請求的正當利益,或者獲取的財物明顯超過債權范圍的,行為人依然可能成立相應的財產犯罪。值得注意的是,案例(四)黃某敲詐勒索案中,黃某行使的是損害賠償請求權。關于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行使,原則上也不成立敲詐勒索罪。張明楷教授對此論述道:“因為行為人的手段與目的均具有正當性,至于賠償數額,則取決于雙方的商談。但是如果行為人以加害生產商的生命、身體、財產等相要挾而且所要求的賠償數額明顯超過應當賠償的數額的,由于手段不具有正當性,目的超出了應當賠償的范圍,應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三)權利基礎事實審查與認定的必要性
犯罪動機是刺激、促使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內心起因或者思想活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以及所實施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亦涉及被害人對案件是否存在過錯的問題,是重要的量刑情節。通過對權利行使與財產犯罪界分標準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返還原物請求權權利還是債權權利,對犯罪事實的定性和量刑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民事糾紛的基礎事實嚴重影響到罪與非罪、定性量刑時,公安機關有必要對此類基礎事實進行充分的調查取證,有必要盡可能查清事實。案例(五)張某某盜竊案中,馬某是否拖欠張某某錢款,是查明張某某犯罪動機的基礎事實。馬某與張某某有無債權債務關系,系民事爭議,一般應當按照民事訴訟的相關規則進行審理。通常情況下,對于該種民事糾紛,應當由張某某提起民事訴訟,以確認其與馬某之間存在債權債務關系,并判令馬某償還其錢款,履行給付義務。但在雙方對該債權債務關系存在爭議且未提起民事訴訟的情況下,偵查機關應當充分認識到,當某一民事爭議的基礎事實關系到權利行使的必要性,關系到定罪量刑時,則有必要盡可能查明。
參考文獻:
[1]張明楷.無權處分與財產犯罪[J].人民檢察,2012(7).
[2]張明楷.論財產罪的非法占有目的[J].法商研究,2005(5).
[3]童德華,胡亞龍.財產權利分離模式下財產罪法益的類型化研究[J].江漢論壇,2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