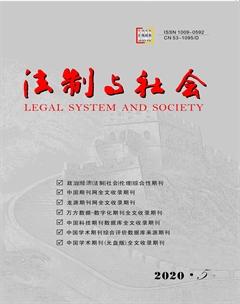民俗與法治的統一
張錦超
關鍵詞 民俗 法治 民族精神 法律信仰
作者簡介:張錦超,河南理工大學文法學院。
中圖分類號:D6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5.243
一、民俗與法治的內涵價值初探:打開法治信仰的連接點
何謂“民俗”?民俗學者鐘敬文曾在《民俗學概論》中談到,“民俗,即民間風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它包括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飲食、居住、服飾、婚姻、喪葬、宗教、祭祀、歌謠、競技等許多方面。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社會意識的形成離不開社會物質條件、社會生產力水平。因此,民俗的產生歸根到底是依附于社會形態,是由一定時期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作為扎根中國大河文明的民俗,因其宗法維系的紐帶作用,而逐漸形成了一種社會倫理規范,就如費孝通《鄉土中國》所描述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鄉土社會秩序。傳統的民俗生活已經塑造了人們心靈的價值觀:歷史的經驗即是現世的經驗,依照傳統所為可以生活得很好。這樣的心靈價值觀是與法治理念所背道而馳的,換言之,內心排斥法律是法治建設的最大障礙。
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建構一種新的社會文化意識形態比解構一種固有的文化價值觀念更為困難,因此尋求二者之間的銜接點成為民俗與法治內在統一的關鍵。那么當前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法治?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理清中國的法治變革歷程。中國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工業文明席卷中國,以自由平等為基石的西方法治理念也逐漸滲透到中國大地。中國以禮制為核心的差序格局與西方以法治為核心的團體格局發生激烈碰撞,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的封閉狀態被打破而邁入了以法律移植與法律改革為中心的現代化法治進程中,但劇烈的法治變革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格格不入使法治理念很難廣泛深入到中國農村地區,由此,這為鄉規民約這種習慣法留下了廣泛的存續空間。
當今我們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市場經濟自由的本質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民俗的精神價值,市場經濟的生命和靈魂是信用,而這種品質恰恰蘊藏于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當中,中國自古倡導童叟無欺,而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的中國廣袤的農村孕育了這種契約精神。由此觀之,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品質為我們的法律建設儲備了一個“富礦”,通過這種民俗精神的挖掘,我們更能把握法治建設與改革的方向。
立法以人民為中心,反映人民大眾的呼聲,是我們的目標和方向。重塑法治信仰需要我們尊重廣大農村地區的風土人情,在此基礎之上實現民俗與法治的融合發展。民俗相較于法治具有使廣大民眾自覺信仰的鄉土情結,雖然國家制定法在國家強制力的保障下,似乎更容易得到貫徹,但是真正能夠深入人心并自覺信仰的法律,通常是那些與中國傳統民俗價值理念相似的規定。
法律不是萬能的,中國傳統的民俗理念仍維系著廣大農村地區的結構秩序。因此,在國家制定法與中國傳統民俗習慣法相沖突時,我們不能機械化地強調以國家制定法來同化鄉規民約,而是應該采用一種較為折中的方式,來尋求國家制定法與民俗習慣法的互相妥協與合作。
二、民俗與法治的文化價值分析:塑造民族特色法治精神
民俗習慣法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公信力和生命力,從歷史法學派的觀點來看,法律主要體現為習慣法,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超立法, 鄉間民俗作為一種習慣法,它的形成根植于中國悠久的農耕文化,這種文化特性使得這種民俗理念,深埋于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認同當中,因此立法改革不得不考慮這種治理形而加以融合。
法律像語言、風俗、政制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即趨于消逝” 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個民族社會生活作用的結果。這為我們的立法改革指明了一個堅守的標準。而法治之所以與民俗不同,是由于其產生的方式不同。法治模式來源于制度建構的過程,其以國家強制力作為后盾,而民俗是社會經驗積累的過程,是約定俗成的秩序規范,是一種直接的生活方式和制度體現。這種自發的秩序規范自然會受到人們的普遍遵守。因此,孟德斯鳩指出“法律是制定的,而習俗存在于人們的感悟。”阿奎那也曾指出,“習慣理性和意志大小的表現具有法律的力量,它可以取消法律,也可以作為法律的解釋者。”
“習俗是銘刻在人們的心里,并形成了規范人們的真正的法律,它無時無刻不在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可以不知不覺地以習慣的力量代替權威的力量。” 當正式制度過于超前或過于落后而偏離了人們的需求和能力時,人們的實際行為就會在制度與習俗之間尋求某種平衡,集中體現了過去和現在生活方式的習俗能否戰勝體現部分現在的而且更多的是未來生活方式的制度規范,這就要看當時具體條件下兩者的對比關系。法律制度的不被接受和法外制度的盛行,也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民俗習慣法的強大優越性。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價值的連接點,來緩解民俗與法治的沖突,而這個連接點即為我們獨樹一幟的民族精神。挖掘本民族特色精神,以精神特質作為先導,在堅守本民族民俗的過程中將法治精神貫穿其中,實現二者的深度融合與有機統一。就如伯爾曼在《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一書中所論述的那樣:“法律不是作為一個規則體,而是作為一個過程和事業,在這種過程和事業中,規則只有在制度、程序、價值和思想方式的具體關系中才具有意義。從這種廣闊的前景出發,法律淵源不僅包括立法者的意志,而且也包括公眾的理性和良心 ,以及他們的習俗和慣例。”
我國的法治建設因起步較晚,而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此,對于我們來說,最好的法治建設并非是簡單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選擇,而是在中國豐富的本土資源的基礎之上進行法治建設。這一過程顯然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深刻的理論建設來實現這一法治設想。因此,在推進法治建設的過程當中,如何將國外法律制度的閃光點轉化為我國本土的一些先進的原則和精神,對于我國推進法治現代化進程至關重要。法治建設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一國的法治建設不僅要體現制度本身的內在精神,更需要展現一國的文化內涵。因此在法律引進或移植的過程當中,這些制度應該真正的同中國本土社會所具有的民族精神相協調。在我們進行頂層設計的過程當中,不僅要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改革,而且還需要強化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法治精神培養,實現法治精神信仰塑造的協調統一。唯有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才能扎根本土,全局發展,實現民族精神與法治精神的和諧統一,塑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三、民俗與法治的時代碰撞:建設成熟型法治國家
近年來,隨著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治國理念的深入提出,加之由于全國各地煙花爆竹生產和燃放過程中存在的安全隱患和對環境產生嚴重污染等諸多原因,全國各地均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煙花爆竹禁放政策。禁放政策直接導致了春節期間燃放煙花爆竹的傳統民俗的危機。
民俗和法治的博弈,在過去的18年之中經歷了漫長的調整與融合。但這種融合是否已經根深蒂固,融入到人們的精神理念當中,還是一個問題。法治改革的目的在于實現社會的公共福利,在環境保護與傳統民俗之間,這種差異可能顯得難以抉擇。一方面,禁放政策體現了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健康中國理念,但另一方面,春節期間燃放煙花爆竹是中國幾千年來民俗積淀的自然結果。一刀切的禁放政策,將使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復興更加缺乏群眾基礎,從而導致民眾喪失對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
但是,民俗與法治融合的問題顯然人們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禁放政策只能符合一部分民意,而另一部分則是傳統的堅決捍衛者。而如果通過法律的方式解決這種問題,必然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障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法律社會公共利益平衡的核心在于使各方利益得到兼顧,禁放政策則直接打破了法律天平的平衡,從而讓社會公共利益站在了功利主義的肩膀之上。18年來民俗與法治的博弈,充分證明禁放法規由于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而喪失了其存在的廣泛的社會基礎,最終勞而無功。一個脫離于本民族傳統民俗的立法,將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文化理念,如污染法律源頭一樣,破壞了人們對法律權威的尊重與信仰。我們應該在尊重歷史傳統和關懷民生之間保持平衡,這樣才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公眾也將不難理解政府,從而使政府法規更容易被尊重和實施。
通過上述這個時代熱點的評析,我們可以得出緩解民俗與法治沖突的基本路徑,為建設成熟型法治國家提供一些方向。
首先,法律制度的制定要尊重社會民俗。思想觀念的轉變總是滯后于社會制度的變革,新的法律制度會在長時期內存在于舊制度所普遍規范的社會習俗和人們的行為習慣之中。因此法律的制定不會立即得到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可和尊重,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不斷得到認同的過程。人類社會的生生不息使傳統民俗更加煥發生命力,它是一個國家的制定法所無法回避的民族文化價值的縮影。我們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公正地正視民俗習慣法,汲取民俗的合理內容,吸納傳統的積極因素,使得法治建設具有堅實的社會基礎,以求天理、人情、國法的內在統一。
其次,法律的貫徹要注重法治宣傳與精神文明建設協同并進。人的現代化是法治文明建設的基本出發點。法治的徹底貫徹需要精神文明建設保駕護航。一個國家即使擁有最現代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但是如果遵守并付諸實施的人,從心理、思想和行為方式上沒有實現由傳統的人到現代的人的轉變,那么法治的現代化將難以得到推進和實現。因此,我們應該在法律制定的同時,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建設,使民眾的法治認知達到一個更高層次的水平,以至于實現民俗與法治精神的高度統一,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法治社會的發展進步中促進社會文明風貌的改變。
最后,法治的建設要注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法治精神相結合。不僅要“突出中華文化的地位”來彰顯民族特色,而且要“結合當今時代的條件”來突出先進性和世界性,以促進國家法律制度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協調發展,進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法治文明建設的高度統一。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產物,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反映了整個民族的精神文化風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以整個中國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為中心,真正體現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精神內涵。這需要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法治建設協調統一,加快中國法治化進程,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文化力量,著力建設成熟型法治國家。
注釋:
鐘敬文.民俗學概論[M].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呂世倫.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
薩維尼.論當代在立法和法理學方面的使命(英譯本).第27頁.
[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M].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312頁.
阿奎那政治著作選讀[M].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26頁.
[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71頁.
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頁,第263頁.
[美]伯爾曼著.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賀衛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