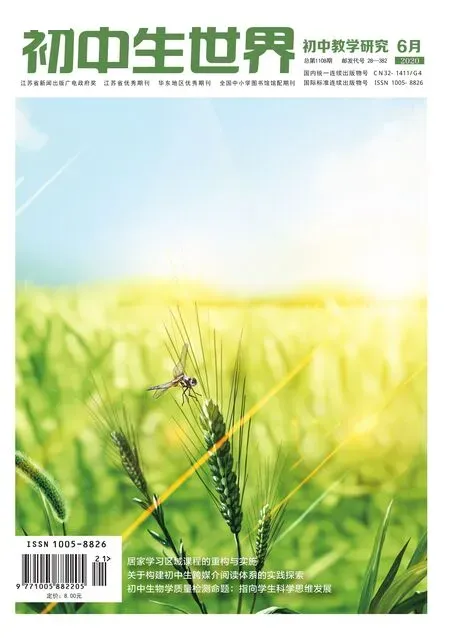多重對話助力細讀 “二次開發”豐實文本
——以《湖心亭看雪》教學為例
■夏熔亮 徐宏壽
語文教材“二次開發”是教師參與課程開發的方法之一,體現了教師較強的文本解讀能力和創造性思維能力。華東師范大學俞紅珍教授指出:“教材的‘二次開發’,主要是指教師和學生在實施課程過程中,依據課程標準對既定的教材內容進行適度增刪、調整和加工,合理選用和開發其他教學材料,從而使之更好地適應具體的教育教學情景和學生的學習需求。”教學《湖心亭看雪》,可以通過多重對話,助力文本細讀,并通過多種方法進行“二次開發”,深入挖掘文本價值。
一、比較閱讀,突出技法巧妙
用其他課文進行比較閱讀,可以更清楚地辨別并掌握寫作技法,且感受不同語言風格。把本文寫景文字與《濟南的冬天》第4段進行比較閱讀,可以更容易弄清白描手法的藝術特點及其作用。
這段文字描寫白雪覆蓋下的小山,與《湖心亭看雪》一文相比,雖然寫的都是冬天雪景,但細細分析,還是有很多差別的:①前者寫的是雪后天晴,景物明朗,色彩多樣;后者寫的是夜晚,“上下一白”,色彩單一。②前者寫的是山上雪景,景物稍多而有層次;后者寫的是湖上夜雪,景物較少,朦朧依稀。③前者視線由高到低,因是小山,視野不寬;后者泛舟西湖,水面開闊,天空遼遠,視野寬廣。這些因素的不同,決定了兩位作者描寫景物時,采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老舍用工筆細描法,依空間順序,移步換景,從山上、山尖、山坡一直寫到山腰,一筆筆輕描,雪景的顏色、形態、情態盡收眼底;而張岱采用工筆白描的手法描繪西湖雪景。這種白描手法,抓住景物主要特征,用簡練樸素的語言勾勒出一幅“上下一白”、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圖,使人置身于一種審美的藝術境界之中。
二、配圖誦讀,彰顯意境高遠
適時恰當地利用圖片進行“二次開發”,可以使課文內容更加直觀形象,生動可感,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想象。蘇軾評論王維作品時所言“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八個字,后來成為評判一首好詩、一幅好畫的重要依據。著名畫家黃永玉的《湖心亭看雪》寫意圖,是“二次開發”的極佳資源。PPT左邊投影文字,右邊呈現畫作。學生緩慢齊誦,讀到“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時,教棒在畫上圈一個圓圈,意為天、云、山、水已經渾然融為一體;讀到“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時,教棒在畫上方的一道淺淺的墨線上從左到右緩緩移動;讀到“湖心亭一點”時,教棒指向墨線下邊的一個黑點;讀到“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時,教棒指向黑點右下方短短的一葉扁舟。可以說,文中有畫,畫中有文;文、畫結合,相得益彰;配圖誦讀,漸入佳境。
不僅如此,課文和畫作都采用了白描手法,有不少“留白”。教師可以讓學生一邊以自己喜歡的方式誦讀課文,一邊欣賞大師畫作,同時驅遣自己的想象力。這樣,學生的目光在文、畫之間不斷游移,抽象思維和直觀思維也在不斷轉換,想象力在不斷飛馳,誠如葉圣陶先生所言,“領會著作者的意境,想象中的眼界就因而擴大了,并且想想這意境多美,這也是一種愉快”,學生自然容易沉浸在作者所描繪的天地蒼茫、高曠遼遠、天人合一的意境中。
三、增刪調換,感受語言精妙
“一字未宜忽,語語悟其神。”讀書時一詞一句都要重視,只有細細揣摩,品詞析句,才能感受語言的表現力。我們可以通過對關鍵詞句增、刪、調、換,讀中揣摩,讀中辨析,讀中玩味,感受文字背后的精彩,從而發現作者用詞的精妙所在。
如“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一句,連用三個“與”字,是否顯得啰嗦?能否刪去三個“與”字?能否把三個“與”都改成“、”?經過討論,我們發現:刪去三個“與”字,或者都改成“、”,固然也寫出了天地間一片蒼茫的景象,但四種事物之間似乎有了界限;而原句四種事物之間,連用三個“與”,給人一種獨特的視覺感受,雪后夜色中已經天地相連,渾如一體,難以分辨。“舟中人兩三粒”也完全融入天地山水之中,傳達出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賞析“惟長堤一痕……舟中人兩三粒而已”一句時,可以采用換詞的方法來辨析。原句能否改成“惟長堤一道,湖心亭一座,與余舟一艘,舟中人兩三個而已”呢?很明顯,改了之后,全是平常所用量詞,毫無新意,與作者高雅的情趣風格迥異。而“一痕”“一點”“一芥”“兩三粒”,不但視線由遠及近,景物由大而小,而且比喻貼切形象,切合夜晚泛舟湖上的視覺感受,讓人感受到天地山水之浩瀚,舟中人物之渺小。由此可見,采用增刪調換法進行“二次開發”,不僅可以感受作者語言的精妙,而且可以發現作者遣詞造句背后隱含的言語思維和智慧表達。
四、同中辨異,突破教學難點
教學難點如何突破,歷來是個難題。如果采用同中辨異的方法“二次開發”教材,就能深入淺出,撥云見日。《湖心亭看雪》的教學難點,便是引導學生通過對敘事寫景的分析,感悟作者孤寂高雅的精神世界。難點如何突破?金軍華老師提供了一個好方法。講完本課后,他呈現柳宗元《江雪》一詩,在學生朗讀后,提出一個問題:假如時空可以穿越,讓張岱與柳宗元在湖心亭相遇,張岱會和柳宗元成為知交嗎?這一石激起千層浪。學生紛紛發言,大多是從張岱和柳宗元追求相同的“境”(冷寂、蒼茫的雪景)這個角度出發,得出兩人會成為知己的看法。這時,金老師提醒學生從形象上分析,并進行追問:有沒有人認為兩人不會成為知交呢?經過對兩文中“獨”的細讀交流,結合不同的寫作背景,有幾個學生認為,張岱是不會和柳宗元成為知交的,雖然二人追求的“境”相同,但二者所傳達的“情”卻不一樣。張岱遺世獨立,孤芳自賞,超凡脫俗,而柳宗元參與革新,官場失意,充滿傷感。
為了突破教學難點,教師先提出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讓學生參與討論。在多數學生認識流于淺近、趨于一致的情況下,教師進行有效追問,引導學生思維向深處發展,由外在的“境”同轉向內在的“志”異,“向青草更青處漫溯”。同中辨異,要善于在細讀文本時找準突破口,通過涵泳詞語、分析不同生活背景,走進其靈魂深處。這樣,學生的認識在討論和點撥中才會提升層次和境界,思維才會向縱深發展,教學重點難點自然就會迎刃而解。
五、適時補白,體悟潛在志趣
海明威說過:“好的文學作品像冰山只露一角,百分之九十藏在水下。”那“藏在水下”的部分,通常就是留白。《湖心亭看雪》也有多處留白,如湖心亭、長堤、扁舟和舟中人影影綽綽,以及文末舟子說話之后作者的反應,這些都沒有清晰地描寫出來,值得學生去想象。通過補白的方法進行“二次開發”,可以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景,使課堂教學內容更加豐實。
如王君老師執教此課,連拋四個問題展開對話:舟子說他癡,他會辯解嗎?為何(不會)?當時他會是怎樣的表現?此時此刻,他心里會說什么呢?這樣進行有效追問,一步一步打開學生的話匣子,引導學生通過對話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在教師巧妙的點撥和學生精彩的補白中,作為明遺民,作者內心深處的故國之思,以及遠離世俗、孤芳自賞的情懷,自然地外顯出來。
陶行知先生曾經說過:“處處是創造之地,時時是創造之時,人人是創造之人。”“二次開發”語文教材,不僅僅是課程開發的需要,也是專家、名師的職責,更是新時期每個語文教師專業發展的必然選擇。面對統編版語文教材,每個語文教師都應學會開展多重對話,細讀文本,吃透教材。在此基礎上,選取適宜的方法,創造性地“二次開發”教材,把握文章精髓,發展學生思維,只有這樣,語文課堂才會有更多精彩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