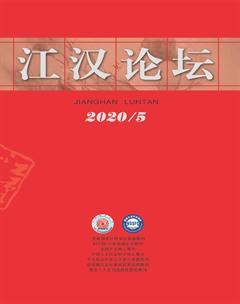海德格爾人的本真生存思想探析
摘要: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的快速發展,一方面來自外界的誘惑在顯著增多,人們容易忘記自己本身,忘記自己的初心,也就是說人的生存存在著沉淪的傾向;另一方面來自人們內心的個性追求也越來越強烈,希望領悟和實現自己的本真生存。如何從人的沉淪中走出來,通過領悟走向本真生存,這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海德格爾從存在的角度規定人,具體從“存在狀態上的”與“存在論上的”存在兩個方面,論述了關于人的本真生存思想,指出了此在的本真生存方式和特性,即此在在籌劃、畏和向死亡存在中領悟生存的本真狀態。海德格爾關于人的生存之觀點,特別是其中如何從生存的沉淪走向本真生存的觀點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有益啟示。
關鍵詞:海德格爾;此在;人的本真生存;馬克思主義
中圖分類號:B516.54?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0)05-0033-07
當今世界,一方面全球化的趨勢在不斷加劇,另一方面人們越來越注重發展自己的個性。這就意味著,一方面來自外界的誘惑在顯著增多,人們容易忘記自己本身,忘記自己的初心,也就是說人的生存存在著沉淪的傾向;另一方面來自人們內心的個性追求也越來越強烈,希望領悟和實現自己的本真生存。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呢?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作為個體的人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人是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存在的,因此,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社會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沒有脫離社會的人,也沒有脫離人的社會,這是我們討論人的生存的基本前提。馬克思一方面批判費爾巴哈“假定有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的個體”,而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①;另一方面強調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即體現人的個性、特點的全面發展。如何理解二者的辯證關系,值得我們深入思考。海德格爾關于人的生存的觀點,特別是其中如何從生存的沉淪走向本真的生存的觀點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有益啟示。
一、人的本真生存與沉淪是此在在世的兩種基本方式
生存在海德格爾看來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他說:“人的這種存在方式,我們稱之為生存(Existenz)。只有在存在領悟的基礎上生存才是可能的。”②他對人的生存的研究,是從“此在”(Dasein)入手的,“此在”在海德格爾那里實際上指的就是人,不過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而是此時此地生存著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此在的特點就在于它的此。海德格爾指出:“基于存在領悟,人就是這個‘此(Da),它以其存在而使存在者被首次突入而啟開,以致于存在者作為存在者能夠對它自己顯示出來。比人更原始的是人的此在的有限性。”③此在的本質在于生存,此在生存的本真狀態就在于它的個別化及不可替代性。海德格爾關于人的本真生存的思想是建立在他對于“存在狀態上的(ontisch)”存在與“存在論上的(ontologisch)”存在的區分基礎上的④。海德格爾從存在狀態上的與存在論上的存在兩個方面,論述了關于人的本真生存的主要思想。
(一)此在在世
此在一出生就被拋入世界,在海德格爾看來,此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此在總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在世的澄清曾顯示出:無世界的單純主體并不首先‘存在,也從不曾給定。同樣,無他人的絕緣的自我歸根到底也并不首先存在。”⑤
海德格爾反對將此在孤立起來,然后再去尋找此在與世界(包括世內存在者)、此在與他人的通道或橋梁,而認為此在在世是一種整體現象,此在與他人、此在與世界本來就是混然一體的。而這正是此在生存論分析的現象學基地。在海德格爾那里,一方面,此在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存在也不可能離開此在,用波爾特的話說就是“存在(Be-ing)不可能在沒有此在的情況下發生,而此在本身則除非對存在(be-ing)作出回應,就不會存在。海德格爾稱這種相互依賴為‘轉向。我們日常的自我解釋沒能認識到轉向”⑥。
海德格爾認為,此在生存即此在的在世。“‘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簡稱在世——引者注)這個復合名詞的造詞法就表示它意指著一個統一的現象。這一首要的狀況必須作為整體來看。”⑦ 但這一生存狀況本身則首先是一種存在狀態上的,而不首先是存在論上的,它是此在生存論存在論分析的基礎。因而“我們現在必須先天地依據于我們稱之為‘在世界之中的這一存在機制來看待和領會此在的這些存在規定。此在分析工作的正確入手方式即在于這一機制的解釋中”⑧。
在之中(in-Sein)與在之內(Inwendigkeit)不同。在之中就是指此在的生存狀態,不是指傳統意義的將一個獨立于所謂世界之外的人放置到類似于容器一般的世界之中去,也“絕沒有一個叫做‘此在的存在者同另一個叫做‘世界的存在者‘比肩并列那樣一回事”⑨,而是指此在和它的世界混然天成、融為一體的狀況,當然這里的此在是有所作為的。在之內則僅指兩個在空間之內具有廣延的存在者就其在這一空間中的處所而相向具有的存在關系。在生存論存在論上,“在之中”是更為源始的關系,而“在之內”則是衍生出來的。“在之中”是使“在之內”的傳統空間關系成為可能的先驗條件。因為“在之內”是靠此在而得以領悟和揭示的,而此在又必須在世,“只有領悟了作為此在本質結構的在世,我們才可能洞見此在的生存論上的空間性”⑩。
概而言之,在生存論存在論上此在在世是指此在、世界、世內存在者(又稱為周圍世界或世界)三者的融為一體,須臾不可分離。一方面,此在是世界的此在,說到此在同時也就設定了世界的世內存在者,此在生存著就是他的世界。另一方面,世界又是此在的世界,說到世界也不能離開此在和世內存在者的設定。“如果沒有此在生存,也就沒有世界在‘此。”{11} 這就是說,對此在和世界的領悟、解釋是一種整體性的,也是一種循環式的。
(二)由沉淪過渡到本真生存的關鍵在于此在的獨特領悟
海德格爾認為,此在作為能在,在生存論上就是被領悟的此在生存的全部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可分為本己的和非本己的兩種,這兩種可能性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此在生存的本真狀態就是此在本己可能性的開展狀態,此在生存的沉淪狀態就是此在非本己可能性的開展狀態。此在的本真存在方式和特性表現為,此在在籌劃、畏和向死亡存在中生存的本真狀態。
此在生存狀態上的沉淪,即此在以閑談、好奇、兩可等方式存在,是因為此在在日常生活中以常人的方式存在,并且“此在首先是常人而且通常一直是常人”{12}。這個常人標識著此在的生存論沉淪狀況,這種沉淪在本質上也屬于此在的存在。正如陳嘉映所說:“沉淪本質地屬于此在,而不是個人或社會的某一不幸階段,仿佛可以靠文化的進步消除。沉淪中的生存論存在論的要點在于:此在不立足于自己本身而以眾人的身份存在。失本離真,故稱之為‘非本真狀態(Uneigentlichkeit)。相應地,本真狀態(Eigentlichkeit)被定義為此在立足于自己生存。”{13} 也就是說,這種沉淪是此在的非本真存在方式,它并不是外在于此在的,但相對于此在的本真生存方式來說,它不是源頭而是衍生的,因為沒有反映此在那獨特的“此”。“海德格爾通過此在的日常生活領悟人的生活方式,認為沉淪是人的命運,人在沉淪中喪失了本真的自我而迷失于常人的同化之中,這是一種不負責的存在方式。”{14}
但這并不是說,此在的非本真生存方式就毫無意義,實際上人這種生存的沉淪在一定意義上說,能夠減輕自己的心理壓力,尤其在現代社會生活和工作節奏非常快、壓力非常大的情況下,沉淪這種生存方式有一定的減壓作用。“在共世界的領域里產生了關于現存在是誰的問題,也就是關于實存的主體的問題。……海德格爾認為,這個主體寧可說就是‘人們,也就是非本然的自己。在這個非本然的自己中,重要的就是與別人保持距離,這別人對任何明顯的例外都加以壓抑,把一切存在的可能性都拉平,把通向事象的一切原來的路遮蔽起來,回避作出任何決斷,取消現存在的責任,從而減輕現存在的負擔。”{15} 因此,這種非本真的生存方式,對于蕓蕓眾生來說,有時也是可供選擇的一種生存方式。甚至可以說,沉淪是此在在世的常態。“在世總已沉淪”,“為什么人不生存在源頭?因為人已經綻出:‘沉淪正是為了能在世。”{16}
但是,這種非本真的生存方式從根本上說存在重大缺陷,比如:“人們惰于思考,懼于負責,久而久之便陷入了一種迷茫,無法判斷真實與否,無法展現自己的能在,不再有堅定的信仰和目標,盲目迷信常人,走一步看一步,沒有未來,只能渾渾噩噩度過余生。”{17}
因此,此在并不能一直沉淪于常人之中,它還得發現自身。這種發現自身就是在生存論上從此在的非本真狀態進入此在的本真狀態。這種由非本真狀態進入本真狀態的關鍵途徑就是領悟,就是要將此在用以把自身對自己本身阻塞起來的那些偽裝拆穿。具體說來,此在由非本真狀態進入本真狀態是通過先行的決心進行的,決心意味著讓自己從喪失于常人的境況中被喚起。這種喚起,不是要在生存狀態上使此在完全脫離世界,脫離他人,而是通過“決心恰恰把自身帶到當下有所煩忙地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之中,把自身推到有所煩神地共他人的存在之中”{18},從而“讓一道存在著的他人在他們自己最本己的能在中去‘存在,而在率先解放的煩神中把他們的能在一道開展出來”{19}。
當然,這種反省自己、認識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不能由其他人代替的。正如賀麟所說:“要探討人生問題,就是要人自己研究自己,反省自己,大凡了解外物易,了解自己最困難。所以人生問題實在是最困難、最不容易研究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最重要、最大、最不易得解答的問題。”{20}
為什么人們能夠領悟此在的本真生存呢?在海德格爾看來,是緊迫性使然。“沒有了緊迫性,存在(be-ing)本身就不可能發生。自身性就是‘召喚和歸屬的瞬間場域。召喚就是存在(be-ing)的召喚;如果我們傾聽它(b?觟ren),我們就歸屬于它(geb?觟ren)。因此自身性發生在轉向的瞬間之中,發生在存在(be-ing)與此在的共屬之中,而緊迫性則讓這種共屬發生。”{21}
二、此在(人)本真生存的獨特性質
此在的本質就在于它的生存,生存著的此在具有不代替的向來我屬性。“作為對此提出的絕對聚集,存在并沒有衰退。它在一種獨一無二的可怕性中顯示出來。”{22} 此在的生存與其它世內存在者的存在有著本質的區別,突出表現在此在是存在論地存在著的,他能進行追問,具有領悟、解釋、言談等諸種存在樣式,他能為自己的生存進行籌劃,組建此在的能在,對此在的存在有所作為,而其它世內存在者則不具有這些特性。因此,“不應把人看作是和其他許多事物一起出現的事物的種的實例,而應當看作是與自己的存在有關的存在者。這個存在者的存在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我的存在;它的所是(das Wassein)應該理解為是它可能的存在方式(即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存在),而不應理解為是它所具有的特性的總和”{23}。
此在是作為“能在”而存在的,包含著人作為個體在生存中所能出現的全部可能性,即本己的和非本己的可能性。此在的本真狀態就是此在本己可能性的開展狀態,即此在展開其自身的此,此在的個體化存在。
(一)此在存在狀態上的本真展開狀態——籌劃
所謂生存狀態上的籌劃,指的是在拋擲中把可能性作為可能性拋到自己面前,讓可能性作為可能性來存在。這就是說此在的籌劃活動,是此在將自己的種種可能性在空間中一一展示出來。因此,海德格爾說:“籌劃是使實際上的能在得以具有活動空間的生存論上的存在機制”,并且“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在籌劃著。”{24}
我們可以用比喻的方法來說明籌劃活動的意思。如用一匝卷著的布來比喻此在存在的種種可能性,我們將這卷布打開,使它平坦地展開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領悟它,揭示它。這就像此在生存的籌劃活動。此在的籌劃活動即是此在通過生存將此在生存論上的全部可能性一一展示在當下的活動空間里。不過對卷布的打開活動是來自一種外在的力量,而此在的生存籌劃活動則是出于此在自身的力量。卷布的每展開一圈,都面臨著還打不打開的選擇。同樣,此在的籌劃活動在活動空間中,每進一步展開自己的此也都面臨著選擇,這乃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決斷狀態。
在這種決斷狀態中,良知在呼喚,“良知的呼喚具有把此在向其最本己的能自身存在召喚的性質,而這種能自身存在的方式就是召喚此在趨往最本己的罪責存在”{25}。這種此在的生存選擇與自己本真存在狀態相關,它必須照顧到此在本身的責任,下定決心,作出決斷。因為在當下的空間里,此在只有展開屬于此在自身的一種可能性。所以,海德格爾說:“呼聲并不給出任何理想的普遍的能在供人領會;它把能在展開為各個此在的當下個別化了的能在。”{26}
從正面解釋是如此,如果從反面來說,此在的籌劃活動在這種決斷的狀態中,具有“不”的性質。所謂“不”的性質指的是此在在當下活動空間里,只能開展此在的一種生存的可能性,這就意味著它同時不展開此在的其他可能性,但這并不是說這些其他可能性就不為此在所擁有。
卷布全部被展開,它就會完全敞開而呈現在我們面前。這整個展開此在之此的籌劃活動,可以領會為此在存在的揭示活動,即所謂去蔽活動。這種卷布的展開活動,其目的不是為了找出卷布里面的珍珠或其他東西,而是這種去蔽活動本身。因為在被卷著的布里面完全沒有其他東西,根本就沒有什么珍珠,卷布完全展開而呈現在我們面前,那么這種展開活動也就完成了。與此相似,此在的生存籌劃活動或去蔽活動,其目的在于此在在當下的生存活動的空間里展示自己的此,展示自己的個性,就是展示屬于自己的本己可能性;而不是為了尋找籌劃活動之外的、此在生存背后的所謂某種本體。
在海德格爾看來,此在的本質就在于它的生存,就在于此在趨向存在(zu-Sein)。這種本真生存是由每個獨具個性的此在個體的本質決定的,而不是由外界其他的原因決定的,所以他指出:“此在擬想出一個計劃,依這個計劃安排自己的存在,這同籌劃活動完全是兩碼事。”{27} 此在的生存籌劃活動是要使此在成為其所是的,而擬計劃然后執行則是從外部強加給此在的,前者是內在于生命的,而后者是外在于生命的,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
(二)此在生存論上的本真狀態——畏
除了在生存狀態方面展開此在存在的本真狀態外,海德格爾認為此生存論上的本真狀態是在畏(Angst)中得以展開的。他說:“畏把此在拋回此在所為而畏者處去,即拋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那兒去。畏使此在個別化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這種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領會著自身,從本質上向各種可能性籌劃自身。因此有所畏以其所為而畏者把此在作為可能的存在開展出來,其實就是把此在開展為只能從此在本身方面來作為個別的此在而在其個別化中存在的東西。”{28} 這就是說,此在在其個別化為最本己的在世過程中,所領會的此在本身本己的可能性,也就是此在在在世的籌劃活動中所領會到的一種情緒。
此在在世的籌劃活動每在當下的空間里展開自身的本己可能性時,總是面臨著一種選擇,總能感到一種責任、罪責。此在每當面臨這種公開出為了選擇與掌握自己本身的自由而需的自由的存在的情況,它總是感到一種無可名狀的恐懼,即感到畏。
這種畏不是來自外界,而是來自此在存在自身。海德格爾說:“在畏中,周圍世界上手的東西,一般世內存在者,都沉陷了。‘世界已不能呈現任何東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所以畏剝奪了此在沉淪者從‘世界以及公眾講法方面來領會自身的可能性。”{29} 正由于畏是指此在在開展其自身本己的可能性中領會著自己,而不是從世界和公眾方面展示自己,因此畏是此在內在的。也就是說,沒有世界和其他世內存在者的陪伴,此在孤獨地將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受其他存在者的遮蔽,有一種完全來自自身的畏懼情緒,海德格爾稱這種狀況為“無家可歸”(Nicht—zuhause-sein)。
為此,海德格爾特別區分了畏(Angst)和怕(Furcht)。畏是此在在本真地展示自己可能性的籌劃活動中,從自身可能性方面領會到的一種情緒。因而它沒有外界對象,而完全是來自自己在世的生存籌劃活動本身。但怕則不同,它是一種非本真的存在狀態,它具有怕的對象,“唯一可以是‘可怕的而且是在怕中被揭示的威脅總是從世內存在者那兒來”{30}。這也就是說,怕這種情緒是來源于對世內存在者之怕,怕的對象是“一個世內的、從一定場所來的、在近處臨近的、有害的存在者”{31}。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世內存在者是非此在式的、在此在之外的存在者。“怕之何所怕就是‘可怕的東西,這種世內照面的東西分別具有上手的東西、現成在手的東西與共同此在的存在方式。”{32} 此在之所以對共同此在的存在方式感到可怕,是由于它所怕的是同他人的共在,怕這個他人會從自己這里扯開。并且,“我們不可在存在者狀態的意義下把這種‘會懼怕領會為‘個體的實際氣質,而應把它領會為生存論上的可能性”{33}。
(三)最能體現此在生存的本真狀態——“向死存在”
死亡是此在本身向來不得不承擔下來的存在可能性,因為此在的死亡表明此在不再具有能在的可能性,此在其他的本己的可能性,超不過死亡這種可能性,“死亡綻露為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超不過的可能性”{34}。這就是說,死亡是其他此在不能替代的可能性,如果說此在其他的可能性能夠被替代,那么此在的死亡是說此在的存在終結了,沒有人能夠超越死亡這種可能性而避免死亡。不僅如此,而且只要此在生存著,它就已經被拋入了這種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畏死與對亡故的怕攪在一起。畏死不是個別人的一種隨便和偶然的“軟弱”情緒,而是此在的基本現身情態,它展開了此在作為被拋向其終結的存在而生存的情況。畏死是此在內在的生存方式之一,而對亡故的怕則是把死亡當成外在的東西,在死亡面前表現出來的一種“軟弱”情緒。
只要此在生存著,它就實際上死著,但首先和通常是以沉淪的方式死著。此在首先和通常以在死亡之前逃避的方式掩蔽著最本己的死亡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能夠看到,這個或那個親近的或疏遠的人死了,每天每時都有不相識的人死著。但這句話的意思好象是在說,人終有一死,但自己當下還沒有碰上而已。這樣,死亡被領會為不確定的東西,最主要的是這種東西必定從某個所在到來,但當下對某一個自己還沒有變成現實,因此還不構成威脅。每一個他人和自己都可以令人信服地說,有人死了,恰恰不是我,而是常人,這個常人乃是無此人。這樣“死”被敉平為一種擺在眼前的事件,它雖然碰上此在,但并不本己地屬于任何人。常人則為此首肯并增加了向自己掩蓋其本己的向死存在的誘惑。對此,施太格繆勒說:“對于有限的意識來說,死亡的意識是本質的。因為此外沒有任何東西能像死亡那樣把人從他的日常生活中拋出去,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像死亡那樣迫使人意識到他的限度,然而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像死亡那樣提高人對實存的投入(der existenzielle Einsatz)的必要性的認識。”{35}
但是,“一向本己的此在實際上總已經死著,這就是說,總已經在一種向死亡的存在中存在著”{36}。常人掩蓋起死亡之確定可知性質中的特有性質就是死亡隨時隨刻都是可能的。死亡作為此在的終結乃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此在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確知的、而作為其本身則不確定的、超不過的可能性。死亡作為此在的終結存在于這一存在者向其終結的存在中。向死亡存在先行到可能性中去,才使這種可能性成為可能并把這種可能性作為可能性解放出來。這種死亡是把此在作為個別的、內在的東西來要求此在,也就是說,在先行中所領會到的死亡把此在個別化到它本身上來,這樣一來此在才能夠本真地作為它自己而存在。這是因為,“在絕望中本然的實存就得以實現了,因為誰完全陷入絕望之中,誰就獲得了本然的自己”{37}。
三、人的現實生存是個性與社會性的辯證統一
由上述海德格爾關于此在生存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他是非常重視個體的存在即人的生存的,雖然他也強調共同此在和共同存在,但第一位的仍然是此在。正如陳嘉映所說:“無論他怎樣愿意強調共在這一規定性,實則仍把此在當作先于他人和共在的東西了。”{38} 實際上人的現實生存,既是個體的存在,又是社會的存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的存在是個體性與社會性的辯證統一。
(一)個體人生存的意義與責任的領悟
海德格爾所說的人的本真生存,是要強調此在的個體性的優先地位,即此在在追問和領悟存在的意義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以此在來領悟和揭示存在的意義,必須先領悟此在的生存,而只有在本真生存狀態下,才能從源頭上領悟那獨一無二的“此”。因此,此在的決斷、籌劃、畏、向死存在等都是個體性的,都是不能替代的,可見與其他存在者不同的此在在海德格爾眼中的地位,以致有人以此來攻擊他。“在海德格爾看來,人是與自己的存在有關的,這一點可能成為如下指責的根據,即只有具有自我中心觀點的人才是海德格爾分析的出發點。”{39}
其實這種指責雖然抓住了海德格爾的一些傾向性特點,但并不是完全符合實際。原因在于:海德格爾重視此在的優先地位,并且強調此在與世內存在者的區別,但他從未說要以自我為中心來追問存在的意義;他反對以此在為中心而其他存在者圍繞在周圍,而是強調此在在世的一體性,強調共同存在與共同此在。
實際上,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可以說沒有個體的人,就沒有社會。馬克思并不否認個體人及其特殊性,他說:“人是一個特殊的個體,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成為一個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同樣地他也是總體、觀念的總體、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會的主體的自為存在,正如他在現實中既作為社會存在的直觀和現實享受而存在,又作為人的生命表現的總體而存在一樣。”{40} 個體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條件,個人的素質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就具備了基礎。因此,馬克思、恩格斯說:“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41}“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42}
就人的生存來說,個體生存意義的領悟只能靠個體自己,他人有時可以給予啟發,但是不能替代。正如賀麟所說:“切身的人生問題,全待自己反省、體察、自求解答,他人頂多只能盡提醒啟發之責,此外實無能為力。”{43} 對理想、使命的領悟、牢記和實現,離不開個體的努力,不管多么遠大的理想、多么崇高的使命,其實現最終都要落實到個體人的身上。“人的使命或天職,也可以叫做人生的理想。但是使命固是理想的,同時也是現實的,它是我們此時此地即在執行,即須執行的使命。理想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地提出此理想或彼理想;使命是決定的,或幾乎可以說是人不能自主、不能不遵從的天命。理想是主觀建立的,使命是客觀賦予的,是國家給予的,時代給予的,或是上司賦予的。”{44} 黨賦予的使命、國家賦予的使命、人民賦予的使命、時代賦予的使命,我們必須牢記,扎扎實實落實到自己的實際行動中去實現,這是我們每個人必須負起的責任。
(二)共同此在與共同存在
海德格爾反對先將主體與客體孤立起來作為前提,然后再去尋求它們統一的途徑這種做法。在他看來,人總是生活在世界之中,人與世界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人與世界融為一體,而不是人孤立地獨立地存在于世界之外,也不是凌駕于世界之上或躲在世界的背后。
從存在狀態上說,海德格爾認為世內存在者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雖然這一點在其后期則有所改變。但在存在論上來說,則世內存在者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它要靠與此在的共同存在來揭示。同時當下的上到手頭和在手上的世內存在者,也可呈報他人的存在。海德格爾認為這種情況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此在與世內存在者的共同相遇。
此在同周圍世界的世內存在者(又可稱為用具或自然)打交道的過程就是此在在世的煩忙過程。在煩忙中,即使當下上手狀態的世內只存在某種東西,如鐘表,但“在使用當下而不顯眼地上手的鐘表設備之際,周圍自然世界也就共同上手了”{45}。因此,當下上手狀態的世內存在者是可以揭示的,則其它世內存在者也是可以揭示的。此在同世內存在者打交道是通過上手和在手進行的,但這并不是說此在孤立地存在于世內存在者之外,而是存在于統一的世界之中。“共在是此在的本質規定性。即使無人在側,此在的存在仍是共在。海德格爾不愿先設定一個孤立的主體,然后再把一個孤立的它物和他人附加到這個主體周圍。”{46}
不僅如此,此在在同用具打交道之際,也同其他人共同照面了。這個此在同其他人的共同照面是以非此在式的世內存在者呈報出來的,在生存論存在論上也必須在這個角度上進行闡釋。“世界向來已經總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47} 而此在同其他此在通過煩忙方式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則稱為他人的共同此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內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48} 世界不僅對此在開放,而且對其他此在式的存在者也是開放著的,換句話說,此在在這個世界之中是以世界之內的存在方式來照面指的也就是上述這種情況。
此在發現他人的此在可以從世內存在者方面進行,而且“此在首先發現‘自己本身在它所經營、所需用、所期待、所防備的東西中——在首先被煩忙的周圍世界上到手頭的東西中”{49}。這就是說此在當下和通常是從自己的世界來領會自身,他人的共同此在則往往是從世內上手的東西來照面。他人的這種照面,并不是作為現成的人和物來照面,而首先是在他們的在世中碰到他們。“他人的這種共同此在在世界之內為一個此在從而也為諸共同在此存在者開展出來,只因為此在本質上就自己而言就是共同存在。”{50}
(三)小我融入大我,達到二者的辯證統一
海德格爾通過此在領悟和揭示存在,此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雖然也講共同此在與共同存在,但他們對此在的作用遠遠低于此在對他們的作用。此在被拋入世界,在世界之中生存的前提就是必須有物質生活資料,如果連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沒有,那一切就無從談起,而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生存離不開既有的社會物質條件,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的生產方式決定人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51} 也就是說,人的本真生存也好,非本真生存也好,物質資料的生產是最基礎的條件,離開此一切無從談起。這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觀點。
不僅如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與物質生活是統一的,“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52}。嚴格地說,人們的物質生產方式是更基本的,它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53}。
人們在生產和生活的過程中,需要相互打交道,必然發生各種交往,形成各種關系、各種共同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非常緊密,抽象的個人只是理論生活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個人的生存對社會依賴的程度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高,共同體對個人生存的意義也越來越重要。“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54} 因此,我們必須反對自我中心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提倡集體主義。實際上沒有脫離社會的孤立的個人,也沒有脫離個人的空洞的社會。堅持個人與社會的有機的辯證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觀點。
總之,如何做到感悟本真的自我與融入世界相統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結合中國的實際,就是如何處理小我與大我的辯證關系,在這里個體人實際上是小我,社會(尤其是國家與人民)是大我。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青年的人生目標會有不同,職業選擇也有差異,但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國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與時代同步伐、與人民共命運,才能更好實現人生價值、升華人生境界。離開了祖國需要、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賞都會陷入越走越窄的狹小天地。”{55} 這就給我們處理人的個體性與社會性的辯證關系指明了方向。
注釋:
①{5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531頁。
②③{22} 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17、118、634—635頁。
④ 關于海德格爾對“存在狀態上的(ontisch)”與“存在論上的(ontologisch)”的區分的論述,請參見拙文《論“存在狀態上的”與“存在論上的”的區分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意義》,載《德國哲學》第9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⑤⑦⑧⑨⑩{11}{12}{18}{19}{24}{25}{26}{27}{28}{29}{30}{31}{32}{33}{34}{36}{45}{47}{48}{49}{50} [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43、66、66、68、70、431、159、354、355、177、322、335、177、227、227、225、225、172、174、300—301、305、88、146、14、146—147、148頁。
⑥{21} [美]波爾特:《存在的急迫——論海德格爾的〈對哲學的獻文〉》,張志和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247—248頁。
{13}{16}{38}{46} 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85—86、105、81、80頁。
{14}{17} 張倩倩、劉明文:《此在沉淪的當下表現》,《南方論刊》2016年第2期。
{15}{23}{35}{37}{39} [德]施太格繆勒:《當代哲學主流》上卷,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95—196、192—193、185、183、178頁。
{20}{43}{44} 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80、80、81頁。
{4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頁。
{41}{52}{53}{5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7、147、199頁。
{4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55}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頁。
作者簡介:汪世錦,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副主編,北京,100732。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