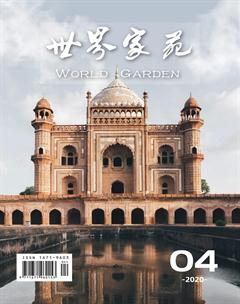新冠肺炎疫情中謠言傳播機制與辟謠策略探析
宗青
摘要: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暴發,成為一起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引發全球關注。與之前“非典”疫情時的媒介環境不同,如今,移動媒體普及,社交平臺的信息交流活躍,形成了特殊的信息傳播語境。一方面,移動網絡使得信息傳播變得快捷而暢通,另外一方面也為網絡謠言提供了傳播便利,有學者稱,新冠病毒帶來了全球第一個社交媒體性的“信息疫情”(infodemic)。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謠言作為案例,分析新媒體環境中網絡謠言的傳播方式、特點及相關影響,對重大疫情中的謠言傳播機制作出分析,并探討如何進行有效治理。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網絡謠言;傳播機制;謠言治理
1 疫情環境中網絡謠言的新特點
“謠言”是生活用語,法律上對謠言的表述為“虛假信息”,在傳播學中謠言被定義為未經證實卻廣泛流傳的信息。未經證實的信息與虛假信息有所區別,因為前者未必是虛假信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諸多未經證實的信息在社交網絡平臺涌現,相當一部分被證實為謠言,也有信息在事后被證實為真。
本文討論的“網絡謠言”,是指通過網絡平臺進行傳播、交流和互動的虛假信息,對正常的信息傳播起到干擾作用,并亟需治理。疫情中的網絡謠言,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0.1 謠言主題與疫情的發展幾乎同步
2019年12月1日,《柳葉刀》雜志發表文章,披露了首位發病患者,由此開始出現有關疫情的話題討論。然而在疫情暴發初期,與疫情相關的信息缺乏,人們對該疫情既充滿恐懼,又不知從何種渠道可以獲取準確可靠的信息,各類謠言因此有了存在空間。“白巖松專訪鐘南山”的謠言被大規模轉發,原因和背景就在于此。同時,也因對疫情情況掌握的事實不足,由此衍生出許多模糊和不確定的信息,例如“未出現人傳人”到后期被證實“存在人傳人”。
隨著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網絡謠言也隨之發生變化,辟謠的內容也有所不同。如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疫情謠言專區中,在疫情暴發高峰期,該階段平臺上共有290條謠言,內容多與健康有關,雙黃連、板藍根、阿莫西林等藥物先后成為可以治療新冠肺炎的“有效藥物”,“口罩”、“消毒”等也成為高頻詞,到了疫情后期,謠言則多與開學時間、復工復產、交通恢復等相關,呈現出相當的同步性。
0.2 謠言傳播與新的傳播語境密切相關,“群圈”成為謠言重地
2003年“非典”暴發,以“非典”為主題的謠言卻相對較少,因為當時缺少相應的傳播支持,公眾獲取信息的途徑主要來自于主流媒體,而主流媒體對信息的把關相對嚴格,信息的真實性較高。近年來,隨著移動媒體的高速發展,移動網絡使用已經成為極為普遍的現象,只要擁有一部智能手機,人人都手持“麥克風”,都是傳播者。
疫情期間,北京師范大學新媒體傳播研究中心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網民在疫情中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為網站、電視、微信和手機新聞APP,使用占比都達5成以上,分享信息則主要通過朋友圈或群聊。而據北京零點有數數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布的一份監測數據(2020年1月 25-30日)顯示,公眾了解疫情信息的 幾 大 渠 道 主 要 是 微 信 群/朋 友 圈 (63.9%)、門 戶 網 站/新 聞 客 戶 端 (48.2%)、微信公眾號(38.2%)1.3 謠言傳播在形式上有所變化,“再造事實”讓謠言顯得“逼真”
通過微信等社交媒體傳播的謠言,多以文字、圖片、視頻或語音等形式,低成本的 “有圖有真相”讓謠言看起來很“真實”,尤其是對于不熟悉時新技術的老年人群體,對拼接的圖片和視頻深信不疑,屬于謠言的“易感人群”。紐約大學社交媒體和政治參與實驗室曾對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的臉書平臺上謠言信息進行分析,發現65歲以上的用戶中又11%分享過謠言信息,謠言信息的數量是18—29歲年輕用戶的近7倍之多。
加上老年人群體對健康類的信息尤為關注,疫情主題的謠言成為“痛點”,雖然有的信息看起來就是似是而非,但是他們寧可信其有,也要將它分享到家庭群中,提醒家庭成員。
此外,在謠言傳播形式上,此次疫情中更多借助了“名人效應”。“鐘南山”、“張文宏”、“李蘭娟”等傳染病領域的專家都成為高頻詞。冠以名人,謠言看上去更為可信,這與疫情語境下的謠言生產有直接關系。
2 疫情中的網絡謠言所產生的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涉及面極大,傳染性極強,公眾由對疫情的關注和猜測轉為擔憂和恐懼,又因缺少有效信息而變得焦慮、懷疑甚至憤怒,社交平臺上不僅有道聽途說真假不明的各類信息,也有因負面情緒而滋生的謠言。從個體角度而言,因文化程度、認知水平存在差異,對同一信息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面對謠言,不同群體的反應狀態也不盡相同。
當群體因謠言而出現恐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壞社會正常秩序,甚至影響政治安定。謠言雖小,影響卻可能極大,因此,許多政府部門的官微和一些主流媒體,都專門辟出版塊進行辟謠。
與此同時,當我們在討論謠言時,被討論的謠言可能并不完全是虛假信息,而是一條等待核實和驗證的信息。比如“李文亮醫生事件”,他在某微信群內的發言,是早期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討論,當時被判定為“謠言”,事實上,該討論是基于一定的依據,對初期的疫情防治具有相當重要的提示作用。又比如“氣溶膠傳播”一開始也被認為是謠言,之后專家對此傳播方式做了確認和科普,證實其并不完全為虛假信息。
不過,從整體上來說,所謂“謠言”,即為暫且不能被證實和認定的信息,出處也十分可疑,而經由沒有邊界的網絡平臺,傳播速度更快,傳播范圍更廣,產生的負面影響也由此更大,網絡謠言的治理勢在必行。
3 如何治理與疫情相關的網絡謠言
在移動媒體的傳播語境下,網絡謠言的傳播速度之快,有人將此現象形容為“真相還在家中穿鞋,謠言已經走遍天下”。加上網絡謠言又多以社交媒體進行傳播和流通,監測與治理的難度也由此變大。如何有效治理網絡謠言,尤其是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當中,治理與疫情相關的謠言,也是對疫情防控的應對手段之一。
根據疫情中網絡謠言的傳播特點及其產生的影響,筆者對此提出以下五個方面的建議,以供討論。
3.1 通過專有渠道進行積極辟謠
在疫情初期,公眾對該傳染性疾病缺乏必要的了解,獲取的信息中,謠言與科學知識混淆在一起,很難分辨。可以說,公眾對新冠病毒的正確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隨著各類謠言而往前推進的,其中傳播最為盛行的謠言,包括此次新冠病毒就是“非典”卷土重來等。
美國著名人格心理學家奧爾波特曾推導出過一個謠言傳播的公式,即“R=i*a”(謠言流通量=問題的重要性*證據的曖昧性)。他認為對于人們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正規傳播渠道不暢通或是功能減弱,缺乏可靠的信息,謠言的傳播量會增大。根據該理論可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人們對于病毒來源、如何傳播、治愈率等相關問題極為迫切地希望獲取相關信息,假如官方信息提供不夠及時充分,謠言便有了極大的生存空間。
針對疫情中的網絡謠言,各級政府部門先后建立了辟謠平臺,借助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設立辟謠官方賬號,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專門設立疫情辟謠專區,實時針對疫情謠言進行辟謠,極大提高了辟謠效率。在真假信息的交鋒中,用科學知識戳破謠言,讓公眾在對比中實現信息的有效甄別。民眾了解的正確的疫情知識越多,謠言的影響則越微小,傳播空間也越小,并通過此次重大事件,完善了治理謠言的機制建設。
3.2 主流媒體應當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期間,相當數量的謠言是通過微信進行傳播的,但是與此相悖的是,據北京零點有數數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布的一份監測數據(2020年1月25-30日)表明,僅有4.2%的公眾把“個人微信群/朋友圈”選為信任的信息渠道。也就是說,雖然網絡謠言多以社交媒體進行傳播,但是多數公眾并未將此作為信任的信息來源,主流媒體發布的疫情信息因其專業性而被大眾所信任。
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央視媒體及地方媒體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深入疫情中心,進行跟蹤報道,還原現場圖景。同時,主流媒體在發展過程中,報道形式也發生了變化,除傳統的文字和圖片形式外,短視頻、VLOG等報道形式都被運用到,充分滿足了不同群體的受眾獲取信息的習慣和需求。媒體與公眾也進行了充分的對話,并施以影響,比如主流媒體呼吁出行要戴口罩,對疫情的減緩起到了重要作用。
3.3 注重網民的媒介素養
2020年5月由廣州大學數字傳播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承辦的“疫情中的傳播倫理和社會治理”云論壇中,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黃珊教授提到,疫情中的謠言不排除存在一些惡意、故意編排散布的,但是絕大多數信息的傳播是基于對現狀的不安而產生的傳播,針對此現狀,網絡謠言治理應強調綜合治理,對于惡意的謠言編造和傳播應當以法律手段進行處理,對那些沒有惡意的流言傳播者,則應該通過提高其媒介素養,實現對網絡謠言的間接治理。
5G時代到來,信息傳播更為便捷,受眾參與傳播更深更廣,提升用戶的媒介素養,打造一個健康的網絡生態,本身也是對網絡謠言的有效防范手段。
(作者單位:江蘇現代快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