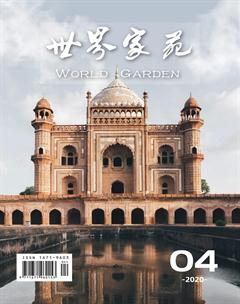從中蘇互派大使及移交舊俄使館問題中淺析加拉罕對華活動的作用與影響
杜依璘
摘要:1923年5月31日,《中蘇協定》簽署完畢,蘇聯全權代表加拉罕就此展開了新一輪對華活動。依據協定的第一條,加拉罕提議中蘇互派大使,同時,敦促北京政府落實協定,盡快移交舊俄使館,但由于主觀原因與歷史遺留問題,導致這兩件事歷經波折才得以解決。通過簡明地梳理蘇聯在華設立大使與收回舊俄使館的交涉過程,可以得知加拉罕在其中采取的策略,進而探究此階段加拉罕的對華活動產生了何種影響。
關鍵詞:加拉罕;蘇聯駐華大使;俄國使館;外交團
加拉罕(Л. М. Карахан)是中蘇關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執行蘇聯對華政策的核心角色之一。1923年,加拉罕以蘇聯全權代表分身來華,通過談判與北京政府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即《中蘇協定》),促成中蘇兩國恢復正常外交關系。中蘇復交后,加拉罕首先需要完成兩項任務是:一,就任蘇聯駐華的正式外交使節,向中華民國總統呈遞國書;二,收回屬于蘇聯的在華使館及各地領事館,維護蘇聯在華利益。
1 加拉罕提議在華設立大使級外交代表
《中蘇協定》的第一條規定:“本協定簽字后,兩締約國之平日使領關系應即恢復。中國政府允許設法將前俄使領館舍移交蘇聯政府。”由此來看,互派外交使節是1924年中蘇復交之后第一件需要商定的要事。
20世紀,駐外使節一般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級為大使,第二級為特命全權公使,第三級為駐辦公使,第四級為代辦。并且,兩國互相派駐的外交使節的等級是對等的。
近代外交實踐表明,一國政府往往會將一等或二等公使派駐到不重要、弱小或不友好的國家。在中國就是如此,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各國派遣的駐華使節最高等級也不過特命全權公使,未曾有過在華設立大使的先例,直到加拉罕來華。
加拉罕在設使問題上另辟蹊徑,主張將中蘇的外交代表由公使升格至大使級別。與北京政府簽訂協定后,加拉罕很快將這個想法通報給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Г. В. Чичерин),以征求政府的同意,加拉罕認為,在中國設立大使具有極為重大的政治意義。“中國一直以來都在爭取列入一等強國之席,但列強始終予以拒絕。”蘇聯與中國互設大使,意味著蘇聯愿意以平等、友善的姿態與中國交往,這一點將使得蘇聯與所有帝國主義列強區別開來,也有利于蘇聯提升在華影響力。
按照慣例,蘇聯駐華的正式外交代表可以加入由列強駐華公使們組成的外交團。所謂外交團本不行使任何法律性質的職能,但從清末開始,北京外交團的行為就已超越了職能范圍,時常通過發布集體照會向中國政府抗議或施壓,借此干涉中國內政。
在加拉罕看來,蘇聯代表出現在外交團中同樣具有重大意義,蘇聯代表能夠阻礙外交團在中國肆意橫行,“因為,如果外交團現在以集體照會的形式與北京內閣交談的話,只要有一位蘇聯公使提出反對,就足以讓任何一份集體照會都無法發出。” 外交團侵犯中國利益的謀劃往往是秘密商定的,蘇聯代表加入外交團后可以打破這種局面,將各國公使討論的問題公開化。加拉罕向報界表此透露了此意:“余加入使團后,必盡余最善之努力,為公道正義張目,以求改善向來東交民巷之空氣。”
加拉罕目前身份未定,他所持國書上并沒有說明他的等級,針對這一問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經討論后決定,向加拉罕發出兩份國書備用,繼續觀察中國形勢再決定加拉罕以大使或是公使的身份遞交國書。
6月6日,加拉罕與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會晤,就兩國互設大使館問題交換意見,顧維鈞對蘇聯的提議表示歡迎,但以“兩國交涉在精神不在形式”為由擬互派公使,并建議將這個問題與中蘇訂立新約問題一同留到中蘇會議上解決,加拉罕斷然拒絕了這個建議。之后,加拉罕得到消息稱,顧維鈞在內閣會議中對互設大使館一事持否定立場,顯然,顧維鈞更加在意外交團的反應,他擔心只有蘇聯的外交代表成為大使可能會引起外交團的抗議,為自身招致麻煩。
不僅是顧維鈞,就連莫斯科當局也對加拉罕的提議有所顧慮:如果蘇聯大使突然出現在全是駐華公使的外交團中是否會在北京引發巨大爭執?對此,加拉罕的看法是,外交團可能會排斥突然出現的蘇聯大使,但不可能因外交使節的等級問題與蘇聯發生表面上的沖突,問題將由中蘇兩國政府協商解決。
為了促使顧維鈞盡快表態,加拉罕決定發表一份照會。起草完照會后,加拉罕立刻將它發給了報社,授意記者們開始撰寫評論。6月13日,加拉罕照會顧維鈞,正式提出兩國互設大使的建議,強調蘇聯此舉是出于對華平等、公正、互讓的原則。
加拉罕有較大的把握爭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不過,萬一北京政府拒絕提議,加拉罕則準備借助輿論批評北京政府,對外宣稱“中國政府由于害怕帝國主義者,因此不接受這份榮幸,而我們將遷就公使的等級。”
照會一經發出,引起了外交團的驚詫,北京政府外交部也陷入困境。顧維鈞收到照會不能不對互設大使的提議予以考慮,但受制于外交團的態度,沒有立刻給出答復,而是動員外交團各國一同升為大使,企圖以這種方法緩和僵局。
加拉罕從報紙上得知了這個消息,并沒有過多理會,他篤定各國公使不會答允,“因為這將使他們陷入愚蠢又可笑的境地”,事實確如加拉罕所料,6月下旬,顧維鈞的動員計劃未能成功。與此同時,加拉罕也清楚外交團對他的敵視。外交團既不希望蘇聯駐華大使成為外交團的領袖,又開始在移交舊俄使館的交涉上刁難蘇聯,但加拉罕的關注重心從不在于爭取外交團領袖的地位,也不在于同外交團搞好關系,而是獲得中國輿論對蘇聯的支持。
發表照會后,加拉罕曾多次催促顧維鈞盡快回應蘇聯的請求,而顧維鈞總以內閣總理患病不能出席閣議為由繼續拖延,直到顧維鈞任代理總理一職后,才無可推諉,7月12日,顧維鈞在內閣會議上提出中蘇互派大使案。14日,北京政府復照加拉罕,表示接受蘇聯的提議,同日,北京政府通知駐莫斯科代表李家鰲,指示李家鰲將復照轉告蘇聯政府。15日,加拉罕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稱,“奉派為駐華特命全權大使并送國書副本,請定期覲見。”
經過十余日的籌備后,31日,加拉罕在懷仁堂覲見總統曹錕,呈遞國書。自此,加拉罕作為蘇聯駐華大使正式到任,他也是中蘇關系史上第一位大使級的外交代表。
2 蘇聯收回舊俄使館的交涉
2.1 舊俄使館問題的由來與外交團的阻撓
1901年,清政府與十一國列強簽訂《辛丑條約》,將北京東交民巷劃為外國使館區,“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處,并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準在界內居住……中國國家應允,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使館區儼然成為了“國中之國”。1904年,簽訂《辛丑條約》的列強們又一同簽訂了《議定書》,對北京使館區的管理章程進行增改。
1920年,北京政府取消了舊俄使領待遇,此時中蘇尚未恢復正常的外交關系,而俄國使館位處使館區內,故交由外交團暫管,外交團又委托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Willem J. Oudendijk)代管。
《中蘇協定》簽訂后,加拉罕于6月6日與顧維鈞會晤時提出向蘇聯移交使館的要求,北京外交部于9日照會外交團,請求外交團領銜公使歐登科將舊國使館移交給蘇聯外交代表,歐登科于11日回復,借口“應由俄國正式派遣中國之外交代表,前來請求移交時,始能予以考慮”,拒絕移交。
23日,顧維鈞在外交部舉行午宴,加拉罕應邀在場,借機詢問外交部何時答復荷使照會,顧維鈞的回答是照會的內容還需要仔細斟酌。加拉罕得到的內部消息卻是另一種說法:其實外交部已經擬好回復歐登科的照會,只是顧維鈞一直在猶豫,要求重新修訂。加拉罕猜測顧維鈞可能受到了美國公使或是其他某列強公使的警告,他不愿得罪外交團,才會一直拖延。
在等待顧維鈞發出照會的期間,加拉罕將自己下一步的打算告訴契切林:最多再等一周,北京外交部若再無反應,則由自己致信荷蘭公使,請求他移交使館的鑰匙,但是,“如果他們固執不肯又拖延的話,那么,只剩下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了”。不過,加拉罕覺得,外交團面對直接的請求多半不會制造障礙,不久就會同意交出使館的鑰匙。
然而,加拉罕很快就意識到收回使館的問題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中蘇協定》的第三條規定,兩國將在中蘇會議上廢止一切舊約,另訂新約,不僅如此,加拉罕還在與北京政府簽訂的《秘密議定書》中同意在新約未訂之前,一切中蘇舊約“概不施行”。《辛丑條約》屬于舊約范疇之內,但該條約是包括俄國在內多國共同與中國締結的,舊俄使館在東交民巷使館區享有的部分職能與集體治外法權正是源自該條約,蘇聯如果單方面宣布廢止中俄《辛丑條約》,等于破壞了締約國的一致性原則,加拉罕不得不因此感到擔憂,蘇聯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會喪失對俄國使館的權利,最終導致使館無法被收回。
6月27日,顧維鈞照會荷蘭公使,再次請求將使館移交蘇聯代表。7月1日,英、美、法、日、意、比、西、荷八國駐華公使就答復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舉行會議,商定出了移交使館的兩個前提條件:“由蘇聯派出正式代表逕向使團接洽,并由蘇聯代表切實表示‘尊重使館界一切規則,方可將使團保管之前俄使館交與蘇聯代表。”7月12日,外交團復照外交部,再次駁回請求,并轉達1日會議的精神,直接指出中蘇之間的協定“不能損害中國與八國中各個成員已成之條約”。
2.2 加拉罕與外交團之間的交涉
因外交團在移交舊俄使館問題上展示出無禮態度,中國民間已掀起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熱潮。見中國輿情激憤,歐登科在7月20日離開北京,外交團領銜公使之位暫由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Jacob G. Schurman)代理,隨之,使館交涉的事務也轉至舒爾曼身上。
北京政府出面請求外交團移交舊俄使館無果,只好請加拉罕親自與外交團交涉,加拉罕對此表示同意,強調自己不會因收回使館而接受任何條件,“至遵守使館界內協定章程一節,本代表亦未便予以擔保,致成為一種含有條件之交還,損失國體。不過此項章程既為有關系各國所協定,則本代表遷入后,當可提議變更。”
24日,顧維鈞介紹加拉罕與舒爾曼二人舉行會談。因蘇聯在《中蘇協定》中宣稱放棄在華舊約及特權,舒爾曼要求加拉罕為接收使館做出保證,加拉罕解釋稱,蘇聯并未放棄《辛丑條約》的權益,只是會在將來考慮放棄,蘇聯雖然不贊成《辛丑條約》的規定,但會遵守其義務,一旦確定廢棄舊約必定會通知各國。會談的最后,加拉罕同意將會談記錄交給舒爾曼以供外交團討論。26日,加拉罕致舒爾曼兩封信函,在一封中聲明自己不會承認任何條件,在另一封中要求外交團移交使館與鑰匙。
7月31日,加拉罕就任蘇聯駐華大使,外交團提出的兩個移交使館的前提條件已滿足其一,再加上,如今外交團中的英、意、日三位公使都表示愿意為加拉罕居中調和,移交舊俄使館的交涉似乎漸入佳境。
8月13日,因舒爾曼回國,改由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擔任領銜公使,與加拉罕繼續磋商。目前,外交團的各國公使都獲得了本國政府對移交舊俄使館的批準,18日,芳澤謙吉代表外交團照會加拉罕稱,鑒于加拉罕已做出保證,外交團同意交還舊俄使館及鑰匙,但蘇聯需繼續承擔《辛丑條約》的義務。各國公使不希望因蘇聯放棄《辛丑條約》的利益而損及自身利益,在照會中表示“自有為本國政府保留‘放棄此種權利、利益、及因條約而生之義務之自由行動”。
照會還有一份附件,芳澤謙吉代舒爾曼轉告加拉罕:美國承認交還使館不代表美國有承認蘇聯之意。加拉罕對美國公使這番的聲明深感不悅,將附件退回,此事使得交涉一度陷入停頓。隨后的一段時間里,照會的附件在芳澤與加拉罕之間發出又退回,往返數次,8月30日,加拉罕在退回附件時還附上了一段文字,借此表達他對日本公使左右為難的體諒之情,以及拒絕接受美國這種帶有仇視蘇聯之意、不符國際公法與習慣的聲明。
加拉罕無法接受18日照會的附件內容,也不想承認任何條件,困惑于是否回復照會以及如何回復照會,于是,詢問契切林的意見。
契切林電告他:“外交人民委員部認為,沉默意味著同意,因此,不能不對芳澤照會中外交團的意見予以回復,不過,如果我們現在就將我們所有的理由都和盤托出,外交團就不會交出使館的鑰匙了。”所以,加拉罕只需要在復照中指出蘇聯方面負責接收使館工作的人選,并簡要說明自己不能接受18日照會中公使們所說的內容即可。
為了闡明蘇聯立場,分別向中國政府和外交團給出合理的交代,契切林還對加拉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遷入使館后,應聲明廢止舊約一事將在日后的中蘇會議上以簽訂新約的形式解決,還需聲明1904年議定書與《辛丑條約》無關,宣布1904年議定書對蘇聯不再具有效力,最后,待中俄《辛丑條約》廢止后,應向外交團表明,蘇聯愿意與他們商定使館區的暫行管理章程,并準備遵守1904年議定書中不違背蘇聯對東方國家政策的那一部分內容。
加拉罕按照契切林的指示回復外交團,于8月25日照會英國公使,同時抄送至日本公使,催促外交團移交使館,告知已派出參贊克雷什科(Н. К. Клышко)負責接收工作,又說自己對18日照會中公使們提出的附加意見“不能全予容納”,但“不至阻礙訂立俄大使館與各國使館間在使館界之臨時辦法。”
此時,外交團內部的態度已基本松動,準備近日內著手交還使館,但法國公使不滿于加拉罕在照會中有所保留的態度,要求加拉罕做出進一步的保證,外交團派出意大利公使斡旋此事,勸說加拉罕提交一份有關蘇聯履行《辛丑條約》義務的書面保證,9月12日,加拉罕照做,外交團遂于當日決定,同意將舊俄使館交還給蘇聯駐華大使。
在中蘇復交后數月移交舊俄使館一案終于塵埃落定,9月24日,加拉罕遷入蘇聯使館,10月,加拉罕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請中國士兵擔任蘇聯使館的守衛,以示蘇聯放棄了辛丑條約。加拉罕還對外宣稱:“收回舊俄使館為蘇聯應享之權利,雖使團曾加阻撓,但仍無條件收回,遷入使館,并不影響反帝政策。”
3 結語
通過中蘇復交后設立大使與移交舊俄使館問題,可見加拉罕的對華外交活動對于中蘇關系的發展以及蘇聯對華政策的落實意義重大。
從中蘇關系的角度來看,在加拉罕的提議下,蘇聯要求與中國互派大使級外交代表,在外交上以平等原則對待中國,尊重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有助于中蘇關系進一步發展,并且,蘇聯大使進入北京外交團后將繼續施行公開外交,這勢必會減弱外交團對中國內政的干預。
對于蘇聯對華政策來說,加拉罕出色地完成了對華外交任務,從外交團的掌控中收回舊俄使館,成功地維護了蘇聯在華利益,又引導中國輿論,借外交團干涉中蘇互設大使與移交舊俄使館的事實激起中國各界對蘇聯的同情與支持,從而達到在華宣傳反帝思想的效果。
此外,也不應忽略加拉罕在處理使館移交問題時表現出的兩面性與實用主義色彩,加拉罕對華宣稱蘇聯將放棄舊俄在華特權、廢止中俄舊約,但為了收回使館,加拉罕違反了《秘密議定書》的規定,向外交團聲明蘇聯仍是《辛丑條約》的簽字國之一,還做出了蘇聯仍會承擔《辛丑條約》義務的保證。
參考文獻:
[1] 薛銜天,等.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17—1924年)[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2] [英]勞特派特修訂,王鐵崖,陳體強譯.奧本海國際法(上卷·平時法·第二分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3] 李勃.外交學[M].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
[4] Карахан — Чичерину,2 июня 1924 г. //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и Г. В. Чичерина с полпредом СССР в Китае Л. М. Караханом:документ,август 1923 г. — 1926 г. [M]. Москва:Наталис,2008 .
[5] 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復旦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編.大事史料長編草稿·一九二四年六月[M].上海: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復旦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出版,1960.
[6] 朔一.俄大使問題與俄使館問題[J].東方雜志,1924(16).
[7] Карахан — Чичерину,16 июня 1924 г. //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и Г. В. Чичерина с полпредом СССР в Китае Л. М. Караханом:документ,август 1923 г. — 1926 г.[M]. Москва:Наталис,2008.
[8] 唐啟華.1924年“中俄協定”與中俄舊約廢止問題——以“密件協定書”為中心的探討[J].近代史研究,2006(03).
[9] 梁為楫,鄭澤民.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
[10] См.: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и Г. В. Чичерина с полпредом СССР в Китае Л. М. Караханом:документ,август 1923 г. — 1926 г. [M]. Москва:Наталис,2008.
[11] 李嘉谷.中蘇關系(1917—1926)》[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基金項目:基金項目:黑龍江大學研究生創新科研項目“加拉罕對蘇聯對華政策影響問題研究(1923—1926)”階段性成果(編號:YJSCX2019-052HL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