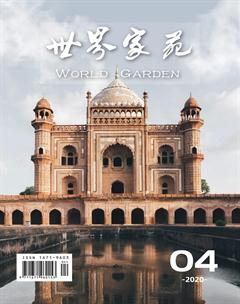論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話語政治”
陸歡歡
摘要:本文所論述的拉克勞、墨菲“話語政治”建構的內在邏輯是以話語為中心的政治,他們用結構主義、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來構造他的“話語政治”他們把政治主體多元化了,把一個統一的階級變成了很多的利益群體,他們沒有談到民族解放的問題,他們認為的政治主體可能就是一個不同群體利益。而馬克思的“階級政治”顯然是以階級為中心的政治,馬克思在批判政治經濟學視角下,在資本主義剩余價值體系和唯物史觀的根本方法中解決了階級問題,顯然是兩這種不同的路線。
關鍵詞:拉克勞;墨菲;馬克思;話語;階級;政治
英國后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拉克勞、墨菲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已經不可能了,他們拒絕經濟與政治相互作用的必要聯系。他們所謂的革命主體不是一個階級,而是話語主體,他們是靠話語構造的一個少數的群體。而話語本身有很多話語來爭奪意識形態屬民,其實是一場很分散的“話語”運動。
1 “話語政治”的理論來源
“話語政治”的概念,主要包含了3個層面的含義,有對政治的理解、對階級的解構和對話語的提出。在拉克勞與墨菲這里,話語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言說,它以索緒爾的語言學為基礎,揉合了拉康的知識考古學,更得益于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他們把“這種在其自身之內既包括語言成分又包括語言外成分的整體”,指稱為話語。它通過強調主體、社會以及政治的話語構造特征,解構了現代哲學關于話語與實在的二元對立,建構了一種“話語存在論”。它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所有對象與行為都是有意義的,而意義都是“接合”的產物,是由特定的規則體系歷史地建構起來的。任何意義都具有關系性特征,即使是單個語詞,其本身也是能指與所指結合而成的一個關系性結構。通過諸多差異性原素的“接合”,意義得以不斷產生。而這種“接合”又是暫時的、動態的,所以新的認同即意義不斷地通過新的“接合”被締造。質言之,話語就是“來自連接實踐的結構化總體”。
2 “話語政治”的基本內涵
“話語政治”以話語為中心的政治,它把政治主體多元化了,把一個統一的階級變成了很多的利益群體,談不到民族解放的問題了,他可能就是一個不同群體利益的話語之爭。拉克勞、墨菲是一種微觀革命,馬克思是一種宏觀的革命。拉克勞、墨菲認為馬克思是一種宏大的解放敘事,所以要解構他。20世紀70年代以后晚期資本主義發展,有這樣一個的特點,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已經不存在了,分裂成很多的少數群體,所以是他們的話語權力之爭。微觀的群體斗爭最后就是話語政治,就是他們所主張的那種斗爭模式。他們認為馬克思,這種模式已經失去了那個條件。因為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發展,矛盾已經消解了。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已經占據了一個統治地位,所以說階級政治不太可能了,因為階級主體消滅了,所以他們才采用話語政治。他們認為話語政治才有可能,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依然主張革命,但是革命的模式不是一個宏觀的階級。機械的“話語政治”拉墨認為人類解放是不可能的,他們就是為了政治而政治,所以他們認為應該從人類解放回歸到政治上,他們不考慮宏大的目標,他們是為了少數人的運動而運動。他們不承諾他們這個運動為了人類解放,就是為了反抗而反抗,沒有目標,這就是他們說的像政治的回歸,就是向激進的少數派的回歸。這個回歸其實它是保守的,他們承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推翻是沒有可能的,階級政治都不可能了,更不要談人類解放,他們好像激進實則保守。拉墨的話語批判是在合法性之內進行的,其實他們承諾了資本主義制度是合法的,所以他們采取的政治方案一定是民主解決的,話語的爭吵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內來談論問題,前提就是不推翻法律的合法性,所以他們還是在黑格爾法哲學范圍之內來談的,所以這個政治一定是“合法”的政治活動。
3 拉克勞、墨菲與馬克思:兩種政治觀的比較
3.1 馬克思“階級”理論的立場
馬克思道出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主張,始終關切以人為核心的價值關懷。馬克思的階級是在“異化”狀態下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積累以及在這種積累共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形成了所謂的資產階級。由于資本的非正義生存方式下產生了私有制,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了,它是一種資本主義制度。西方國家法律、法治體系、政治制度、管理制度相當完善,要想徹底的推翻私有制,必須要有成熟的無產階級組織。無產者在資本主義剝削的進程中,逐漸形成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形成后才有意識的進行政治活動、有組織的政治活動,以前可能都是零星的不滿、發泄情緒,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徹底的改變世界。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普遍的階級,即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形成了才能在法律的框架之內或者說才能超出法律的框架,超越資產階級作為人類社會最后一個政治范疇的合理性,就變成了“共同體”。但是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只要資本的力量、資本的邏輯沒有消退,那么階級就不可能退出歷史舞臺。現如今,雖然叫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是資本在統治力量,作為階級的政治仍然存在。
根據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最終構想,共產主義階段是不存在階級的。先是政治解放,然后是人類解放,最后到人類共同體階段勞動成為了第一需要。勞動是全社會的、生產的財富也是全社會的,不從屬于哪一個階級,因為階級已經消亡了,這是馬克思最后一個理想的狀態。最后理想的狀態是政治超越了階級、國家以及種族,變成了一個全球化的概念,如全球治理、國家治理。馬克思談及,國家的功能除了鎮壓和統治的功能,還有管理和對外交流的功能。那現在國家已經被超越了,那就是后民族國家,也就是全球治理。那么馬克思的政治觀,按照馬克思最后構想是沒有政治、沒有階級,也沒有階級意義上的政治,最后變成了在人類共同體類的意義上的自由人聯合體的自我管理。重新思考馬克思的“階級”,在其整個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就馬克思的終極思想和對共產主義來講,它將被超越。但只要資本在統治著,那么階級理論就是政治最合理最現實的形式。所以在這個角度,馬克思永遠不會被逾越,馬克思作為階級的政治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內是不可以被超越的,而拉克勞、墨菲他們想把階級消解,那是不得要令的,他們永遠沒有達到馬克思那樣一個認識高度。
3.2 拉墨“話語”理論的合理性與局限性
拉克勞、墨菲建構的“話語”理論體系,其實是對馬克思的政治形態,即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的解構。在拉墨這里,“話語”理論主要借鑒于后分析哲學的語言學、拉康的“縫合”概念以及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為了構建他們的話語體系。在特定情況下,他們認為“話語”才有可能。在這個意義上還是激進的,他們依然主張革命,但是革命的模式不是一個宏觀的階級這樣一個模式。馬克思的階級政治觀,按照馬克思最后的設想是沒有階級、政治的,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政治?馬克思的階級政治觀就是一種“類”的解放。解放它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類解放,政治也不是作為階級的政治,是人類的政治。人類的政治已經不是組織結構、等級觀念意義上的政治,政治的內涵其實也發生了變化。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就變成了生產者、自由勞動的生產者的自我管理,是自治這樣一個共同體。“自治”這樣一個共同體,那其實就是浪漫的工會。前南斯拉夫講了工人委員會,原來的時候工會是獨立的,與黨、機關、政府是敵對的,工會是為了工人爭取權力。所以,這個時候的工會是有利打破官僚主義的,因為它是全體工人的利益,全體工人的利益就是生產者的利益。那如果在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或者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全體勞動者的利益,但全體勞動者進去工廠的大門那一刻,也是受紀律和組織的管理,對工人的管理其實是有這樣一個統治因素。自我管理也可以說是自治,是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找“代理人”,是一種民主的形式,工會就是它的自治組織。我們初級階段其實在這個過程中就被異化,因為你選出的這些官員他們不代表你的利益,工會主席也不一定代表工人的利益,慢慢的可能在談判的過程中,他就被異化并與官員勾結在一起和管理者聯合。所以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對政治的理解、政治主體、政治的斗爭形式是都在發展變化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你必須承認拉克勞、墨菲的“話語”在西方20世紀70年代特定的社會階級結構、社會背景下是有其合理性的,它是一種新的政治狀況,或者說賦予了政治特有的內涵。
但是拉克勞、墨菲的話語理論只是局限于西方的議會政治或者是合法性之內的政治傳統,他們不會說改變世界,只是在合法性制度前提之下的一種改良,表面上很激進,實際上不可能改變。拉克勞、墨菲的話語理論是將社會等同于話語,將客體視為話語語境接合現實的存在物,其實他們同樣也表現出很明顯的“本質主義”和“還原主義”的特征。顯然,后馬克思主義者所堅持的與他們要批判的對象所不同僅僅是:用“話語”偷偷地置換了“階級”。
4 結語
在當代資本主義發生巨大變化背景下,研究拉克勞、墨菲的話語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變化和新形式的發展有一定的參考意義。然而,我們要準確地把握后馬克思主義的性質,以馬克思主義當代性價值為指導,來研究他們的新觀點、新方法和新結論。
參考文獻:
[1] 周凡.后馬克思主義:批判與辯護[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2] [英]恩斯特·拉克勞,查特爾·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基金項目:此文系2019年黑龍江大學研究生創新科研項目資助項目,(編號:YJSCX2019-046HLJU)。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