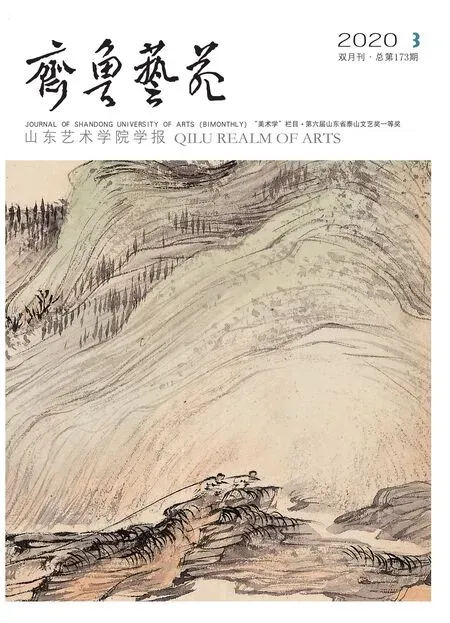神性與民族意識的完美統一
——亞納切克《格拉戈爾彌撒》探析
肖安平
(山東藝術學院現代音樂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前言
《格拉戈爾彌撒》是亞納切克1926年創作的作品,次年做了修訂。時值作曲家邁入72歲的人性成熟與創作的高潮,這可以從他的《伶俐的小雌狐》(1921-3)、《馬克羅保羅案件》(1923-5)以及著名的《小交響曲》等作品中看出。長期的創作也豐富了他的人生經歷,并為《彌撒》這部舉世之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品體現了作曲家極大的創作激情,飽含對人性的深刻反思與和作曲技術的最后總結。在亞納切克的創作中,宗教題材的音樂相對較少,盡管他在《彌撒》之前已創作有多部宗教體裁作品,但均具有一定的練習含義并大都遺失,如《捷克贊美詩》《管風琴曲》等,之后采用拉丁文創作的《摩拉維亞我們的父親》(1901; revised, 1906)以及《彌撒短曲》(1907-8),都沒有取得較大的成功。而《格拉戈爾彌撒》似乎是他一生也是最后對神性的徹底醒悟,與其他西方宗教題材音樂作品對上帝純潔而明確的崇拜與呼喚不同,他以民族性為橋梁,達到對神性的高度認知與融合,這在西方音樂歷史上是鮮見的。
亞納切克出生在一個有著傳統信仰的家庭中,他的祖父與父親皆是當地女王修道院唱詩班的成員,他本人最早接觸到系統的音樂教育也是在唱詩班進行的,可以說宗教信仰在這個家族中根深蒂固。盡管后期的亞納切克由于各種原因,在一段時期內對宗教失去了信心,成為一個泛神論者,不像他的祖輩那樣執著于教堂音樂,但是少時的經歷,特別是修道院的音樂主管在他的心靈里種下了民族音樂的種子,為他創作《格拉戈爾彌撒》打下了基礎。
對于亞納切克宗教觀起到重大影響的是歐洲“塞西莉亞”運動(1)18、19世紀的一些宗教音樂家們認為,音樂中出現了過多的器樂形式,宗教音樂應回到16世紀的范例中,即以人聲為主的宗教崇拜表達。,這場遍及歐洲各地的運動,意在恢復16世紀被禁止的教堂中的器樂音樂,它們在19世紀的德國得以復興,其影響遍及德語言系的各個國家,使得宗教器樂音樂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卷入這場運動的音樂家們都在探索器樂音樂在表現宗教虔誠中的不可替代性,二者的關系并非不可調和,此時器樂音樂的身份有了很大轉變,正大光明地進入了教堂成為表現宗教的重要載體。亞納切克順從了這樣的社會音樂潮流,開始逐漸改變自己對宗教的理解,從思想與靈魂深處接納宗教,并采用宗教的題材表達對神的崇敬。
亞納切克在《格拉戈爾彌撒》中將器樂與人聲高度融合,氣魄恢宏,充滿了強烈的戲劇性,既有歌劇、交響樂的因素,同時作曲家很好的將西方作曲技術和東方音樂元素融為一體,禮拜儀式的莊嚴與民族魅力并行而發,在斯拉夫人所特有的原始粗獷的呼喊與力量中得以完成。
一、音樂文本(經文版本)的選擇
縱觀西方宗教音樂,特別是彌撒曲,大多對拉丁文有著深刻的眷戀,如貝多芬的《莊嚴彌撒》、莫扎特的《安魂彌撒》、斯特拉文斯基的《詩篇交響》等。也許很多作曲家認為拉丁文是最具音樂性的語言,也許他們認為拉丁文是最靠近上帝的語言,因為拉丁文是圣經的早期文本,因此大型宗教作品采用拉丁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亞納切克并未遵循,而是采用了古老的教堂斯拉夫文。很顯然與德國作曲家勃拉姆斯一樣(2)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采用了德譯版本的《圣經》作為彌撒的素材。,亞納切克對古斯拉夫文的選擇是他對捷克——斯拉夫的深情厚誼。亞納切克是捷克民族獨立奮斗與勝利過程的見證者,他的作品充滿了對捷克——斯拉夫的情懷,即便是對宗教的理解也從民族的視角進行詮釋,這在西方作曲家中是少有的。
捷克是一個信奉天主教與東正教(3)大多數生活在捷克西部的人信奉天主教,而捷克東部主要信奉東正教,與俄羅斯相同。的國家,同時長期以來受到世界各地的特別是俄羅斯的斯拉夫(4)斯拉夫民族是起源于東歐的民族,后分裂成很多國家,這些國家包括以俄羅斯為首的烏克蘭、波蘭、南斯拉夫、斯洛伐克、捷克以及其他的各個斯拉夫民族的后裔國家,在語言和習俗等方面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脈淵源。文化影響。古老版本的斯拉夫教堂彌撒在捷克有著深遠的歷史,亦最具特色。亞納切克曾經與胡科瓦爾德地區的主教會面,表達了自己作為一個教徒和音樂家在教堂音樂創作方面的缺憾。主教說:“音樂大師,你可以創作一些有意義的作品,我這里有很多拉丁文的彌撒。”亞納切克回應:”我不想要拉丁文的彌撒,而是斯拉夫版的彌撒。”[1](P9)在作曲家心中早已認定了只有斯拉夫版本的彌撒才能喚起他創作宗教作品的熱情。亞納切克曾經對他的學生說過:“創作彌撒時用拉丁語來寫,但是要用捷克語思考”。[2](P7)這種通過宗教體裁升華民族情節的意識證實,對于古老的斯拉夫語言版本經文的選擇不是簡單的隨意的,是作曲家經過長時間的深刻思考的最終結果。《格拉戈爾彌撒》對于這位畢生致力于民族音樂發展的、同時又充滿了對上帝崇敬之心的作曲家來講是人生最好的禮拜。
二、作品的本體呈現
《格拉戈爾彌撒》是一部大型的交響混聲四部合唱作品,采用了西方彌撒的常規結構作為樂章的劃分,是現代音樂與古老斯拉夫語的緊密結合,無論是技法還是音樂的發展都充滿了強烈的斯拉夫魅力。作品在第七樂章通過管風琴的狂想式獨奏,表達對斯拉夫古老民族的呼喚,這種獨特的寫法在音樂史上是罕見的,體現出作曲家獨特的構思,粗獷的、原始的、強烈泥土的風格帶來不同凡響的聽覺感受,團結的、堅定的、虔誠的民族特質使斯拉夫的民族意志在宗教的引領下走向最后樂章的頂點。
(一)文本含義
正如前文所言,《格拉戈爾彌撒》是作曲家成熟時期的作品,距離他去世僅有兩年,它似乎成為作曲家以此接近上帝的最后的通行證。每一個人在瀕臨死亡之時都有一種恐懼感,這是人對即將踏入的未知世界的感受。回溯西方音樂歷史,很多作曲家在生命結束前選擇宗教作品的回歸來與世界告別,當中充滿了對生與死的哲理性思考,如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響曲》、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威爾第的《安魂曲》等,似乎只有這樣的體裁才能配得上對人生終極的拷問。在《格拉戈爾彌撒》中,作曲家關注的也是相似的主題,但與其他作曲家不同的是,亞納切克將關注點升華到對古老斯拉夫民族生死存亡的思考,這是這部作品從語言到旋律無一不滲透出強烈的斯拉夫風味的重要原因。基于這一點,作品具有非同一般的境界,民族性與神性達到了高度的契合,如同羅西尼的歌劇《摩西在埃及》(5)《摩西在埃及》是意大利作曲家羅西尼的一部歌劇,作品表現了先知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壯觀歷史事實,作曲家采用這樣的題材寓意深刻而鮮明,表達了19世紀意大利民族獨立的意識。所要表達的那樣,民族的獨立和意志高于一切,而只有在上帝的庇護下,這一理想才能得以實現。作品融合了東西方各自的傳統禮拜儀式的不同特征,采用了民間音樂素材作為陳述的方式。大量的捷克——斯拉夫的風格特征呈現在作品中,這也是有人稱它為《斯拉夫彌撒》的主要原因吧。
(二)音樂陳述
1.組織結構:
這是一部大型的合唱作品,從音樂的體裁角度也可以作為康塔塔來解釋。按照西方宗教禮儀的模式,傳統的常規彌撒由六個部分組成:慈悲經、榮耀經、信經、圣哉經、羔羊經和會眾散去。而這部作品由八個部分組成:
1.Uvod(Introduction)引子
2.Gospodi pomiluji(Kyrie)慈悲經
3.Slava(Gloria)榮耀經
4.Veruju(Credo)信經
5.Svet(Sanctus)圣哉經
6.Agnece Bozij(Agnus Dei)羔羊經
7.Varhany solo(organ solo)管風琴獨奏
8.Intrada小序曲
作曲家特意在開頭與結尾各加了一個樂章,即引子與小序曲,這也是亞納切克獨特的處理方式。本應出現在開頭的序曲,在曲末進行了狂想式的、急切而又昂揚的樂隊全奏與合唱,意味著斯拉夫民族之魂是永無止境的。開放式的結束,符合作曲家的風格以及斯拉夫特征,狂放、豪爽但又透出絲絲的傷感。這在第七樂章中表現的尤為突出。(正像作曲家說的,作品的另一個含義是為了祈求世界的和平,這對于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亞納切克來講是非常值得理解的,他的捷克——斯拉夫——世界和平的意識證明了他當之無愧的地位。)
2.主題動機
這是一個非常有特點的動機,采用了bE到bB繼續下行五度回到bE,然后上行回到bB音上,緊接著采用同樣的節奏型從bD到bB最后落在bE音上,力量感和動態非常強,其音程含量,第一小節為:二個全音一個半音,第二小節為:一個全音一個半音(譜例1)。
譜例1

這里的三個主干音是bE、bB、bD,它們是整個樂章的核心,在不同的聲部不斷出現,貫穿整個樂章,從這里可以看到瓦格納主導動機的影子。隨后bE混合里底亞調式逐漸明朗。這個動機如果排序成bE、bD、bB,《小交響曲》主題的影子也隱現出來。起始音下行進行,一般兩次,然后反向進行,這也是亞納切克音樂動機最顯著的特點:見下方《小交響曲》主題(譜例2)。
譜例2

三音動機非常明顯也具有東歐音樂的特征,同時,空五度音響與三音動機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音響效果,與五聲音階一樣成為捷克音樂的主要特征,也是作曲家作品中最為突出的一面,如下例。
譜例3

顯然,作曲家用材非常的節儉,簡潔的動機具有很強的爆發力,然而這種爆發也在斯拉夫的憂傷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同時這種簡短的動機也是20世紀作曲家所追求的。而后當合唱進入的時候,斯拉夫的自信與堅定、抒情與優美的旋律中透出無盡的渴求(譜例4)。
譜例4

同樣的處理方式,起始音下行,然后繼續下行再反向上升,保持了動機的音型特征。當這個句子過后,緊接著出現了一個由女高聲部唱出的痛苦焦慮的動機:
譜例5

昔日的經歷難以言表,心中的家園就在不遠的前方,音樂在盤旋中尋覓著……直到信經出現,猶如輕輕呢喃,出現了亞納切克最具特色的“語言的旋律”(speech melody):
譜例6

這是作曲家在民間采風時的發現。捷克語言中某些地區說話的音調具有很強的歌唱性,將其加以改造而創作出獨特的風格。相似的創作手法在20世紀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中也可看到,如奧地利作曲家勛伯格的“念唱音調”(6)作曲家要求演員“必須按指定的音符的音高開始,然后立即轉化成或升或降的說話的音調”(于潤洋.西方音樂通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6:346)。,同時代的俄羅斯作曲家穆索爾斯基在自己的歌劇中采用了散文體式作為歌劇的歌詞進行創作。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音樂建立在本民族的語言甚至是俚語與俗語的基礎上,因此他們的旋律充滿了獨有的民族特性,而不是拘泥于古典與浪漫的傳統形式。“語言的旋律”亦翻譯為“說話的旋律”,即旋律的感覺非常像說話,反之說話也像在唱歌。這種情況世界各地都有,比如山東膠東地區的說話語調就十分具有歌唱性。在下面的譜例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主題動機從bE到bB的四度和五度的跳進。
譜例7

譜例8中,下行強勁的旋律與之前形成強烈的對比,這種上下四度進行在亞納切克的作品中屢屢出現,也是他作品核心音調的主要構成特征,下方四度進行也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例證。
譜例8

G:D、C:G:D的進行也是《小交響曲》主題中的A到E四度進行的翻版。從中可以看出亞納切克的主題動機特征基本上是從小級進逐漸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急切的下行進行,即第一樂節多為級進,沒有非常突出的規律,第二樂節大多下行進行。這在他其他的作品中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這種必然的義無反顧的下行,其強烈的戲劇性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也許是亞納切克的斯拉夫情結中所帶來的吧。
3.和聲的結構特征
亞納切克成長的時期正是20世紀民族樂派發展的階段,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之一,他的創作可以說是在民族的土壤中孕育發揚,同時也追隨了時代的風采。如果說民族特征大多表現在旋律的特征方面,那么和聲則突出的代表了他現代的創作意識。在他的作品中傳統居首位,其次是現代手法的運用,這在他很多的作品如《小交響曲》《格拉戈爾彌撒》中均有所體現。
(1)三度疊置和弦
三度疊置和弦是傳統創作意義中重要的基礎和聲表達,這也是亞納切克音樂作品的基石。這在《格拉戈爾彌撒》中也有突出的表現:
譜例9

在上例中,和弦的結構是建立在FAbC以及bDFbA 上,是由大三度與減三度以及大三度與小三度構成。從結構上看,是一個傳統三度疊置的和弦,也許這就是亞納切克對傳統的致敬。
同時,亞納切克也認為,任何音程關系都可以構成和弦,比如三度疊置的高疊和弦或非三度疊置的其他形式的和弦,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作曲家對音響的理解與感受已經開始走向現代。
(2)高疊和弦的運用
亞納切克既是一個傳統與民族的擁護者,同時也是一個開拓者,他徹底顛覆了西方彌撒曲創作的慣例,用獨特的視角和現代的技巧詮釋了一個20世紀的教徒對上帝愛的理解,即真實的愛中不僅有憐憫,同時也有憤怒和懲罰,似乎神與人的矛盾在這里得到逐漸的升級,高疊和弦的構架所造成的不協和音響的獨特音色正說明了這一點。當然在主題動機再次出現的時候,這種矛盾也得到化解。
在下方譜例中,可以見到亞納切克對高疊和弦運用的手法與特征。
譜例10

上方譜例可以看成省略五音和九音的十三和弦,并且長時值延續著,然后進行到bEGB上的開放排列的增三和弦,具有很強的張力,似乎未來的一切都是在一種不可釋放的情緒中進行,罪惡在無休止的撕扯人的靈魂,沒有光亮的閃現。
4.調式調性
(1)教會調式
在調式的使用上,亞納切克再次顯示了他獨特而杰出的才華。正如他在自己的和聲教學中所貫徹的理念那樣,他一改傳統西歐的調式結構形態,而是按照作品的中心內容來設置人工調式,如在作品的第191小節出現了C、D、E、#F、G、bA、bB的音階,在這里作曲家突出了利底亞增四度的效果,但是在最后的三個音中似乎有些弗里吉亞的特征,兩種調式混合在一起有種別樣的感受,這也正是作曲家的獨到之處。宗教含義在這里不言而喻,由于作曲家獨特的一點改變使其具有了不同的味道。
譜例11

(2)五聲性音階結構:
在作品的第三樂章中,作曲家采用了五聲性音階構架了女高聲部,其結構如下:bE、F、G、bB、C,看起來似中國的bE宮調式,但是由于它獨特的旋律法的構架與中國旋法的不同,因此,聽起來非常的特別,原始并具有力量,似乎在呼喚遠古的斯拉夫民族之魂。
譜例12

結語
在以往對20世紀東歐作曲家的音樂學研究中,我們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巴托克以及俄羅斯的作曲家身上,而對捷克、羅馬尼亞、波蘭和匈牙利等其他東歐國家的作曲家的研究有所欠缺。從對亞納切克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東歐音樂的發生與發展完全可以與西歐的強勢潮流相媲美,這些作曲家們不懼于西歐長期的文化侵襲,而是另辟蹊徑尋找民族之根作為創造的源泉,踏出一條與西歐不一樣的音樂之路,為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創作民族音樂做出了典范,而在這些作曲家當中,亞納切克的功績絕不可小覷。
作為有著深遠宗教歷史背景的歐洲作曲家,在宗教中尋求安慰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歷史總令我們無奈,亞納切克——為捷克民族音樂奮斗一生的杰出作曲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沒有得到捷克音樂界的普遍認可,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作為20世紀民族音樂的優秀代表,他的作品擁有具有民族特色的旋律與現代和弦,不僅從三音動機與空五度的并行以及到五聲音階的運用,其中的心力與含義是非常明顯的,即對斯拉夫民族深刻的理解與表達。他將民族的氣質與神性完美的結合在一起。從西方審美與宗教的角度看,神性一定是世界性的,也不代表任何一個特定的文化現象,因此也具有共性的特質,但是亞納切克卻把這種長期的審美與宗教的觀念解放出來,賦予了宗教音樂民族性的特征,這不得不說作曲家獨特的構思與大氣橫貫的創作理念。由此,他創作的重要核心理念是由民族、宗教與現代技術三部分組成,這是亞納切克的成功所在。可以說他的《格拉戈爾彌撒》是迄今為止最為民族、最為獨特、最為宏偉的作品,稱它為20世紀最著名的彌撒曲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