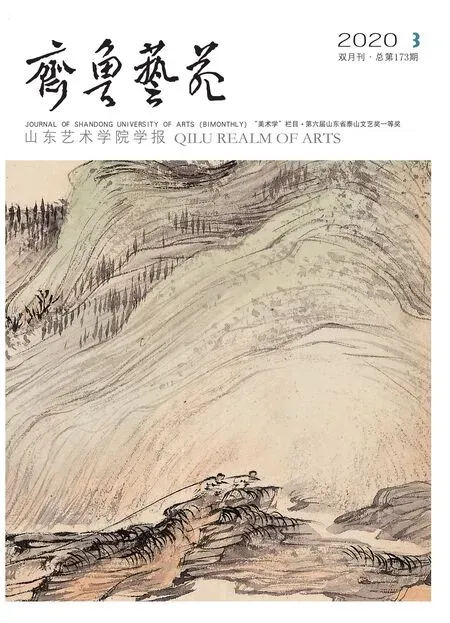建構傳承人口述史的理論模型
——評馮驥才主編《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
毛曉帥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300)
自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來,“非遺”保護已經成為民間研究領域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之一。關于“非遺”保護的學術探討文章更是數以萬計。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甚至成了一門新興的學科。然而,我們不禁要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是什么?到底應該如何保護?是否有規律和方法可循?這些都是需要我們直接面對的問題。馮驥才主編的新著《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為我們系統解答了上述問題。該書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1&ZD064)資助成果,由華文出版社于2016年12月正式出版。
一、《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內容概述
《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一書共五章,分為三個部分。緒論是全書的第一部分,作者在緒論中闡明了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的目的與意義;分析了當前口述史研究的現狀;指出了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的重點與難點。作者認為,“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做口述史,是意義非凡、開天辟地式的工作,它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創造了全新的技術與手段,開創了全新的思路與格局。”[1](P8)
第一至三章是全書的第二部分。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了傳承人口述的特征及傳承人口述史的認識價值。作者認為,傳承人的口述具有文化主體性和原生性、自律性和自為性、多重建構性;傳承人口述史具有重要的身體經驗價值,是民間文化的重要內容。基于口語文化特征,特別是口語思維特征的探討,作者在第二章著重分析了傳承人口述行為機制及記憶的規律。作者認為,記憶具有選擇性,傳承人往往會根據某種需要而重新建構記憶,而口述者對于“意義”的編織機制更值得關注。第三章,作者就傳承人口述史的身體性特征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傳承人口述史是由內化到外化的身體表達,承載了傳承人的生命情感和主體意識。
第四和第五章是全書的第三部分。作者在這一部分主要討論的是傳承人口述史的訪談方法、書寫方法,傳承人口述史檔案的整理與保存等具體可行的操作方法和策略。
總的來說,全書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學術視野開闊。首先,作者不只是就非遺本身而論非遺,而是充分借鑒和參考了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民族學、文學、藝術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跨學科的視角;其次作者還分析和總結了國外的一些口述史研究案例和經驗,可謂是中外結合。二是內容的全面、詳實,本書基本上涵蓋了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各個方面,每個方面的研究與論述都是基于作者對學術史的全面梳理基礎之上,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學術思考。三是本書的開拓性,作者通過詳實的資料建構起了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理論模型,是國內第一本對傳承人規模化的口述史理論研究的專著,為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掀開了新的篇章,為我們今后進行傳承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依據。
二、本書的學術貢獻
回顧學術史,可以發現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幾類:第一類是關于傳承人命名、認定、管理、培訓等相關制度和機制的研究,例如孫正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命名研究》[2]、馮莉《傳承人調查認定看當前“非遺”保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3];第二類是關于非遺傳承人的保護方法、原則、存在問題及相應對策的分析,例如劉魁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的整體性原則》[4]、苑利《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研究》[5];第三類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等概念和學科本身的學理探討和理論建構,例如巴莫曲布嫫《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概念到實踐》[6]、劉錫誠《傳承與傳承人論》[7];第四類是各類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的記錄和書寫,例如馮驥才主編的《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叢書》(1)該叢書是中國民間文化杰出人物認定命名工程成果的集結,由馮驥才、白庚勝主編,目前已出版30余本傳承人調查專著。和《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2)該叢書全套共14本,由天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正式出版發行。。然而,“傳承人的理論研究,是指引傳承人研究及保護走向深入的必由路徑,但我國現行的傳承人理論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8](P83),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傳承人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還缺乏學理上的探討。馮驥才主編的《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一書首次在理論上系統地提出了民間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傳承人問題。筆者認為,《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一書主要的學術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明確了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
當前,我國關于傳承人的定性和定義研究還不夠深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是什么,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傳承人的關系還沒有從學理上闡釋清楚。一些學者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是“文化”(3)例如張紀鋆《非遺,核心價值在“文化”》,《湖南日報》2015年12月14日第002版。,一些學者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是“傳承”(4)例如龔平《傳承:“非遺”保護核心所在》,《蘇州日報》2008年9月3日第A09版;余悅《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十年回顧與理性思考》,《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9期。。無論是“文化”還是“傳承”,其著眼點無疑都是“物”,即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技藝”或者“記憶”本身。而馮驥才先生主編的這本《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則是貫徹了他一貫以來的人文主義精神和以人為本的學術思想,其著眼點在“人”,而不是“技藝”和“記憶”,凸顯了傳承人作為文化持有者和實踐者的主體地位。正如賀學君所說,“必須相信,只有(特定民族社區的)人才是(特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無可替代的能動主體”[9](P106)。通過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分析及對近年來中國非遺保護實踐的經驗總結,作者明確地指出:“傳承人不僅是記憶和技藝的載體,更是傳統文化的見證者和傳播者,是民間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本。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最核心、最關鍵、最要害的就是保護傳承人。為傳承人做口述史和口述史研究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得力、最有效、最有益的工作之一。”[10](P7)對傳承人的理解、了解、觀察和研究,是真正理解、了解、觀察和研究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最好途徑。由此,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傳承人的關系得以闡釋清楚,傳承人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
(二)奠定了以“對話”和“交流”為核心的方法論基石
馮驥才先生是口述史實踐的先行者。早在1986年,作為文學家的馮驥才就利用口述史的方法,做了100個人“文革”十年的口述實錄,出版了《一百個人的十年》一書,引起了文學界、史學界的廣泛關注。這也是后來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思想來源和學術起源。后來,馮先生又先后主持了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調查和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調查,出版了《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叢書》和《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在這些寶貴的口述史實踐的基礎上,作者積極借鑒了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經驗,結合當下的非遺保護實踐,奠定了以“對話”為核心的方法論基石。首先,研究者在對傳承人進行口述史訪談時,是一種平等的對話、交流關系。以往,學者們討論非遺傳承人時往往是高高在上地談原則、方法,或者就概念、理論本身來分析,他們大多沒有親自到田野中去,與傳承人進行平等地互動與交流。我們從馮先生的實踐和總結中可以發現,只有深入田野,與傳承人進行平等的交流和對話,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的生活。其次,傳承人與其所在的社區、生活世界之間也是一種對話的關系。再次,傳承人與民間文化、歷史文化之間也是對話的關系。以“對話”為核心的方法論的確立,“有助于傳承人樹立自我的主體意識,有助于文化傳統的存錄,更有助于文化傳承機制的良性運轉”[11](P177)。
(三)建構了傳承人口述史的理論模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操作方法
作者在對國內外口述史研究案例和經驗的充分總結、分析的基礎上,結合近年來中國非遺保護的實踐,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傳承人口述史理論模型,為“傳承人口述史”這一嶄新的學術概念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支撐,把傳承人口述史提升到了學科分支的地位。在《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一書中,作者還就傳承人口述與記憶的規律和機制進行了總結。遵循了這些規律,了解了這些機制之后,我們才能把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好地傳承下去。此外,作者還就口述史的訪談方法、書寫技術和手段、資料的留存和檔案整理方式等內容做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并列舉了多個例證,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為今后的傳承人口述史研究,乃至更廣泛的口述史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法和依據。
三、反思:走向更加廣泛的日常交流實踐
除了上述學術貢獻之外,筆者認為本書在民俗學研究方面也帶給我們許多啟發。首先,民俗學是一門與“人”打交道的學問,其核心在“人”。無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還是普通的山野鄉民,我們只有與他們建立起平等交流、對話的關系,深入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才能真正了解其所擁有的民間文化。正如劉鐵梁教授所說,“對于民間文化進行研究也好,進行保護也好,最根本的途徑就是要與作為文化傳承者的個人和群體進行面對面的對話與交流。”[12]而口述史是我們了解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徑。
其次,關注普通民眾的日常交流實踐,應是今后民俗學的出路所在。就民俗學研究來說,掌握某種技藝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或者會講述某種民間文學文類的故事家、歌手畢竟是極少數。我們需要面對的更多的是分布在各個社區、村落中默默無聞的普通民眾。以我自己近年來在北京市各區縣進行的民俗志田野調查經歷來看,我們在田野作業過程中遇到最多的其實是訪談對象關于自己的經歷的敘事,或者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個人生活史。每個人都有權利、有意愿講述自己的個人故事。這種個人故事其實是他們最重要的交流實踐方式,關系到地方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建構,關系到他們地方感的獲得,關系到地方社會的歷史和集體記憶。這些生動的個人故事也是我們理解民眾生活方式、地方社會運轉的重要依據。因此,我們有必要擴展民俗學的研究范圍,關注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個人敘事與交流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