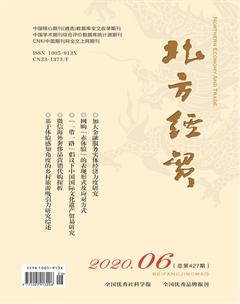上市公司漂綠行為市場反應研究
陳暉麗 郭嘉梅


摘要:漂綠與綠色發展互為對立面,已成為綠色發展一大阻礙,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漂綠事件的研究對推動企業、社會和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與建立良好的市場秩序至關重要。本文以2017年《南方周末》公布的中國漂綠榜的上榜公司華北制藥作為案例分析對象,運用事件研究法對其兩次漂綠事件進行分析,旨在探究環保處罰日資本市場對漂綠事件的反應,并分析造成差異的因素。研究發現,資本市場對兩次事件體現出不同的懲戒效果,漂綠程度越嚴重,政府處罰力度越大,市場反應越顯著越持久。本文的研究不僅豐富了漂綠行為市場反應的相關理論,而且對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完善市場體系提供一定的政策借鑒。
關鍵詞:漂綠行為;市場反應;華北制藥;環保處罰
中圖分類號:F830?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20)06-0137-03
一、引言
人類利用自然資源使資本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卻常常忽略了大自然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綠色發展理念的提倡,我國對環境保護越來越重視。2014年4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將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201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明確“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為納稅人。可見,綠色發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然而,一些企業仍然為了經濟利益以身試法。從2015年中國石油(股票代碼:601857)蘭州石化環境污染事件,到2019年6月鼎龍股份(股票代碼:300054)武漢工廠因私設暗管外排污泥等環保違法事件,這些上市公司不斷刷新著人們的視線。他們無不標榜著綠色企業形象,宣稱會履行好企業社會責任,卻屢屢被曝光。這種虛假的企業社會責任現象被稱之為“漂綠”。
“漂綠”一詞是“綠色”(green)和“漂白”(whitewash)兩個詞的混合體,是企業虛假環保宣傳以及粉飾行為的代名詞。“漂綠”在1986年由美國環保主義者Jay Westerld提出,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綠色營銷運動。Ramus and Montiel(2005)[1]認為,“漂綠”意味著公司偏離了對積極環境政策的承諾,即企業承諾會履行環保政策,卻被發現存在環保違法行為。2009年《南方周末》發布的“中國漂綠榜”正式將“漂綠”概念引入中國公眾視野。
企業既然表示自己是綠色環保企業,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企業進行漂綠?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表明,漂綠的動機主要是信息不對稱、政府處罰與監督機制。Kollman and Prakash(2001)[2]研究發現,綠色產品市場是典型的信息不對稱市場,企業表示自愿遵守環境政策,但既不設定實質性目標,也不具體說明最終結果,導致公眾對企業是否真正執行社會責任是不可知的。黃中偉(2004)[3]在分析漂綠行為時建立了企業和消費者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認為企業選擇漂綠和選擇真綠的利潤差額越小,政府的罰款越重,漂綠的企業也就越少。楊波(2012)[4]建立了企業綠色過程模型,對企業走向綠色過程中的八種狀態進行了靜態和動態分析,發現實施能力不足、實施動力不足都可能引發漂綠。李克和王剛清(2016)[5]利用舞弊三角理論對可口可樂公司進行案例分析,發現采取漂綠行為不僅代價較低,而且能享受到綠色產品帶來的邊際效益,從而有更多資金可以維持其霸主地位。
現有文獻表明,漂綠現象已受到國內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但較少研究關注漂綠行為曝光的市場反應。因《南方周末》頒布的“中國漂綠榜”已有8年歷史,上榜的上市公司有76家,備選企業39家,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度高等優點使其具有較高參考價值。而制藥行業一直是我國綠色防治重點對象,華北制藥又是我國的醫藥龍頭企業,故本文將選取《南方周末》中國漂綠榜的上榜企業——華北制藥集團為案例分析對象,通過事件研究法探討華北制藥先后兩件漂綠事件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造成其差異的原因,以了解資本市場對同一企業漂綠事件顯著性及持久性原因并提出相關建議。本文的研究不僅能補充漂綠行為市場反應方面的相關理論,還有利于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完善市場體系,可以加深對漂綠行為的認識和理解。
二、漂綠事件描述
華北制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國最大的制藥企業之一,公司的前身華北制藥廠是中國“一五”計劃期間的重點建設項目。1992年重組設立華北制藥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在上交所掛牌上市(華北制藥,600812)。2003年國家環保總局(即現在的環保部)制藥廢水污染控制工程技術中心中試基地在此掛牌。2015年被評為河北首家環境管理自律體系建設試點單位。華北制藥曾表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型國企,在省政府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有信心有能力在打造綠色工廠方面積極作為,努力做行業的排頭兵。然而華北制藥集團卻屢次因環保問題被立案處罰。
2016年1月華北制藥被當地群眾反映污染問題嚴重,投訴至中央環保督察組。2016年1月29日至31日,河北省環保廳、省公安廳組織13名執法人員與3名制藥行業專家成立聯合調查組,對華北制藥集團10家企業進行了現場調查。聯合調查組針對華北制藥集團部分企業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設施、固體廢物未按要求進行處置、污水超標排放、部分工藝尾氣無組織排放影響周邊環境等行為,下達了《關于限期整改環境違法違規問題的通知》。華北制藥集團兩家公司被立案處罰,三家公司涉嫌環境違法犯罪問題移交公安部門處理。2016年6月3日河北華藥環境保護研究所(一車間)被罰款189.9658萬元。2016年6月6日華北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制藥總廠)被罰款30萬元。
2017年11月7日河北省環保廳廳長到制藥總廠現場檢查時,發現廠區104車間生產過程中密閉不嚴、VOCs和異味治理措施不到位、搬遷進展較慢等問題。華北制藥的行為被判定為違反《大氣污染防治法》,隨即進入立案處罰程序。2018年5月10日河北省環保廳出具行政處罰決定書,罰款20萬元。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中國股票市場交易數據庫、東方財富網、《南方周末》、河北省環保廳網站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二)事件研究窗口選擇
本文案例分析方法為事件研究法。具體的,將環保處罰公示日定義為事件發生日(t = 0)。若事件發生日為非交易日,則順延至下一個交易日。
2016年6月3日和2016年6月6日都是第一次事件的環保處罰日,剔除節假日和停牌日后兩個交易日相鄰,故將2016年6月3日定義為事件日(t = 0),事件窗口期為(-4,10)共15天,估計窗口期為(-185,-6)共180天。第二次事件環保處罰日為2018年5月10日,定義為事件日(t=0),事件窗和估計窗同第一次事件。
(三)回歸模型
在事件研究法中,本文采用市場模型對企業的正常回報率進行估算:
Rt=α+βRmt+ε? ? ? ? ? ? ? ? ? ? ? ? ? ? ? ? ? ? ?(1)
其中,Rt為股票在第t日的實際報酬率,Rmt則為股票在第t日的市場報酬率,α和β為回歸系數,而ε為隨機誤差項。運用最小二乘估計法對數據進行回歸,可得到回歸系數α和β的值。再根據得到的α和β值估算出股票在事件窗口內的預期收益率E(Rt)。然后計算出股票在事件窗里的超額收益率(AR)和累計超額收益率(CAR):
AR=Rt- E(Rt)? ? ? ? ? ? ? ? ? ? ? ? ? ?? ? ?(2)
CAR=∑AR? ? ? ? ? ? ? ? ? ? ? ? ? ? ? ? ?? ? (3)
最后,在得出累計超額收益率CAR后,對CAR進行單樣本t檢驗,檢驗其與總體均值的差異是否顯著。
四、市場反應與差異分析
(一)第一次事件
在事件日之前,CAR值已有較大幅度下降。華北制藥在2016年5月28日發布關于公司獲得《藥品GMP證書》的公告,這一利好信息并沒有使CAR值上升,反而下降,說明市場可能出現了提前反應。6月3日和6月6日,河北省環保廳公示了對華藥環境保護研究所有限公司和制藥總廠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之后CAR值連續幾天大幅度下降(見圖1)。可見漂綠事件曝光對股價有較大的負面影響。
(二)第二次事件
在事件日前CAR值的大幅下降,可能受2018年5月7日華北制藥原董事長王社平涉嫌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唐山市人民檢察院向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這一事件的影響,也可能是市場出現提前反應。在河北環保廳公示對華北制藥的行政處罰書后第二個交易日,CAR值呈現出先下降,之后開始波動回升的趨勢(見圖2)。說明市場對此次漂綠事件是有懲戒效應的。
(三)CAR值檢驗
對CAR值進行單樣本T檢驗,兩次事件的CAR值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
(四)兩次事件的差異分析
上述分析可知,資本市場對華北制藥兩次漂綠事件均有懲戒,但是反應程度有所差異。第一次事件CAR值整體小于0,在事件日有大幅度下降且持續時間長,之后便呈波動下降趨勢。第二次事件CAR值整體大于0,事件日市場反應快速但只持續一天,之后呈波動上升趨勢。可見,第二次事件較第一次事件市場反應不顯著且持續下降趨勢維持較短。
造成上述差異的原因主要是,漂綠事件的嚴重程度不同。第一次事件情節嚴重,多家公司參與漂綠,漂綠程度高且罰款多;第二次事件只有華北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被查出有環保違法行為,情節相對弱,漂綠程度低,政府罰款少。因此,漂綠事件越嚴重,政府處罰力度越大,市場負面反應就越大且越持久。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運用事件研究法,探究華北制藥兩次漂綠行為處罰公示日的市場反應,發現資本市場對這兩次漂綠事件均做出了具有懲戒效應的反應,但是反應程度有所差異,漂綠程度越高,市場反應越顯著越持久。因此,上市公司應投入更多的環保資金,加快設備革新和技術轉型升級,從源頭上減少生產經營過程中污染物的排放。在日趨加強的環保監管力度下,從長遠角度考慮,選擇環保不僅成本效益最高,還能樹立起良好的企業形象并得到消費者信任,為我國的環保事業貢獻一份力量。
參考文獻:
[1] Ramus C A, Montiel I. When? ar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 form of greenwashing?[J]. Business & Society, 2005, 44 (4):377-414.
[2] Kollman K, Prakash A. Green by choice?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in firms' responses to EMS-based environmental regimes[J].World Politics, 2001,53(3):399-430.
[3] 黃中偉.對我國企業實施綠色營銷的思考[J]. 管理觀察,2004(4):36-38.
[4] 楊 波.環境承諾為什么演變為漂綠:基于企業綠色過程模型的解釋[J].管理現代化,2012(4): 37-41.
[5] 李 克,王清剛.基于舞弊三角理論的企業漂綠行為分析及治理──以可口可樂公司為例[J].財會通訊,2016(19):9-12.
[責任編輯:龐 林]
收稿日期: 2020-03-06
作者簡介:陳暉麗 (通信作者)(1985- ),女,廣東潮州人,博士,研究方向:資本市場、公司治理與會計信息;郭嘉梅(1996- ),女,廣東湛江人,本科學生,研究方向:資本市場與會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