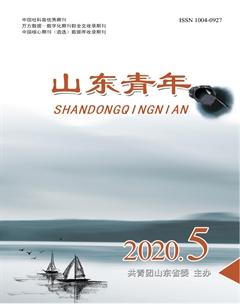斐多篇中靈魂與肉體的關系
歐星洋
摘要:
柏拉圖的斐多篇是較早提到靈魂與肉體的關系的哲學文本,鑒于這個主題在后來的哲學史中討論較多,作者認為厘清柏拉圖哲學文本中的靈魂與肉體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哲學史上相關哲學討論的意義所在。本文中,作者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1)斐多篇中有關靈魂與肉體的論述,柏拉圖對于這兩個概念的具體主張是什么,以及它們是否清晰。(2)有關靈魂與肉體關系的論述,柏拉圖在這個問題上是否給出了成功的論證。(3)柏拉圖關于靈魂不朽的論證,柏拉圖對于靈肉關系的探討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靈魂不朽的論證,以及靈魂不朽的論證是否是有效的。關鍵詞:斐多篇;靈肉關系;靈魂;肉體
一、斐多篇中關于靈魂不朽的論證
蘇格拉底在斐多篇中提出了幾個關于靈魂不朽的論證,要論證靈魂不朽,需要證明兩個前提。
(1) 靈魂在出生前一直存在著。
(2) 靈魂在死后也一直存在。
加入靈肉關系的表述后,可以改寫為:
(1) 靈魂在進入肉體前是存在的。
(2) 靈魂在離開肉體后依然存在。
斐多篇中的幾個靈魂不朽的論證都圍繞這兩個命題進行。
從70d開始是蘇格拉底的所謂“循環論證(cyclical argument)”。在此前的69e中,西庇斯指出了蘇格拉底關于“死亡對于哲學家而言是幸事”的論證中存在的問題,那就是蘇格拉底并沒有提供足夠的理由說明為什么靈魂在死后依然存在,并擁有著一定的力量和智慧,按照許多人的觀點,靈魂在離開人身體后就“如同煙霧,一陣風就把它驅散了”。何以保證它不會這樣呢?蘇格拉底的論證如下。
他首先說明了“對立面”的概念。一對對立面中的兩者總是互相轉化,例如某物之所以是大的,是因為它原先較小,反之亦如此。在這里,“對立面”指的是一對相對的事物的屬性。而柏拉圖的看法是,對立面其中的一個屬性一定是由另一個屬性而來的。
以“生”與“死”也是這樣一對對立面為前提。可以得出結論,“生”這個屬性來自“死”這個屬性,而“死”這個屬性來自“生”這個屬性。也就是說:目前具有“死”屬性的事物,原先是具備“生”屬性的。目前具有“生”屬性的事物,原先具備了“死”屬性
如何理解這兩個結論呢?以人為例,人身上的“生”屬性來自于“死”屬性,也就是說,活人先前是死人。死人先前是活人很好理解,但如果活人先前是死人作為同等的結論一起得出的話,可以借由此說明靈魂轉世說的正確性。如果人死后靈魂就消失的話,那么靈魂轉世也將不可能。又由剛才的證明,我們知道靈魂轉世是可能的,因此人死后靈魂不會消失。
這個論證至少有三個問題。
第一,對立面的概念并不清楚。仔細觀察蘇格拉底關于對立面概念的描述就可以發現,蘇格拉底關于對立面相互轉化的說法完全建立在這樣一個命題上:
命題P:某物x之所以具有屬性p,是因為該屬性由p的對立面q變化而來。
蘇格拉底關于對立面的定義似乎是這樣:
定義O:不同時地出現在同一個實體上的兩個相反屬性稱為一對對立面。
某物x之所以是小的,是因為x原先是大的。但問題是,情況不一定是這樣。在更多的情況中,x之所以是小的,是因為與它相對比的y是大的。也就是說,一對對立面不一定出現在同一個實體上,它們更可能分別出現在兩個不同的實體上。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蘇格拉底“那有對立面的一定是由它的對立面轉化而來”到底是什么意思。以這兩種情況為例。
1. 某物x之所以是小的,是因為x原先是大的。
2. 某物x之所以是小的,是因為y是大的。
當談到變化時,有兩個因素是必要的,它們分別是同一性和時間。同一物體在不同時間中的狀態相差別,這個時候我們才說它的狀態發生了變化。不同的物體在不同時間中的狀態相差別,這個時候我們并不認為物體的狀態發生了變化。在第二種情況中,某物x的屬性并沒有出現變化,它之所以是小的,不是因為它的“小”屬性是由“大”屬性變化而來,因此蘇格拉底關于對立面一定相互轉化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第二,“生”與“死”這兩個屬性是不是對立面?我們注意到,小與大是互為否定的關系,是兩個相反屬性。但是,生與死是互為否定的嗎?如果死的否定一定是生,生的否定一定是死,那么生與死才是互為否定的。然而我們知道,有些事物是既不能算作生也不能算作死的,例如一塊石頭,既不能說是活著的也不能說是死的。100年后的美國總統,也無法說是活著的還是死的,因為他還沒有出生。因此說生與死互為對立面是有問題的。“生”的對立面應該是“非生”,而“死”的對立面應該是“非死”。
第三,同一性問題。依照柏拉圖的說法,當個體處在靈魂與肉體相結合的狀態時,就認為它具有生屬性。但問題是,這樣的定義方法不適用于死屬性。當靈魂與肉體分離也就是個體死亡之后,就無法確定維持個體的同一性的標準是什么了,一旦無法確定同一性,那么死亡之后個體將不復存在。按照斐多篇中的思想,肉體是有朽的,靈魂是不朽的。如果以肉體作為同一性的標準,那么死亡之后個體也將不復存在。實際上,在關于對立面的說法中,是存在一個默認前提的,那就是死亡之后個體依然存在,否則依照定義O,這時候將不存在對立面,也就談不上生與死兩種屬性的相互轉化了。
因此,靈魂被視為維持同一性的標準。然而問題在于,任何關于靈魂的同一性的判斷都是缺乏依據的。我怎么知道從死屬性轉變為生屬性的這個靈魂,與之前某個經歷了死亡的靈魂是同一個呢?或者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個在出生前剛剛產生的靈魂,這樣一來盡管我們可以說后來靈魂經歷了從“死”到“生”的過程,但卻不能說它是“前世”的某個靈魂。
蘇格拉底似乎意識到他的論證是不充分的,因此他還有進一步的說法。他認為在任一對對立面之間,存在兩種變化過程,分別是由其中一個對立面到另一個對立面的變化。例如從小到大是一個,從大到小是另一個過程。他的具體論證過程是這樣的:
前提1:對任何一對對立面a與b來說,只要存在從對立面a到對立面b的變化過程,那么從對立面b到對立面a的變化過程也必然存在。
前提2:從對立面“生”到對立面“死”的過程是確實存在的。
結論:從對立面“死”到對立面“生”的過程必然存在。
這個論證看上去的確比第一個更有說服力,但有著同樣的問題,因為“生”與“死”究竟是不是一對對立面是有問題的,所以前提2是有問題的。另外,前提1是建立在經驗觀察上的公理,但是這個公理并不是自明的。我們觀察到人的自然衰老過程,但是從未觀察到返老還童的現象,因此前提1也是有問題的。
從72e開始是蘇格拉底的另一個關于靈魂不朽的論證,被稱為回憶論證(Recollection Argument)。論證的主要目的是證明靈魂在出生前是存在著的。結合在美諾篇中提到的論證,蘇格拉底認為人類的知識有一部分是后天無法學到,是只能通過回憶想起來的,在出生前就學到的知識。因此,靈魂必須在出生前就已經存在,否則無法解釋我們如何在出生前擁有知識。
蘇格拉底首先提出論點:學習就是回憶。為了闡明他的主張,他先解釋了什么是回憶。他認為回憶是當一個人通過看與聽等直接知覺接受到的知識,使得他想到了另外的不一樣的知識。回憶是一種知識的聯想作用,這種聯想不但發生在相似的事物之間,也可以發生在不相似的事物之間。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間接的獲取知識的方法。
在解釋清楚回憶之后,蘇格拉底開始區分“相同”與“相同的事物”,例如相同的石子。這兩者有著明顯的差別,后者是我們能夠直接知覺到的,而前者不是。但是我們的確擁有關于前者的知識,如果這些知識不是來自于出生后的直接知覺,那么它們一定在出生前就已經存在了。而我們之所以能掌握它們,是通過回憶的方法。首先我們知覺到“相同的事物”,因為相對起“相同的事物”“相同”是更加完整的存在,兩者之間存在關系,所以我們能由其中一方聯想到另一方。通過這種方法我們掌握了關于“相同”的知識。
既然知識在出生前就已經存在,我們的靈魂必定在出生前就已經掌握了它們,而如果靈魂在出生前不存在的話,上述說法就不可能成立,因此靈魂必定在出生前就已經存在。
蘇格拉底關于靈魂不朽的回憶論證十分復雜,柏拉圖在這部分中的許多用語比較模糊,但是要大致地理清楚論證的線索還是可以的。簡單地說,蘇格拉底的論證可以分為兩步。
(1) 如果我們的一些知識只能通過回憶得到,那么這些知識必定在出生前就具備了。
(2) 如果我們在出生前就具有知識,那么我們的靈魂必定在出生前就已經存在。
論證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一些知識在出生前就已經具備”,蘇格拉底提出了幾個理由來支持這個命題。這幾個理由都與柏拉圖的理念論有關。
1. 我們確實擁有著一些知識,它們無法為感官知覺所獲得,只能通過“回憶”獲得。在接觸到“相同的事物”時,我們察覺到它們是在模仿某種更為完善的實體,盡管它們與那種更為完善的實體之間是模仿與被模仿的關系,但前者畢竟是殘缺的,因此與后者有著區別。這些知識并非來自感官知覺,但卻為我們所有,唯一合理的解釋似乎是我們在出生前學到了這些知識,在出生后的某個機緣下回憶起了這些知識。
2. 出生前已經具備了的知識使我們能夠獲得相關的知識。如果不是已經具備了關于“相同”的知識,我們就不可能獲得關于“相同的事物”的知識。關于“相同”的知識是關于完善的實體的知識,正因為我們事先具備了這種知識,我們才能判別出那些缺陷的實體即“相同的事物”,關于它們我們才能有相應的知識。
關于第一個理由:柏拉圖在試圖論證靈魂不朽時,借用了他的理念論,這樣一來使得論證更具有說服力,但同時也把理念論中固有的問題帶到了論證中。他似乎認為,關于更完整的實體也就是理念的知識,無法來自于感官知覺,這一點似乎是正確的。關于“相同”這個理念的知識是一種通過反省得到的知識,我們沒有辦法直接感知到“相同”。但這就意味著關于“相同”的知識是來自生前的知識嗎?按照柏拉圖的說法,我們關于“惡魔”“丑”“惡”這些有著缺陷的東西的知識應該也是來自于生前的,因為這些東西我們都沒辦法感知到。因為在論證中加入了理念論,反而使論證本身變得可疑。
關于回憶本身,在文本中,蘇格拉底本人也承認回憶并不是一個特殊的用法。如果說回憶被用于獲取被遺忘掉的知識,那么這就不等于說回憶只能用于獲取生前的知識。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回憶起的知識充其量是關于比較久的事情。如果這種用法是為柏拉圖所承認的話,那么那些只能通過回憶得到的知識也未必就是生前的知識。
另一個問題是,柏拉圖如何確認他關于理念的知識是真的,而不是幻覺?比如說“關于理念的知識是生前得來的”這一知識,蘇格拉底在文中的說法似乎是直覺到的,而這種直覺反過來加強了他對這一知識是真的的信念。但是一種關于某知識的直覺能夠說明這種知識是來自于生前的嗎?鑒于蘇格拉底的神秘信仰,我們完全可以說這種直覺是來自于神的指示,是當下的全新知識,也就是說“關于理念的知識是來自于神的指示”同樣可以是一個直覺知識。直覺知識不一定是真的,“關于理念的知識是當下直覺到的”是真的知識,而“關于理念的知識是生前得來的”則很難說是。
關于第二個理由:第二個理由讓人想到美諾篇中的美諾悖論,如果不事先具有知識,則無法尋求知識。在美諾篇中,蘇格拉底借這一悖論說明靈魂回憶說。在這里,蘇格拉底采取了同樣的思路進行論證。但是,如果不借助先天知識就可以解釋美諾悖論的話,基于這個理由的論證就不再是可靠的了。
依據洛克的觀點,人心在剛降生的時候是一張白紙,不存在先天知識。但是不存在先天知識,我們就無法獲取知識了嗎?似乎不是這樣的,我們憑直覺知道,知識的獲取關乎的不應該是知識,而應該是獲取知識的能力,也就是認知能力。而關于認知能力,洛克并不反對它的先天性。
如果我們的假設是正確的,同知識的獲取過程相關的,并不是知識本身,而是認知能力。那么人類完全可以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學習。
討論過步驟(1)后,我們再來看看步驟(2)。
條件句(2)的問題相對來說更加明顯。知識是先天的,并不等于說,靈魂在生前存在。可以看到,前者是一個知識論命題,而后者是關于本體論的命題。當然,蘇格拉底為了使得論證更為合理,假設了靈魂具有獲取知識的能力,但在本體論的意義上,這樣的屬性對靈魂而言是不必要的。
事實上,當今世界上仍有很多人主張先天知識是存在的,但卻并非都是靈魂論者。我甚至可以假設在我出生之際,有人向我的腦中植入了某種記憶,我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先天的知識,而這其中并沒有靈魂的參與。
現在,讓我們假設先天知識是存在的,我能夠提供兩種解釋,來說明條件句(2)中的疑點。
1.進化論的解釋,我們可以想象,動物并不具備如同人類般的高級知識,而對于單細胞生物來講,則很難說它們是具有知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隨著進化等級的遞增,物種的知識能力也在遞增。當遞增到人類這一進化等級時,物種誕生了“具備先天知識”的知識能力。
2.“場”的解釋,我們可以想象有一個存儲知識的“場”,這個“場”中的知識存儲隨著人類歷史的增長而增長。在嬰兒剛出生的時候,會受到這個“知識場”的影響,而獲得先天性的知識。
以上兩個解釋雖然還很粗糙,但足以證明,(2)并不一定是正確的。關于(2)的有效性,柏拉圖并沒有提供充分的證明。
二、結論
本文主要對斐多篇中的兩個主要論證進行了梳理。我們發現,在論證靈魂不朽的時候,靈魂本身的性質對如何推進論證起到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說,柏拉圖在整個斐多篇中,側重于探討靈魂的本質。其中,靈魂與肉體的關系作為靈魂本質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柏拉圖重點探討的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靈魂不朽很大程度上是靈肉關系的意義上說的。基于蘇格拉底關于死亡的定義:死亡是靈魂與肉體的分離,靈魂是會死的亦或是不會死的,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一個靈魂與肉體關系的問題。只是在論證的過程中,蘇格拉底較偏重于討論靈魂,而有意或無意地忽略肉體的討論。關于肉體我們能知道的,無非是肉體是有朽的,是被動的,失去靈魂是無生命的,一些沒怎么經過論證的性質而已。由于這種有意或無意的偏重,使得斐多篇看上去更像是靈魂本質的深入探討,而它對靈肉關系的探討則是淺嘗輒止,又或者只是為了進一步探討靈魂本質而做的必要準備。在涉及到肉體時,蘇格拉底常常只能給出一些粗糙的結論,無法支撐起他關于靈肉關系的任何觀點。
本論文出于篇幅所限,沒能詳盡地討論蘇格拉底關于靈魂不朽的幾個論證。蘇格拉底采取的論證,使用的概念,都十分復雜,以至于要仔細討論每一個論證都足夠寫成一篇論文。不足之處,以及有遺漏的地方,希望今后能夠補正。
[參考文獻]
[1]丁紀. 柏拉圖《斐多篇》論靈魂不朽[J].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 (4).
[2]賴竹燕. 柏拉圖《斐多》中的信念、肉體、靈魂[J]. 九江學院學報, 2007, (5).
[3]齊晶. 從靈魂不朽到拒斥死亡——柏拉圖對話錄《斐多》篇[J]. 社會科學家, 2005, (1).
[4]宋繼杰. 柏拉圖《斐多篇》中的“跟有”與“跟名”[J]. 世界哲學, 2012, (6).
[5]衛春梅.柏拉圖《斐多篇》中的哲學咨詢[J].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2, (4).
[6]張文舉. 柏拉圖《斐多篇》的論證及其啟示[J]. 北京社會科學, 2000, (2).
[7]張文舉. 《斐多篇》的邏輯結構及主題分析[J]. 甘肅高師學報, 2000, (6).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