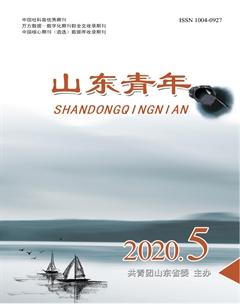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比較研究
王文君

摘要:
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與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都是在可能無法履行的合同屆滿之前,賦予其中一方采取措施避免進一步損害的權利。但由于產生背景、立法觀念上的差異,兩項制度在概念、性質、適用情形、責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很多不同,將兩者進行對比研究并加以區分實屬必要。此外,我國《合同法》同時采納了這兩項規范,導致兩者的適用存在一定沖突。綜合學術界的各項觀點,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兩項制度應當并行規范,并明晰其適用范圍,才能更好地保障締約雙方的利益。這也需要未來的立法進一步解決。
關鍵詞:預期違約;不安抗辯權
一、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的聯系
我國《合同法》第68、69條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又在第108條規定了預期違約制度。必須承認的是,這兩項制度作為調整履約期限未屆滿的情況下,締約一方無法履約的手段,確有一定的相似性。兩者的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上:
(一)立法目的相似
兩種制度中,無論是不安抗辯權“合同一方當事人可能不履行合同”、抑或預期違約“合同一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期屆滿前拒絕履行”,只要債權人有明確合理的理由,且履行了通知義務,在對方沒有提供適當擔保的情形下,債權人都有權終止自己的履行。兩種制度都是對合同預期不履行的救濟制度,是為了提前保障合同中債權人的利益,使其在對方高度可能無法履行義務的情形下免于履行合同而受到損失。同時,兩制度的時間都規定在合同履行期限屆滿之前,有“防患于未然”的意味,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減少司法機關負擔的作用。
(二)制度價值類似
《合同法》的規范價值在于調節合同關系,在不干預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保障市場交易安全與社會公共利益。因此,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均秉持公平公正原則;在其中一方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賦予其采取一定措施保障自己財產的權利,是社會一般交易習慣的體現;同時,兩制度都起到了及時使債權人從已無法實際履行的合同中脫身的作用,有利于市場秩序的保護。①
(三)兩種制度的功能存在一定的重疊與交叉
不安抗辯權和預期違約制度雖然規定的內容存在差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合同當事人在履約期限屆滿之前,采取一定措施防止自己財產受損的權利,保障了市場交易的安定性。同時,兩項制度也都允許當事人先憑借自己的力量采取救濟措施,達到了節約司法成本和訴訟經濟的目的。
二、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的差異
(一)含義和性質均不同
1.不安抗辯權的含義與性質
對于不安抗辯權的定義,我國很多學者都已經做出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其中,王利明教授認為:“不安抗辯權主要針對相對人請求權,屬異議權。其法律效力是行使有關權利以消滅或延緩對方主張。”②而李永軍教授認為,不安抗辯權指當事人形成約定后,若對方明顯存在履約困難的危險,在對方未恢復履行履約能力或提供擔保前,相對人可拒絕支付。③綜合上述兩項主流觀點,我們可以看出,現今學界對于不安抗辯權的定義并沒有本質區別:一般而言,不安抗辯權指的是履約過程中,后履行義務的一方可能喪失履約能力時,應先履行義務的另一方可借此主張不履行合同義務的一種抗辯事由。
顧名思義,在性質上,大部分學者認為不安抗辯權屬于抗辯請求權,筆者也同意此種觀點。臺灣學者鄭玉波“抗辯權乃抗衡請求權也”,直接揭示了不安抗辯權是一種對抗合同相對人履約要求的請求權的本質。
同時,抗辯權是法律在特定情況下賦予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抗辯事由,因此這種抗辯權又是相對臨時的權利。我國《合同法》第68條采用列舉法,規定了締約人適用不安抗辯權的四種情形。當這些情況消失時,不安抗辯權也會隨之消滅,相對人得繼續要求履約。比如,崔建遠等學者就論述:“履行雙務合同時,不安抗辯權表現的法律效力屬于一時抗辯權,對方的債權并不實質滅失。相對人若支付對價或足額擔保,抗辯權人就應恢復履行。”④因此,不安抗辯權在性質上是一種一時的、可隨時消滅的抗辯請求權。
2.預期違約制度的含義與其性質
一般論文似乎很少直接表述預期違約制度的定義,而常常用分類法對其界定。⑤學術界主要采取兩種方法定義預期違約,第一種是將預期違約分為明示違約和默示違約,將違約行為分為(1)債務人期前明確拒絕履行;與(2)債務人以客觀行為表示自己將不能按時履約。此學說的支持者包括英國的特里特爾⑥、我國學者王利明⑦等。另一種定義方式是將預期違約分為預期拒絕履行和預期履行不能,其劃分標準在于債務人是主觀不愿履行還是客觀無法履行。此觀點支持者包括周黎明⑧等。但根據《合同法》第108條,我國《合同法》對預期違約的定義劃分偏向于明示和默示違約;事實上,我國學者也一般都選擇此種劃分方式。⑨因此,筆者認為第一種分類方式能更準確地表述預期違約責任的產生情形。
綜上所述,從含義上看,不安抗辯權指的是在后履行合同一方有可能出現不履行義務的情況、且經通知無法提供擔保時,可以不履行義務以保障自身權益的抗辯權,在性質上屬于一種抗辯請求權;而對于預期違約,我國學界普遍從行為方面進行界定,是債務人明示或默示自己不會履約的情形下,債權人享有主張違約責任的權利,性質上屬于一種違約責任形式⑩。二者在概念和性質方面都存在明顯區別。
(二)適用范圍不同
在適用范圍方面,第一,兩制度適用的前提條件不同。根據《合同法》,不安抗辯權要求締約雙方的義務具有履行的先后關系。只有依約需要先履行的一方才有權提出不安抗辯權;但預期違約制度則不要求存在先后順序,只要一方可能不能履約,另一方就能主張預期違約。第二,兩制度適用的情形也不同。不安抗辯權將適用范圍限定在債務人不能履行義務的客觀事實,不包括對方直接表示自己不再履約的情況,這對保障締約人的利益來說顯然是不利的。而預期違約在我國《合同法》規范下,適用情形不僅包括“因為履約義務人的某些表現而對其是否能夠履行義務產生合理懷疑”,也包括對方明確表示自己不會履行義務。因此,預期違約適用范圍要大于不安抗辯權。
但必須明確的是,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默示預期違約和不安抗辯權適用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存在重合。因此,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的規范是否應該在我國適用、應該擇一規范還是兩者并行,法學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大致分為三種學說。
第一派學者主張刪除合同法中的預期違約規范,認為現行合同法的三種抗辯權已足以保障當事人利益,吸收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有畫蛇添足之嫌。B11在我國現行《合同法》下,預期違約制度適用標準規定模糊,只有明示默示的概括性行為規定。因此,只要借鑒預期違約制度完善我國不安抗辯權制度即可,沒有必要另行安排預期違約的法條。B12
另一派學者則恰好相反,主張刪除抗辯權B13。他們認為預期違約制度涵蓋的范圍不僅包括合同當事人可能不履約,還包括當事人明示拒絕履約的情況,其適用范圍明顯廣于抗辯權。而且預期違約制度是一項積極的違約責任請求權,能夠賦予合同當事人在不利狀況下,主動采取措施保障自己利益不受損害的權利。因此預期違約制度就足以保障締約人的權益。
而折中派認為: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的規范可以并行不悖。原因在于:不安抗辯權應限定在防御范疇,其他如請求解除合同、提供擔保等積極行為應適用預期違約(進攻范疇)。B14其中韓世遠教授就主張,由于預期履行不能排除締約人提供擔保,所以不可將預期履行不能一律認定為先期違約。B15正確做法應該是同時賦予債權人要求充分擔保的權利和不安抗辯權,使債權人在主動采取措施要求債務人表明態度的同時,也享有使用抗辯權保護自己權益的被動權利。王利明教授也認為,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性質不同,是兩個互相區別且無法互為替代的制度。B16
綜合上述觀點,筆者認為折中說較為合理。從法律理論方面進行分析,不安抗辯權和預期違約雖然都是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違約行為進行規范,但在適用情形上,不安抗辯權偏向于因客觀原因導致的債務人可能失去履行能力B17,如果客觀情形變動,債務人仍有繼續履約的可能,因此只有在對方無法提供有效擔保時才可主張解除合同;而默示預期違約則偏向于締約一方主觀上不想履行,因此對方無法擔保時可以直接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二者理論上的適用情形顯然有所差異。雖然《合同法》第68條第2款在不安抗辯權適用情形中納入了“轉移資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將不安抗辯權的評價范圍擴大到包括債務人具有不履行義務的主觀惡意,但是,這并不能影響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兩制度以債務人的主觀惡意為劃分標準,在適用情形上各司其職。李建星指出,正確的做法是將該規范視為一個法律漏洞B18,于司法實踐中將“抽逃、轉移資金以逃避債務”的情形糾正評價為預期違約。
總而言之,不安抗辯權應當調整的是債務人客觀無法履約的情形,預期違約應當調整的是債務人主觀拒絕或以行為逃避履約的情形,兩者適用范圍存在差異。在立法實踐中,我們應當采納折中說,將不安抗辯權和預期違約同時納入我國合同法體系,同時在法條中將二者的適用范圍予以進一步明確劃分。
(三)法律救濟方式不同
首先,《合同法》明文規定,在對方可能無法履約的情形下,適用不安抗辯權制度需要通知相對人、在對方無法提供有效擔保的情況下申請解除合同并賠償損失。換句話說,行使不安抗辯權只有兩個結局:(1)對方提供擔保,合同繼續履行;(2)對方無法提供擔保,當事人只能主張實際損失,而不能主張違約責任。但在預期違約制度下,如果當事人默示違約且不能提供有效擔保,債權人一方面可以直接適用《合同法》第94條“合同法定解除權”,提出無法達成合同目的而解除合同,也可以直接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債權人可以根據自身利益選擇獲得違約賠償,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債權人的權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兩者最后適用的效果出現了差異:如果選取違約賠償,那么預期違約產生的救濟效果可以達到類似合同履行完畢的狀態;而不安抗辯權只能選擇解除合同、要求損害賠償,則使雙方當事人回到了締約之前的原始狀態。
其次,從根本上說,預期違約事實上認定了合同相對人的行為具有違約性質(雖然合同未屆履約期限),但不安抗辯權僅規定了對方可能無法履行義務時對合同另一方的救濟,連違約責任也無權主張。顯然在不安抗辯權理論下,締約方并不成立實質違約。正因如此,不安抗辯權屬于對抗他方履行請求的消極手段。它不能積極防衛債權實現的風險,即使其適用條件在一定程度上與 “默示違約”的外在表現并無不同,但實務中,先履行方往往也只能中止履行、等待合同屆滿再主張違約責任。B19但如果適用預期違約、主張對方主動終止合同的履行,合同當事人則可以積極行使權利,終止合同并請求賠償損失。
綜上所述,從兩項制度的救濟方式來看,不安抗辯權僅有基于締約過失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救濟手段較被動,有時不能充分保護締約人權益;而預期違約在相對人有主觀過錯時,可以積極主動地終止無望履行的合同、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在救濟手段上顯然更加有效。
(四)其他方面的差異
總的來說,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的含義與性質不同、適用范圍不同、使用制度產生的法律效果也存在差異。筆者認為,上述三點是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兩項制度的根本區別。同時,二者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別。
1.締約雙方是否存在履約先后關系不同
我國《合同法》規定,不安抗辯權的適用主體為“應當先履行義務的當事人”,也就是說,不安抗辯權必須在締約雙方所負的義務不是同時履行的前提下,才能由先履行義務一方主張。但預期違約并未對主體做特殊限制,由此可知,預期違約制度適用于所有合法有效成立的合同,其調整范圍顯然廣于不安抗辯權。
2.兩制度法系來源不同
不安抗辯權最初來源于大陸法系,而預期違約制度最初來源于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立法邏輯上存在根本差異。首先,大陸法系屬于成文法,主要追求法律規范的嚴謹和成熟。不安抗辯權在《合同法》規范中隸屬于三個合同履行抗辯權,邏輯嚴謹地規范了合同履行抗辯制度。而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則屬于判例法,其是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逐漸得到確立和完善的,因此更多地體現了實踐中的法益衡平。從最早提出預期違約責任的霍徹斯特訴德拉陶爾案件,到確立默示預期違約制度的辛格夫人訴辛格案件,雖然預期違約不符合一般“違約在先,違約責任在后”法律邏輯,但為維護實質正義,衡平法孕育了預期違約的概念。B20
3.兩制度立法觀念不同
在大陸法系的觀念下,合同是雙方的合意,“它強調雙方交易的等值性,以及風險的合理負擔”B21。在無法正常履行時,最優解應當是雙方協商,達成新的合意之后繼續履行;但在英美法系中,根據美國《合同法重述》,合同屬于單方允諾,一旦一方無法履行,無論什么理由都必須承擔違約責任。
因此,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立法觀念的區別也反映到了預期違約和不安抗辯權的制度規范上: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給締約方履約能力的恢復留有余地,最大限度地維持合同效力;但英美法系中預期違約制度的立法目的,則是在允諾不能實現時確保債權人可以得到違約賠償。
4.兩制度側重保護的法益存在一定不同
正是因為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立法邏輯與立法觀念上的差異,預期違約制度和不安抗辯權制度側重保護的法益也存在區別。作為一種抗辯請求權,不安抗辯權在訴訟中的作用偏向于消極防衛,是針對合同另一方出現的無法正常履約的高度風險情形下,對自我權益的一種保護,往往是在一方要求另一方先行履約的前提下才提出的抗辯理由。鄭玉波認為:“不安抗辯權的法律價值是防御而非攻擊,請求在先,防御在后。而不安抗辯權屬于對抗權。”B22梁慧星也認為:“只有一方先請求履約,另一方才能行使不安抗辯權。大陸法系的三個抗辯權都是防衛性的。”
B23
綜上所述,不安抗辯權在訴訟中起到消極防衛的作用,是一種防衛性的抗辯請求權。在具有先后關系的雙務合同中,如果在后履行義務人本身沒有對待履行能力,卻仍要求在先義務人先履行,這就增加了先履行義務人的風險,使其處于被動地位。B24因此,不安抗辯權注重的是先履行義務人的風險免除,是在履約不能的風險下,對抗自己履約義務的權利。而預期違約是相對積極的請求權,當法定事由發生時,允許締約人主動中止,要求未能履行約定的一方承擔違約責任,其側重保護的應是市場的交易秩序與安全。
三、總結
不安抗辯權發源于大陸法系,是調整合同履行期屆滿前締約人無法履行的制度;預期違約產生于英美法系國家,同時規范債務人拒絕履行和默認不履行的情形,亦有其實踐意義。這兩項制度有其相似之處,也存在數項差異。為更直觀地表述兩項制度的關系,筆者在文末列表格如下,對前文論述進行簡單總結。
[注釋]
① 王利明:《預期違約制度若干問題研究》,載政法論壇,1995年第2期,第18頁.
② 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頁.
③ 李永軍:《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頁.
④ 崔建遠、韓世遠:《債權保障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頁.
⑤ 劉子金:《預期違約制度研究》,鄭州大學,2005年,第35頁.
⑥G.H.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10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9. 796.
⑦ 王利明:《預期違約制度若干問題研究》,載政法論壇,1995年第2期,第18頁.
⑧ 周黎明:《國際商法》,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69頁.
⑨ 李偉:《不安抗辯權、給付拒絕和預期違約關系的思考——以德國法為中心的考察》,載比較法研究, 2005年第4期,第59頁.
⑩ 王利明:《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5-13頁.
B11 李永軍: 《合同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0版,第521頁.
B12 王富洲:《論〈合同法〉刪除預期違約制度之必要性》,載《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類似觀點亦可參見梁慧星: 《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頁;朱廣新:《合同法總則》(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頁.
B13劉凱湘、聶孝紅:《論〈合同法〉預期違約制度適用范圍上的缺陷》,載《法學雜志》2000 年第1期.
B14類似觀點參見葛云松: 《期前違約規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頁;齊恩平: 《先期違約的法律救濟權及比較研究》,載《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0 年第1期,第22頁.
B15韓世遠: 《合同法總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頁.
B16王利明:《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5-13頁.
B17傅鼎生:《不安抗辯適用之限定》,載法學,2008年第8期,第153-159頁.
B18李建星:《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的完全區分論》,載《政治與法律》,2017年第12期,第123-135頁.
B19陳柏霖:《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比較研究》,復旦大學,2008年,第29頁.
B20王艷.:《預期違約制度研究》,中國海洋大學,2013年,第40頁.
B21王澤鑒:《民法債編總論·基本理論·債之發生》,臺北: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版,第70頁.
B22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頁.
B23梁慧星:《民法總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頁.
B24夏寶森,趙鵬:《試論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載河北法學,2002年第1期,第24頁.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1]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335.
[2]崔建遠、韓世遠.債權保障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192.
[3]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4]李永軍.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97.
[5]李永軍.合同法(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10 版.
[6]周黎明.國際商法[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169.
[7]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8]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81.
[9]朱廣新.合同法總則(第二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10]葛云松.期前違約規則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
[11]王澤鑒.民法債編總論·基本理論·債之發生[M].臺北:臺北三民書局,1993.70.
[12]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3]G.H.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M]. 10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9. 796.
參考學位論文
[1]劉子金.預期違約制度研究[D].鄭州大學,2005.35.
[2]陳柏霖.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比較研究[D].復旦大學,2008.
[3]王艷.預期違約制度研究[D].中國海洋大學,2013.
參考期刊論文
[1]王利明.預期違約制度若干問題研究[J].政法論壇,1995,(2):18.
[2]王利明.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19(06):5-13.
[3]韓世遠、崔建遠.先期違約與中國合同法[J].法學研究,1993(03):33-38.
[4]李偉.不安抗辯權、給付拒絕和預期違約關系的思考——以德國法為中心的考察[J].比較法研究, 2005(04):57-63.
[5]王富洲.論〈合同法〉刪除預期違約制度之必要性[J],《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
[6]劉凱湘、聶孝紅.論〈合同法〉預期違約制度適用范圍上的缺陷[J].《法學雜志》2000 年第1期.
[7]齊恩平.先期違約的法律救濟權及比較研究[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8]王雷.論我國〈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J].朝陽法律評論編輯委員會編:《朝陽法律評論》(2012年第1期),華僑出版社2012年版.
[9]傅鼎生.不安抗辯適用之限定[J].法學,2008(08):153-159.
[10]李建星.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的完全區分論[J].政治與法律,2017(12):123-135.
[11]邵東華.合同概念的產生和發展[J].天中學刊,2005,(3): 32.
[12]夏寶森,趙鵬.試論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J].河北法學,2002,(1):24.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遼寧 沈陽 11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