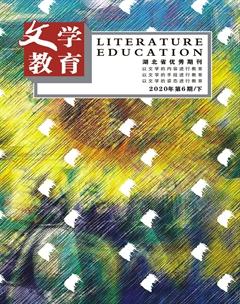無厘頭的民間邏輯

杜琪峰曾經說,拍周星馳的電影,可以不需要自己這個導演。這是一句玩笑話,不過也說明了周星馳獨特的表演藝術,是自成一體的,以至某種程度上不受導演和劇本的影響,反過來為影片預設了某種風格和基調。所以,就像影迷指認的那樣,我們有理由命名一種“周星馳電影”,包括他主演和導演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公認的代表作。
差不多二十年前,《大話西游》在內地剛火的時候,許多影迷學會了一句粵語“無厘頭”,且被視為周星馳電影專屬的美學標記。什么是無厘頭,那些擠在宿舍對著大腦袋顯示器前仰后合的大學生們,自然說不出個道道;不過京城里的先鋒理論家及時提供了一個洞明世事的診斷,叫“后現代”。但什么又是后現代,就更加讓人“不知所謂”了。二十年過去了,周星馳從星仔、星哥變成了星爺,在內地打破了一次又一次的票房記錄,收割著一撥又一撥的粉絲,理論家早已不理會這個大眾文化現象了。而當第一撥粉絲開始謝頂,在周氏喜劇中逐漸看出悲劇來時,終于明白,哪里有什么無厘頭,哪里是什么后現代,周星馳電影的世界,根本就是我們自己的故事,就是一群小人物,面對種種不甚如意的處境,左突右撞,捶胸頓足,裝瘋賣傻,又或破涕顏開的命運。無厘頭中的邏輯性和我們的命運一樣嚴絲合縫。這個邏輯,其實就叫作民間。
一
民間是什么樣子?二十年前上海的文學評論家們發明的一些說法廣為流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狂歡。據說民間就是一種狂歡狀態,而這個詞則意味著上下顛覆,群魔亂舞,藏污納垢,當然也包括自由、活潑、本能、欲望等等。但是,這些說法恐怕寄托的是大都市文人們不安分的想像,與社會學意義上的那群人有關,但并不能等同。
周星馳的電影描繪的是后面這個民間,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是小人物們的人生幻想。毫無疑問,這個幻想里有狂歡,有顛覆,但不是全部。不如說,這個被正經的理論家不屑的世界,流轉的主題恰恰是正義、崇高、善良、英雄以及愛情。讓我們仔細想想,周氏有哪部電影顛覆過人類的這些基本價值?沒有。幾部經典的公案戲如《九品芝麻官》、《審死官》以及《算死草》,贊美的不是正義嗎?《回魂夜》里犧牲的Leon身上沒有崇高嗎?《新精武門》中因誤以為打死師父而甘受懲罰的劉晶不崇高嗎?此外,哪個80后沒有接受過《大話西游》的愛情啟蒙呢?哪個不是被朱茵在《逃學威龍2》中羞澀、躲閃的眼神打動過的呢?這里面哪里有價值的顛覆?
不如說,在先鋒理論家眼中,這恐怕是一個正能量到乏味的世界吧。因為近幾十年間的文藝界,流行一種美學潛規則,仿佛只有發掘出人性的黑暗,解構或混淆傳統的價值,才足夠先鋒。某位經常上鳳凰衛視的文學評論家甚至總結出一個金科玉律,說明確的是非觀念是俗文學的標記。理論家的立場何以如此呢?因為顛覆恰恰代表某種資格,某種優勢,不是誰人都行的。
顛覆從來是權勢者的肆意,民間的價值觀其實是趨向保守的。理論家們想像的民間,據說是發生在統治薄弱的地方,所以為自由或藏污納垢留下了空間。這恐怕也是一廂情愿的想像。相反,藏污納垢永遠發生在統治最強大的地頭,發生在大內野史,朱門青樓,以及VIP會所。顛覆價值的永遠是意氣風發隨心所欲的權勢者,是《世說新語》里的王謝子弟,是時尚領袖,因為這是他們與下層相區隔的標牌。所以,周星馳讓《食神》中熾焰沖天的史蒂芬·周在西裝革履的隨從中獨穿一件褲頭出場時,絲毫不會令人驚訝。而民間,因為他們往往是被壓迫與被損害者,是顛倒了的世界的受害者,是流行價值的負極,所以首先需要的不是解構和顛覆,而是小心翼翼的保守,保守住一點價值的防護衣,以免徹底淪為異類。
二
英雄是民間世界的另一個主題,但周星馳告訴我們,這個主題的意義遠比我們想像的復雜。
《逃學威龍》是無厘頭英雄形象的代表作。雖然片子的內涵不如其他一些作品豐富、厚重,但其精彩的構思最能體現英雄對于民間的意義與機制。這個飛虎隊員假扮學生返回校園當臥底的故事所講的,其實是一場高中生的青春期夢幻,它圓了青春期男生的所有夢想:帥氣、聰明、英勇,還能征服美麗的女老師。但這個夢體現的是一種普遍的人格機制。
這個機制就如同皮影戲,英雄是線頭上的剪影,現實是提線的演手。但是,從來不是演手在操縱皮影,而是皮影在引導演手。沒有前頭的剪影,提線的歌喉發不出高亢的心聲。英雄的夢幻就是那個皮影,它為現實提供前行的想像。就如同在電影里,飛虎隊第一殺手周星星是英雄,同桌黃小龜是相形見絀的小丑;而在電影外,黃小龜是眾人的現實,周星星則是他們的夢幻。
《逃學威龍》所顯示的這個英雄機制,在民間邏輯中具有普遍意義。英雄是民間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主題之一,民間傳說中從來不乏英雄,因為他們最迫切地需要一個想像的剪影來指引他們卑微的當下。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正是士兵的真實心理機制。因為真正玩世界于股掌之上者,不再需要一個英雄形象來鼓動自己。將軍們的夢幻,是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他們喜歡某種舉重若輕,他們的目標是更輕,是隱士。英雄是屬于民間的,是屬于小人物的。所以只有最鄉野的戲文,才喜歡三國水滸,喜歡云臺二十八將瓦崗三十六友等等。
有些理論家說周星馳塑造的是“反英雄”,說明他們完全不了解這個英雄機制。在周星馳電影中,英雄從來是最強勁的主題。《逃學威龍》里的警員周星星是英雄,《武狀元蘇乞兒》里的蘇察哈爾燦是英雄,《新精武門》里的劉晶是英雄,《國產凌凌漆》里豬肉佬特工是英雄,《少林足球》里的眾師兄弟是英雄,《功夫》里的小混混阿星最后成了英雄。哪里有反英雄?
不過,理論家們創造的“反英雄”一詞還是捕捉到了無厘頭英雄的一些特殊之處。電影中的英雄某種意義上是現代都市的產物,是都市中產者們的夢幻剪影,是他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處境的對應物。因為只有中產者既有受壓制激發英雄夢的動機,也只有他們才能回頭比比落跑者不斷地確認和培育這個夢。007電影就是這些都市中拘謹卑微的男性們的夢幻,一個可以持續滑入持續沉睡的夢幻。持續沉睡是說,現狀總是壞到讓他們生發英雄夢幻,又沒有壞到讓夢驚醒過來。夢幻的發生,需要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某種平衡。
三
但對小人物而言,最不易維持的恰是這種平衡。所以,英雄夢幻對于民間,就具有了正負兩種可能的效果。除了正面的引導和催眠,它還能成為一道強光,一面照妖鏡,愈發照見現實的不堪。這是民間的英雄夢的復雜之處。
而且,英雄的夢幻需要不斷的滋養,不斷的自我催眠。要維系英雄夢,民間文化有兩件最常用的法寶。第一種,有學者稱之為“機智”。機智不是一般所謂的智慧,而是周星馳電影中整蠱專家、扭計祖宗式的智慧。機智人物是民間文化中的一類光彩奪目的形象,阿凡提是最為人熟知的代表。這類“機智人物”是生活中的弱者,卻是精神上的強者,他們最善于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戲弄或戰勝現實中的強者。機智人物是民間自我肯定的一種方式,它不是“卑賤者最聰明”式的盲目自戀,而是對自身現實的情形判斷——民間的卑賤地位不是由于“我很蠢”,而是“我沒有辦法”。所以機智的重心,是發現高貴者的愚蠢,利用他們的漏洞;機智發揮的途徑,則往往漠視高貴者們的通行辦法。前者在周星馳電影中的經典例子,莫過于《九品芝麻官》中包龍星誘使常威承認罪行;后者的例子則比比皆是,比如包龍星通過和人吵架習得了判案辯護的嘴上功夫,《算死草》中陳夢吉建議酒樓老板表演跳樓來攬客,《唐伯虎點秋香》中唐伯虎以夸張的自殘博取華府的同情,或《國產凌凌漆》中用色情錄像帶代替療傷的麻藥,等等。喜劇人物形象的魅力,不僅在于它的卑微,更在于他們的機智。卑微對應著觀者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機智則寄托著觀者的自我肯定和超越的希望。
民間英雄夢的第二件法寶,我想稱之為“傳奇”,即對某種奇跡的狂想。對奇跡的嗜好在民間文化中根深蒂固,絕非沒有來由。當現實與理想之間有道路可通達時,或者至少能讓人看到這條道路時,人不會陷入狂想。比如,某種意義上農民和中產者都不會陷入狂想,他們能看到自己的努力與成效,所以農民相信人勤地不懶,中產者相信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對于他們,狂想是種有害的東西。但對于那些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看不到任何通道的人,狂想就成了支撐夢幻的唯一條件。所以民間文化喜歡傳奇,喜歡天降仙女,喜歡樹落金子;周星馳電影中的小人物,也各有各的特異功能,《賭俠》和《賭圣》中的阿星有天眼通,能看穿底牌,《新精武門》中的劉晶右臂天生神力,《少林足球》中的眾師兄弟各有絕學,就是這個道理。
但這兩件法寶,不足以支撐英雄夢的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英雄夢幻對于小人物,就不再是種引導,而是一種逼視,愈加顯出他們的卑微,這樣,英雄夢也就變成了惡夢。于是,抵制英雄夢幻的誘惑,甚至鏟除英雄夢幻的苗頭,就是一種非常必要的防護措施。這才是周星馳電影中反英雄的真實含義。反英雄不是指擁抱英雄的反面,不是像理論家有時候用“審丑”所說的那樣。不,它絕不是某種天生或自甘沉淪的癖性。反英雄的根基仍然是英雄崇拜,它是英雄崇拜的副作用,是對所有那些成不了英雄的人、所有超越現狀的努力的否定、嘲諷甚至仇恨。
電影有兩種方式呈現這種對英雄的抵制。一種方式由配角形象來承擔。周星馳的電影中塑造了一系列形象生動的配角,比如如花、醬爆、吹簫萍、達文西、阿歡、齙牙珍,以及周星馳的黃金搭檔吳孟達出演的無數角色。但他們的功能不是直接現“丑”。電影要呈現的,不是他們丑,而是要呈現他們想變美的笨拙與無效,暴露他們要超越的努力及其夸張的失敗,它要觀眾一起嘲笑他們的失敗,嘲笑他們的努力。《少林足球》中安排了一場戲,讓眾兄弟肆意地嘲笑阿梅的化妝效果,就是導演對這個意圖的表白。在這種方式中,主角與配角往往承擔不同的功能,主角是英雄,或最終會成為英雄,配角不只是凡人,而是成為英雄之路上的失敗者。
這種主角和配角之間的關系,用王晶導演的行話,就是上把和下把的關系。但上把和下把也可能由主角自己一身二任,周星馳所有的英雄形象往往都是上下把并存的。《國產凌凌漆》作為對OO7系列電影的解構,就是最精彩的一個例子。凌凌漆既是英雄,也是一個時常出糗的豬肉佬;它不會用槍,但將切肉刀能運用到出神入化;它是大隱隱于市的特工,但也是一個付不起過夜費的無賴。人物形象上的矛盾導致整個故事像一段不斷被插入了包袱的單口相聲,敘述的條理不時被打斷。但這正是無厘頭英雄的復雜之處,即一邊是對英雄夢的渴望和放縱,一邊是對英雄夢的恐懼和拒絕,反英雄們實際上徘徊在沉入夢幻與抵制夢幻之間。
四
使得民間的英雄夢幻如此糾結的,是來自現實的障礙。這個障礙除了生存條件的種種匱乏,還有來自權勢層的壓迫,包括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壓迫。對于民間而言,如何在現實中克服這種壓迫是個難題,如何在心理上克服這種壓迫更是個繞不開的難題。周星馳自己導演的幾部作品中,這個主題一再出現,縈繞不去。它既是周星馳的某種個人情結,也是民間文化的一種潛意識,一種無法回避的困擾——是去超越自己被壓迫被侮辱的境地,還是超越這個壓迫結構本身。
在周星馳自己導演的作品如《國產凌凌漆》、《喜劇之王》、《食神》、《少林足球》、《功夫》,包括近來的《美人魚》、《新喜劇之王》,以及陳嘉上導演的《武狀元蘇乞兒》中,這個困擾的主題一路貫穿了下來。導演讓主角經歷命運的大起大落,仿佛就是對這個問題中各種立場各種可能的探索。而周星馳電影的偉大,正在于它選擇了后一個立場。《食神》中,如日中天的史蒂芬·周飛揚跋扈,卻遭到他人嫉恨身價敗落,流落廟街的小食攤。在他帶領街坊再次打拼事業的過程中,才又尋回了良知與初心。《功夫》中的小混混阿星,平日受盡他人欺凌,所以一心想加入斧頭幫,可是一路陰差陽錯,終于改邪歸正,成為真正的英雄。《武狀元蘇乞兒》的經歷更是當得起周星馳的經典臺詞,“人生的大起大落太快,實在是太刺激了”。紈绔子弟蘇察哈爾燦為了一見鐘情的女子一句戲言——她的夫君要“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武功蓋世,狀元之才”——去考武狀元,卻被貪官陷害,淪為乞丐,不料卻成了丐幫幫主,最后選擇行乞人間。這些都是對那個壓迫結構的真正超越。
對壓迫的超越,也意味著對自己出身階層的認肯,和向這個共同體的回歸。周氏的電影塑造了許多充滿溫情的民間共同體,比如《行運一條龍》中的行運茶餐廳,《龍的傳人》中的大澳,《食神》中的廟街,《功夫》中的豬籠城寨等等。這里不只是小人物們日常揾食的環境,也代表著一個有人間溫情的家園。周星馳的電影中的主角,經過逃離、失敗,和更高層次的領悟,最終回到他們的這個出發點。就像《食神》中,斯蒂芬·周最終認識到,真正的食神不是權勢,而是善良。這是民間艱難的自我確認。
當年讀大學時,經常聽文化人講,香港是個文化沙漠,言下之意是香港沒有高雅的文藝。估計周星馳的電影在他們眼中也只能算這沙漠中的一堆沙丘吧。我不了解高雅的文化什么樣子。不過我發現,與周星馳同齡的內地電影人,拍的人物是和他們自己的身家一路高升的。拍農婦起家的,最后拍起了帝王將相;拍胡同串子的好夢一日游的,最后只玩私人訂制;拍小偷起家的,最后一定要拍跨國資本家。周星馳,無論當主演還是導演,幾十年間始終在上演小人物的卑微與傳奇,慰藉著一代又一代的影迷和粉絲。那么,就讓這樣的沙漠,能沙化得更廣闊些,更永恒些吧。
胥志強,文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