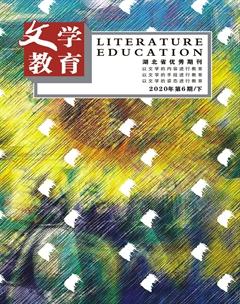小田岳夫《魯迅傳》的版本變遷
李天然 孫立春
內容摘要:小田岳夫著《魯迅傳》是世界上第一本完整的魯迅傳記。該書于1941年在日本出版后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多次再版,且其各版均在內容上有所改動,可以說從一個側面體現了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中日關系影響下的日本魯迅觀的嬗變。隨著《魯迅傳》的多次再版,其中的魯迅形象也與日本的歷史社會狀況產生了深刻的關聯。
關鍵詞:小田岳夫 《魯迅傳》 版本變遷
在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視域下,小田岳夫是一個處于文學版圖邊緣的作家。但若是對魯迅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和接受加以考察的話,那么小田岳夫必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小田岳夫所著《魯迅傳》作為世界上第一本完整的魯迅傳記,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該書于1941年在日本出版后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多次再版,且其各版均在內容上有所改動。
1.初版《魯迅傳》——大東亞思想的縮影
1940年6月,小田岳夫在雜志《新風》上發表了《魯迅傳》第一回,隨后因《新風》廢刊而被迫中止;后受龜井勝一郎等人之激勵,開始了初版單行本《魯迅傳》的創作,于1941年3月15日由筑摩書房出版;而創作期間又于1940年9月至11月在《新潮》上連載了三回《魯迅傳》傳記梗概。值得注意的是,從《新風》廢刊到初版《魯迅傳》最終面世,日本文學界對這部作品傾注了異樣的關注和熱情。在《新風》廢刊導致《魯迅傳》連載終止之后,文壇上不乏惋惜之聲。考慮到《魯迅傳》連載及出版正值侵華戰爭的特殊時期,這種現象就更加耐人尋味了。為何侵華戰爭不僅沒有撲滅,反倒像是激發了日本作家們追懷魯迅的熱情呢?筆者認為,日本作家當時對魯迅及其境遇的關心,反映出的是大東亞思想之語境下日本社會對待中國的情感復雜性。
日本作為東亞近代化的先驅,逐漸接受了西方的東方主義偏見,使其在先進的西方與落后的東方這一近代化圖式中漸漸喪失了其單純的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而將其人格投射到了整個東亞,這也是大東亞思想產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當時以大東亞思想為指導所描繪的世界圖景之中,日本天然地面臨著兩重對立:在全球范圍內面臨著西洋(帝國主義)與東亞(被壓迫民族)之對立,而在東亞范圍內又存在著日本(帝國主義)與東亞各國(被壓迫民族)之對立。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之下,包括日本作家在內的日本民眾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將作為客體的中國“內化”的邏輯:中國雖是當下的敵人,卻也是將來日本所主導的與西方世界相對立的大東亞圖景之中的一部分,因而是亦他亦我的存在。因此,當時的日本作家在戰時對魯迅表現出的強烈興趣,某種程度上就是來源于大東亞思想蒙蔽之下所產生的對于東亞各國乃是一體的錯覺。魯迅生于中國,留學日本,有著極高的東方傳統教養,同時又積極吸收西洋文化,因而魯迅其人的經歷包含了以上兩重對立中的所有元素,這在軍國主義政府看來便成為了“大東亞共榮”的絕佳例證。
小田岳夫曾說自己創作《魯迅傳》乃是源于某種不可名狀的沖動。從初版《魯迅傳》中我們可以看到,小田的創作沖動很大程度上傾注在了從軍國主義意識形態對魯迅的經歷進行解讀上頭。在初版《魯迅傳》的后記中,小田岳夫有意識地將魯迅放到了東西對立的語境當中,指出中日在吸收西方文明之時盡管存在不同之處,但兩者在對置于西方文明這一點上又是統一的。這無疑反映了日本作家們在大東亞思想影響不可避免地產生的畸形東亞觀,而魯迅在此處便是小田岳夫思考這種東亞觀時的載體。
2.從“支那”到“中國”——《魯迅的生涯》
1949年9月20日,鐮倉文庫出版了第二版《魯迅傳》,并改名為《魯迅的生涯》。巧的是,1946年出版的中文版《魯迅傳》(夜析譯)所用的譯名正是“魯迅先生的一生”,但小田岳夫改名是否與此有關就不得而知了。小田岳夫在后記中寫到,《魯迅的生涯》乃是對于魯迅傳作了若干修補,并根據今天的日本之形勢施以若干訂正而成的。在日本戰敗以后,中日關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日本試圖用大東亞體制構建的優勢地位被徹底地逆轉了。在這樣的戰后圖景中,中國成為了優勢的一方,而不再是被侵略的對象,因此日本作家看待中國、看待魯迅的方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上文已提到,侵華戰爭時期日本作家對魯迅的關心,來自于大東亞體制下產生的一種想象的連帶感。但隨著日本戰敗,這種連帶感也就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一同破滅了。而小田岳夫在創作《魯迅的生涯》時清楚地意識到了時局的變化。他在后記中寫到,由于日本被自己昔日眼中的弱國、手下敗將——中國徹底打敗了,因而日本恐怕得放下架子來認真審視學習中國的長處了。當然,要讓在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之下習慣了唯我獨尊的日本民眾從心理上徹底接受侵略者到戰敗國的身份轉變,也絕非是一日之功。小田在后記中便強調日本并非是被中國的一己之力打敗,這自然是在暗示美國參戰的重要性。小田強調這一點,某種程度上還是出于兩重對立的視角,即日本之戰敗是東亞敗給了西洋,而非東亞的內部瓦解。由此可見軍國主義政府雖然破產,但其在思想上的余毒卻尚存。當然,就小田岳夫意圖通過魯迅取法中國這一行為來看,他已然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大東亞共榮之思想的荼毒,這一點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不僅如此,小田岳夫在《魯迅的生涯》中還表明,寫作本書是為了樹立健康的兩國關系,為了日本民眾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國盡一份綿薄之力。可以看出,魯迅便是小田為日本民眾所選擇的“教材”。
在《魯迅的生涯》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之處,便是文中的“支那”一詞都被改為了“中國”,而該書出版11天后,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了。小田岳夫在中國發生劇變的前夕做出如此改動,恐怕也是因為其預感到了今后之“中國”將不同于往日之積貧積弱的“支那”了。因而,小田岳夫此舉恐怕也是上述歷史狀況影響之結果。魯迅在此自然也就由揭露舊中國積弊的“支那作家”,變成了蘊含著某種新中國萌芽的“中國作家”。
3.歷史境遇的重合——第三版《魯迅傳》
1953年7月15日,第三版《魯迅傳》由乾元社出版。在后記中,小田說本書之再版是由于戰敗數年之后,日本成了如舊中國一般缺乏獨立性的國家。日本戰敗之后,聯合國軍(事實上為美軍)根據《波茨坦公告》占領了日本,日本進入了長達7年的GHQ占領時期。1951年9月8日,包括日本在內的49個國家在美國舊金山簽訂《舊金山和約》,并于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而這正是《魯迅傳》第三版出版的一年之前。《舊金山和約》簽署之后,日本表面上恢復了主權國家的地位,但于第三條中,日本同意美國對于琉球群島等諸島實施托管,這意味著日本主權國家身份的不完整。更為重要的是,同樣在1952年,日本與臺灣國民政府簽訂《中日和約》,成為美國在東亞牽制中俄的一枚棋子,也就是說獲得主權國家身份的日本卷入更為復雜的東西冷戰格局之中,并成為美國的傀儡。小田在第三版《魯迅傳》后記中強調日本現今缺乏獨立性,恐怕也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在小田看來,此時的日本正處于魯迅生前的中國那樣缺乏獨立性的半殖民地位置上。不得不指出,中國的喪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乃是拜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所賜,而日本失去獨立性則是軍國主義政府咎由自取,因而這種將二者作比的看法自然有失偏頗。但第三版《魯迅傳》在經歷了出版《魯迅傳》和《魯迅的生涯》之后,終于來到了與其內容相符的戰后的歷史語境中。正是由于日本此時的社會狀況與《魯迅傳》中的社會狀況發生了這種重合,因此《魯迅傳》較之前兩個版本來說,有著更深刻的歷史意義。
小田岳夫在該版《魯迅傳》中著力強調魯迅的文學家身份,這恐怕與當時中國國內對魯迅評價的轉向不無關系。在序章中,小田岳夫引用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的評價——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樣是將魯迅看作是諸多身份的統一體,毛澤東強調的是建立在文學這一基礎上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身份,而小田岳夫強調的卻是魯迅的文學家身份及其作品藝術價值的獨立性。
4.回到原點——第四版《魯迅傳》
1966年10月28日,第四版《魯迅傳》由大和書房出版。該書較之前幾個版本,可以說是最為忠實地還原了初版《魯迅傳》。在序章中,小田岳夫與25年前的自己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在初版《魯迅傳》中,小田寫到:“事變對于中華民族來說若是一縷曙光的話,那么魯迅就是死在了黑暗當中;若是情勢從此惡化下去的話,那么魯迅至少是得救了。若是中國經過這次事件的洗禮卻舊態依然的話,魯迅的努力恐怕就都是徒勞了”。而在第四版《魯迅傳》中,小田岳夫則在新的歷史狀況下對這段文字進行了回顧,認為“從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其后的發展來看,抗日戰爭后的中國確實迎來了曙光”。日本戰敗之后中國所發生的巨變完美地印證了小田岳夫在1941年出版《魯迅傳》中的話,而出版《魯迅傳》中關于魯迅是“死在了黑暗中”還是“得救了”的懸念,也終于在25年后的第四版《魯迅傳》中得到了回答:魯迅是死在了黑暗中,但他的努力終究沒有白費,為中國帶來曙光的正是中國共產黨。
綜上,魯迅的形象借由小田岳夫的《魯迅傳》越境到了日本,又在該書25年的多次再版中,隨著歷史社會狀況的變化而不斷產生新的意義。從二戰時“大東亞共榮圈”之縮影,到戰敗后學習中國“長處”的媒介,再到冷戰格局下作為被占領國的歷史境遇的重合,最后是25年后對魯迅之死的蓋棺定論。我們可以看到,隨著《魯迅傳》的多次再版,其中的魯迅形象也與日本的歷史社會狀況產生了深刻的關聯。
參考文獻
[1]小田嶽夫.魯迅伝[M].筑摩書房,1941.
[2]小田嶽夫.魯迅の生涯[M].鎌倉文庫,1949.
[3]小田嶽夫.魯迅伝[M].乾元社,1953.
[4]小田嶽夫.魯迅伝[M].大和書房,1966.
(作者介紹:李天然,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文學;孫立春,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碩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文學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