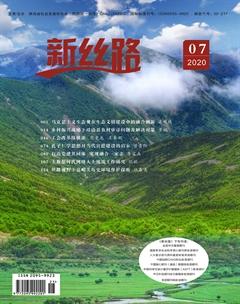疫情防控下的公民基本權利保護
潘越娟
摘 要:保護公民基本權利日益成為我國應急法律體系的主題之一。此次疫情中,人民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具有法律依據,合法有效;盡管如此,這些措施卻會限制公民某些基本權利。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這樣的突發事件,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并未對不可克減之權利予以明確規定,呈現出對公民權利保護不足、缺乏財產補償規定的特征,因此應當加強對公民權利保護、完善對公民財產補償規定,同時加快《緊急狀態法》出臺,以此保障社會非常時期下的公民基本權利。
關鍵詞:疫情;權利;保障;防控
自2020年春節突然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來,各地政府為防止疫情進一步擴大,紛紛出臺多項措施,其中交通管制、人員隔離是最為常見且有效的防控方式,這些措施是否合法,以及有何依據,值得探討。同時,民眾為響應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大多愿意舍棄自身部分權利。由此可見,在突發事件中,政府為快捷有效地進行治理,采取的措施必然會導致自身權力擴大而使公民權利受到限制,體現了權利限制思維。但應注意某些權利不可克減,我國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家公約》不僅規定在社會非常時期下可以限制公民基本權利,同時明確劃分出不可克減的公民權利。此次突發事件,為完善我國應急法律體系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一、疫情防控中政府典型治理措施的法律依據
1.交通管制的法律依據
《突發事件應對法》第三條對什么是突發事件進行了界定,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采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人民的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是典型的公共衛生事件。而根據衛鍵委發布的公告可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屬于乙類傳染病,因此亦適用《傳染病防治法》有關規定。新型冠狀病毒具有傳染性,為切斷傳播途徑,防止疫情快速蔓延,各地區相應采取了交通管制等預防措施。
2.人員隔離的法律依據
傳染病隔離是指將處于傳染病期的傳染病人、疑似病人安置在指定的地點,暫時避免其與周圍人群接觸,便于對其進行治療、護理以及一種應急處置措施。隔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縮小傳染范圍,減少傳染病傳播的機會,屬于一種醫療防控措施。《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條屬于對甲類傳染病可采取的措施,而衛鍵委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歸入法定傳染病中的乙類傳染病,且由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具有傳染性強、傳播速度快等特點,因此有必要對其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因此可以適用此條規定。
與此同時,《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條對拒絕隔離或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治療的人員規定了相關法律責任[1]。
二、疫情防控措施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
1.公民基本權利受到限制
2004年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我國憲法,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已進入關鍵時期,全國應對突發衛生事件的特殊時期,在該階段下側重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
新型冠狀病毒作為乙類傳染病,群眾在感染之初并不能憑借外在特征作出確診,因此為進行徹底排查,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有必要對可能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人通過隔離措施予以排除。同時,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醫療機構可以對確診患者、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觸者采取隔離措施,隔離措施必然會影響公民的人身自由。但新型冠狀病毒具有感染性,可以通過飛沫傳播病毒,若放任上述三類人員自由活動,會造成更大范圍的人員感染,不利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這些措施限制了公民某些基本權利,但均有法律依據,具有合法性,公民出于更好維護社會公益和公共秩序的目的,具有容忍的義務。
2.公民重要權利不可克減
疫情爆發以來,在人民群眾的積極配合下,各級人民政府采取的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盡管有法律依據,但不可否認這些措施限制了公民某些權利,政府權力相應擴張,為防止其超出合理的擴大范圍,須嚴格遵循公民重要權利“不可克減”原則。
不可克減原則指無論國家處于任何情況,締約國都不得減損或損害人權條約所規定的某些特定權利。目前國際上三個綜合性人權條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家公約》、《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歐洲公約》和《美洲人權條約》對此項原則作出規定。盡管上述文件對不可克減的權利數量和內容規定不同,但均對某些重要權利不可克減作出強調,反映出確定不可克減權利對保護在緊急狀態下的公民權利的至關重要性。根據該項原則,無論國家處于何種狀態,對于公民的某些權利絕不能克減,這一原則清晰劃定了政府對公民權利限制的范圍,由此對政府權力擴張作出防范,保障公民權利不受侵犯。
三、疫情防控措施呈現的法律不足之處
1.對公民權利保護不足
社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為合法、及時、有效地處置突發情況,結束社會非常狀態,我國各級人民政府紛紛依據現有的法律制度出臺治理舉措。在此狀況下,人民政府在有效應對突發事件的同時也需要保護公民權利,但二者之中必有側重,為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保護大多數公民的權益以及保障公民個人的生命健康權,在對公民權利作出最低保障的基礎上必然會克減公民某些權利。在《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多部法律中規定,社會非常時期公民需承擔一定義務,但在法律規定中對公民權利的保護部分卻規定甚少。
2.對公民財產補償不足
根據《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十二條,為應對突發事件,有關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可以對單位和個人的財產予以征用,若財產被征用或征用后毀損、滅失無法返還的,應當給予補償。同時,《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臨時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的,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能返還的,應當及時返還。由此可知,政府在突發事件中,可以征用公民某些財產,且在無法返還原來財產的情況下,應對公民作出補償,但不難看出法條對公民財產予以補償的規定很是粗陋。
四、健全對公民基本權利保護的法律規定
1.加強對公民權利保護
人民政府在保障多數公民權利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盡可能縮小對公民個人權利造成的損害,最大限度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在法律規定中堅持遵循比例原則。
與此同時,我國于1998年10月5日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家公約》,該《公約》中明確規定禁止歧視、生命權、禁止奴隸制等八項不可克減的權利。盡管國內日益保障公民權益,但此次突發事件中適用的多部法律,卻并未像國際人權公約一樣明確列出不可克減的公民權利,因此,此次疫情后,應當在我國應急體系下的法律法規中對不可克減的公民權利予以詳細規定。但我國國情復雜,在明確規定不可克減權利時應結合我國現行《憲法》和其他相關突發事件的法律法規,而對于《公約》中規定的八項不可克減之權利應當是突發事件下公民權利克減的底限,通過此種列舉式規定防止過度限制公民權利,進而充分保護公民權益。
2.完善對公民財產補償規定
第一,對需進行國家補償的緣由予以明確。其一、因國家征用、征收行為遭受損失。突發事件下,國家現有資源有限,為加緊應對危機以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必要時需對公民個人財產進行征收、征用。征收是國家從被征收公民手中取得所有權,征用僅擁有使用權。在危機處置結束之后,國家應予以退還被征用財產,否則需對公民進行補償。其二、因公共利益需要遭受損失。當社會處于非常時態時,國家為保障大多數公民利益,公民個人私益必然會讓位于社會公益。在社會公共利益受到脅迫時,在“權利位階”理論指導下往往會犧牲個人利益,公民為此受到的損害不應由公民個人承擔,而應由國家對其進行適當補償。其三、國家其他合法行為對公民造成的損失。
第二,對國家補償方式、補償程序予以明確。突發事件下國家補償方式可以包括以下幾種:對在突發事件下被予以征用的財產可以返還原物的應當將原物返還;若財產在使用期間不慎損壞或丟失,則應對公民給予一定的金錢或其他財產性權益補償;此外,公民財產在征用期間被使用所導致的一定程度的磨損,應支付相應報酬。在突發事件結束之后,若無法返還公民財產需對公民進行補償時,補償程序應與一般補償程序相區別開來。在被征用期間,公民財產為社會公益作出巨大貢獻,因此在突發事件結束之后,應設立特別部門專門處理補償事項,且另作補償標準,擴大補償數額。
3.加快《緊急狀態法》的出臺
雖然《緊急狀態法》早已經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國務院2004年立法計劃中,但直至現在并未出臺,而是于2007年頒布《突發事件應對法》,且輔之以多部專門性法規,如《地震應急法》、《防洪法》、《傳染病防治法》、《消防法》等。
從性質屬性上看,《突發事件應對法》屬于行政類法律規范,對在突發事件下的行政機關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間的權力義務關系進行調整,而《緊急狀態法》則明確緊急狀態的決定、宣布、實施、終結、等程序以及各階段下的權利義務分配,兩部法律性質完全不同。與此同時,《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六十九條對在本法難以調整時該如何適用法律進行了規定,發生特別重大突發事件,本法和其他法律法規難以消除而又需要進入緊急狀態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國務院依照憲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決定[2]。說明當面對特別重大的突發事件而《突發事件應對法》難以對其進行調整時,就需要《緊急狀態法》介入,以恢復社會正常秩序。
由此可知,制定《緊急狀態法》是我國未來的必然之舉。在《緊急狀態法》中,應明確規定緊急事件的管理部門,我國于2018年3月設立應急管理部門,用以指導各地區各部門應對突發事件,規定有關組織和人員對突發事件進行處理的相應程序以及必要的措施。同時,為保障公民私權利限制的規定不被濫用,應當對其規定一定的懲戒方式。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39條規定:“……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的,可以由公安機關協助醫療機構采取強制隔離治療措施……”。
[2]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人民日報,2007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