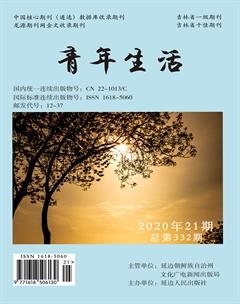關于網絡游戲主播的身份屬性研究
楊苗
摘要:學術界關于游戲主播身份屬性的爭議,以及關于游戲直播整體畫面是否構成作品的爭議越演愈烈,依據羅馬公約、WPPT和我國著作權法對表演者的規定,游戲玩家可以被認定為作品的表演者,游戲整體畫面則屬于對游戲作品的表演,則與網絡游戲直播有關的法律關系可以厘清,各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沖突也可以得到解決,引導游戲產業健康發展。
關鍵詞:網絡游戲直播;表演者;游戲整體畫面
網絡游戲直播一般是指“以 PC 端、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終端為載體,依托網頁或客戶端技術搭建虛擬網絡直播間,為游戲主播提供實時表演創作以及支持主播與用戶之間互動打賞的娛樂形式”。我國目前司法的保護機制對于網絡游戲直播著作權的焦點問題,即游戲主播的直播行為是否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范圍,網絡游戲直播畫面是否屬于作品。國內當前學術界針對游戲直播的主要觀點為:在部分網絡游戲直播中,主播的游戲操作畫面基本等同于游戲本身的運行畫面,最終形成的游戲直播畫面的著作權應該屬于游戲開發者。然而針對特定類型游戲直播的直播畫面,開發者可能只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主播的游戲操作對最終作品的形成作出了絕對性的貢獻,直播所臨時呈現的游戲操作畫面可能產生有別于游戲固有素材的獨創性內容,可構成基于原作品的演繹作品,主播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演繹作者,享有相應的演繹作品的著作權。而直播行為是否構成合理使用同樣應以游戲類別為劃分標準,競技類游戲的網絡直播具有很大商業價值,對游戲商業市場的潛在推廣遠大于其對市場的破壞效應,不屬于游戲作品著作權限制的例外,而應被視為合理使用。
斗魚直播侵權案是耀宇公司與美國維爾福公司簽訂了關于2015年DOTA2亞洲邀請賽的合作協議,主要負責此次賽事在中國方面的電視轉播,但是廣州斗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在沒有獲得耀宇公司許可的情況下,采用非法技術手段在同一時間實時播放并配加主播點評講解。耀宇公司認為斗魚公司的行為嚴重侵犯了自己的網絡直播權。最終法院判決斗魚公司并未侵犯原告的著作權權利,理由如下:一方面原告提出的視頻轉播權并不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法定權利,另一方面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主要是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的創新創造,游戲整體畫面未包含其中,因此也無法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法院最終認為被告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嚴重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
“斗魚侵權案”屬于中國首例電競直播侵權案,審判結果意義重大,法院最終認為游戲直播畫面不屬于作品,因為游戲賽事本身并沒有劇本,比賽畫面都是比賽雙方選手按照游戲規則操作形成的,瞬間的動態畫面,具有隨機性和不可復制性,比賽結果也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游戲整體畫面不構成著作權法下的作品。
“夢幻西游2”侵權案中法院認為游戲整體畫面屬于類電作品。此款游戲是一款在線的多人角色扮演類游戲,用戶可以通過登錄游戲運營商服務器,選擇自己鐘意的人物角色進行技能操作,用戶在游戲操作過程中調令游戲資源庫中的文字,圖片、音效和技能動畫等元素進行組合,最終呈現出動態的游戲畫面,但實質上涉案游戲實質上是一款可運行的計算機軟件程序,其運行結果即游戲程序自動或應游戲用戶交流指令產生。
本文認為,就游戲整體畫面是否構成作品而言,法院在斗魚案中的認定更具有說服力,而在《夢幻西游2》案中法院對競技類網絡游戲的過程雖然詳細客觀的精彩描述,但這并不能證明游戲整體畫面可以構成類電作品。并且在游戲過程中,用戶每次操作呈現的游戲整體畫面具有不確定性,永遠無法實現通過相同操作形成完全一模一樣的游戲整體畫面,因此本文認為把具有隨機性的游戲整體畫面認定為類電作品不具有合理性。因為著作權法對作品的規定是:“作品”必須是人類的智力成果,是能被他人客觀感知的外在表達且須具有獨創性。游戲玩家通過操作隨機生成的游戲整體畫面并不滿足著作權法的規定。另外游戲直播通過直播游戲主要是為了吸引觀眾圍觀,賺取更多的流量以換得更大的經濟利益,游戲主播的操作也是瞬間主觀意識控制的,并未來得及思考更說不上具有獨創性的表達自己的思想。所以說把瞬間形成的不確定的游戲整體畫面規定為作品不具有社會價值,更起不到鼓勵作者進行創作的意義。
有學者提出游戲操作過程和體育賽事很像,有基本的動作、規則和策略安排,但是過程有很大的隨機性,以及很難再復制完全相同的過程,游戲整體畫面也難以被歸類為類電作品,而且每一次的游戲操作形成的畫面都不相同,若認定游戲整體畫面構成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那一個互動式的電子游戲會產生無窮盡的著作權,這種保護也不具有現實性和合理性。從著作權法的基礎以及游戲市場需求考慮,被固定在有形載體上的游戲畫面才有構成類電作品的可能性。既然游戲整體畫面并不能構成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那關于網絡游戲整體畫面屬于游戲開發商還是游戲玩家并沒有過多的意義。本文認為游戲整體畫面并不構成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而是屬于對游戲作品的表演,游戲玩家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表演者,在其依法向游戲作品的著作權人行使義務后亦可對其表演享有表演者權。
《羅馬公約》第3條(a)款規定:“表演者意指演員、歌唱家、音樂家、舞蹈家和以表演、演唱、演說、朗誦、演奏或以其他方式表演文學或藝術作品的其他人”,可見《羅馬公約》下的表演者僅指表演狹義的文學或藝術作品的表演者。為彌補《羅馬公約》對表演者概念規定的不足,WPPT第2條(a)款對表演者概念加以補充:“表演者是演員、歌唱家、音樂家、舞蹈家和以表演、演唱、演說、朗誦、演奏、詮釋(interpret)或其他方式表演文學或藝術作品或民間文藝表達的其他人”。可見與《羅馬公約》相比,WPPT分別在表演方式和客體兩個方面擴充了表演者范疇。在表演方式方面,它增添了以表現作品通過詮釋方式的表演者,其典型代表就是樂隊指揮或舞臺劇的導演,他們雖然不親自參加表演,但卻可把自己對作品的理解或詮釋融入到表演中。在表演客體方面,它則補充了民間文藝表達的表演者,民間藝人由此被納入表演者范疇。《羅馬公約》和WPPT對“表演者”概念做出規定后,并沒有對“表演”也做出規定,在國際條約和我國的著作權法規定的表演行為屬于面向公眾的表演行為,并沒有規定表演行為地和觀眾所在地必須是同一的。
所以本文認為不論表演者是通過肢體動作或面部表情,或者通過解讀作品引導他人進行表演,亦或通過操作機器設備終端實現遠程信息輸入,只要他以自己的方式使的原作品的個性化內容得以展示,就可以認定他構成對原作品的表演,從而可以被認定為表演者,享有著作權法規定的表演者權利。音樂家通過琴鍵完成對音樂作品的表演,那游戲玩家通過控制并操作電子設備完成對游戲的表演,這兩者之間并沒有實質性區別。再者如果戲劇舞臺表演被固定為電影,構成作品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是現場的戲劇舞臺表演只能是對作品的表演,就是因為被固定在有形載體上的表演具有唯一性,現場表演每次都是不一樣的,具有不確定性。網絡游戲更是如此,同一玩家在不同時刻操作形成的游戲整體畫面不同,因此游戲直播也只能視為對游戲作品的表演,而非類電作品。
我們把游戲玩家的行為認定為對游戲作品的表演,那學者也沒有討論游戲整體畫面是否屬于作品的必要,因為作品的表演可受到著作權中表演權控制,包括游戲主播的以直播形式進行的表演行為。這樣學術界關于游戲主播身份的爭議,游戲直播畫面是否屬于作品的爭議,以及權利沖突問題就可以得到梳理和解決。總之,如果認可游戲玩家的表演者身份,則其對游戲作品的表演行為可由游戲開發商通過著作權人的表演權控制,游戲整體畫面可同時受到作者的著作權和表演者鄰接權的控制,相應的權利邊界在現行著作權法體系下也比較容易界定。與網絡游戲直播相關的法律關系可得梳理,相應的權利沖突問題可得到解決。
參考文獻:
[1]王遷.電子游戲直播的著作權問題研究[J].電子知識產權,2016,(2):11—18.
[2]蔣一可.網絡游戲直播著作權問題研究——以主播法律身份與直播行為之合理性為對象[J].青年法苑,2019 年第7 期.
[3]劉銀良.游戲網絡直播的法律關系解析[J].知識產權,2020,17-26.
[4]祝建軍.網絡游戲直播的著作權問題研究[J].知識產權,2017,(1):25—31.
[5]焦和平.網絡游戲在線直播的著作權合理使用研究[J].法律科學,2019,(5):71-81.
[6]朱藝浩.網絡游戲直播畫面的著作權定性及歸屬規則[J].人大法律評論,2018年,(3):331-337.
[7]劉超 .網絡游戲及其直播的法律適用———以“耀宇訴斗魚案”為例[J].福建警察學院學報, 2016,(3):94 -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