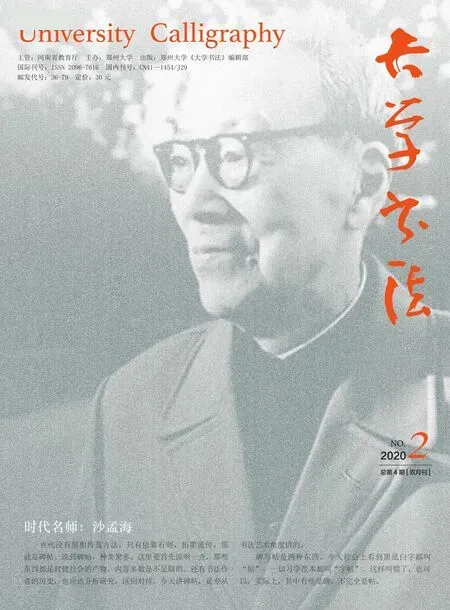論書法專業古代漢語子課程的設置問題
⊙ 楊吉平 宋金京
作為相對而言的新專業,每個高校在書法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上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作為專業基礎課程,古代漢語則是每個學校書法專業都在開設的必選課程。而在不同的院校,除了古代漢語課程之外,還開設了與之相關的子課程,但所開課目則有區別。這些課程可以歸入專業基礎課程、專業主干課程、專業選修課程這三類課程之中。
對書法專業而言,古代漢語課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古代漢語的經典教材—王力先生主編的四冊本《古代漢語》,基本涵蓋了古代漢語所有的知識。此教材體例科學,內容豐富,文本選用合理,校對質量也高,應該是書法專業古代漢語課程的必選教材。學習古代漢語的主要作用是幫助學生解決閱讀使用古代漢語的基本問題,即語言問題、文字問題。語言問題要解決的是古代漢語的詞匯、語法、修辭等問題;文字問題要解決的是字音、字義、字形三大問題。從本質上而言,書法是古典農耕文明的產物,能夠進入古漢語語境,才能進入書法藝術的語境,這就是古人所說的由“技”達“道”、由“書匠”到“書家”的飛躍,古代漢語的主要作用就是這種飛躍的中介。
古代漢語的子課程,首先便是專業基礎課—現代漢語。現代漢語表面上看與古代漢語不同,但其實質內容則是古代漢語的基礎。現代漢語的主要教學內容仍然是語言文字,但與古漢語的區別是講授內容為現代漢語,也就是相對于文言文的現代白話文。現代漢語教學應與古代漢語進行密切聯系,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其語法相對具有穩定性,詞匯也具有關聯性與延續性,兩者的修辭教學內容也有許多類似之處。尤其在語音、文字這兩部分,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更是一個一脈相承、延續發展的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而文字與書法的關系又是合二為一的密切關系。在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漢語便是古代漢語的預科課程,上好這門課是上好古代漢語的基礎。
而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現代漢語當然也有其獨立的教學價值。古代漢語主要培養學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文言文寫作則不是古代漢語的教學任務。現代漢語除了培養學生閱讀白話文的能力,還需要培養書法專業的學生具備語言表達的能力,這種表達分為口頭表達和書面表達兩種,而尤以解決學生寫作中普遍存在的語言、詞匯、語法、修辭問題為重(應用文寫作課程與本文關系較遠,在此不作討論)。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漢語的教學內容要大于古代漢語。
現代漢語教學與古代漢語教學的關系,可以舉例說明。例如在詞匯教學中,可以通過講解分析學生耳熟能詳的詞語去探求古漢語詞匯與現代漢語詞匯的關聯關系。比如,“妻子”在古代漢語中指兩種人,即現代漢語中的妻子和兒女,其中的“妻”就是現代漢語中的妻子,“子”就是現代漢語中的兒女。又如《史記·秦本紀》有此句子:“秦每破諸侯,寫仿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其中“寫”的詞義對學生來說比較難理解,教師完全可以啟發學生聯系“寫意、寫實、寫生、寫照”等現代漢語詞匯中的“寫”對之進行理解性聯想,讓學生通過古今詞義的聯系記住“寫”在此處為“模擬、仿照”的意思。當然,這種教學方法實際上對教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本身先要打通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二者之間的壁壘,并培養語言比較的思維習慣,才能很好地完成兩門語言課程的教學任務。
第二是中國古典文學課程,該課程應屬于專業選修課。古典文學與古代漢語關系密切。一方面,古代漢語課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經典的古代文學作品作為閱讀范本進行教學活動的;另一方面,這兩門課程的教學任務也是密切相關的。古典文學課程的主要教學任務是培養學生閱讀、欣賞、分析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能力;古代漢語課程的主要教學任務是學會給古書標點斷句和把文言文翻譯成現代文,培養學生閱讀和理解文言文的能力。前者屬于文學藝術課程,重在提高文學欣賞水平;后者屬于語言課程,重在培養古代漢語閱讀能力。但作為日常使用現代漢語的當代人,二者都要落實到培育學生學習文言文的能力上。因此,書法專業的古典文學課程教學,是建立在學好古漢語知識基礎之上的,是必須的。可見古典文學課程在書法專業中的重要性,也因此書法專業的古典文學課程在專業課程中的課時與學分占比都應該是最高的。書法自古以來就與中國的古典文學、古典文化緊密相連,二者相互影響、互為補充。王僧虔在《筆意贊》中提出:
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1]
其意就是說,在進行書法創作時不能僅停留于追求外表的美觀,更要追求其內在的精神內涵,而這種精神內涵的取得,許多程度上源自于書法創作者深厚的文學、文化底蘊的支撐。書法藝術作為農耕文明的產物,本身便根植于古典文學的沃土之中,所以古人在這方面的學習內容是得天獨厚的,對于文學素養水平的訓練是常態的。當代教育當然不可能像古人那樣只念好四書五經、唐詩宋詞之類便可,但書法藝術作為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化素養必須盡量接近古人,古典文學素養必須要達到一定水平。反觀當下的高等書法教育,許多學校在教改過程中不斷消減文化課程的數量,以至于取消了古典文學課程,這直接導致了學生對古典文學相關知識的缺失,也使學生在書法學習過程中只能關注到技巧層面,失去了提高文化修養、豐富精神內涵的機會,這樣的狀況延續下去勢必會阻礙書法教育未來的發展。
第三是文字學課程,這門課應歸入專業主干課程。清代以前的人上學讀書一般先從讀《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開始,然后四書五經、諸子著作、二十四史等。如前所述,書法產生于農耕文明時代,書法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正適合《說文》與四書五經一類教學內容。而《說文》的學習在古代屬于小學的范疇,在現在則屬于文字學范疇,因其難度,對當代人來說反而成為“大學”了。
文字學首先研究的是字義(訓詁)和字音(音韻),書法專業的學生不過文字的字音與字義這一關,古代漢語便很難學好,與之相關的古代書論、古典詩文便難以讀懂及運用。
書法是書寫文字的藝術,文字是書法的載體。現代文字學除了研究字音、字義,主要研究的是字形,這與書法直接相關。早在殷商時期,甲骨文就已有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了,它的形體結構和造字方式,為后世漢字和書法的發展奠定了原則和基礎。傳統的“六書”造字法包括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等,其中的指事、會意、形聲造字法又都是以象形為基礎的造字方法,都與字形關系密切。這就是說,文字學與書體研究關系密切,這是該課程成為必修課程的主要原因。
另外,《說文》的檢字法是以文字學原則來劃分的,而不是以部首檢字法原則劃分的,因而對學習者有提示詞義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幫助學生弄清造字的原理,理解式地去學習古文字形(尤其對篆書、篆刻創作中記憶字形作用明顯),而非死記硬背。這樣可以較大程度上減少書法專業的學生在書法創作中出現文字性錯誤的問題。
第四是詩詞欣賞與寫作課程(也有稱為詩詞寫作課程、古詩文欣賞與寫作課程的),該課應歸入專業選修課程的必修課程。書法作品的文本內容(書寫內容)以古詩詞居多,學會欣賞、寫作古典詩詞是對書法專業學生的基本要求。王力先生的《詩詞格律》摘編自他的《古代漢語》第四冊的詩律和詞律部分,但這是一本屬于語言學的著作,只討論聲韻、詩詞格律及相關語法問題,而不涉及詩詞寫作方法及欣賞方法的問題,而寫作與欣賞部分應屬于古典文學范疇。所以說,詩詞欣賞與寫作課程屬于古代漢語與古典文學相結合的綜合性課程。為此,筆者編著了專門的詩詞寫作與欣賞課程教材《詩詞作法通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該教材便有“詩的寫作方法”“詞的寫作方法”“詩詞欣賞的方法”三章內容。在這個意義上講,詩詞欣賞與寫作課程算是古代漢語與古典文學兩門課程的子課程。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2]對于書法專業的學生則可以說“不知詩,無以書”。書法專業的學生除了學習臨摹經典碑帖、了解基本的書法理論及美學知識,還要注重自主地進行詩文寫作與欣賞的系統訓練,從而在文化體驗上更接近書法藝術的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國內開設書法專業的院校大多依附于美術學院或者某一專業,在課程設置上產生了分歧:應該按照書法的專業特殊性來獨立設置,還是按照傳統的美術類學科來設置?這樣的爭議已經存在多年,卻依然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而現在的基本情況是,大部分院校專業技法課占據了大量的課時安排,而相關文化理論課程則占比較小,這直接導致了“重技巧,輕理論”“重實踐,輕文化”的局面,而這種局面應該得到改變。
還須提及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是中國文科類大學和綜合類大學最早開設的專業之一,古代漢語課程則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專業基礎課。從性質上看,古代漢語課程是一門基礎知識和應用能力并重的課程,而古典文學、詩詞欣賞與寫作課程也應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子課程,這些課程能夠幫助學生更好地培養語感與閱讀古籍的能力,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培養學生的語言實踐能力,要求學生在熟練地學習古代漢語相關知識的前提下,培養出欣賞古典文學作品甚至寫作古典詩文的能力。而實際現狀是,各大學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幾乎都沒有開設單獨的古詩文欣賞與寫作的相關課程,這是不正常的、不應該的。而書法專業作為延續中華民族文脈的專業,應該擔當起漢語言文學專業未能擔當起來的歷史使命,這樣可以進一步樹立起書法專業的權威地位,使這個專業不斷走向成熟,最終取得和一些傳統專業相同的甚至是更高的專業地位。

陳大兵 章草 戰國·子思《中庸》三章 昭通學院(本科)
注釋:
[1]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62.
[2]錢穆.論語新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