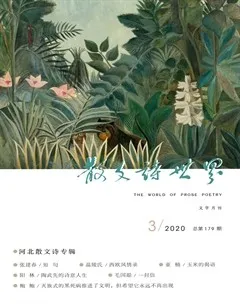陶武先的詩意人生(外一篇)
陽林
李白花前飲酒,蘇軾赤壁抒懷,鄭板橋癡眼望竹,陶淵明種菊東籬,縱然這世界動蕩沉浮、光怪陸離,在生活中握一分詩意的底色,便如花有了香,山有了樹,水起漣漪,畫龍點睛,日常俗世的種種,平淡中有心動,瑣碎里有溫情。能有這樣生活狀態的,需超脫的心胸與格外的慧根,現在的陶公便是這樣,愜意地過著自己的詩意人生。
陶公曾是仕途中人,我與他交往多年,一直認為他是最沒有“官氣”的一個,其素樸正直、親切慈祥。他很早就具有“詩人自覺意識”,看待事物時目光獨特、全面且客觀,思考也更為深邃。他曾說過,若以時間為線來劃分,人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而每個階段,都有它所須肩負的責任。
成長階段是從出生到就業,這段時間的主要任務是長身體、長知識,以學習和吸收為主,從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孩,成長為具備一定科學知識與能力素養的人。接著是從參加工作到退休的漫漫過程,人們通過不斷學習和實踐,做更多有益工作,為社會做更大貢獻,以此獲取人生的價值感和成就感。當然,最后的階段便是從退休一直持續到終老,保重身心,健康長壽,成為要務。
在人們的印象中,詩人放達飄逸,官員中正端嚴,仿佛這是兩種水火不相容的性格特征,在退休前后的陶公身上,卻“轉換”得如此順暢,平滑過渡,簡直讓人疑心他和“竹癡”鄭板橋是同類人物,一輩子都在勤勤懇懇為官,踏踏實實為老百姓謀福利。但骨子深處的詩人氣質,浸潤了人生旅途,在他們身上,官員與詩人,兩種身份毫不沖突,完美融合,甚至彼此助益,以詩人之細膩情思,關注民生之微,又以官員之高屋建瓴,賦詩氣象萬千。
陶公剛退下來時,手邊還有兩本理論書尚未看完,正式離開工作崗位那天,他啪一聲果斷關上理論書,切換到自己的“興趣”頻道。從這天起,看的書、做的事,大都服務于興趣,而非其他。年過六十的陶公,終于有了閑暇時光與舒怡心態,游弋于詩詞之中,偶有一句“妙得”,便有十足的愉悅情緒,從內心冉冉升起。
陶公的《畫堂春·春蘭》,讓人百讀而不厭:婆娑弄影映南窗,風回幾縷幽香。楚辭相識度炎涼,含笑伴春光。不慕浮華塵世,鐘情寧靜蕭墻。青妍何必抹濃妝,素雅自流芳。
古人詠蘭,多見“孤傲”之意。自屈原在《離騷》中濃墨重彩感情充沛地寫蘭花、喻君子,后世文人再寫關于蘭的詩詞,都將蘭花“架”上了寂寞君子的高位,而陶公起首便是“婆娑弄影映南窗”,仿佛是一幀絕美的電影畫面,主角未出場,映入觀眾眼簾的是“南窗之影”,這影又是“婆娑”的,裊娜、神秘、簡素、克制,美中又帶三分怯。
楚辭與屈原,成就了幽蘭之美,花中君子,從此傳世聞名。但陶公用一句“含笑伴春光”,將神壇上的“君子花”詠成了知冷知熱知肺腑的良伴。孤傲之人,常年板著臉孔、苦著心腸,又怎會“含笑”?又怎肯“屈尊”和百花相伴,共享明媚春光?單是上闕,便大為改寫了人們心中對蘭花“不敢親近”的隔膜感和距離感,花中君子,也是如此可親可近可交流的,不再郁郁寡歡,不再孤芳自賞。這又何嘗不是詩人陶公自己的人生寫照呢?
擁有細膩而深沉的情感“觸須”,是一個詩人的天賦所在,更是架通心與心之間無隙交流的橋梁。陶公為官多年,從未有哪一日丟棄過誠懇樸實之念,他以自己的一顆心去體悟民心,以自己的寬慈關愛,去切實幫助他人,和基層人民,真正能水乳交融地打成一片。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陶公趕往青川指導救災。當他看到青川木魚中學的娃娃遺體無法認領,就那么擺放在露天中,小小的尸身開始散發臭味時,他竟克制不住心里翻涌的悲痛,雙眼發紅,攥緊拳頭,在原地走了幾圈,才讓理智恢復正常,平靜情緒,向抗震救災的干部提出了明確和具體。那一刻的陶公,不僅僅是一個省領導,他是父親,是家長,是有血有肉的人,為天災落淚,為幼小無辜的生靈落淚,更為大災后人們的惶恐、慌亂、無措落淚。
陶公后來含淚書寫了《震區情》,山河破碎,傷亡慘重,是災禍橫降,災區人民奮起自救,各路大軍緊急救援,是情滿人間。傷痛與悲壯,凝于筆尖,陶公一筆一劃,如舞金戈,如立大椽:
地動驚濤裂岸,山崩亂礫飛煙。霾壓叢林留斷壁,風嘯邊城落廢垣。悲啼血雨天。
童叟相依凍餒,寡鰥互慰孤單。疾度懸危泥濘路,痛解生靈破碎間。愛憐同宇寰。
一個真正的詩人,一定是擁有一種大的悲憫情懷,他不僅僅局限于咀嚼自己的小情小緒,而是有著為民眾承擔苦難的勇氣。正是純粹至真的悲憫心腸,令陶公在任時,成為了眾所公認的、嚴格講究“認真對待每個小人物、做好每件小事情”的領導。
陶公曾經在一次春節前,帶隊去一個邊遠山區慰問困難戶。交談之中,了解這家人之所以困難,是在于一個“病”字:一家三口,全靠男人在鐵路上辛苦工作,每月賺八百多元,這家女人患有嚴重的腎病,每個月需要兩次血液透析,一次兩百多,一個月就要花掉家庭總收入的一半,剩下一半,還要供養孩子念書,供家庭各項開支,難免捉襟見肘,苦于應付。陶公將當地主要負責人拉到一旁,問他有沒有辦法,將這家患病女人治療期間的透析費用給解決了?這名負責人當即表態,下去就想辦法解決此事,陶公還找了當地人大主任當“監督”,開玩笑說如果你解決不了,就由我來辦。主要負責人表態說他一定辦到,不負囑托。
倘若只是給這家貧困戶在春節慰問時送點水果米面,再說幾句祝福的吉祥話,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明年這家照樣受病拖累,無法步出更加困難的行列。陶公也深知自己能力有限,“解放全人類”,那是理想的期盼,但遇到問題,不能逃避,解決一個就少一個問題。
陶公去慰問一家企業的貧困戶,發現這個貧困戶情況有些特殊,她身體有點毛病,不過生活自理無大礙,四十歲左右,一個人生活。陶公出門和工會的女同志講:“你們能否幫幫忙?”工會女同志不解陶公何意,陶公笑稱:“你們多費費心,幫著給這位同志介紹一下對象,讓她家庭得以完整,明年來了,說不定非但不是困難戶,還是和諧家庭。”
陶公的話,讓工會幾位女同志呵呵笑,這卻是陶公的肺腑之言。這位困難戶,她困難的根源在于一個“獨”字,解決了婚姻問題,才能讓她真正安樂地生活。這是實質性問題,既然遇到了,就不要回避,而應該去分析,去解決,開一劑“方子”,指一條“活路”。
陶公真是這樣想的,勿以善小而不為。看起來,解決因病致貧人員每月的透析費、解決困難戶的婚姻問題,都是小事,但正因為陶公采取了自己鮮明的“個性態度”,去真正做了實事,哪怕這實事如此細微,多多少少也會對基層干部帶來一點影響,讓他們有機會養成更為細致的工作作風。這種激勵作用,勝過于在大會上反復倡導,在文件中重點指出,這是一堂有血有肉有態度的“現場課”。
千年前的蘇軾,曾留名言“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不管他到哪個地方任職,凡事都盡力而為,以出世的態度干著入世的事業。在惠州,蘇軾設計了廣州最早的自來水供水系統,在黃州,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孤兒院,在徐州,不追求任期效益,帶著百姓老老實實大修水利……真正的詩人,心是和民眾系于一處的,接地氣、慰蒼生、得民心。蘇軾也好,陶公也罷,他們為官時,是真正值得人尊敬與愛戴的好公仆,不存作秀之念,不持面子之思,所念所想,所作所為,憂庶民、行實事,都出自一顆詩人高貴而純粹的真心,細膩又深沉。
許多人從高位退下來,便覺得各種不適,頓感人生惶惶,目標盡失,到底意義何在?陶公卻能迅速將他的退休生活過得詩意盎然,多彩多姿。并不是退休讓他忽然“啟悟”,而是他的性格中,一如既往便是如此的真誠豁達,面對自己不矯飾,面對他人不浮夸,縱然離開仕途,不過是換了另一處風景看人生,他樂得興趣十足地享受生活、體味人生。
陶公偶爾垂釣一下,他喜歡“穩坐釣魚臺”時的從容淡定,有魚兒上鉤時的警覺機敏,即使枯坐一天釣不上一尾魚,也不改快樂依舊。他欣喜于親嘗過程品百味,有所體悟與獲得,結果并不重要。陶公笑言,爭強斗勝這種事,不適合“晚來釣翁”。釣魚的陶公,也會詩興大發,佳句天成,揮筆寫下了“橫桿點破一江滄”。這一句詩璞玉渾然,又氣勢開闊、寓意深遠,細細一截釣魚竿,如同俠士寶劍在握,干將莫邪,誰與爭鋒?一個“破”字,實在是神來之筆。
陶公選擇打乒乓這項活動,作為退休生活的“健身首選”,還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對于老年人而言,打乒乓的好處,首先是運動成本低,地方相對容易找到,乒乓球有時一個月都打不爛一個,經濟價值實在不高;其次是運動壽命長,六十歲的老人可以打,那么七十歲、八十歲呢?照樣可以打,因為它活動半徑不大,老人不用打一場球跑得氣喘吁吁,這項運動愛好,可以一愛就是多年;最后是運動傷害小,沒有太大沖撞性,對于老人而言,可以選擇“溫和”的方式打球,而不必顧慮劇烈運動給身體帶來的傷害隱患。陶公愛上乒乓之后,還童心未泯地賦詩贊嘆:小小銀球飛夢想,悠悠弧線放光華。
退休后的陶公,讓人驚喜地發現了他曾是被仕途所“掩蓋光芒”的詩人,才華熠熠,佳作迭出。他對故鄉充滿愛,“平生在蜀,古稀尋蹤”,下筆便是美麗畫卷,灑滿陽光的攀枝花是“兩江映碧座青山,四季浮香伴木棉”,渾然險峻的劍門關是“萬夫不敵雄關險,千載曾嗟蜀道難”;陶醉于銀杏秋色:“瓊枝金葉灼西窗,盡染高天淡抹墻”;他抒發著幽幽古情:“莫道風塵留故事,從來歲月鑒知音”;真心贊頌著平凡的綠化工人:“櫛風沐雨叢中笑,調色留芳世上春”;他也描繪著深山春早圖:“杜鵑破曉啼空谷,笑語村姑采早霞”;他感嘆年歲光陰:“不負青云志,當還白首魂”……陶公的詩詞,取材平實,用語從容,卻在這凡俗之景中,勾畫出了不一樣的人生大美。這是常常被我們所遺忘的美,沉淀著豐厚深邃的感受,一讀之下,只覺眼前如畫,再讀,齒頰留香,三讀,思緒翩飛。每每誦讀,都有新意和所得,才知陶公詩句之妙,“言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
文如其人,詩傳心聲。陶公的詩詞寫作,從不攀附權貴,反而向“泥土”扎根,裝卸工、環衛工、建筑工等“藍領”盡皆入詩;大禹、李冰、司馬相如、諸葛亮等蜀地先賢躍然紙上。陶公是當代詩人中少有的涉筆于科技領域的創作者,這也源于他過往扎實過硬的工作作風,如今“文理兼備”與時俱進的生活態度,在書寫科技時,氣象萬千,聲勢磅礴:“難窮歲月鑒精英,不盡乾坤毓大成”。他發自內心地贊頌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古代的賈思勰、孫思邈、沈括,還是當代的華羅庚、袁隆平、李國杰,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國之重器”,值得陶公以壯美深情的詩行,書寫科技星光照亮世界的豪情飛揚。
一個真正忠于自己內心的詩人,不但具有細膩纖柔的“觸覺”,行走天地之間,感知人間冷暖,懷悲憫大愛之心,書“草根”之情感與尊嚴,還得保持一顆清醒警惕之心,不時跳出舊日窠臼,重新觀照和打量,思索和推敲,給出更為理性的認識。陶公認為“愚公移山”精神可嘉,但其行為方式值得商榷,說放在當今角度看,愚公移山,不如智叟修路成本低,其而且影響生態平衡,他為何一定要和一座山死磕上呢?不如另辟蹊徑,或者干脆搬家,這也好過“子子孫孫”都跟著他做一件艱苦浩大任務,將大好年華全都花費在賭氣與固執上吧?
即使面對自己非常喜愛的大詩人蘇軾,陶公也并不盲從,他讀了蘇軾的《題西林壁》,認為“即景明理,耐人尋味;余興未盡,拙和一首”。蘇軾寫“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陶公相和為:“要識匡廬真面目,還須出入此山中。” 若一葉障目,人們何不拿開遮眼的葉子?若不識廬山真面,何不“能出能入”,視線遠遠近近、深深淺淺,發現與探究,而不是只余嘆息,只留嗟嘆。陶公在詩歌中表現的、極為可貴的反思精神,其實與他的“科技思維”一脈相承,不盲從于權威,不迷信于經典,面對先賢前輩,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這讓陶公的詩詞,情趣、意趣與理趣并重,讀來讓人受益匪淺。
經歷了人世七十余年的風雨洗禮,走過了山川大海,看過了世間百態,現在,陶公迎來了他寫作的“黃金時代”。豐厚的生活積淀、深厚的文學功底、開闊的寫作視野,讓陶公之詩詞如被歲月磨洗的玉石,顯出了生命本真的意義。
陶公是個認真的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他“適應時世,方圓自我”,盡心盡力完成了自己所肩負的任務。在應該用功學習、苦練本領的階段,在需要忘情工作、無私奉獻的階段,他都牢牢把握住了時代的要求,社會的需要,真心實意去付出去實踐。那么,在人生的第三階段,他欣然愿意聽從內心的聲音,選擇去做一個快樂自在的老人,一個真情真性的詩人,恬淡而安然地享受幸福的退休時光,讓平凡日子過得充滿詩意,全情投入,自在達觀,不亦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