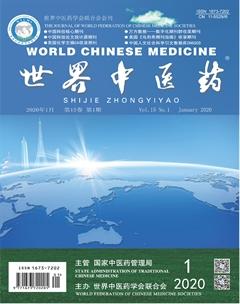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感染性肺炎現代中醫診療建議方案與探討
王金榜 梁保麗 孫樹椿
編者按:自2019年12月以來,以我國湖北武漢地區為中心,全國各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持續增加,現已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全球性暴發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形勢嚴峻。疫情發生以來,全國醫療工作者奮戰在防疫一線,在防治過程中,中醫藥彰顯了特色和優勢。
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繼承人,河北省中醫院中醫藥特色研究室主任王金榜教授是國醫大師李士懋先生的開門弟子,一直秉承“堅持中醫思維與核心價值觀指導下的現代中醫臨床,突出中醫藥特色,提高綜合服務能力和救治水平”的理念,從事中醫溫病學、中醫骨傷科教學及臨床、科研35年,對溫病學多有研究和體會。根據國醫大師李士懋先生“平脈辨證”的思辨體系和國醫大師李佃貴教授的“濁毒證”理論體系,王教授對武漢疫區及全國各地的疫情及防控、診療方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思考,綜述如下,以饗同道。
文中觀點僅供參考、交流之目的,不代表本雜志社觀點。歡迎業界同仁共同討論,分享體會。
摘要?自2019年12月以來,以我國湖北武漢地區為中心,以人群集散輻射傳播為特點,全國各地病例陸續出現增加。疫情發源地罹患患者早期以身熱不揚、干咳氣促、身楚乏力為主要癥狀,以脈濡緩、舌苔厚膩、胸部X線檢查顯示炎性反應性改變為特征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感染性肺炎為主的新型傳染病。疫情傳入地的患者早期癥狀由于地域的不同,有所差異。各地傳統中醫、現代醫學先后集體或個人出臺了相關診療方法和建議方案。作為現代中醫,按照習近平主席:“遵循中醫發展規律,傳承精華,守正創新”和“中西并重”的指示精神。為規范這一新型傳染病“瘟疫”的認知和診療,綜合相關資料,根據疫情演變規律,結合個人經驗與體會,特此探討COVID-19感染性肺炎的診療建議方案。
關鍵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濕濁瘟疫;診斷與辨證;治療;解表化濕;宣暢氣機;清熱解毒;開竅醒神;醒脾化濕;新加升降散;宣白承氣湯;涼開三寶
Suggestions?and?Discussion?on?Diagnosis?and?Treatment?of?the?Novel?Coronavirus(COVID-19)Infectious?Pneumonia?in?Modern?Chinese?Medicine
WANG?Jinbang1,LIANG?Baoli2,SUN?Shuchun3
(1?Characteristic?Research?Office?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Hebei?Hospital?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Shijiazhuang?050011,China;?2?The?Third?Hospital?of?Hebei?Medical?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51,China;3?China?Academy?of?Chinese?Medical?Sciences,Beijing?100700,China)
Abstract?Since?December?2019,the?number?of?pneumonia?cases?caused?by?the?novel?coronavirus(COVID-19)has?been?increasing?in?China.The?center?of?the?novel?coronavirus?is?in?Wuhan,Hubei?Province,with?the?characteristics?of?population?distribution?and?radiation?transmission.In?the?early?stage,the?main?symptoms?of?the?patients?in?the?origin?of?the?epidemic?were?lack?of?body?heat,dry?cough?with?shortness?of?breath,and?lack?of?strength?in?body.At?the?same?time,the?main?signs?of?the?patients?were?smooth?and?slow?pulse,thick-greasy?tongue?coating,and?inflammatory?changes?on?chest?X-ray?examination?in?this?new?infectious?diseases.The?early?symptoms?of?patients?in?the?epidemic?area?are?different?due?to?different?regions.Many?researchers,including?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modern?western?medicine,have?issued?relevant?diagnosis?and?treatment?methods?and?suggestions?in?the?name?of?collective?or?individual.Modern?Chinese?medicine?should?follow?the?instructions?“Following?the?law?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development,inheriting?the?essence?and?keeping?the?initiative?and?innovate”?and?“Emphasizing?both?western?medicine?and?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by?chairman?Xi?Jinping?in?relevant?work.In?order?to?standardize?the?cognition,diagnosis?and?treatment?of?the?novel?coronavirus(COVID-19),the?writer?hereby?discussed?the?suggestions?for?diagnosis?and?treatment?of?the?novel?coronavirus(COVID-19)according?to?the?relevant?data,the?law?of?epidemic?evolution?and?personal?experience.
Keywords?Novel?Coronavirus(COVID-19)/2019?Novel?Corona?Virus(2019-nCoV);Pneumonia;Damp?turbid?plague;Diagnosis?and?syndrome?differentiation;Treatment;Relieving?superficial?dampness;Promoting?Qi?movement;Clearing?heat?and?removing?toxicity;Inducing?resuscitation;Enliven?the?spleen?and?resolve?damp;Xinjia?Shengjiang?Powder;Xuanbai?Chengqi?Decoction;Liangkai?Sanbao
中圖分類號:R512.99;563.1+9;R254.3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20.01.007
自2019年12月疫情爆發以來,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第一批國家專家到達武漢,第一時間(2019年12月31日)發現并命名了本病是由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即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引起[1]。2020年1月2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委派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劉清泉教授、廣安門醫院齊文升教授等緊急奔赴武漢,深入臨床一線,調研和診療疫情,先后觀察、會診200余例患者,并與武漢當地專家研討,獲取大量信息,初步制訂了本病的中醫證治方案,提交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專家組進行討論,納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印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中發布[2]。截至2020年1月26日24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收到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2?744例,重癥病例461例,累計死亡病例80例,疑似病例5?794例[3]。2020年1月24日Lancet在線發表題為“Clinical?features?of?patients?infected?with?2019?novel?coronavirus?inWuhan,China”的研究論文,認為發病時的常見癥狀為發熱(40/41例,98%),咳嗽(31/41例76%)和肌痛或疲勞(18/41,44%)。40例患者中有22例(55%)出現了呼吸困難[4]。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本病常見的臨床表現為發熱、乏力、干咳為主要表現,少數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腹瀉等癥狀。重癥病例多在一周后出現呼吸困難,嚴重者快速出現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膿毒癥休克、難以糾正的代謝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礙”。值得注意的是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為中低熱,甚至無明顯發熱。部分患者僅表現為低熱、輕微乏力等,無肺炎表現,多在一周后恢復。多數患者預后良好,兒童病例相對較輕。死亡病例多見于老年人和有慢病患者[2]。期間,全國各地先后出臺了具有當地特點的中醫診療方案。
如何把握本病的流行病學特點和診治規律,我們對武漢疫區及全國各地的疫情及防控、診療方案進行了研究與思考,以期正確認知,準確用藥,提高臨床療效,降低危重癥發生率,減少病死率,增加治愈率,更好地體現和發揮中醫藥的作用和作為。西醫學對本病雖然檢測方法、重癥救治技術先進,但治療上尚缺乏有效的藥物。而中醫學對“瘟疫”的認知有悠久的歷史,有豐富的診療經驗。“天人合一、取類比象”的形象思維與“整體、融合、動態、辨證、中和、治未病和人文關懷”的核心價值觀,古老而先進,全面而系統。遵循習主席“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的指示精神,結合現代科技成果檢測檢驗方法和先進可靠的救治技術,充分發揮中醫藥特色,建立更加全面、完整、系統的“現代中醫診療模式”,特此從現代中醫角度對本病的概念與發病,流行病學與病因病機、診斷與辨證,分期分型中藥治等進行了回顧性研究,為規范這一新型傳染病“瘟疫”的認知和診療,促進中醫藥發揮更大作用,特此探討《COVID-19感染性肺炎的現代中醫診療規律》的建議方案。
1?關于COVID-19的概念與發病
1.1?概念?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是中國醫學專家發現而命名的。屬于β屬的新型冠狀病毒。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指出:“溫疫之為病,……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COVID-19為“濕性濁毒”,屬于天地間的雜氣之一,為天行之氣,包括在“疫癘之邪”的范疇。疫癘之邪又稱“癘氣”,是六淫邪氣中具有強烈傳染性,并能引起廣泛播散、流行的一類致病因素,又有“雜氣”之稱。其所導致的疾病為“瘟疫”,隸屬于溫病的范疇。
溫病命名大都和季節密切相關,唯獨“瘟疫”是以致病特點命名的。《溫病條辨》記載,溫病者,有風溫、有溫熱、有溫疫、有溫毒、有暑溫、有濕溫、有秋燥、有冬溫、有溫瘧,計有9種溫病。其中溫疫是指發生于一定季節,感受疫癘之邪,具有強烈傳染性并能引起廣泛流行的急性外感熱病。吳鞠通自注曰:“溫疫者,厲氣流行,多兼穢濁,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素問·刺法論》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是說溫疫具有廣泛流行性和強烈的傳染性。“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是說善于養生,正氣充足的人就不會被傳染發病。本病湖北武漢疫區COVID-19及其感染性肺炎具備流行性、傳染性,屬于急性傳染病,且以上焦肺系和中焦脾胃為主要病位的傳染病。
1.2?發病特點?武漢地處荊楚大地,漢江平原的東部。市內江河縱橫、湖港交織,水域面積占全市總面積25%。2019年12月以來陰霾冷雨纏綿不斷,地域更顯潮濕。氣候屬北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具有常年雨量豐沛、日照充足、雨熱同季、冬冷夏熱、四季分明的特點,冬季平均氣溫在0~8?℃。自2019年12月進入冬季,時值冬至前后、數九寒天,本該寒邪當令而未至,氣溫應寒而反暖。“應寒反暖,非其時而有其氣”,不時之氣留連持續。這樣,天暖地濕,濕熱氤氳,而易產生疫癘之邪的“濕性濁毒”。這種氣象物候異常是本次疫情發生的外在病因基礎。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九省通衢”的武漢,不但具有鮮明的物候特點,而且具有“江河湖泊并存,因水而生,得水而興,靠水而居”的地理特征。特殊的地域文化,孕育了獨特的生活方式。由于人們“攝生不當”,膳食多以“魚蝦”等寒性的水產品為主;居處也多潮濕寒冷;社區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參差不齊[5],加之運動不當等多種因素傷及脾胃,以致形成脾失運化的濕性體質,形成本次疫情發生的內在病因基礎。“同氣相求”,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感染“濕性濁毒”(COVID-19)的疫癘之邪而發病。
除了武漢疫區發病的地域特點以外,全國播散輸入性感染地區的疫情,也表現除了較為明顯的地域特點。根據不完全統計中醫專家在武漢疫區掌握的200多例本病患者的發病與臨床資料表明,本病疫區的病因是以“濕”為基本屬性的疫癘之氣,“濕為陰邪,易傷陽氣,濕性黏滯,易傷脾胃,阻遏氣機”。發病季節具有“濕濁”或“寒濕”的物候特點;病邪性質具有“濕熱”或“寒濕”特性,因此,本病可歸屬于瘟疫的“濕熱疫”或“寒濕疫”,可統一命名為“濕濁毒疫”。其他地區的疫情雖有各地域物候特點和人的個體差異,而出現不同表現特點,但總不離“濕濁毒疫”的一般規律。
2?流行病學與病因病機
2.1?流行病學特點?從流行病學推斷,本病的傳染源主要是天行之氣的濕濁疫毒和罹患COVID-19感染性肺病的患者;其傳播途徑主要是人與人的傳播。自然界的空氣、飛沫和人與人的聚集相互接觸,通過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膚黏膜而傳播。吳又可說:“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他認為疫癘之邪感染人體“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邪從口鼻而入”,又說:“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其易感人群不分老幼,普遍易感,“皆相染矣”但總以濕性體質,正氣不足之人多見。老年人及有慢性病基礎者感染后病情較重,兒童及嬰幼兒也有發病。總之本病的流行病學特點可歸納如下。1)傳染源:目前所見傳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2)傳播途徑:經呼吸道飛沫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亦可通過接觸傳播;3)易感人群:人群普遍易感。老年人及有基礎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較重,兒童及嬰幼兒也有發病[2]。
2.2?病因病機
COVID-19致病具有特殊性。對本病的病因病機做出清晰的判斷,對本病的防護和醫學觀察、辨證論治和養護十分重要。現代中醫對“濕濁毒疫”的辨證是根據傳統中醫學“望聞問切”和現代臨床疫情監測檢驗的“五診合參”,確定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體質類型、證候類型和疾病狀態與階段,指導臨床救治和醫學觀察。
來自疫區的臨床資料顯示:本次武漢COVID-19感染患者的病史及早期癥狀的主要特點:1)具有流行病學的病史2)早期癥狀有發熱或不發熱。多數患者以發熱為主要癥狀,但表現為身熱不揚,不惡寒,也有部分病例不發熱;3)伴有肺系癥狀干咳、氣促、少痰,咽喉不利;4)伴脾胃癥狀,食欲不振,乏力倦怠,甚或惡心、大便溏瀉等;5)伴有口干,口苦,不欲飲;6)舌質多暗或邊尖稍紅,80%的舌苔表現為厚膩。7)實驗室檢測: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降低,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胸部影像學正常,或早期呈現多發小斑片影及間質改變,以肺外帶明顯[6]。可見,同一地域,由于感邪途徑和不同的體質的差異等,出現了不同的表現特征。因此,掌握疫情的大樣本發病規律,由此“審證求因,謹守病機”,通過辨證明確感染者的證候類型和個體差異,對疫情既要整體的觀察,又要動態的把握,采取“整體、恒動、辨證、治未病”的思維和方法,才能完整、系統的把握本病的病理演變過程,早期截斷病機,扭轉病勢,事前控制,爭取主動,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事中應對,事后忙亂,追擊于后,這樣才能更好的對疫情進行積極主動的論治和防控。
本病的病因是“濕濁疫毒(COVID-19)”其致病的病因病機是辨證的核心。國醫大師李佃貴教授的“濁毒理論”明確涵蓋并闡釋了本次疫情的病因病機。國醫大師李士懋先生“平脈辨證”思辨體系的核心是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平脈辨證,抓住辨證要點,才能早期判斷病機,對本病的辨證具有指導意義。李士懋先生明確指出:一個完整的辨證應包括“定性、定位、定量、定勢”4個方面,稱之為“四定”。
2.2.1?定性?即確定本病的陰陽寒熱溫涼的病性。患者脈象濡緩,平脈濡緩主濕。早期主癥發熱,身熱不揚,舌苔厚膩等均為濕性特點;加之COVID-19病毒產生的物候條件、流行病學特性,綜合判斷,COVID-19病毒具有“濕”與“陰寒”基本屬性的“濕性濁毒”。濕邪的基本特點為“濕為陰邪,易傷陽氣”是指濕邪具有陰寒的特征,所以仝小林院士稱之為“寒濕疫”;“濕性黏滯,易阻遏氣機”表現為病程纏綿,病程與潛伏期較長;“濕性重濁”表現為身體酸楚、乏力倦怠等。如果脈濡數,平脈則為濕租氣郁,郁而化熱;特別是在北方暖冬多風時節,又間有風溫襲肺,濕熱上蒙的證候,出現發熱、頭痛(如裹)、口干咽痛的癥狀。
2.2.2?定位?即確定本病的病理部位。患者脈象濡緩,或有寸沉無力,主濕阻中焦,清陽不升;早期主癥食欲不振,乃脾胃運化失常之象;同氣相求,濕邪“易傷脾胃”故多有脾胃消化系統的癥狀表現。《溫疫論》說“惟疫乃傳胃”;患者脈濡或沉而躁數,又主濕租肺衛肌表經絡,早期主癥或發熱,頭痛,干咳少痰,肌痛痠楚、咽痛等,乃肺氣不利,濕租肌表經絡之象。“肺主氣、司呼吸”“濕邪易阻遏氣機”故多有肺系呼吸道的癥狀和“不通則痛”表現。薛生白在《濕熱病篇》中說:“濕熱證,始惡寒,后但熱不寒,汗出,胸痞,舌白,口渴不引飲”,不僅確立了濕熱病的提綱,更加強調了濕邪阻遏肺脾氣機的病理病位。綜合判斷,本病早期病位在上焦肺衛(包括肌表經絡、呼吸道),中焦脾胃(包括肌肉四肢、消化道)。
2.2.3?定量?即確定本病的輕重程度。平脈辨證即可判斷本病的早期的輕重程度。如果脈象和緩則為正常體質;脈象濡緩則為濕阻輕證體質;脈象濡數則為濕郁化熱證;脈象濡滑數有力則為濕熱重證;脈象寸沉不足則為清陽不升證等,平脈是“觀其脈證,謹守病機,隨證治之”的重要指征。當然無論易感人群,還是罹患患者的主癥也是判斷病情輕重的重要指標。現代臨床檢測檢查技術更是要充分運用和判斷的特殊方法。但是,只有脈象更能早期、方便、準確的做出病情輕重的判斷。臨證能守善變,是醫者高水平的體現,守與變的原則是“謹守病機”,而判斷病機最重要的是平脈。本病雖然是濕性濁毒,病程纏綿,但畢竟是疫癘之邪,其變化多端不容忽視。平脈象、抓主癥、尊重現代檢測檢驗技術,綜合判斷,更能準確、及時的掌握本病的輕重程度,做出有效的處理。
2.2.4?定勢?即確定本病的變化、轉歸和預后。脈由濡緩轉為和緩則病輕向愈,脈由濡緩轉濡數、滑數、細數,或脈從有力轉無力,則反應病重病進。變化是疾病的基本特征。本病發病早期,由于濕邪的基本特性,早期變化相對緩慢,但是,“肺為嬌臟”,不容寒熱。中期一旦變化,就會發生嚴重的轉化,而發生重癥或危象。《溫熱論》指出“外邪入里,與之相摶。在陽旺之軀,胃濕恒多;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濕邪黏滯,日久閉肺,出現肺氣郁閉證;濕邪從陰則寒化,出現濕邪困脾證或邪伏膜原。濕邪從陽則熱化,出現熱入氣分,陽明熱盛證、陽明腑實證;肺與大腸相表里,肺氣郁閉與陽明腑實,肺失宣發肅降,與陽明腑實不通形成惡性循環的重癥;或從燥化傷陰,傷陰耗氣、熱盛動血,灼傷脈絡、瘀血凝滯,瘀閉心包,從而出現咳喘、呼吸困難、咯血的重癥。若不及時救治,則病情進一步加重,濕毒瘀閉神明,氣機閉阻熱厥出現“內閉外脫”的危癥,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而危及生命。所以及時的把握脈象,預判病機;密切觀察主癥變化,預判病情;實時檢測和監測生命體征、血氧飽和度等。可見早發現、早診斷,對本病的轉化、轉歸和預后做出前瞻性的判斷,從治未病的高度,謹守病機,或早期宣肺化濕,去除病邪,截斷病機,或升陽化濕,健脾和胃,扶助正氣,中期宣肺開閉,通腑泄濁,扭轉病勢,避免出現內閉外脫的危癥,是治療本病的一個關鍵環節。一旦危象顯露,及時的跟進呼吸機輔助通氣,甚至應用體外膜肺氧合(ECMO)等救治措施,中西醫結合,優勢互補,以期患者轉危為安,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死亡率。后期注意轉歸和預后,或清解余熱,或益氣健脾,或醒脾和胃,或活血通絡等,全程辨證論治,采取針對性措施,防止死灰復燃,病情反復。
綜上所述,本病的病因COVID-19可認定為“濕濁疫毒”具有“濕”的基本特性和“陰寒”的早期屬性;其病機的基本特點可概括為“濕(濁)、毒(熱)、瘀(血)、閉(脫)、虛(弱)”。單獨出現時證候單純較輕,復合出現時證候復雜較重,甚至危重。臨床當仔細診斷與辨證。
3?診斷與辨證
這次疫情是“濕濁毒疫”引起的急性傳染病,也已明確為COVID-19感染所致。全國各地的疫情防控現實和經驗教訓啟示我們,充分的利用現代檢驗檢測方法,明確診斷,發揮中醫藥“三因制宜”辨證論治的優勢和特色,實施“五診合參,病證結合”現代中醫思維模式,便于對疑似感染者和確診發病者,實施分類、分期、分型,有效的進行家庭個人隔離、醫學觀察和住院治療的管理,減少傳播感染明確疑似和確診病例,提高臨床治愈率,降低死亡率,保證防控治療效果,對疫情的防控和管理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3.1?診斷[2]
3.1.1?診斷要點
3.1.1.1?臨床表現?基于目前的流行病學調查,潛伏期一般為3~7?d,最長不超過14?d。以發熱、乏力、干咳為主要表現。少數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腹瀉等癥狀。重型病例多在1周后出現呼吸困難,嚴重者快速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膿毒癥休克、難以糾正的代謝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礙。值得注意的是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為中低熱,甚至無明顯發熱。部分患者僅表現為低熱、輕微乏力等,無肺炎表現,多在1周后恢復。從目前收治的病例情況看,多數患者預后良好,兒童病例癥狀相對較輕,少數患者病情危重。死亡病例多見于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礎疾病者。
3.1.1.2?實驗室檢查?發病早期外周血白細胞總數正常或減低,淋巴細胞計數減少,部分患者出現肝酶、肌酶和肌紅蛋白增高。多數患者C反應蛋白(CRP)和紅細胞沉降率升高,降鈣素原正常。嚴重者D-二聚體升高、外周血淋巴細胞進行性減少。在咽拭子、痰、下呼吸道分泌物、血液等標本中可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核酸。
3.1.1.3?胸部影像學?早期呈現多發小斑片影及間質改變,以肺外帶明顯。進而發展為雙肺多發磨玻璃影、浸潤影,嚴重者可出現肺實變,胸腔積液少見。
3.1.2?診斷標準
3.1.2.1?疑似病例?結合流行病學史和臨床表現綜合分析。流行病學史:1)發病前14?d內有武漢地區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續傳播地區的旅行史或居住史;2)發病前14?d內曾接觸過來自武漢市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續傳播地區的發熱或有呼吸道癥狀的患者;3)有聚集性發病或與COVID-19感染者有流行病學關聯。臨床表現:1)發熱;2)具有上述肺炎影像學特征;3)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有流行病學史中的任何一條,符合臨床表現中任意2條。
3.1.2.2?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具備以下病原學證據之一者:1)呼吸道標本或血液標本實時熒光RT-PCR檢測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陽性;2)呼吸道標本或血液標本病毒基因測序,與已知的新型冠狀病毒高度同源。
3.1.3?鑒別診斷?主要與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人偏肺病毒、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冠狀病毒等其他已知病毒性肺炎鑒別,與肺炎支原體、衣原體肺炎及細菌性肺炎等鑒別。此外,還要與非感染性疾病,如血管炎、皮肌炎和機化性肺炎等鑒別。同時還要與風溫病、春溫病、濕溫病、暑溫病、秋燥病、冬溫病和傷寒等鑒別。
3.2?辨證?目前,武漢的新增確診和疑似病例仍在增加,其他各地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都是經武漢輸入性病例,所以目前觀察到病例的病因屬性和病機特點大致相似。但由于不同的地域、感染途徑和感染患者的個體差異,隨著發病的不同階段,其病理類型各有不同。
根據COVID-19病毒肺炎的回顧性臨床觀察和瘟疫病的演變規律,本病總的表現出了“濕濁毒疫”本病天地人三毒合一的演變特點。早期病位在上焦衛分,以肺、脾病變為中心;中期重癥出現中焦氣分的病理改變,留戀從化,或郁閉肺氣,表里同病;或從陰寒化,傷及脾胃,清陽不升;或從陽熱化,氣分熱盛、陽明腑實,蒙蔽清竅或熱閉心包;中期危癥涉及下焦營血分,或從燥化,傷陰耗氣,灼傷脈絡,瘀血阻滯,甚至出現內閉外脫的危癥,出現肺、脾(胃、腸)、心(腦、心包)以及肝腎等多臟腑的功能失調;后期余邪留戀、或肺脾氣虛、或瘀血阻絡等。所以,臨床辨證當綜合運用“三焦辨證”“衛氣營血辨證”“臟腑辨證”等,對本病的病程分期、病理階段,病情輕重和轉歸預后做出判斷,明確證候分型,指導治療和養護。
4?辨證論治
“辨證觀、恒動觀”是現代中醫治療的核心優勢。中醫學強調審證求因,極其重視病因治療。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明確指出“大凡客邪貴乎早逐,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患者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復。欲為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耳”。所以,瘟疫的治療以祛邪為第一要務,釜底抽薪,邪去則正安。中醫學極其重視審察病機,把病機作為治療的核心依據。臨床上能守善變,是治療的最高境界。證變機活,法無定法,方無定方。溫病大家葉天士言:“隨證變法”。張仲景在《傷寒論》中鮮明指出“觀其脈證,謹守病機,隨證治之”。
“中和觀,治未病”是現代中醫的特色優勢。中醫學重視“和”的理念。《黃帝內經》云:“熱者寒之、寒者熱之”。《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荀子》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中醫學重視治未病,貫徹“治其未病,三期養治;未病先防,切斷病源;重視祛邪,早期治療;截斷病勢,防止傳變;重視調理,防止反復”的原則。臨床治療以藥物的偏性和適宜技術的特長糾正人體的陰陽失衡,總不離祛邪扶正,瀉實補虛,糾偏救弊,致其中和,恢復“陰平陽秘”的大法。
“融合觀、人文觀”是現代中醫的基因優勢。中醫學是整體醫學,從整體觀出發,主張“天人合一、形神合一”。有容乃大,與時俱進,守正納新。在治療方法上,一方面堅持中醫理論指導,遵循中醫發展規律,充分發揮中醫藥特色;另一方面尊重現代醫學理念和現代檢測檢查手段,充分發揮臨床檢測和救治技術,中西并重,優勢互補,實施現代中醫的診療模式,認為情志因素在瘟疫的治療過程中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全程人文關懷,精神心理干預,更好的救治COVID-19病毒肺炎,防控其感染傳播,保障病患者健康。
4.1?基本原則?根據病情嚴重程度確定治療場所[2]:1)疑似及確診病例應在具備有效隔離條件和防護條件的定點醫院隔離治療,疑似病例應單人單間隔離治療,確診病例可多人收治在同一病室。2)危重型病例應盡早收入ICU治療。
4.2?一般治療?1)臥床休息,加強支持治療,保證充分熱量;注意水、電解質平衡,維持內環境穩定;密切監測生命體征、指氧飽和度等。2)根據病情監測血常規、尿常規、CRP、生化指標(肝酶、心肌酶、腎功能等)、凝血功能,必要時行動脈血氣分析,復查胸部影像學。3)根據氧飽和度的變化,及時給予有效氧療措施,包括鼻導管、面罩給氧,必要時經鼻高流量氧療、無創或有創機械通氣等。4)抗病毒治療:可試用α-干擾素霧化吸入(成人500萬單位/次,加入滅菌注射用水2?mL,2次/d);洛匹那韋/利托那韋(200?mg/50?mg)2粒/次,2次/d。5)抗菌藥物治療:避免盲目或不恰當使用抗菌藥物,尤其是聯合使用廣譜抗菌藥物。加強細菌學監測,有繼發細菌感染證據時及時應用抗菌藥物[2]。
4.3?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療?1)治療原則:在對癥治療的基礎上,積極防治并發癥,治療基礎疾病,預防繼發感染,及時進行器官功能支持。2)呼吸支持:無創機械通氣2?h,病情無改善,或患者不能耐受無創通氣、氣道分泌物增多、劇烈咳嗽,或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應及時過渡到有創機械通氣。有創機械通氣采取小潮氣量“肺保護性通氣策略”,降低呼吸機相關肺損傷。必要時采取俯臥位通氣、肺復張或體外膜肺氧合(ECMO)等。3)循環支持:充分液體復蘇的基礎上,改善微循環,使用血管活性藥物,必要時進行血流動力學監測。4)其他治療措施:可根據患者呼吸困難程度、胸部影像學進展情況,酌情短期內(3~5?d)使用糖皮質激素,建議劑量不超過相當于甲潑尼龍1~2?mg/(kg·d);可靜脈給予血必凈100?mL/d,2次/d治療;可使用腸道微生態調節劑,維持腸道微生態平衡,預防繼發細菌感染;有條件情況下可考慮恢復期血漿治療。患者常存在焦慮恐懼情緒,應加強心理疏導[2]。
4.4?中藥分期分型治療
根據罹患患者的流行病學情況,對疑似疑似病例的狀況、確診患者的證情、當地氣候特點以及患者不同體質等情況,分別歸類處理。醫學觀察的病例,建議根據體質特點,規范的使用中藥制劑:如倦怠乏力,脈虛的氣虛體質者,推薦口服玉屏風散、氣陰兩虛體質者推薦口服生脈飲;納呆、脘痞、脈濡的寒濕體質者推薦口服藿香正氣;頭痛、咽干、脈濡躁數的風熱體質者推薦口服連花清瘟,或升降散免煎顆粒;頭痛咽干,便秘尿黃,脈濡滑數的表里同病體質者推薦防風通圣、雙黃連口服液等。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建議參照下列方案進行辨證分期分型論治。
4.4.1?早期(潛伏期)
是指早期確診和疑似的病例,也包括感染COVID-19病毒,處于潛伏期的感染者。肺為嬌臟,乃清虛之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脾主運化水濕,同氣相求,濕性疫癘之氣,常可直取中焦,易傷脾胃。肺合全身皮膚,脾主肌肉四肢,脾土生肺金,母子相生,共同受邪,所以早期證候多以肺脾病變為中心。以下只是常見或可預見的證候類型,臨床也可見2種和2種以上的證候復合出現,當以辨體辨證為準。可參照邪在上焦衛分,宜辛香透達,多用芳香清宣藥物如藿香正氣、三仁湯等。吳鞠通講“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葉天士講:“在衛汗之可也”,薛生白認為:邪在表分用藥取藿香、香薷、蒼術皮、薄荷、牛蒡子,挾風頭痛者加羌活等味。總之,早期治療宜謹慎、細化各種體質、證候類型,對早期治愈、防范傳播,控制疫情十分重要。
4.4.1.1?寒濕郁肺證?辨證要點:惡寒,身熱不揚,干咳少痰,身體倦怠,肌痛乏力,納呆、便溏,舌邊尖稍紅,舌苔厚膩,脈濡緩。較多見于確診病例初期或醫學觀察期的患者。病機:寒濕郁阻,肺氣不利,肺衛失宣。治法:宣肺透邪,健脾化濁。推薦方劑:麻黃加術湯,藿香正氣散。常用藥物:麻黃、杏仁、桂枝、白術、藿香、佩蘭、茯苓、紫蘇葉、白芷、陳皮、桔梗、蒼術、羌活、厚樸、生半夏、甘草等。方解:麻黃加術湯出自張仲景《金匱要略》濕病篇,方中麻黃湯辛溫發汗,宣肺解表給濕邪以出路,白術健脾除濕。麻黃得白術發汗而不過汗,白術得麻黃,以行表里之濕。藿香正氣散出自《和劑局方》。本方藿香理氣和中,辟惡止嘔,兼治表裏;蘇葉白芷桔梗,散寒利膈,以發表邪;厚樸達腹,行水消滿,陳皮半夏,理氣化痰,以疏裏滯;苓術甘草,益脾去濕,以補正氣。正氣通暢,邪逆自除。兩方各有側重,亦可合用加減。
4.4.1.2?濕阻肌表經絡證?辨證要點:不發熱,或身熱不揚,惡寒,無汗,頭疼身痛,肢體痠楚,舌苔白膩,脈濡。較多見于確診病例初期或醫學觀察期的患者。病機:風寒濕邪,郁阻肌表經絡。此處惡寒是“濕遏陽氣”之象,不同于傷寒惡寒之重,也有別于風溫病惡寒之輕。治法:祛濕解表,宣肺化濁。推薦方劑:神術散,宣痹湯。常用藥物:蒼術、荊芥穗、藁本、干葛、麻黃、甘草、前胡、桔梗、川芎、白芷、防己、杏仁、滑石、連翹、山梔、薏苡仁、半夏、晚蠶沙、赤小豆等。方解:神術散出自《醫方類聚》,方藥組成:炒蒼術、荊芥穗、藁本、干葛、麻黃、甘草各等分。本方解表達邪、宣肺祛濕。宣痹湯出自《溫病條辨》為祛濕劑,組方:防己、杏仁、滑石、連翹、山梔、薏苡仁、半夏、晚蠶沙、赤小豆皮。具有清化濕熱,宣痹通絡的功效。主治風濕熱痹。癥見濕聚熱蒸,蘊于經絡者。
4.4.1.3?濕蒙清竅,濕困脾胃證?辨證要點:惡寒,午后身熱,頭痛如裹,肢體倦怠,胸悶不饑,口渴不欲飲,苔白膩,脈濡或弦。較多見于確診病例初期或醫學觀察期的患者。病機:濕濁上蒙,清竅不利,中困脾胃,氣機不暢。治法:宣暢氣機,芳香化濕,通利小便。推薦方劑:三仁湯,藿樸夏苓湯。常用藥物:藿香、川厚樸、半夏、赤苓、杏仁、生薏苡仁、白蔻仁、豬苓、淡香鼓三錢、澤瀉、通草、飛滑石、竹葉、厚樸、生薏苡仁。方解:三仁湯出自《溫病條辨》為祛濕劑,具有宣暢氣機,清利濕熱,開上宣中滲下之功效。主治濕邪上蒙清竅,頭痛如裹,《素問·生氣通天論》:“因于濕首如裹”;藿樸夏苓湯出自《醫原》,能宣通氣機,燥濕利水,主治濕邪困阻中焦脾胃者。芳藿樸夏苓湯集芳香化濕、苦溫燥濕、淡滲利濕三法為一方,外宣內化,通利小便,可謂治濕之良方。
4.4.1.4?風熱濁毒,侵襲肺衛證?辨證要點:發熱或不發熱,干咳頭痛,咽干口渴,倦怠乏力,少氣懶言,脈濡數或細數。病機:冬天溫暖多風,宜產生風熱時毒,兼挾濕性濁毒,侵襲肺衛,易致肺衛失宣,表里同病。較多見于北方干寒風燥地區輸入性確診或疑似病例的初期或醫學觀察者。治法:辛涼解表,清透肺衛。推薦方劑:新加升降散,銀翹散、桑菊飲加減、桑杏湯。常用藥物:連翹、銀花、桔梗、薄荷、竹葉、生甘草、芥穗、淡豆豉、牛蒡子、桑葉、菊花、杏仁、蘆根、桑葉、香豉、梔皮、梨皮、沙參、藿香、扁豆、僵蠶、姜黃、蟬蛻、生大黃等。方解:新加升降散是國醫大師李士懋先生楊栗山的升降散提出的加減方(見后述)。銀翹散、桑菊飲與桑杏湯三方均出自《溫病條辨》,均為辛涼解表的方劑,用治溫病初起之表證。但銀翹散解表清熱之力強,為“辛涼平劑”;桑菊飲肅肺止咳之力大,而解表清熱作用較弱,為“辛涼輕劑”。桑杏湯為治療溫燥傷肺輕證的常用方。具有辛苦溫散,涼潤清肺的特點。臨癥應用,均應加減使用。
4.4.2?中期(進展期)
是指確診病例早期失于治療的階段。葉天士在《溫熱經緯》中說“在陽旺之軀,胃濕恒多,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濕性濁毒留戀日久,郁閉肺氣,或因感染患者體質陰陽狀態的不同,或因治療不當,濕性濁毒轉歸從化,變證蜂起,出現COVID-19肺炎的重癥階段。根據來自疫區的臨床資料合濕性濁毒“瘟疫”的演變規律,可見以下證候類型,臨床也可見2種和2種以上的復雜證候,當以辨證為準。治療上參照邪在中焦氣分,當分清濕熱孰輕孰重,濕重者宜苦溫燥濕為主,清熱為輔如藿樸夏苓湯等;熱重者宜苦寒清熱為主,化濕為輔,如王氏連樸飲,黃芩滑石湯等;濕熱病重者宜清熱化濕并舉,如甘露消毒丹,蒼術白虎湯等;若濕濁化熱,陽明熱盛,則用白虎湯,若陽明腑實則宜涼隔散通腑瀉熱,靈活加減運用。及時采用“病證結合、中西并重”的診療措施,提高綜合救治效果。
4.4.2.1?濕濁蘊毒,郁閉肺氣證?辨證要點:高熱,喘憋氣促,動則氣短,咳嗽咯痰,痰少色黃或白,或伴咯血,口渴不欲飲水,倦怠無力,不思飲食,腹脹便秘,舌質暗紅或紅,苔濁膩或黃膩,脈滑數。病機:濕濁纏綿,郁而化熱,熱毒壅肺,肺氣郁閉,表里相傳,熱移大腸,腑實不通。濕濁內郁,氣機阻滯,津液不得上乘則“口渴不欲飲”。治法:清熱解毒,宣肺通腑。推薦方劑:宣白承氣湯,新加升降散。常用藥物:杏仁、瓜蔞、生石膏、連翹、葛根、柴胡、當歸、生地黃、赤芍、桃仁、紅花、枳殼、甘草。僵蠶、蟬蛻、姜黃、大黃等。方解:宣白承氣湯出自《溫病條辨》方藥組成為生石膏、生大黃、杏仁粉、瓜蔞皮。本方為肺腸同治,宣肺通腑清熱代表方。國醫大師李士懋先生認為:楊栗山于《傷寒溫疫條辨》中已再三闡明溫疫屬郁熱這一觀點。他說:“雜氣由口鼻入三焦,怫熱內熾,溫病之所由來也”。“溫病得天地之雜氣,怫熱在里,由內而達于外”。溫病的本質是郁熱,透邪外達的原則貫穿于衛氣營血各個階段。透邪的關鍵在于暢達氣機,而升降散行氣活血,能升能降,正可疏通郁熱外達之路,故溫病衛氣營血各個階段皆可化裁用之,是故升降散乃治溫疫之總方。本病濕濁阻滯,其病機一是氣機郁滯不暢,二是熱郁于內不能透達。因此治療原則一是宣暢氣機,祛其壅塞;二是清透郁熱,但清熱時,一定要“勿過寒涼,”因過寒則遏伏氣機,則熱邪更不易透達,當選用寒而不遏之品清熱最宜。方中以僵蠶為君,辛咸性平,氣味俱薄,輕浮而升,善能升清散火,祛風勝濕。蟬蛻為臣,甘咸性寒,升浮宣透,可清熱解表,宣毒透達,為陽中之陽。姜黃為佐,氣辛味苦,行氣活血解郁。大黃為使,苦寒瀉火,通腑逐瘀,推陳致新,擅降濁陰。氣血暢達,清升濁降,郁伏于內之熱自可透達于外而解,故凡郁熱者皆可以升降散主之。由于致郁原因,熱邪輕重,正氣強弱的不同,故臨床應用時,尚須依據病情靈活化裁。因濕遏熱郁者,加茵陳、滑石、佩蘭、石菖蒲等。溫邪襲肺致者,加淡豆豉、梔子皮、連翹、薄荷、牛蒡子等。情志怫郁者,加玫瑰花、代代花、綠萼梅等。瘀血而致者,加赤芍、牡丹皮、桃仁、紅花、紫草等。痰濁蘊阻者,加瓜蔞、川貝母、黛蛤散、杏仁、竹瀝等。食積中阻者,加三仙、雞內金、炒枳殼等。陽明腑實熱郁者,加芒硝、枳實,郁熱重者加石膏、知母、黃芩等,熱郁津傷加蘆根、天花粉、石斛等。熱郁兼氣虛者,去大黃加生黃芪、黨參、升麻、柴胡等,肝經郁熱上擾者,加桑葉、菊花、苦丁茶、梔子、石決明等。應用廣泛,加減頗多。
4.4.2.2?濕濁困脾,清陽不升證?辨證要點:身熱不揚,頭昏頭痛,納呆欲吐,胸脘痞滿,倦怠乏力,便溏不爽,舌苔白膩,脈濡緩或濡數,兩寸沉而無力。病機:濕邪困脾,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較多見于確診病例或醫學觀察期較長從陰從寒轉化的患者。治法:健脾化濕,升陽降濁。推薦方劑:升陽益胃湯。常用藥物:黃芪、半夏、人參、獨活、防風、白芍藥、羌活、陳皮、茯苓、柴胡、澤瀉、白術、黃連、升麻、川芎、葛根、炙甘草。方解:升陽益胃湯出自李東垣《內外傷辨惑論》,本方補益脾胃升陽,清熱除濕降濁。全方補氣與升陽藥配伍,補中寓升;健脾與利濕藥配伍,補中有瀉;升陽與滲利藥同用,升清降濁,健脾與清熱同治,補中有瀉,標本兼治。
4.4.2.3?濕濁困阻?內陷膜原證?辨證要點:往來寒熱,胸悶嘔惡,納呆,頭痛,心煩,口苦,咽干,目眩,舌邊深紅,舌苔垢膩,或苔白厚如積粉,脈弦數按之減,或弦濡數。較多見于確診病例初期或醫學觀察期較長的患者。病機:濕濁中阻,樞機不利。《濕熱條辨》:“邪由上受,直趨中道,故病多歸膜原”。治法:和胃降逆,祛濕化濁。推薦方劑:小柴胡湯、達原飲。常用藥物:柴胡、半夏、人參、甘草、黃芩、生姜、大棗。檳榔、厚樸、草果、知母、芍藥、黃芩。方解:達原飲出自吳又可的《溫疫論》篇。國醫大師李士懋先生說:“邪伏募原,表里阻隔,高熱惡寒,汗出,頭身痛等,非一般芳香化濕所能勝任。方中常山、草果、厚樸、檳榔等,潰其募原伏邪,石菖蒲、青皮開痰下氣,黃芩、知母和陰清熱,甘草和之。對于濕熱蘊阻高熱不退者,達原飲療效非常顯著,常可1~2劑即退熱。該方較之藿香正氣、三仁湯、六合定中等方雄烈。余掌握此方的應用指征有二:一是脈濡數,或濡滑數大,必見濡象。濡即軟也,主濕,非浮而柔細之濡;二是苔厚膩而黃,或厚如積粉。見此二證,不論高熱多少度,惡寒多重,頭身痛多劇,或吐瀉腹脹等癥,皆以達原飲加減治之,每獲卓效。小柴胡湯和解少陽,方中柴胡清透郁熱;黃芩苦寒,清泄少陽之邪熱。二藥合用,則經腑并治,清熱解郁,復少陽疏泄條達之性。黨參配姜、草、棗,健脾益氣,培補中州,是針對半虛、半陰的一面,半夏重在交通陰陽。柴胡清透郁熱;黃芩苦寒,清泄少陽之邪熱。二藥合用,則經腑并治,清熱解郁,復少陽疏泄條達之性。
4.4.2.4?濕濁化熱,肺胃同病證?辨證要點:發熱或高熱,胸痛脘痞,咳嗽咯痰,或痰少色黃,口渴,倦怠無力,咽喉紅腫,小便黃,舌紅或暗紅,脈濡滑數。病機:濕濁郁久化熱,濕熱阻肺,陽明熱盛,濕熱病重,肺胃同病。較多見于確診病例或醫學觀察期較長從陽從熱轉化的重癥患者。治法:祛濕化濁,清熱解毒。推薦方劑:甘露消毒丹,白虎加蒼術湯。常用藥物:藿香、白蔻仁、石菖蒲、淡黃芩、黃連、連翹、綿茵陳、川貝母、射干、飛滑石、木通、薄荷、厚樸、半夏,生石膏、知母、生地黃、蒼術等。方解:甘露消毒丹出自葉天士的《醫效秘傳》:“病從濕化者,發熱……濕邪猶在氣分,用甘露消毒丹治之”。王孟英在《溫熱經緯》說:“此治濕溫時疫之主方也……溫濕蒸騰,人在氣交之中,口鼻吸受其氣,留而不去,乃成濕溫疫癘之病,而為發熱倦怠,胸悶腹脹,肢酸咽腫,斑疹身黃,頤腫口渴,溺赤便閉,吐瀉瘧痢,淋濁瘡瘍等證。但看患者舌苔淡白,或厚膩,或干黃者,是暑濕熱疫之邪尚在氣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本方芳香化濕、苦溫燥濕、淡滲利濕,治濕三法具備。是治療濕濁毒疫的良方。白虎加蒼術湯出自《活人書》。具有清溫燥濕的功效。主治本病熱重于濕的患者。
4.4.2.5?濕濁蘊毒,蒙蔽心包證?辨證要點:或發熱,身熱不揚,神識昏蒙,舌質紅或絳,舌苔黃膩,脈濡滑數。病機:濕濁蘊熱,波及營分,釀痰成毒,蒙蔽心包。辨證關鍵是濕濁重,熱度輕。可見于確診病例重癥危重患者。治法:清化濕熱,豁痰開竅。推薦方劑:菖蒲郁金湯加減、蘇合香丸。常用藥物:鮮石菖蒲、廣郁金、炒山梔、連翹、菊花、滑石、竹葉、牡丹皮、牛蒡子、竹瀝、姜汁、玉樞丹(山慈菇、五倍子、千金子霜、大戟、朱砂、麝香、雄黃組成)、蘇合香丸。方解:菖蒲郁金湯出自《通俗傷寒論》具有清熱化濕,豁痰開竅。主治濕熱痰濁,蒙閉心包,神識昏蒙,間有清晰,譫語時作,身熱不重,舌尖絳,苔黃垢而膩等證。因濕濁偏盛,故用溫開蘇合香丸,溫開醒神。
4.4.2.6?化燥入血,邪閉心包,灼傷脈絡證?辨證要點:發熱,神昏譫語,煩躁不安,胸痛、喘促、咳血、便血,舌質紅絳,脈細數。病機:濕濁化燥化火,深入血分,濁閉心包,神志不清;灼傷肺絡,血逆脈外;或灼傷腸絡,迫血下行。可見于確診病例的危急重癥,證候復雜,常合并出現。治法:涼血解毒,活血止血,開竅醒神。推薦處方:犀角地黃湯,解毒活血湯。基本藥物:水牛角、生地黃、牡丹皮、赤芍、連翹、葛根、柴胡、當歸、桃仁、紅花、枳殼、甘草,送服涼開三寶。方解:犀角地黃湯出自《外臺秘要》,具有清熱解毒,涼血散瘀之功效。主治熱入血分證,熱擾心神,身熱譫語,舌絳起刺,脈細數;熱傷血絡,斑色紫黑、吐血、衄血、便血、尿血等,舌絳紅,脈數。解毒活血湯出自王清任《醫林改錯》,本方以桃紅四物去川芎,涼血活血,合四逆散加連翹、葛根清熱解毒透邪。臨床應用于治療本病出現彌漫性血管內凝血(DIC)危急重癥階段。如高熱或有神志障礙加安宮牛黃丸或紫雪散;喘重加葶藶子、麻黃;大便秘結者加芒硝、枳實。
4.4.3?極期(危重期)
是指確診病例或失于治療,濕濁毒邪,進一步化燥傷陰,內閉心包;由于真陰耗竭,失血過多,氣無依附,真氣外脫,呈現一派“內閉外脫”的兇險證候。病情惡化出現或可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感染性休克、彌漫性血管內凝血”等多臟器功能衰竭,氧合下降,肺部CT檢查有大量的滲出的重癥危象階段。此時當“病證結合、中西并重”,及時采用吸氧合呼吸機支持等ICU重癥醫學的多學科救治,提高患者的生存效果。
4.4.3.1?內閉外脫證?辨證要點:高熱,神志昏迷,煩躁不安,喘促氣短,氣虛不足以息,或汗出淋漓,極度乏力,或伴手足灼熱及手足逆冷,或伴少尿,口唇發紺,面色黯黑,舌暗紅或絳,苔濁膩或黃膩,脈沉細數,或脈散大無力。病機:本證虛實兩端。若濁毒內陷,內閉外脫,以高熱、喘憋、神昏為主癥。邪熱內閉,陽氣不得外達則熱深厥深;或真陰耗傷,氣隨血脫,在外表現為“休克”的手足四逆;在內表現為邪熱迫肺或陰不納氣的呼吸喘促。內閉外脫,虛實當辨,已然屬于危急重癥,當仔細診斷與辨證。治法:清熱解毒,開閉救逆;或滋陰斂陽,益氣固脫。推薦方劑:犀角地黃湯,來復湯、參附龍牡湯,送服涼開三寶。常用方藥:山萸肉、生龍骨、生牡蠣、生杭芍、野臺參、炙甘草、人參、附子、生大黃、水牛角、生地黃、赤芍、牡丹皮、龍骨、牡蠣,安宮牛黃丸、紫雪散至寶丹。方解:本證須辨清虛實。邪熱內閉,則宜犀角地黃湯送服涼開三寶以清熱涼血解毒開竅醒神,已如前述。若真陰耗竭,陽氣外脫則以來復湯等急煎服用。來復湯出自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方中以山萸肉為主藥,萸肉較參、術、芪更有救脫之功。萸肉之性不獨補肝,凡人身之陰陽氣血將散者皆能斂之,故救脫之藥,當以萸肉為第一。生龍骨、生牡蠣斂正氣不斂邪氣,若煅之則其性過澀,亦必于外感有礙,故生用。白芍與甘草同用,甘苦化合味近人參,合以野臺參共奏補益元氣、回陽救逆固脫之功。用于陰陽俱竭,陽越于上的脫證;參附龍牡湯回陽救逆,功似來復湯,犀角地黃湯已如上述,臨癥當仔細推敲加減應用。關于溫病涼開三寶,吳鞠通自注:大抵安宮牛黃丸最涼,紫雪次之,至寶又次之,主治略同,而各有所長,臨用對證斟酌可也。整體而言,安宮牛黃丸長于清熱解毒豁痰,紫雪長于熄風止痙,至寶丹長于芳香開竅、化濁辟穢。前述蘇合香丸芳香開竅,行氣溫中,治療寒濕閉的代表方,臨床中若濕邪困阻心包竅,常用蘇合香丸開竅。
4.4.4?后期(恢復期)
是指各種確診、疑似病例和醫學觀察期的患者,經過治療,表現為余邪留戀,邪去正虛;肺脾氣虛,脾胃呆滯的恢復期。
4.4.4.1?余邪留戀證?辨證要點:身熱已退,低熱,煩躁,納差不食,胸悶,大便黏滯不爽,舌質暗,苔多膩,脈濡細數無力。病機:邪氣已退,正氣未復。多為余邪未解,氣陰兩傷,脾胃呆滯,中氣未醒。治法:輕清芳化,清解余邪;醒脾和胃,益氣養陰。推薦處方:薛氏五葉蘆根湯。基本方藥:藿香葉、薄荷葉、鮮荷葉、冬瓜子、佩蘭葉、枇杷葉、蘆根、西洋參、茯苓、白術、扁豆、生麥芽等。方解:五葉蘆根湯出自薛生白《濕熱病篇》,藥物芳香化濕,醒脾和胃,同時輕清宣肺,益氣養陰而不礙濕邪,有利于肺脾功能的恢復。
4.4.4.2?肺脾氣虛證?辨證要點:干咳、氣短、倦怠乏力、納差嘔惡、痞滿、大便無力、便溏不爽、舌淡胖、苔白膩,脈濡細無力。病機:邪氣已退,正氣未復。多為脾肺氣虛,脾胃呆滯。治法:補益肺氣,芳香醒脾。推薦處方:六君子湯加減。基本方藥:黨參、炙黃芪、茯苓、藿香、半夏、陳皮、砂仁、佩蘭葉、枇杷葉、白術、扁豆、生麥芽等。方解:六君子湯出自《醫學正傳》,具有益氣健脾,芳香醒脾,理氣化痰,補脾以益肺氣,補土以生金。
4.5?養護
我國學者發表在《柳葉刀》雜志的研究結果顯示,從武漢41例COVID-19感染病例來看,COVID-19感染具有與SARS相似的呼吸系統疾病臨床癥狀,病死率也不容小視[6]。因此,對這一正在流行疾病的危害嚴重性和積極防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現代中醫對于“瘟疫病”的養護有豐富的經驗。一方面針對瘟疫的發病及流行特點采取相應的防護措施,另一方面遵循“治未病”的理念,提出了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運動有度、情志有和養生的“四大基石”。無論感染者疑似病例、確診病例,還是已發病、未發病,都可參照執行。
4.5.1?防護措施?參照《協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護手冊》。
4.5.2?養生“四大基石”?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關于發布的《中國公民中醫養生保健素養》國中醫藥辦發〔2014〕15號]。
5?討論
5.1?關于溫疫治療總以祛邪為第一要義?從本次疫情臨床實踐資料來看,防控全程貫徹了“祛邪”這一要務。這與溫病學中溫病和“瘟疫”的論治規律是一致的,也符合歷代醫家的經驗總結。但需要注意的是,本病在病源發生地的疫區,其早期病邪具有“濕濁”屬性,不同于長夏季節濕溫病的“濕熱病邪”,亦不同于“暑溫夾濕”,是屬于疫癘之氣的“濕濁毒疫”。因此臨床治療(早期)側重于祛濕,而非苦寒清熱,如果冒然清熱解毒,過早用寒涼藥物,必然會導致濕邪加重,會出現“冰伏”氣機,反生“厥證”,或“開門緝盜,引邪入里”,從而影響治療效果或加重病情。所以本病應在辨治規律基礎上,注重濕邪的祛除,芳香化濁避穢,透表散邪,升降脾胃,以給邪以出路,是中醫治療的核心。中醫祛濕,一者重治法,宣開肺氣、健脾運濕、芳香化濕、清肝利濕、淡滲利濕,給邪以出路;二是重病位,在上宜開、在中宜化、在下宜利;又在表宜宣、在經宜通,因勢利導;三者重量化,區分濕熱孰輕孰重,分消走泄;四重從化,依據體質,從陰則寒化,從陽則熱化;五重配伍,善用達藥;六重善后,清解余邪,扶助正氣,防止死灰復燃。但是,在全國各地輸入性疫情來看,由于各地的自然條件、地域特點和致病特點以及治療實踐的病例報道的不同,初發病例和感染者又有不同的表現差異,如山西經驗(屬于華北黃土高原,氣候寒冷、多風、干燥,出現類似“冬溫”特點,慎用化濕藥,酌用潤燥、生津、養陰之品)因此,抓住COVID-19的基本特性,全程貫徹“三因制宜”辨證論治的原則,“觀其脈證,謹守病機,隨證治之”是現代中醫永恒的治療法則。
5.2?關于本病早期是否存在寒邪表證?關于早期是否存在寒邪表證目前存在爭論。早期患者多具有發熱、無汗、乏力等癥狀,同時伴有口干。上述癥狀容易被醫家依據《傷寒論》太陽病具有“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的癥狀,而誤辨為感受風寒濕夾雜而侵襲人體衛表所表現的表證、太陽病,進而誤用辛溫解表發汗治療。對此,歷代前賢多有論述。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指出“溫疫初起,先憎寒而后發熱,日后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于經,不可認為傷寒表證,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熱亦不減”。本次疫病初起,鼻塞流涕等表證相對少見,雖有發熱、體痛,但多為低熱,身熱不揚,無明顯惡寒表現。本病以濕邪致病為特點,起病纏綿,進展緩慢,且不見其“寒主收引”的特點,但濕為陰邪,易傷陽氣,自有寒性,所以仝小林院士等稱之為“寒濕疫”,是指濕邪郁閉肌表經絡,衛陽郁閉,失于溫煦則惡寒頭痛身痛。楊栗山在《傷寒溫疫條辨》明確提出“凡見表證,皆里證郁結。浮越於外也,雖有表證實無表邪。斷無正發汗之理”。如何從理論與診療實踐上,把握象與質的矛盾統一,這是提高中醫學術水平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我們認為本病早期雖有惡寒一證,仍以濕濁為主,并非外感傷寒表證。
5.3?關于本病的分期與傳變?傳染病與其他疾病相比較,臨床突出的特點就是發病過程中病理演變的階段性,分期便于傳染病的疑似病例的醫學觀察管理和確診病例的臨床救治,同時又不影響辨證分型論治。根據來自原發于疫區和輸入性疫情臨床確診病例200余例分析,可將本病分為4個階段,早期(潛伏期)、中期(進展期)、極期(危重期)、后期(恢復期)。其中早期大概1~10?d,進展期10~20?d,極期(危重期)20?d以上。恢復期1周左右。關于本病的傳變,依據薛生白《濕熱病篇》,本病存在順傳的正局和逆傳的變局。濕性黏滯,病程纏綿,留戀在肺,在一經不移,在早期經治療后,大部分患者在本期治愈,是為順證。若病情在10~14?d逐漸出現高熱、神昏、喘憋、咯血、便血,此為濕濁疫毒從化,從寒則困阻中焦、清陽不升,邪伏膜原、蒙蔽清竅;從熱從燥,則濕濁化熱化燥,熱壅肺胃,耗傷真陰,灼傷脈絡,甚或內閉心包,出現陰陽離絕的危象,是為逆證。關于本病的傳變,有學者認為本病進展期和極期的咯血癥狀,不屬于熱入營血階段表現[7]。其依據是本病歸屬于濕性瘟疫范疇,病性為濕毒化熱,除外出血癥狀外,并無其他明顯熱入營血的指征,如“身熱夜甚,口干反不甚渴飲,心煩不寐,時有譫語,斑疹隱隱,舌質紅絳,脈細數等”,并非熱熾營血、迫血妄行,而是濕毒化熱,濕邪困阻氣機,熱無出路,損傷肺絡所致,仍以祛濕清熱宣肺為主。我們認為不妥。其一,本病雖為“瘟疫”,但不出溫病演變規律;其二病邪從化,體實陽旺之人,從熱從陽轉化,化燥傷陰,灼傷脈絡,逆入營血;其三有明顯的熱入營分“逆傳心包”的表現如神昏、譫語、口唇發紺、舌質絳、脈細數等,但見一癥便是。特別是DIC的出現。所以溫病大家除三焦辨證外,多用衛氣營血辨證實踐。邪熱入營入血后,迫血妄行,灼傷脈絡可致出血。如葉天士所謂“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所以說本病發病過程是可以出現熱入營血階段傳變的,可以卻非必然。
5.4?關于西醫西藥
5.4.1?抗病毒藥物?近日美國報道了1例COVID-19肺炎經remdesivir抗病毒治療痊愈的病例[8],仍有待于臨床循證醫學證據。目前尚無循證醫學證據支持現有抗病毒藥物對COVID-19有效,更無針對COVID-19的特效藥物。可酌情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2粒/次,2次/d,14?d為1個療程。
5.4.2?輸液治療?臨床觀察到大量的病例因住院治療而進行了大量的輸液治療,加重了濕濁疫毒的“濕性”,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濕邪化燥、傷陰的特點,有可能加重加速了病情的變化,有待于進一步研究。但對于危重患者的全身營養、支持療法和維持內環境平衡以及中藥注射制劑的應用,具有積極無可替代的作用。
5.4.3?糖皮質激素?長期大量使用糖皮質激素可造成激素性骨質疏松癥和股骨頭壞死,所以不建議早期大量使用。重癥患者可根據患者臨床病情及影像學表現早期使用,酌情延長療程。但循證醫學證據不足。
5.4.4?免疫球蛋白?一般不建議使用。重癥患者依據病情可酌情早期靜脈輸注免疫球蛋白0.25~0.50?g/(kg·d),3~5?d為1個療程[9]。
5.4.5?抗生素治療?抗生素的應用缺少循證醫學證據。根據患者臨床和影像學表現,如不能除外合并細菌感染,輕癥患者可口服相關肺炎的敏感藥物,如頭孢或氟喹諾酮類;重癥患者需覆蓋所有可能的病原體。
5.4.6?關于ICU和現代救治技術?作為現代中醫應同步熟練掌握和應用ICU和氧療和呼吸支持療法。對危重患者及時實施重癥醫學的多學科診療和技術,更好的保障治愈率。
6?結論
本病屬于中醫屬于溫病的“濕濁毒疫”范疇,其病因是感受的是“濕性濁毒”是“疫癘之邪”,疫癘之邪又稱“癘氣”,是多種致病因素的總稱,因此又稱“雜氣”,它是指六淫邪氣中具有強烈傳染性,并能引起廣泛流行的一類致病因素。感染人體“多從口鼻而入”,因此又不同于六淫邪氣,雖然屬于溫病,又不同于“四時溫邪”。但由于其發病的季節和物候條件,又兼有“濕熱病邪”的部分特點。演變規律具有上中下三焦和衛氣營血傳變的正局和變局;病理證候的變化具有階段性,“濕性濁毒”是病因病機的核心,具有濕濁留戀傳變和從陰從陽的轉化規律。具有三期由輕到重到危急的變化,病死率較高。但如果早期發現,早期防控,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可以早期治愈,預后大多良好。
原發于武漢疫區和輸入性疫區,由于天時、地域和感染者的差異,要遵循因時、因地、因人“三因制宜”的辨證論治原則,既掌握規律,又要靈活運用。同時要注意和“四時溫病”的聯系與鑒別。
COVID-19這一新型冠狀病毒的宿主和中間宿主,尚未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人與人的飛沫、接觸、氣溶膠等通過呼吸道、皮膚黏膜的感染是主要的傳播途徑。病毒或某種戾氣,作為某種生物或致病因素數不勝數,在自然界中宿主各種生物或某種條件,和諧相處,早已存在了幾十億年而維持著自然界的平衡。人類的產生,從原始的農業社會算起至今不過萬年,同樣病毒或某種戾氣宿主包括野生動物、人類在內的各種生物體,存在于某種條件下,而維持著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某種平衡。當天氣物候變化、季節四時變換、加之地域的不同,特別是人類的異常生活和過度的生產,某種平衡被打破,反映到人類就會因此而致病,這符合中醫學“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法則。也因此,為中醫藥防治傳染病的治療提供了機遇。這次防治COVID-19肺炎的實踐,足以證明了中醫藥學大有作為,應該作為主體醫學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數千年中華文明史上,中醫藥學對于溫疫診治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發揚。
現代中醫秉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血統和“基因”,“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與時俱進,守正創新。不僅自我完善,而且汲取了現代科技成果和現代臨床先進的有效方法,極大的提高了綜合服務能力和救治水平。針對本病的預防和保健,除了建議戴口罩,勤洗手,室內通風等,注重隔離等防護措施,更能發揮傳統中醫養生保健的“四大基石”作用,做到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運動有度,情志有和,休養生息;針對早期輕癥病例,建議居家隔離觀察治療;針對重癥患者的治療,建議住院綜合治療,在中醫思維和理念(整體、動態、融合、辨證、中和、治未病和人文關懷)的指導下,中西醫結合并重,優勢互補。中醫藥的早期干預,可有助于降低病死率、增加治愈率、提高預后的優良率。
特別說明,無論指南、共識,還是方案,都不是僵死的,更不能限制臨床醫生的思維。本案為COVID-19感染性肺炎這一“濕濁毒疫”型瘟疫診療的建議方案,必須根據各地疫情的實際和當地氣候、地域特點和罹患患者的個體差異,遵循辨證論治的原則,參考應用。
參考文獻
[1]Zhu?N,Zhang?D,Wang?W,et?al.A?novel?coronavirus?from?patients?with?pneumonia?in?China,2019[J].N?Engl?J?Med.DOI:10.1056/NEJMoa2001017.
[2]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辦公廳,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EB/OL].[2020-01-27].http://www.nhc.gov.cn/xcs/yqfkdt/202001/3882fdcdbfdc4b4fa4e-3a829b62d518e.shtml.
[3]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截至1月26日24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最新情況通報[EB/OL].[2020-01-26].http://www.nhc.gov.cn/xcs/yqfkdt/202001/3882fdcdbfdc4b4fa4e3a829b62d-518e.shtml.
[4]HUANG?Chaolin,WANG?Yeming,LI?Xingwang,et?al.Clinical?features?of?patients?infected?with?2019?novelcoronavirus?in?Wuhan,China[J].The?Lancet,[2020-01-24].DOI: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0)30183-5.
[5]鐘文娟,方嬌榮,明新貴.武漢市社區居民心理健康狀況調查[J].中國公共衛生,2009,25(3):279-280.
[6]Chan,J.,Yuan,S.,Kok,K.,et?al.A?familial?cluster?of?pneumonia?associated?with?the?2019?novel-coronavirus?indicating?person-to-person?transmission:a?study?of?a?family?cluster[J].The?Lancet,[2020-01-24].pii:SO140-6736(20)30154-9.DOI:10.1016/SO140-6736(20)30154-9.
[7]王玉光,齊文升,馬家駒,等.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肺炎中醫臨床特征與辨證治療初探[J/OL].中醫雜志.[2020-01-2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129.1258.002.html.
[8]Michelle?L.Holshue,M.P.H.,Chas?DeBolt,M.P.H.,Scott?Lindquist,M.D.,et?al.First?Case?of?2019?Novel?Coronavirus?in?the?United?States[J].N?Engl?J?Med,[2020-01-31].DOI:10.1056/NEJMoa2001191.
[9]李太生,曹瑋,翁利,等.北京協和醫院關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建議方案(V2.0)[J/OL].協和醫學雜志,[2020-01-3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882.r.20200130.1430.002.html.
(2020-01-26收稿?責任編輯:王明)
作者簡介:王金榜(1963.08—),男,教授、主任醫師,研究方向:中醫骨科,中醫藥特色,E-mail:wjbshijzh138@sina.com通信作者:孫樹椿(1939.07—),男,主任醫師,研究方向:中醫骨傷,E-mail:sunshuchun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