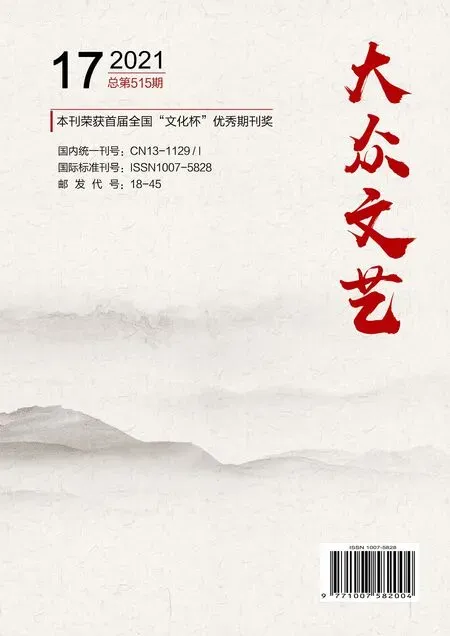淺論《中國醫生》里的中國美學意蘊
王雯杰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 210097)
近年,我國涌現大量醫療題材紀錄片,如《人間世》《手術兩千年》等,或直面醫患關系,或介紹醫療發展,這些優質的紀錄片受眾廣,口碑好,影響大。2019年5月,由國家衛健委健康報社等出品的紀錄片《中國醫生》始播,今年初亦有人民網、新京報等多家媒體引用該紀錄片致敬一線醫護人員。《中國醫生》從醫生的角度敘述,真實反映了中國醫生的生存狀態和工作樣貌,展現的正是“中國的醫生”,是“中國的醫護”,浸潤了中華文明,獨具中國美學意蘊。
一、親親之美:立愛自親,親親及人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幾乎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信仰,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家”與西方哲學大相徑庭。西方自柏拉圖《理想國》以降,均將“家”排除在外,柏拉圖提倡廢除家庭,黑格爾認為家庭的核心規定是愛,與自由精神沖突。與需要青年人冒險的海洋文明不同,農業文明的中國更需要長者的經驗,且多在氏族內部傳播,逐漸形成了一個個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活動群體,在個人與天下之間,“家”這一中間紐帶的地位可見一斑。
《尚書·堯典》有“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九族”為“家”,首先要家庭和睦,萬邦才能和諧。《禮記·中庸》“親親為大”,以尊愛父母優先。《容齋隨筆》“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親親”的范圍逐漸擴展,首先是親及整個家庭。家庭在社會學中分為核心、主干和擴展家庭,成員范圍不斷增大,至擴展家庭,旁系親屬也都納入其中。
與儒家“親親”相對,墨家提倡“兼愛”,其根本差異不在“愛人”的范圍,而在于哲學出發點不同,“親親”之愛為尊愛;“兼愛”之愛與希伯來文化中的“愛人”有相似之處,以利益為出發點,“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在利害準繩之下人人平等,人人相親。
醫生是救死扶傷的代表,療救患者,獲取成就感,以更大的熱情和更為精湛的技術投入到新的療救中似乎是“兼愛”。在《中國醫生》的醫生視角下,不難發現似乎并非如此,醫生與患者建立情感之基礎是站在患者家庭中類比“同情”。耄耋老人是家的向心力,中青壯年是家的支撐力,黃發垂髫是家的生命力……中國醫生幾乎都有無意識的“親親”,在“親親”的情感美學下,療救更顯柔情,而失敗的痛苦感也會放大。《中國醫生》展現出來的醫生之“愛”的美學根源在“親親”,而不是效率和利益促成下的“兼愛”。清代醫學家吳尚先之“一人生死,關系一家,倘有失手,悔恨何及。”(《理渝駢文續增略言》)正是無數中國醫生的內心寫照。
關于“一家醫院聯系著多少家庭”的旁白臺詞在片中出現數次,醫院里家的凝結比任何公共建筑之中的更為震撼,生命的誕生與死亡,疾病的康復與惡化,死生使物理結構上有限的醫院在哲學、美學領域無限擴張,“生生之美”在醫院里集中展現,《中國醫生》也抓住了這個原始沖動。
二、生生之美:周流不虛,向生向美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間生是永恒不變的主題,“生生”是使生生,是生的動態呈現,其美學內涵包括生機勃勃之生和創生之生。
如果把“生生”當作生命的常態,疾病便是變態,醫生的治療是將變態的“生生”轉化為常態,治愈則“生生之美”生,不幸則歸于自然,再度走向“天人合一”,實現生命的閉環。
紀錄片中醫生拯救病人于危難,讓急速走向死亡的生命重回“生生”之軌。醫生“力挽狂瀾”,變化激蕩人心,人重新進入“生”的“元”維度。也有一些醫生的治療不甚急迫,唇裂患者生命無礙,但“生生”的持續性和活力度受到影響,整形醫生的治療是對“生生之美”的更高一層追求。《中國醫生》中的整形科醫生對于唇裂縫合頗有深思,考慮到縫合之后皮膚的生長,特在縫合之處略微堆高使皮膚舒展后能夠變得平整。“生生”本就是一種持續運動,醫生將經驗轉變為先驗,培養預見性的目光。脊柱的矯正不以直為唯一標準,亦考慮患者的性別、年齡,是將其看作社會屬性的人。處理糖尿病人足部潰爛,常見手段是截肢。紀錄片對焦一位看護醫生,悉心護理病患瘡口,減少截肢可能,提高生活的質量,瘡口的生長愈合也是一種持續的動態變化,看護順應變化,向好發展,“生生”不言而喻。
紀錄片沒有忽略治療的巨大壓力下的種種矛盾,療救希望與現實處境,有效治療手段與患者個人意愿,有限科技水平與治療愿望等等。矛盾之生生是常態,在此常態下醫生不斷追尋矛盾消失的變態,是“生生之美”的張力。
“生生之美”還有“時”的轉變,《周易》將人的生命狀態分成否時、泰時等不同的時。醫療是科學,生命體征應當以怎樣的醫療科技手段應對,恰好與“時”之美相吻合,對生命的救治是對生命之時的轉變,這是一種對規律的把握與遵循,醫生精細洞察、精確判斷、精準施策,與“時”相應而能“生”。
從社會分工的角度,醫生這一職業與其他勞動沒有區別,凡勞動皆有“生生之美”,農作物的蓬勃生長,建筑物的從無到有,內蘊“創生”的力量,醫療也不例外。硬件相當時,醫生的軟實力至關重要,也就是醫生的“創生”性。
《說文解字》中“生,進也。像草木生出土上。”草木的破土、生長、成熟到枯萎消逝是生的贊歌;人出生在地球之上,兼有多種屬性,歷經種種風雨。醫生對于患者的救治幫助其走向“生”,盡可能書寫“生生之美”;醫生同樣是土上草木,救治的喜悅與失敗的傷痛常伴,周流不虛,向生向美。
三、仁德之美:懷仁予仁,以德為先
醫學凝結著時代最為先進的科學技術,當醫學人工智能達到一定水準,醫生在絕對精準、無須休息的人工智能面前是否會失去價值?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勝任外科手術,是否還有必要培養生命有限、存在失誤可能的外科手術醫生?
現階段人工智能道德原則內置設想廣受關注,然而道德本身具有發展性,適用此時此地未必適用彼時彼地,比起將此刻的價值觀植入人工智能中,似乎更應以形而上的高度,超越人類自身特定價值觀的局限,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若挑戰成功,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對人類構成生存威脅,這又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倫理問題。醫療行業中人工智能似乎可以作為一種工具存在,發揮其醫療技術上的專用性,嚴格分工。“只發展專用人工智能,不讓人工智能發展越過圖靈奇點。”[1]工具論下的人工智能無法完全取代醫生,如果“親親”的主體非人,其對象能否感受到“親”,如果“生生”的施予者永無變化,渴望“生”之人是否會感到可怖。
“博學而后成醫,厚德而后為醫,謹慎而后行醫。”(《中國醫生》第一集)就目前人工智能發展來看,“博學”和“謹慎”無疑完勝人,“厚德”則成為醫生不可取代的一個重要維度。“醫德”是普通大眾對醫生提出的要求和期望,更是醫生自己踐行的規范和準則。“醫德”之中,有“仁”有“德”。
“仁者,愛人。”(《論語·顏淵》)“仁”是一門關于人際關系的學問。《論語·雍也》指出“仁”的根本含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醫者仁心”的一個方面就是醫生與病患及其家屬的人際關系由“仁”維系,方法之一就是“親親”;另一個方面是醫生個人的修身,由己推人必先自我成“仁”,以“仁”修身,因為“仁是一個極崇高而又切實際的生活理想”[2],兼有美學的高度和有實踐的可能性,醫生懷“仁”,不斷精進醫術,攻克難題,與患有終身性疾病的病人簽下“終身契約”,用十年的研究回應曾經的救治失敗和遺憾,在“仁”的理想召喚下行“仁”樂“仁”。
就“德”的倫理學而言,道家和儒家截然相反,前者將“德”視為人之本心,追求清靜無為、自然合道的出世之德;后者將“德”置于社會維度,追求“以德治國”的入世之德。在美學領域,儒道兩家的“德”達成和解。“盡管在倫理道德的含義上儒道兩家是由分歧的,儒家強調‘修身養性’的‘仁義’‘充實’,而到家凸顯的是‘法自然’的‘無為’‘素樸’。在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功能上,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也都鼓吹它們的倫理道德作用。”[3]因此將“仁”與“德”結合有其可能性和成立性。中國美學將“德”注入文學藝術的教化功能中,醫生“厚德”約束其技術的發揮。在《中國醫生》里有為病人爭取醫療補助的醫生,有毫無保留地提供診療方案的醫生……這是廣大中國醫生的縮寫。
不得不提到緊張的醫患關系,任何人際關系均是由交往雙方共同維系的,因此病患一方而言也應懷“仁”予“仁”,以“德”為先,這對醫生亦是一種寬慰。盡管紀錄片中并未專門對焦于此,但從醫生心聲的流露中可以感受到患者對于治療的進行和醫生修養、技術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影響。
仁德相連,既是中國醫生的個人修養,亦是理想實踐,這些都是現階段的人工智能所無法取代的。
四、結語
縱觀整部《中國醫生》,其記錄對象包括中國醫生與護士;其敘述視角還包括病人、病人家屬及醫護人員家屬等等,這些視角的展現和傳達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作為紀錄片最大的特色,應當對醫生視角挖掘更深。
在紀錄片里提取“親親”“生生”與“仁德”三個美學意蘊,美學不僅存在于高閣之書籍之中,中國美學也同樣活躍在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有美學的光亮。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周易·系辭上》)日新之“生生”與“德”相連,醫生醫術的進展,對病患生命的延續與改善,造就這樣持續不斷的變化可以說是“德”。“仁者”之“愛人”是個人的修養,“親親”從親緣關系出發而擴展到無數的命運共同體之中,“仁”的修養與實踐亦是從小家走向大家,二者擴展的范疇正相一致。“生生”理想之實踐依靠“親親”之基礎,良好穩固的醫患關系方能讓治療與撫慰的效果最大化。因此,“親親”“生生”與“仁德”在中國醫生身上不是三個獨立的存在,而是相交相融,相互作用,更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