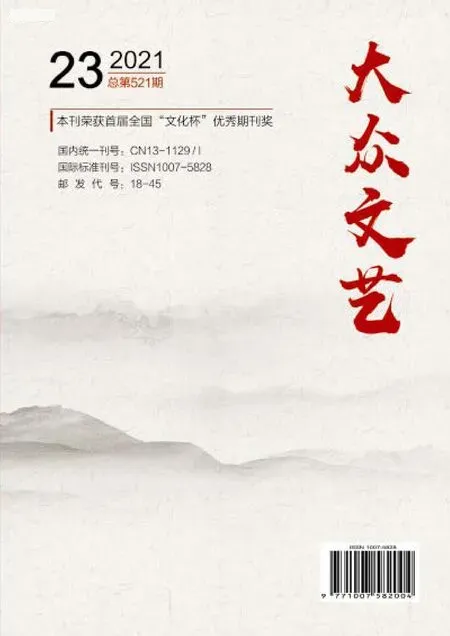論后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中對指物定義的批判
(昆明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云南昆明 659500)
一、指物定義的來源
指物定義,又稱指物解釋,是一種指稱論的意義理論,曾一度在西方語言哲學占主導地位,它是語言哲學的核心理論之一。在西方語言哲學中,指物定義有著悠久的歷史,它是關于一個詞的意義的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作為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在他的著作《形而上學》中,他說:“每一個字必須指示可以理解的某物,每一字只能指示一事物,決不能指示許多事物,假如一字混指著若干事物,這就該先說明它所征引的究竟屬于其中哪一事物。”[1]在這里,亞里士多德明確指出,一個詞應該指向一個事物,也就是說,語詞與所指的具體對象必須一一對應,我們對于語詞的定義必須按照具體事物來進行。
在中世紀,指物定義也有其支持者。奧古斯丁在其《懺悔錄》第一卷第八節中有過相關論述,維特根斯坦后來在《哲學研究》第一部分直接進行了引用,他說:“當成人稱呼某個對象并且轉向這個對象時,我注意到這個情況,并且明白這個對象是用他們發出的聲音來標示的,因為他們想要把它給指出來。”[2]奧古斯丁在這里把實指定義的具體場景描繪出來,也就是說,成年人一邊發出某種聲音一邊轉向這個對象,并且用手指向這個對象。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就可以學會某個符號或語詞的意義,進而去正確使用它們。
在近代,英國哲學家密爾(J.S.Mill)是指物定義的一個主要的倡導者。他認為每個名稱都代表著某種事物,一個名稱所代表的事物就是這個名稱的意義,也就是這個詞的意義。這種關于對后面的語言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羅素便是其重要的繼承者。羅素也認為,一個詞的意義并非來源于語詞本身,而是來源于其外在的某些東西。他說:“所有的詞都具有意義,這就是說,它們是一些代表它們之外的某些東西的符號。”[3]后來,早期的維特根斯坦也繼承了這種指稱論的理論,但在后期,他放棄了指稱論,因為他發現所謂的“簡單對象”并不存在,由此便開始了對早期指稱論進行批判的道路,從而發展出了自己后期的思想。
二、后期維特根斯坦對指物定義的批判
1.指物定義并不能涵蓋所有語詞
按照傳統的指物定義,每一個詞都代表著一個對象,而這個對象便是這個詞的意義。但是維特根斯坦發現,并非所有的詞都可以代表著某一具體的對象,并且這些詞很多,例如“這”“那”以及“紅”“藍”以及等詞,它們并非名稱,也并不代表著具體的對象。數字也是如此,“2”“5”這樣的數字不代表任何對象,也不為特定的對象命名。也許有人認為可以通過說出“這個數叫作2”來為“2”下一個指物定義。但維特根斯坦指出,“這個數叫作2”說明說話人已經明白了關于數的概念,也就是說,在“這個數叫作2”這個指物定義之前,我們需要對關于數的理解進行一番解釋,然而這個解釋勢必又會讓我們繼續追問下去,最終也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解釋。實際上,代表著對象的只有部分名稱,像邏輯專名“這”“那”以及顏色詞和數詞都并不能在現實世界中找到與其相對應的具體事物。
2.指物定義本身便存在著誤解
維特根斯坦在其《哲學研究》第一節中便提出一種設想——“我讓某人去購物。我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五個紅蘋果’。他將這個紙條遞給賣家,后者打開上面寫著‘蘋果’的抽屜,然后在一張圖表上尋找‘紅’這個詞并找到與之對應的色樣,然后他按照順序念出基數詞。”[4]在這里,維特根斯坦設想了一種日常生活的場景,“五個紅蘋果”按照指物定義的觀點,便出現了問題。我怎么知道“五”在哪里?“紅”又在哪里?在我們學習“紅蘋果”時,家長通過指向蘋果,然后告訴我們:“這就是蘋果。”可是他們又如何確定,他們所指向的是“蘋果”而不是“紅”呢?在這里,什么是“五個”“紅”以及“蘋果”的意義呢?我們很有可能把這個指示的動作理解為指的是“五個”或者指的是“紅色”,這種關于指物定義的不確定的因素一直存在。另外,我們也發現,指物定義在這里只能解釋“蘋果”這個語詞所代表的意義,而數詞“五個”以及顏色詞“紅”并不能通過指物定義得到應有的解釋,并且還存在著各種誤解的可能性。
3.指物定義在實際中存在著需要解釋的預設
《哲學研究》第二節,維特根斯坦提出另一種場景例子來指出指物定義的不足。他設想一個建筑工人與一個助手之間的交流。當工人說出“板石”這個詞并指向某處時,助手便走到工人所指向的地方然后拿起一塊板石并遞給工人。這個場景下,“板石”這個語詞的意義似乎就是它所指稱的實際中的板石這個對象。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維特根斯坦并不這樣認為。他認為,當工人指向某處并說出“板石”,然后助手拿起板石并遞給工人這里存在著場景預設。助手是如何得知“板石”一詞是某種東西的名稱?也就是說,助手腦子中最起碼已經有了“名稱”這個概念,比如,他已經學會了問別人:“這叫什么?”或者已經學會了為某一事物取一個名字等等。而所有這些所預設的東西,指物定義都過分粗糙地將其歸于一個對象即“板石”這個語詞的意義之中。維特根斯坦指出,只有已經知道用名稱來做點什么的人才能有意義地詢問名稱。在這里,指稱論的意義理論將其掩蓋,維特根斯坦通過具體實例也指出了這種理論預設的不足。
4.指物定義只表明了語詞使用的準備階段
維特根斯坦指出,當我們通過指向某物然后通過命名來解釋一個詞的意義時,我們并不確定他人是否已經明白了這一定義。比如,我們指向一棵樹,并對別人說:這是樹。這時,其實我們并不確定,聽話人是否明白了“樹”的定義,很有可能他以為我們實指定義的是綠色。那么如何確定我們是否已經明白了某一語詞的意義呢?或者說什么時候我們可以說一個人真正理解了某一語詞的意義呢?
在這里,維特根斯坦提出“意義即使用”這一說法。這一觀點認為,我們不能孤立地去詢問什么是一個詞的意義,而應該在詞的具體使用中去把握該詞的意義。那么,我們如何確定某人是否已經明白了“樹”的意義呢?這可以在他后續對“樹”這個詞的使用當中得到檢測。比如,下次當他看見樹,他指了指樹并告訴我們:這就是樹。這樣,我們可以說,他已經把握了關于“樹”這個詞的意義。相反,當他下次看見一塊綠色的草地然后告訴我們,這是樹時,我們說他并沒有理解“樹”的含義。
然而,指物定義并沒有這種檢測標準,也就是說,指物定義并不在乎語詞在具體生活實踐中的使用方式,而只是選擇為事物進行命名。這種命名往往只是我們認識客觀事物的第一步,只是語詞使用的準備階段,只是關于語詞使用的一種特殊的用法。維特根斯坦明確說道,“人們認為,對語言的學習就在于為對象命名。可以將其稱為詞語使用的準備工作。”[5]命名似乎只是為了談論事物,這只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游戲。“語言游戲”這一概念維特根斯坦強調是人的活動,即“那個由語言以及與語言交織在一起的那些行為構成的整體。”這一概念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們不能孤立地去詢問語詞的意義,而應該在具體的使用場景和情境下去探尋語詞的意義。
5.指物定義只應用于極少數的語言游戲當中
指物定義告訴我們,語言中的每個詞都標示著某種東西。維特根斯坦雖然否認了這種指物定義的方式,但也并不是全盤否定。他說,“可以說,詢問名稱以及與它配套的指物解釋是一個特殊的語言游戲。”也就是說,指物定義或指物解釋并非被語言游戲排除在外,在某些具體的場景下指物定義確實有其獨到之處,維特根斯坦舉出了一個這樣的場景——建筑工人在建造時所使用的工具上有某些符號,工人通過將這種符號給其助手看,然后助手將有這種符號的工具拿過來給工人。在這個語言游戲當中,助手事先并不清楚工人要使用哪種工具,而工人通過符號標示著某個具體的工具讓其建造活動得以延續。在這里,我們發現指物定義是有益的,我們循著某個符號,將符號與工具上的符號進行對照,最后找到具體的建筑工具,讓整個語言游戲變得完整。維特根斯坦將其延伸到哲學領域,他說,“在搞哲學的時候對自己說‘為某個東西命名就像為一個東西貼上標簽’,這常常證明是有益的。”當然,通過維特根斯坦舉出的這種特殊語言游戲的場景,我們也會發現,倘若單單只是命名而沒有助手后續的活動,工人的建造活動也不會得到延續。所以,這里的有益指的是“貼標簽”或者指物定義這種做法讓我們知道命名只是使用的準備工作。
三、對指物定義批判的意義
維特根斯坦對指物定義的批判有其自己的目的。指物定義是一種傳統的語言觀——一個符號對應一個東西,這就類似于奧古斯丁對于語言的看法,也是維特根斯坦本人早期的想法。維特根斯坦指出,我們在搞哲學的時候,從古典哲學起就有一種“本質論”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在我們面對名詞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問“什么是某某名詞的意義?”這種提問方式會自然而然地誘使我們去找出某個對應物或者某個本質(就好像有本質這樣的東西在某個隱蔽的角落等著我們一樣)去回答這個問題。但實際上,維特根斯坦對于語詞的看法,是特別反對這種指物定義的方式的,他將其稱之為“哲學病”,所以他的哲學就是要消除這種“哲學病”,也因此,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的研究中,我們找不到任何一種所謂的本質定義。像上文提到的“語言游戲”,“意義在于使用”實際上維特根斯坦本人并沒有對其下一個明確的本質定義。和維特根斯坦使用的大部分概念一樣,也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多數概念一樣,“語言游戲”其實并沒有明確的界限,有的只是像各種繩子相互纏繞在一起一樣,相互交織但又并不相同的“家族相似性”。實際上,沒有界限,沒有本質的含義,并不影響我們對語詞的使用。所以對指物定義的批判,放在其整個后期哲學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后期哲學存在的一種目的,也可以說是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觀,那就是消除我們的語言作用于我們智性上的困惑,反對“哲學病”,把語言從形而上學的云端拉回到日常使用的粗糙的地面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