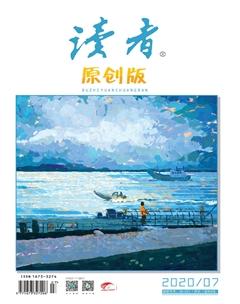如何與孩子“聯合辦公”
林特特

一
孩子喊“媽媽,過來一下”時,我默默在一張白紙上畫下一橫,第10個“正”字完成了。這說明,一早上他已經叫了50遍“媽媽”,而我分別處理了以下這些事情:
1.媽媽,這個字我不認識。
2.媽媽,我想喝口水。
3.媽媽,我可以去下廁所嗎?
4.媽媽,我的尺子在哪里?
5.媽媽,我的筆不夠尖。
6.媽媽,我想要張紙。
7.媽媽,這個單詞怎么讀?
……
“媽媽,這個字我不認識。”
又繞回來了。繞回來好幾輪了……
以上問題,我已經全部處理完。
現在,《新華字典》在書桌上,旁邊是iPad和手機,它們都安裝了字典App,孩子已可以熟練操作了。
水杯也在桌上,水還是滿的、溫的,各種文具列隊展示,刨筆刀、橡皮、尺子、草稿本……等我第50遍過去時,發現橡皮在地的一頭兒,尺子在地的另一頭兒。
那么,一早上,我又做了哪些事呢?
1.開一個電話會議。
2.在筆記本上記錄會議要點。
3.打開電腦,和3個合作伙伴同時溝通。
4.看一篇稿子的反饋意見。
5.列另一篇稿子的提綱。
6.從書房到客廳來回穿梭了100次。
客廳的電視上播著網課,1.5米外是孩子和孩子的書桌,桌上是他所需的一切。
兩個半小時,50遍“媽媽,你過來一下”,平均每3分鐘我被打斷一次。
二
“我們談一談吧。”我舉著畫了10個“正”字的白紙,搬張凳子,坐在他的書桌前。
“談這個我不認識的字嗎?”孩子仰起臉。
“不,那個你不認識的字可以查字典,你早就學會怎么查了。下面,我們來談談這10個字。”
“這字我認識,正!”孩子一副“你以為我是一年級小學生嗎”的表情。
“是的,你已經上二年級了。在學校,你渴了,會自己拿著杯子去飲水機前接水喝;下課10分鐘,想上廁所就上廁所;東西丟了,會找,找不到,會借;筆禿了,會削,而不是一切都在等我。”
接下來,我解釋了10個“正”字的由來,它們代表什么,代表哪些事。我將每一件事由寫在“正”字下,看一看這些叫了我50遍的7件事,究竟哪件真的需要我。
“1.媽媽,這個字我不認識。”孩子讀。
“你可以查字典。過。”我說。
“2.媽媽,我想喝口水。”
孩子的目光投向我,我的目光投向滿滿的水杯,他自己伸手去拿了,喝了。
“除非水杯空了,要動用熱水瓶,否則你自己可以解決,不要來找我。過。”
“3.媽媽,我可以去下廁所嗎?”
“你在下課時間上廁所需要老師同意嗎?過。”
“4.媽媽,我的尺子在哪里?”
“接著讀。”
“5.媽媽,我的筆不夠尖。”
“繼續。”
“6.媽媽,我想要張紙。”
“好,這3個問題其實是同一類,你可以自己找紙或找其他文具。”我指著地上的尺子,桌上的草稿本、刨筆刀。
我讀起最后一條:“7.媽媽,這個單詞怎么讀?你覺得第七個問題和前六個中哪個是一類?”
孩子伸過頭來看,還以為是做合并同類項游戲,拍手道:“第一個!‘媽媽,這個字我不認識。”
“第一個問題是怎么解決的?”
“查字典!”
“你的英語字典呢?”
瞬間,iPad和手機“漂移”到他手上。
“查給我看看?”
“嗒嗒,嗒嗒”,孩子小手指飛快按著,口中準確地念著一個個字母。
三
7件事其實是3件。
經過合并,無非是:1.生理需求,“人有三急”的“三急”;2.“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主要是各種文具、用具;3.知識盲點。
解決方案,呼之欲出。
我在白紙的背面列下:
A.你能直接解決的
B.要用工具解決的
C.可以不解決的
D.必須有人幫助解決的
我們來做選擇題。
“上廁所,應該選ABCD中的哪項?”我問。
“A。”孩子說。
“對。”
“馬桶要是壞了呢?”
“那再來找我。”我回答,又問,“不認識字和筆禿了呢?”
“B。”
“對,如果沒有字典或刨筆刀壞了,你再選D,再找我。”
“那什么選C?什么是可以不解決的問題?”
“舉個例子,上課大家討論時,忽然有人發言錯誤,這事兒就和你沒關系,不需要解決,也不用告訴我。”
“那么,選D的事,就可以找媽媽嗎?”
“寶貝,這段時間,媽媽和你都在家里各忙各的,在媽媽工作的時間里,你可不可以想一想這件事是不是一定要找人解決?是不是除了媽媽其他人也可以做?”
孩子在“爺爺、奶奶、爸爸、媽媽”4個選項里想了很久。
四
“聯合辦公”以來,我終于有了第一個完整的半小時。
千言萬語,匯成4句話,我打印出來,貼在孩子書桌的一角:
1. 你能解決的,不要找媽媽。
2. 能用工具解決的,已經有工具了,不要找媽媽。
3. 媽媽幫你解決過一次,也教過你怎么解決的,不要找媽媽。
4. 你解決不了,想一想,不解決也沒關系的,不要找媽媽。
祝福每一個在家辦公的職場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