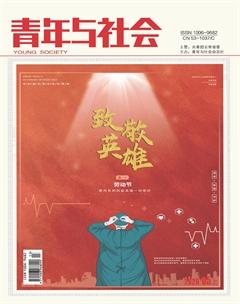“網紅打卡”亞文化現象的產生機理及對青少年產生的影響分析
李欣 劉新玲
摘 要:近兩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互聯網的騰飛,手機短視頻等社交軟件的火爆,在各種美景美照、視頻的推動下,不少“網紅打卡”旅游景點層出不窮。這些“網紅打卡圣地”以視覺消費為基礎,以媒介傳播為推手,以消費者滿足為導向,成長為了這一時代獨特的娛樂、信息、消費的全新結合體。但與此同時,也引發了大量的參與者主體性失落問題。文章亞文化研究的視角出發,探討“網紅打卡”這一現象的發展邏輯,并在此基礎上對此現象進行審視和反思。
關鍵詞:網紅打卡;亞文化現象;青少年
青年亞文化作為一種普遍而又獨特的文化現象,是人類社會文化結構中必然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相對于主流文化,青年一代的文化以其青春性、多變性和挑戰性的特性有別于位居主體的成人文化;而相對于基本認同主流價值的青年文化,青年亞文化則具有非主流、邊緣性的“亞”文化或“次”文化特征。“網紅打卡”現象是兩年來一直廣泛流行于青年群體當中的一種社會現象,伴隨著各種商業營銷和消費主義的鼓吹之下,“網紅打卡”行為泛濫,并且形成帶有鮮明“無腦跟風”色彩的青年亞文化集體,對當代青年的行為和價值觀造成巨大沖擊。綜上所述,“網紅打卡”行為是一種以現實為物質載體,網絡為傳播紐帶,崇尚展現自我,跟隨時尚潮流,但過程中盲目沖動,缺乏思考的青年亞文化現象。因此,深入研究“網紅打卡”亞文化現象產生的原因,分析其對青少年和當代社會造成的影響并對進行反思,對于青少年的價值觀引導具有現實意義。
一、“網紅打卡”亞文化現象的由來及分類概述
“打卡”一詞來自職場,本意是“工作人員上下班把考勤卡放在磁卡機上記錄上班和下班的時間”。但在網絡中傳播后,衍生成為來“提醒戒除某些壞習慣所做的承諾或者為了養成一個好習慣而努力的一種記錄”,繼而演變成為“新生代對某種堅持事宜或態度的記錄”。“打卡”人前往網紅地點,拍照留念,并在社交平臺表示:第一,這個熱議的地方本人來過了;第二,本人拍照或拍視頻而且在社交平臺中上傳了。微信朋友圈中出現的“網紅打卡”是指人們利用微信朋友圈這一平臺, 以展示自我的旅游、出行等成果為主要內容,以文字、圖片、視頻和鏈接分享的方式來發布打卡信息,進而通過好友的評論、點贊,進行人際交往的行為。 其具體表現形式有以下幾類:
(一)“網紅展”。“網紅展”,亦稱“快閃展”,是一種最先由海外興起的沉浸式娛樂展。通過當下最受歡迎的時尚元素及道具,結合VR、投影等新媒體手段,共同組成了聲、光、電的令參觀者有“沉浸式”體驗的幻想世界。2018年起,北上廣深等國內一線城市的熱門商圈、廣場、街區等人流量較大的地方,開始流行以“網紅藝術展”、“網紅沉浸式互動展”等命名的,面積在上百平到數千平米不等的類似展覽,涵蓋不同的主題區,以場景、道具、情節、互動等形式構成了沉浸式的體驗。這些展覽十分吸引年輕的受眾參觀并使其樂于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打卡”式傳播。
(二)“網紅”旅游景點。近兩年,隨著“抖音”、“快手”等短視頻社交軟件火爆,不少曾今小眾的旅游景點也漸漸出現在人們視線中。有時連當地人也不明白,對于他們來說一些常見普通的地方,一夜之間就變得人潮洶涌。就是通過短視頻社交軟件的迅速傳播,讓這些原本小眾的旅游景點甚至是未開發的普通小村落一下子走紅,再加上一些濾鏡、修圖或剪輯效果的美化,讓社交平臺另一端的觀眾看了就躍躍欲試,一時間大批游客慕名而來,特別是在法定節假日里,這些在短視頻等社交平臺爆紅的景點自然成為游客爭相“打卡”的目標。
(三)“網紅”店鋪。“網紅”餐廳、 “網紅”甜品店、“網紅”書店…… 這些“網紅”店鋪都具備一些重要的特點: 第一,顏值高。可能是產品的顏值高,也可能是店鋪的顏值高,并且通過顏值高的產品或店鋪吸引顧客,從而促進消費; 第二,年輕化。網紅店的目標受眾大多都是青少年群體,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較高,更熱愛新穎奇特的事物。因此,網紅店鋪所呈現出的年輕化的狀態,會讓年輕人甘愿買單; 第三,營銷方式新穎。有些“網紅”店鋪本身就是“網紅”所開,因此本身具備大量的年輕粉絲。有些店鋪則是通過明星代言或者各種社交平臺大肆渲染進行推廣,增加知名度。
二、“網紅打卡”青年亞文化現象的生成機理
(一)社會主義事業(工業化)的不斷發展青年亞文化現象的產生創造了客觀的物質條件。如今,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更加富裕,為青年們參與文化活動提供了經濟保障。 機械化則使得人們解放雙手,去從事更加豐富、有創造性的活動,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的工作日從一周六天逐漸減少到五天半,1995年工作日調整為一周五天,公眾假期也相應延長,列如春節、國慶節、勞動節等都增加了假期的時間。這些休閑時間的增多,都為青少年參與各種流行文化和亞文化活動提供了時間保障。“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高速鐵路、民用航空、高速公路等現代交通運輸方式,使“說走就走的旅行”成為現實。
(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為青年亞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求同存異,這就要去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城市的文化也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和多元性。商場、電影院、書店、劇院、展覽館、博物館等作為重要的文化基礎設施,也在不斷的發展和完善,“網紅打卡”青年亞文化在繁榮的城市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舞臺。
(三)一胎政策下的青年亞文化具有獨特性。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家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國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對現代中國家庭的規模和結構的變化產生了決定作用。在我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現代女性一方面受到高等教育,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獨立意識,另一方面受到家庭和社會的壓力,以現代女性為主要群體的“網紅打卡”行為為他們緩解現實壓力,提供了一個出口。同時,“打卡”的用戶很大程度上有外部自我形象構建的需求,并且在這一方面女性大于男性。同時,80后、90后、00后這一代人又與互聯網和社會媒體同時出生,“計劃生育”政策讓他們孤獨、互聯網和媒體則讓他們抱團取暖。“網紅打卡”行為依托于當下年輕人中最火的景點和事物,使得他們能在社交圈展示自我,互相“稱贊”,這是80后、90后、00后抱團取暖的重要方式。
(四)“網紅”經濟下商家的營銷手段加劇了“網紅打卡”行為在青少年中的蔓延。“網紅打卡”的主要分享平臺是微信朋友圈,其分享是一種幾乎零成本、效率卻極高的傳播手段。商家如果在微博、小紅書等年輕人匯集的APP以游客的身份進行宣傳并買“熱搜”占據前排,消費者很難判斷是否是營銷。在“網紅”店鋪如果商家有“朋友圈曬圖打折”的活動,也會有主動幫商家“達成營銷行為”的“分享者”。借助互聯網“云傳播”的效應,使得更多的人直奔心儀的人氣景點“打卡”。在這些人看來,去旅游的目的是為了發朋友圈。他們不太關注自身在旅行中享受了什么,而是“打卡式”奔赴一個又一個人氣景點。然后,一組9張圖將“打卡”景點展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繼續擴散。朋友圈廣告是一種“熟人圈”的廣告, 是基于社交關系鏈的互動傳播, 有很高的傳受信任度。另一方面, 朋友圈中點對點傳播的封閉空間, 使得廣告有更高的到達率。商家這種“熟人營銷”手段加劇了“網紅打卡”行為的蔓延。
三、“網紅打卡”亞文化現象產生的影響分析
(一) 積極影響。第一,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隨著 “網紅”景點在各平臺傳播開來,游客紛至沓來,網紅景區經濟效益可觀。很多原生態自然景觀一躍成為“網紅”,對當地的經濟發展產生著巨大的推動。游客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需要,也大大完善了當地的旅游業。第二,滿足當代年輕人社交需要。朋友圈中的“網紅打卡”實踐者將自己的“打卡”內容展現在朋友圈,在展示自我的同時其實也是想要融入社交圈的表現。別人在“打卡”,而自己沒有,就會有種與群體相背離的不安和焦慮,甚至有種被群體隔離的孤獨感,害怕自己與社交圈中所營造的氛圍格格不入。繼而,原本的“旁觀者”也為塑造理想的形象、獲得彼此的認同肯定,緩解知識焦慮而在不知不覺中加入這個打卡隊伍,轉變為“表演者”。《2018微信年度數據報告》顯示,2018年每天有10.1億用戶登錄微信。除了基本的社交,用戶還會通過微信朋友圈分享生活、表達情感。90后“打卡”群體的微信朋友圈往往涵蓋自己從小到大的親朋好友,“互贊”是與之保持練習和維系關系的一個重要手段。
(二)消極影響。第一,一昧追求“打卡”,或導致文化枯萎。尼爾 波茲曼(Neil Postman)曾在其著作《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談到: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在赫胥黎的構想中,人們將沉溺于工業化、模式化的產品無法自拔,被事物的表象所欺騙,習慣性麻木地接受那些浮于表面的現象,從而喪失了探索真理的能力,真理將被淹沒在無聊繁瑣的世事中。赫胥黎的擔心與 “網紅打卡”行為的出現與流行似乎如出一轍。旅游打卡本事變現對生活的熱愛,但卻在朋友圈中漸漸成為個人通過有選擇地展示來期待獲取他人關注和認可的一種“表演”,打卡人極力在中構建和塑造自己在他人心中理想化形象。所以每當他們在朋友圈完成了打卡時,就開始期待有人點贊、盼望有人評價,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受關注度和存在感。打卡本身只是一種形式,有意義的是打卡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所因為癡迷打卡而忘了初衷,就如同《娛樂至死》中所說,失了探索真理的能力,真理將被淹沒在無聊繁瑣的世事中。在被好友“點贊”過程中,漸漸地會沉浸在被夸贊的優越感與成就感中,變成為了打卡而打卡。而且以點贊的形式來獲取關注度和滿足感的行為會漸漸發展成偏執的心理,長此以往,混淆真實自我和“照片中”自我,產生認知偏差,加劇自我認同危機,并最終迷失真實的自我,甚至還會影響自身的學習實踐能力。第二,時間和資源的浪費。隨著網紅景點的誕生,帶來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如有些景點照片經濾鏡處理后和原貌相距甚遠,沒有達到游客的期望值,最后演變成鬧心之旅。盲目跟風的“打卡”式的行為,不僅造成時間的浪費,也是對社會公共資源的一種浪費。第三,存在安全隱患。“打卡”旅游很難真正享受到旅游所帶來的樂趣。人氣景點人山人海,吃飯、如廁都需要排長龍的尷尬場景尚在其次,關鍵是一些網紅景點位于水邊、山邊,且有的區域處于全開放狀態,人一擁擠,很容易造成意外情況發生。第四,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一些原生態自然景觀遭到大量游客“侵襲”,游客超過地域承載能力,導致當地生態破壞嚴重,給景點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
面對當下最為流行的“網紅打卡“亞文化現象,青少年應該有自己的判斷。歌德曾經說過,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如果旅游淪為簡單的“打卡”發朋友圈,出行只為獲得點贊和他人的羨慕,對于旅游者本身而言,遠遠背離了旅行自身具有的意義。游客更應該要注重旅游本身的意義,從中體會到樂趣,而不是拘泥于形式,過分追求他人的贊賞和執于“打卡”,容易陷入形式化的“打卡怪圈”中,只看重關注度,而忽視自身內在充實與提高。
參考文獻
[1] 陳一,馬中紅. 新媒介與青年亞文化:拍客:炫目與自戀 [M].江蘇: 蘇州大學出版社,2013: 1-5.
[2]馬中紅.新媒介與青年亞文化轉向[J].文藝研究,2010(12):104-112.
[3]陳霖.新媒介空間與青年亞文化傳播[J].江蘇社會科學,2016(04):199-205.
[4]王桂亭.話語權的回歸:論網絡語境下的青年影像[J].當代青年研究,2013(02):23-27.
[5]方健華.賽伯空間:又一個“娛樂至死”的舞臺?——關于網絡文化對青少年發展影響的思考[J].中國青年研究,2014(07):25-30.
[6]徐振祥.新媒體: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機遇與挑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06):64-66.
作者簡介:李欣(1994- ),女,寧夏石嘴山人,碩士,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方向:青年問題研究;劉新玲(1966-),女,河南人新鄉人,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青年發展與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