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位淘汰、組織架構調整,如何向勞動法看齊
李永超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企業生產經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疫情的沖擊導致經濟活動停滯或者放緩,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在企業經營業務難以正常運行的情況之下,采取降薪或者裁減人員的措施無可厚非,勞動者接受或者不接受企業的安排亦情有可原。
有媒體報道,一些城市里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申請勞動爭議仲裁的勞動者時常排起長龍,受到疫情的影響,勞動關系的矛盾依然嚴峻。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既要關注怎么“活下去”,同時也要關注如何處理好與員工之間的關系。
新聞鏈接
據媒體報道,2月12日,新潮傳媒集團創始人張繼學回應公司“減員500人”消息時表示,公司只是在進行合理的部門調整和“271末位淘汰”考核(注,“271末位淘汰”是每年度都會進行的管理考核)。公司技術研發崗、銷售崗和商業事業部等正在招聘100多人。
2月24日,碧桂園宣布對多個區域和集團進行調整,包括將總部投資、設計兩個中心合并,成立投資策劃中心;減少14個區域,調整后共剩下55個區域、指揮部;38位高管換防,34名高管被免職,其中4名另有任用,1名主動離職,總部職能高管和區域總裁輪換。碧桂園總裁兼執行董事莫斌回應稱,“不是裁員,是優化組織架構,做績效考核,員工也有進有退”。
3月29日,有網絡傳言稱“360被曝裁員,比例為15%到20%”,對此消息,360公司向媒體回應稱:目前沒有裁員計劃,為不斷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公司每年都會對人員進行常規化的績效考核優化。隨著業務發展的需要,當前公司正采用社招、校招等方式大力招聘,主要涉及城市安全、企業安全、互聯網、游戲和IoT智能硬件等業務領域。
4月12日,海信集團公布的《海信集團關于優勝劣汰提效求生的說明》稱:受全球疫情影響,家電行業國內外市場均出現較大規模下滑。海信海外業務收入占集團整體收入已超過40%,經營形勢更加嚴峻。我們和所有企業一樣,面臨渡過難關、保住數萬名優秀員工飯碗的艱苦挑戰。為此,我們采取高管帶頭降薪、通過末位淘汰加速員工隊伍優勝劣汰等措施,激發全體員工斗志,層層傳遞壓力、提高系統效率,以穩住業績,且通過逆境鍛造更加健康的企業肌體。目前,網絡已有的關于海信定量裁員的信息,其中的數據并不屬實。
末位淘汰制度與解除勞動關系對應關系
末位淘汰制度屬于一種績效考核制度,簡言之,通過設定考核指標體系,根據對員工的考評結果,對考評結果靠后的員工進行淘汰。無論是361、371機制,還是262、352機制,末位淘汰制度的積極作用在于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消極影響在于該方式過于殘酷,因為終究會有人被淘汰。
這種績效考核方式對應到法律層面,則無法構成解除勞動關系的法定事由,在法律層面與之類似的是“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18號指導案例——中興通訊(杭州)有限責任公司訴王某勞動合同糾紛案中,法院生效裁判認為: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對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條件進行了明確限定。
原告中興通訊以被告王某不勝任工作,經轉崗后仍不勝任工作為由,解除勞動合同,對此應負舉證責任。根據《員工績效管理辦法》的規定,“C(C1、C2)考核等級的比例為10%”,雖然王某曾經的考核結果為C2,但是C2等級并不完全等同于“不能勝任工作”,中興通訊僅憑該限定考核等級比例的考核結果,不能證明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不符合據此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定條件。雖然2009年1月王某從分銷科轉崗,但是轉崗前后均從事銷售工作,并存在分銷科解散導致王某轉崗這一根本原因,故不能證明王某系因不能勝任工作而轉崗。因此,中興通訊主張王某不勝任工作,經轉崗后仍然不勝任工作的依據不足,存在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應當依法向王某支付經濟補償標準二倍的賠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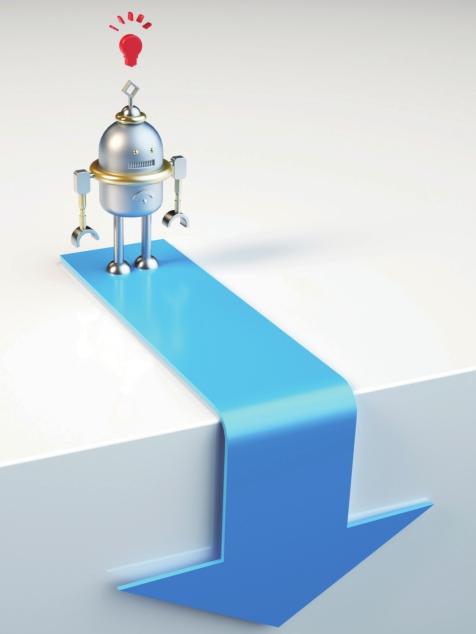
《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民事部分)紀要》中明確,用人單位在勞動合同期限內通過末位淘汰或競爭上崗等形式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勞動者可以用人單位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為由,請求用人單位繼續履行勞動合同或者支付賠償金。最高人民法院法民一庭負責人表示,末位淘汰與解除勞動合同之間不能等同,解除勞動合同必須依法進行。從勞動合同法來看,我國法律沒有允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以末位淘汰為由解除勞動合同,可見企業管理考核中的末位員工被“淘汰”,缺乏法律依據。
其中,“淘汰”作為一個動詞,意指留下好的,去掉不合適的、保留合適的。從崗位任職的角度來看,把不適合崗位任職要求的人去掉是為了“淘汰”,從企業宏觀的角度來看,把不適合企業發展的人去掉也是為了“淘汰”,唯有后者才會涉及法律上的解除勞動關系事宜。
回歸到實務操作上,將末位淘汰制度應用在降職降級、降薪、獎金、培訓方面則相對比較容易實施,即可以事先通過勞動合同或者崗位聘用協議,對末位淘汰制度的規則約定清楚,或者對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規章制度給予確認,那么,從法律角度來看,實施過程中的風險基本上是可控的,當然可以通過事后的協商就降職降級、降薪、獎金、培訓等達成一致,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若將末位淘汰制度應用到解除勞動關系方面,最優的選擇是協商解除勞動合同,配合上述情形應該會得到更佳的應用效果;若想通過不勝任來解除勞動合同,則需要更換為其他的考核方式,比如KPI等。
組織架構調整與解除勞動關系對應關系
實踐中,企業根據自身的經營活動對組織架構進行調整,屬于企業正常的經營活動內容之一。但是,這種調整通常與勞動關系密切相關,可能會引起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勞動報酬、勞動條件等的變化,甚至會直接影響到勞動關系的存續。從法律角度來看,組織架構調整未必構成法定的調崗調薪、調整工作地點的條件;從解除勞動關系的角度來看,涉及組織架構調整時,通常會援引客觀情況發生變化來解除勞動關系,那么,組織架構調整是否會構成客觀情況變化?

原勞動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條文的說明》第二十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但是應當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當事人協商不能就變更勞動合同達成協議的”。這里的“客觀情況”指發生不可抗力或出現致使勞動合同全部或部分條款無法履行的情況,如企業遷移、被兼并、企業資產轉移等,并且排除本法第二十七條所列的客觀情況。同時,北上廣地區的相關案例可供讀者參考。
發生在北京市的一則案件中,法院生效判決認為,原勞動部《關于若干條文的說明》第二十六條規定,“A公司重組公司結構,取消獨立配餐市場業務線,建立分行業的垂直商業模式,系該公司根據生產經營需要,為應對市場變化主動采取的經營策略調整,不屬于‘ 訂立勞動合同時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 的情形。A公司以此為由解除與郭某的勞動合同,系違法解除,應當足額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詳情參見北京一中院[2017]京01民終2833號)。
另一則案件中,法院生效判決認為,B公司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客觀情況發生變化足以導致雙方的勞動合同無法繼續履行的具體程度,其所主張的公司部門合并是其公司內部主觀的經營調整行為,不屬于法律所規定的客觀情況發生了足以導致不能繼續履行勞動合同的重大變化,并且B公司在與劉某協商勞動合同變更事宜時大幅度降低薪酬,屬于單方面變更原有書面勞動合同的內容,明顯缺乏法律依據,B公司以不能協商一致為由解除雙方的勞動合同構成違法,應當向劉某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詳情參見北京二中院[2017]京02民終8363號)。
發生在上海市的一則案件中,法院生效判決認為,從本案現有證據及查明之事實可見,C公司因連年虧損、銷售額下滑進行組織機構調整,劉某所在的工作部門及崗位已撤銷,此系企業根據市場變化調整經營策略,完善企業的組織架構的經營自主權之體現,劉某亦確認組織架構調整后,其原來的針織流水線解決方案組被撤銷。在此情形下,法律明確規定用人單位有與勞動者重新協商變更勞動合同內容的義務,以促成本無法履行的勞動合同通過變更內容后得以繼續履行,維護勞動關系的穩定性。但協商變更屬雙方重新擬定合同條款,雙方當事人可平等協商,根據本案現有證據及查明之事實可見,C公司于原審中提交了國內外派遣意向調查郵件、面談郵件、費用支付協議書、海外派遣協議書解除、終止人員對應進度表、勞動合同協商解除協議等一系列證據,可以證實C公司已就協商變更勞動合同作出相應舉措,劉某主張所謂面談即系了解家庭情況缺乏合理性,本院難以采信,雙方未能協商達成一致意見亦系客觀事實,在此情況下,因協商不成,C公司向劉某發放經濟補償金符合法律規定。劉某要求C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的請求,不予支持(詳情參見上海二中院[2017]滬02民終8634號)。
另一則案件中,受理法院認為,解決勞動爭議,應當根據合法、公正、及時處理的原則,依法維護勞動爭議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本案中,被上訴人D公司因其公司經營發展之客觀需要而決定調整公司架構,撤銷公司的相關崗位,確構成雙方2012年6月1日變更勞動合同時所依據之客觀情況的重大變化。上訴人王某主張因相關崗位取消是D公司自身調整所致,故而不構成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缺乏依據,本院不予采納(詳情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滬一中民三(民)終字第166號)。
發生在廣東省的一則案件中,法院認為,關于解除勞動關系合法性問題,本案中,E公司主張雙方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是指E公司于2014年期間收購F保健消費品事業部和G有限公司后,三合一的銷售部組織架構暴露出銷售結構復雜、效率低、崗位功能存在沖突等弊病,需要進行組織結構調整,將原來的按渠道、客戶大小、區域劃分調整為僅按渠道、區域劃分的經營模式。在E公司于2016年4月進行銷售部組織架構調整時導致部分地區出現缺人或多人的情況而不得不將馬某等人在廣州的崗位撤銷。受理法院認為,《勞動合同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的“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應解釋為因履行原勞動合同所必要的客觀條件,因不可抗力或出現致使勞動合同全部或部分條款無法履行的其他情況,如出現受法律、法規、政策變化導致用人單位遷移、資產轉移或者停產、轉產、轉(改)制等重大變化的情形或者特許經營性質的用人單位經營范圍等發生變化等情形,使原勞動合同不能履行或不必要履行的情況。E公司是因公司合并而對銷售部門的組織架構進行優化調整,此類結構優化調整屬于其經營情況的變化,屬于用人單位根據市場經營情況對公司架構所進行的正常調整,不屬于“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詳情參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1民終14605號)。
根據各地案例判決的觀察和分析,除上海市外,普遍觀點認為,企業組織架構調整無法構成客觀情況變化,若在此時企業需要解除與員工之間的勞動關系,協商解除就是最優的路徑。簡言之,一些報道中提到企業回應有關裁員系人員優化導致的組織架構調整,從法律角度來看該表述并不準確;從實務操作層面來看,若無法與員工達成協商一致,難免會對簿公堂,離職員工成為申請仲裁排隊中的一員,對于企業而言,這何嘗不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損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