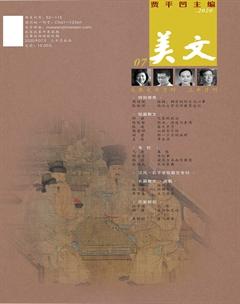取法、悟道與表情
陳俊哲
取 法
書法之所以稱之為書法,是因為書法有法。書法有筆法、字法、章法、墨法、身法之分,有篆法、隸法、楷法、行法、草法之別;有碑學、帖學之分,古法、今法之別;還可以有坐法、站法之分,大字法、小字法之別等等,它是千百年來勞動人民書寫經驗的總結,是運用毛筆合于規律的便于情感表達的書寫技法的總稱。
“書法一定要講法,離開法就不能稱之為藝術。古今中外的書法大家都是在嚴格的法度下進行書法實踐的。”(《胡抗美書學論稿》,第2頁)寫任何字體和書風,都是“戴著鐐銬跳舞”,都必須有技法觀念,受技法約束。不掌握技法,只能是胡寫亂畫、“野狐禪”,是糟蹋行道,就沒有談論書法的資格。
如何取得技法是學書者繞不開的問題。關鍵一條是路子要正,即要解決好目標方向問題、路徑方法問題。我以為要做到“五須”:
一須古。這是取法的目標定位問題。書法取法高古,一般指取以“二王”為代表的魏晉之法。米芾云:“草書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明人范允臨《輸蓼館集》亦云:“學書不學晉人轍,終成下品。”學書須古,取法乎上。對此,胡抗美先生直截了當地說:“當今臨王覺斯成風,即便臨得極像王覺斯,王的前面還有米芾,米的前面還有張旭、懷素,還有歐、顏、柳、褚,還有王羲之、王獻之。既然如此,始臨便習‘二王,豈不高古!”(《胡抗美書學論稿》,第7頁)“二王”的行草書,承漢隸余風,體質高古,是總結前人書法成就的基礎上創造的行草書的新的書體樣式,代表了中國書法藝術的高峰。后來的書家如李北海、顏魯公,蘇、黃、米、蔡等等,莫不把“二王”當作偉大的典范,從中汲取他們所需要的營養而各自成家。孫過庭《書譜》云:“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欲取“心手會歸”“轉用之術”,不自源頭,不循樹干,而趨支流、分條之處,不跟古人而從后人今人,不是取乎其下,舍本求末嗎?
二須專。這是取法的初段功夫。習古人書,必先專精一家,最好取魏晉大家一人為宗主,朝夕沉酣其中,矢志不移。縱有人譽我、謗我,我只不為所動,至于信手觸筆,無所不似的標準才行。孫過庭《書譜》云:“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是這一階段的無等等咒也。要拿出百分之百的勇氣,千百遍地讀與臨結合,把藏鋒與露鋒、圓筆與方筆、折筆與轉筆、提筆與按筆、疾筆與澀筆等基本筆法,把哪粗哪細、哪長哪短、哪大哪小、哪高哪低、哪收哪放、哪快哪慢、哪動哪靜等基本字法,還要把畫與畫之間斷連法、字與字間的顧盼法、行與行間的呼應法、通篇中的黑與白、虛與實的對比法等基本的章法在專精一家中取到手。一根筋,一條道走到黑,不達目的不換帖,一開始就給自己打一口深水井,打牢根基,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
三須博。這是取法的中段功夫。學書若專精一家,不知博研眾體,融會群妙,到頭來為此家所蓋,枉費一生氣力。吃透一家,遍臨百家,才能自成一家,古賢莫不如此。何紹基云,博研眾體,或取其神,或取其韻,或取其勢,或取其用筆,或取其結構,或取其章法,專注于一端,才能有所收獲。如此,每臨必有所收獲,不斷為自己的武庫增添利器,練得十八般武藝,上了戰場,自然呼風喚雨,縱橫捭闔。反之,對眾體知之甚少,技法單一,缺乏表現手段,內心空虛,只能循規蹈矩,重復一家模樣,淪為這家之奴。
四須用。取法的目的全在于運用,運用是對取法效果的檢驗和鞏固。取法和運用一開始就應該結合起來并貫穿取法的始終,讓取法和運用共同促進,讓學書者現學現用,時時嘗到學書的甜頭而樂此不疲。這種臨古取法和創作運用不同階段皆可適用。專精一家時,用“集字”法臨寫,用這一家的面目寫不同的內容,何嘗不是創作運用,而且是實踐證明了的取用結合的“靈丹”。千百年來,有誰能說懷仁和尚用25年集王羲之寫成《圣教序》不是取用結合的杰作。我認為米芾的數十年集古字而成一家,王鐸的“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就是把取法和運用、把繼承與創新結合運用的典范。博涉百家后的運用是運用的較高階段。此時可用一體一家之法臨寫他體他家。例如,某書家用漢簡之法寫漢碑,給碑刻隸書中注入簡牘隸書的自然率真,運用出新境。再如,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說他用王獻之的筆法筆意,臨懷素的《自敘帖》,把《自敘帖》臨出大令的味道,不像《自敘帖》,又像《自敘帖》;不像大令,又有大令;不像董其昌,又是董其昌,這是運用,更是創新。
五須恒。中國書法經典法帖博大精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寶藏。所以臨古取法永遠在路上,沒有完成時。臨帖是書家的畢生功課。常臨常新,臨一次就提高一次,一天不臨就要落伍。數十年來,一茬茬的書法名家潮起潮落,始終站在潮頭的人,是臨帖不輟,活到老臨到老的人。那些出名后不再臨帖,早早定型結殼的人,最終走向式微。
悟 道
《黃帝內經》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陰陽的對立統一是“天地之道”,是世間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規律,他構成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動力和實質內容。用列寧的話說:“他提供理解一切現存事物的自己運動的鑰匙。”(《列寧全集》中文2版,第55卷,306頁)一陰一陽謂之道,書法也不例外。王羲之《記白云先生書訣》云:“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劉熙載《書概》亦云:“書要兼備陰陽二氣。”
其一,陰陽的對立統一存在于筆墨運動的整個過程。線條的長與短、曲與直、俯與仰,字形的大與小、正與攲、動與靜,墨色的濃與淡、枯與潤,章法的虛與實、白與黑、有與無等的對立統一構成書作的實質內容。一畫之內,“橫則上面為陽,下面為陰;豎則左面為陽,右面為陰”(劉熙載《書概》);一字之內,左右或上下間“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孫過庭《書譜》);畫與畫之間有收有放,有俯有仰;字與字乃至行與行之間有正有攲,有開有合等等。可以說,由點畫到結字到篇章的運動中,陰陽的對立統一,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不存在沒有陰陽的點畫形式,也不存在沒有矛盾的點畫狀態。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后》云:“若平直相似,狀與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齊平,便不是書。”正是因為這種漂亮的“美術字”,缺失了“陰陽二氣”,違背了“混元之理”。
其二,筆墨運動的整個過程中,多方面的陰陽對立統一交織起來,但各自特點不同。表現在一幅書法創作過程的不同階段矛盾各不相同。點畫內部主要是方與圓、藏與露、尖與鈍、粗與細、提與按、快與慢、輕與重、疾與澀、中與側等等的對立統一;字內、字與字、字與字組、組與組乃至行與行之間主要是收與放、開與合、斷與連、寬與窄、大與小、正與斜、疏與密等等的對立統一;篇章中主要是虛與實、黑與白、有與無等等矛盾的對立統一。還表現在不同幅書法創作中,矛盾的特點不同。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不同書家、不同情感下的矛盾千差萬別,甚至同一書家書寫同一內容,其作品內部的陰陽變化及其形式構成相去甚遠。這種矛盾的復雜性、特殊性決定了書法藝術作品沒有雷同只有創新,真正的藝術品沒有復制的,復制的叫贗品。那些仿制古人他人作品的抄襲者們,看不到陰陽變化的豐富性、特殊性。對此,胡抗美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泥古、復印、仿制這只不過是簡單的重復勞動而已,談不上什么審美價值。它缺乏的是藝術靈魂,是個人鮮活的意志和綜合素質的修養。這就是流俗!”(胡抗美《中國書法藝術當代性論稿》,第168頁)
其三,陰陽雙方相互制約、互相聯系、互相轉化。一畫的藏與露、疾與澀、方與圓,規定了一字的收與放、正與側、大與小;而一字的這些矛盾又規定了一組、一行乃至終篇的虛與實、黑與白、有與無,正所謂:“一點成一字之規,一畫乃終篇之準。”(孫過庭《書譜》)一畫內須有提有按,一字內需有收有放,一字組內需有左搖右擺,一章節中,前面 “密不透風”,后面需“疏可走馬”,正所謂:“至若數畫并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孫過庭《書譜》)一幅完整的書作就是這樣,“從一筆到千筆萬筆,無非相生相讓,活現出一個特地境界來。”(張式《畫譚》)一幅完美的書作也就是這般,“一點一線、一字一行,其構成正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胡抗美《中國書法藝術當代性論稿》,第60頁)
總之,筆畫線條、結體造型和通篇構成的時空運動中無不體現“天地之道”“混元之理”,書法作品的一畫一字一篇無不被辯證思想的靈光照耀。書法要有思想,思想決定著作品的藝術水平。“書法是外形與作品思想的結合物,沒有思想的作品只能稱之為寫字,根本談不上藝術。”(胡抗美《中國書法藝術當代性論稿》,第139頁)“一幅佳作的效果,便是哲學道理的藝術闡述。書法大師的地位,一般由其作品所表現的哲學思想,如對立統一觀點的運用來評定的。”(《胡抗美書學論稿》,第61頁)不悟天地之道,不諳陰陽兩竅,沒有思想的燈火照亮,書字便如晝夜獨行,全是魔道矣。如此“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孫過庭《書譜》)
書法創作的道理思想源泉本于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一是古人的生產和生活實踐,集中表現在以儒、釋、道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之中;二是今人的生產和生活,包括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自然風光等。我們要多讀書,特別是讀哲學、美學、文學、中國書法史、歷代書論等,還要甘當小學生,到基層去,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中去,到大自然中去,虛心向人民群眾、向大自然學習。劉熙載《書概》云:“與天為徒,與古為徒,皆學書者所有事也。”此言,是有志學書人的寶典。
表 情
表情,就是表達情感。任何藝術都是表達人的情感的。楊雄《法言·問神》曰“書,心畫也”,孫過庭《書譜》言書法是“達其情性,行其哀樂”,劉熙載《書概》云“寫字者,寫志也”……古先賢們一脈相承,揭示了表達情感是書法有別于其他意識形態,而成為一門藝術的本質特征。
列夫·托爾斯泰在《藝術論》中給藝術這樣定義:“藝術是這樣一項人類活動,一個人用某種外在標志有意識地把自己體驗過的感情傳達給別人,而別人為這種感情所感染,也體驗到這些感情。”(《西方文論選》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433頁)情感是人對客觀事物是否滿足自己需要的態度體驗。它作為“心靈中的不確定的模糊隱約的部分”,“純粹是主觀感動的一種空洞的形式”(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34頁),只有借助某種“外在標志”(抽象地說就是“形式”)才能為別人感官接受并體驗。文學借助語言形式,繪畫借助色彩形式,音樂借助旋律形式,戲劇借助身姿形式……而書法是通過什么形式(或“外在標志”)表達情感的呢?胡抗美先生形象地說:“書法是書法家不同情感通過造型元素的擺兵布陣。”“點畫線條的粗與細、長與短;用筆的中鋒與側鋒及方與圓;結體的大與小,正與攲;行的搖擺,列的疏密,組的斷續,塊的呼應等,都不是無緣無故的,既不是古代經典造型的復制,也不是個人書寫習慣的重復,而是手舞足蹈、咬牙切齒、茶飯不香、痛心疾首的演示。”(胡抗美《中國書法當代性論稿》,第342頁)
情感作為人類活動的心理動力之一,在書法創作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造形作用。書法家將自己的人格、理想、目的、需要等一切心理因素凝聚成一種情感力量,借助筆墨線條這種“外在標志”表現出來,完成“情感造形”,造型的結果把情感和形式高度統一為“情感形式”。英國美學家克萊貝爾在他的《藝術》一書中把這種審美的、感人形式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
虞世南《筆髓論》云:“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情通變,其常不主。”虞世南無意之中道出了這種“情感形式”的四個意味特征:
一通于陰陽。情感形式的一舉一動稟持“陰陽二氣”,合于“天地之道”,決非筆墨線條的信馬由韁、胡寫亂畫。
二造乎自然。情感形式的造型結構與生命結構是相似的,是“體萬物以成形”,將人或自然的某種形態化入其中,決非書法家的任筆為體,聚墨成形。用蔡邕《筆論》的話說,“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用宗白華的話說,情感形式“它不是摹繪實物,卻又不完全抽象,有如西洋字母而保有暗示實物和生命的姿式”(宗白華《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
三承載情感。情感形式是書家情感的載體,依格式塔心理學派的看法,其每一個形式單位可以和某一細微的情感因子異質同構。
四不主故常。兵無常形,字無常態。情感形式當如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所云:“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為正,不主故常。”
大凡人們經歷了斗轉星移、淪海桑田之后,其精神世界深邃的層面遇到某種外在因素的碰撞,便情不自禁,形諸于外。情感的力量使書家手中的筆錐像受到某種魔力的裹挾,提按頓挫、輕重快慢,筆力“往往出現時而在筆尖,時而筆肚,時而筆根,或者三者難分難辨的混合運用狀況。”(胡抗美《中國書法藝術當代性論稿》,第157頁)“激動高漲的情緒表現為較強的力度和較快的速度,平和悠閑的情緒表現為較弱的力度和較慢的速度。”(同上,第192頁)書法家的心靈的東西就是這樣順著筆毫噴涌而下,妙緒迭出,創造出連書家自己都感到驚訝的佳妙杰作。王羲之《蘭亭序》正是在惠風和暢、群賢畢至、曲水流觴之后的激情之作,以至于他后來以此為內容再次創作時,總不如意。宋代書家雷簡夫的故事頗有說服力。他在嘉陵江邊為濤聲動容,偶然欲書。他說:“余偶晝臥,聞江漲聲。想波濤翻翻,迅駃掀搕,高下蹙逐奔去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書,則心中之想,盡在筆下矣!”只可惜雷簡夫的寄情之作我等無法見到。觀中國書法璀璨星空,《蘭亭序》《祭侄稿》《自敘帖》《喪亂帖》《寒食帖》等等書法史上的經典作品無一不是有感而發、感情充沛、憂思郁憤之作。千百年來,這些經典杰作穿透歷史的時空隧道,感動著一代又一代人,根本原因在于作品本身深厚的情感力量。
但是,當我們從書法藝術的本質屬性的探究回到當今書壇的現狀時,我們看到的是把漢字寫的橫平豎直、對稱均勻,寫得“漂亮”等同于書法藝術;把機械地模仿抄襲某人某家的書法作品,一種匠人的炫技,等同于書法藝術的偽書法家大行其道。看不到情感的表達,甚至是虛偽的情感表達,完全背離了書法藝術的本質要求,肆意踐踏中國書法藝術的尊嚴而成為怪胎。我們要把藝術之根牢牢扎在傳統經典里,不斷提高辨別是非美丑雅俗的能力,才能與偽書法劃清界限。我們還要不斷加強自身修養,在火熱生活中修煉自己的美好情感,努力使自己的情感更敏銳、更強烈、更博大、更高尚、更真誠,通過提升做人的境界提升作品的境界,這樣我們才能創造出無愧于這個偉大時代的書法藝術。否則終日汲汲于名利,戚戚于貴賤,淪為俗人,字也終是俗字,“惟俗不可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