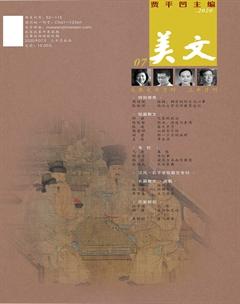陜西“饸饹”之脈絡
張同武
“饸饹”是北方的一種重要面食,陜甘寧青以至蒙晉冀豫等地都吃,而且都認為自己那口更好吃,敝帚自珍、口味習慣。
陜西的陜北、關中地面,饸饹是極其常見的,食材主要以蕎麥面為主,當然,小眾的還有玉米面、紅苕面等,如果愿意,小麥面當然也可以。
之所以會有“饸饹”這種吃法,竊以為是為了把“雜糧”變花樣吃。比如蕎麥,說起來營養價值高、種起來也不挑地,耐寒耐旱耐貧瘠,在自然條件不是很好的地方廣為種植,藉以養活子民。但之所以被稱之為“雜糧”,應該是指小麥、水稻之外的另類,雖則是糧食,但“筋度”較弱、質感粗糲、結構松散,不可能像小麥、水稻那樣的做法和吃法。為了果腹,并為了容易下咽,“雜糧”們就被賦之以各種手法獨特并千變萬化的做法,初衷應該是容易下肚。比如蕎麥面難以搟制面條,也難以做饅頭,琢磨來琢磨去、試驗來試驗去,好像就是做成“饸饹”比較現實、比較好吃,也接近小麥的做法與吃法,所以“饸饹”便大行其道。在這樣的啟示之下,其他的雜糧,比如玉米、紅苕乃至高粱等,也被做成“饸饹”,藉以解小麥匱乏之苦、聊解饞羨面條之情。
不想“饸饹”這種無奈之舉,倒成就了面食的另一種經典做法,也造就了一代美味。“饸饹”以其獨特的口感、豐富的調制手法,進而躋身于面食的主要序列,以至于后來還有人用小麥面壓制饸饹,換個花樣,比較起面條來還是另一種風味呢。
陜西南北狹長,跨越了三個氣候帶。陜南可以視作南方,不用考慮灌溉用水。而陜北乃至關中長期缺水,以至于“治秦先治水”,解決干旱始終是農業重任,而廣為種植蕎麥等雜糧也是應景之選。種得多了,吃的自然多,從陜北到關中,蕎麥的品種也因土壤氣候等原因有所不同,飲食習慣、文化背景乃至經濟發展狀況也大有差別,于是,這“饸饹”也就有了不同的豐富吃法。時間久了,都認為自己那一碗最好吃,這是自然。
前面說過,陜西地界上,從陜北到關中都吃饸饹,但風格各異,各有特色,主要體現在調制饸饹的方式方法,大概分個類,有以下幾個層面:
陜北的饸饹突出了羊肉,作為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交融的地區,陜北的羊很好,羊肉做得更好吃,陜北人擅長做羊肉更極奢吃羊肉,所以在它的幾樣面制品的調制上,一如既往地把“羊腥湯”發揚光大。一碗饸饹,澆上燉得香氣四溢的羊肉,撒點生蔥花、香菜、辣椒面,那滋味就是神仙也抵擋不了,難怪要說“蕎面圪坨羊腥湯,生生死死相跟上”。圪坨,是另外一種塊狀的蕎面制品。羊肉饸饹,是陜北饸饹的不二特色,當地吃“地椒草”長大的羊,在生長過程中似乎就把自己拌和好了,加上當地紅蔥等配料燉得軟爛的羊肉,配上品種獨特的、顏色較白的蕎面,這一碗之中,脂肪與碳水和諧地融合科學地搭配,真真是蕎面饸饹的絕佳伴侶。在陜北,“羊肉蕎面饸饹”隨處可見,幾乎每個地方都做,風格也基本統一,當然突出的是那拌和的燉羊肉,所以定邊、靖邊、橫山、吳起等出產好羊肉的地方,饸饹更好吃。
在陜北,羊肉饸饹既是家常飯,更是待客的首選,如果有紅白事,一定會拉開架勢,大規模地“壓饸饹”。起先的“饸饹床子”無甚奇特,就是一般的支架在熱鍋之上的家用的。后來隨著陜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日子好過了,就連“饸饹床子”也長大了,曾經在一個圖片上看到一個長與高各幾米的巨大的“饸饹床子”,不但效率高了,就連壓制饸饹的場景也有了藝術表演的成分,陜北人骨子里的豪邁與好客于此可見一斑。
關中的饸饹也幾乎是到處都有,但做得比較好的、吃得比較多的相對集中在兩個區域,一是蕎麥的主產區,二是飲食文化與人員流動都比較發達的地方。
關中的蕎麥主產區集中在北部,也就是關中平原與黃土高原的接壤或過渡地段,這些地方耕作條件稍差,更為適宜種植蕎麥。顛撲不破的道理,出產什么吃什么、多吃什么就會做好什么,蕎面吃得多了,自然就做出特色了。

這其中首推淳化、旬邑兩縣。這兩個縣隸屬咸陽,是其“北五縣”范疇,蕎麥種植面積大,蕎面饸饹做得很好吃。這兩個縣的饸饹,特色在于那一鍋“臊子湯”,做這個臊子湯,核心在于“煎辣子油”,它不同于一般的油潑辣子把熱油澆潑在辣子面上,獨特的是它要先在鍋里燒油,待油溫熱,再放辣子面。這里的關鍵有兩點,一是掌握好油溫,二是撒入辣椒面后要快速攪拌,之后慢慢“煎熬”這油辣子或辣子油,這是一鍋臊子湯的靈魂,好吃與否關鍵在此。“煎熬”好辣子油,再依次加入肉蔬配料,再調味、加水或肉湯,最后,一鍋紅艷艷的、配料豐富的、香氣四溢的“臊子湯”即成。好了,只管往壓制好的饸饹上澆蓋,只是那紅得發艷的顏色和似乎遮蓋在上面的一層油脂,初食者往往會畏懼,但嘗試了就丟不下筷子了。這一鍋臊子湯,油而不膩、辣而不燥、滋味醇厚,吃一口饸饹喝一口湯,那感覺就快要起飛了。
與陜北饸饹異同的是,這里的饸饹也是蕎面,臊子也用羊肉,但還有雞肉、大肉、豆腐、紅蘿卜、黃花等物,更豐盛,農耕文化的痕跡更重一些。之所以把“淳化、旬邑”兩縣的饸饹拿到一起說,是覺得風格大體差不多。但人家各自都認為自己的饸饹最好吃,呵呵,這太正常了,誰不認為自己家鄉的那一口更好呢?都好、都不錯。有趣的是,這里的人可能吃饸饹吃得時間長數量多,吃的時候好像更專業,只管吸溜,似乎都不用咀嚼,時間久了,干脆就把吃饸饹叫做“吸”饸饹。“伙計,吸饸饹去!”當是一句熱絡的親近的話,如果到這個地方有人請你“吸饸饹”,那可是把你當自己人了。當然,這里的紅白事也是主打吃饸饹,在路上遇到熟人打招呼“干啥去”?“到娃他姨家吸饸饹去呀!”那是親戚家有喜事呢。
另一個與陜北接壤的地界,銅川,也有好吃的饸饹。當地人都知道“北關饸饹”,那是銅川北關一帶的幾家饸饹做得很有特色。這里的饸饹一般倒不是現壓現吃,而是分工明確,有專門壓饸饹的作坊負責壓饸饹,賣饸饹的攤主批發了饸饹之后,自己準備臊子湯,食客吃的時候再現場“泖”,這個做法與銅川的另一種名吃“耀州咸湯面”類似。這里的饸饹口感更筋道一些,那一鍋“臊子湯”滋味更豐富一些,可能也是沾了當地藥王孫思邈的福澤,熬制的臊子湯里“食藥同源”的調味料更豐足更養生。
銅川是座“煤城”,礦工多,過去的礦工勞動強度大、飯量大、口味重,所以當地的各種飯菜一般都具有口感筋韌、滋味濃厚的特色,“北關饸饹”的特色與成因亦當與此有關。時間久了,大家也就習慣了,口味也就定型了。但這里是藥王孫思邈故里,所以在屬于中藥范疇的中餐調料的運用上很是科學,動輒幾十種調料(中藥材)熬制的那一鍋湯,可是在淡淡的藥香里透著養生的科學呢。外地朋友可能一時難以適應,但完全可以大膽嘗試,吃幾次說不定就離不了呢。
另一個與陜北接壤的地方,歷史名城韓城,地域的、歷史的、人文的原因,吃羊肉的傳統也很深厚,這里的“羊肉臊子饸饹”也很有特色。只是這里的“羊肉臊子”不是直接燉煮,而是要“爤”。“爤”是烹飪技法的一種,幾乎專用于制作“臊子”。韓城的“羊肉臊子”要先“爤”羊肉,再加入壓饸饹的湯,據說這樣的臊子湯顏色好。然后放入米醋、加入用羊油炮制的油潑辣子的紅油,一鍋酸辣的臊子湯即成。吃的時候再加點腌制的咸韭菜、炒制的蔥花,那滋味就是酸辣咸爨了。
韓城文脈深厚、飲食精細,主打羊肉的還有一種“羊肉糊餑”,也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融合的食物精粹,有機會再詳解。
說完陜北和關中北部,該說說西安周邊的饸饹了。
渭南的“南七”饸饹。“南七”是渭南的一個村名,以一個村名成就一個美食稱謂的鮮見,足見它的特色。這個村子有制作饸饹的悠久歷史,一傳十十傳百,示范作用引領,許多人在西安、渭南一帶開店賣饸饹,足見功底深厚。“渭南南七饸饹”調制的臊子有葷有素,但基本與羊肉無緣,葷臊子主打豬肉,素臊子也以咸口為主,賣的時間長了,一般的店家調制臊子的功夫都不錯。結合關中人吃湯面就饃的需要,這里的饸饹店一般都兼賣燒餅或是肉夾饃。吃口饸饹,喝口香湯,再“壓”一口饃,干稀結合、死面與發面結合,口感更豐富,更利于消化。
藍田、灞橋一帶的饸饹。藍田是廚師之鄉,烹飪大師迭出,“勺勺客”們用勞力和智慧給人們送上美味。藍田的饸饹歷史也久,制作的工藝更講究,滋味中和,盡顯專業風范。這個地方早已把饸饹做成了“方便面”,真空包裝、配以脫水蔬菜和各色調料包,買回家去很方便地就可以吃上一碗湯饸饹,很是便捷。灞橋是西安的東部郊區,它制作的饸饹主打“涼調”饸饹,特色是那一碗自家做的“土芥末”,“熗”好的芥末適量地往饸饹里加一點,那股竄鼻的香辣滋味獨特,但萬不可貪多,不然會嗆得你噴嚏連天。
周邊的基本說完了,咱回到美食之都西安。西安的饸饹比較特色的就是“羊血饸饹”了。西安的名小吃里,“羊血”是一個吃法豐富的品類,有羊血泡饃、辣子蒜羊血等,乍聽起來血呼啦碴的,沒見過沒吃過的話聽著都“恐怖”。但中餐里面對幾種動物血脂的烹制是很得法的,也成就了許多美味,完全不是臆想的那樣。比如吃羊血,就是把新鮮的羊血凝結成塊后蒸熟,之后切條切塊而食,其他的血脂類吃法也大抵如此。具體到“羊血饸饹”,做法是用滾燙的豬大骨、老母雞等精心熬制的熱湯“泖”幾遍饸饹,再配上羊血條、老豆腐、粉絲之類做成。羊血性平、入脾經,有活血、補血、化瘀之功用,古代早已有醫用、食療歷史,調制得法,很是美味。
陜西“饸饹”的基本版圖大致是這樣。但上面只是按地域,并且以蕎麥饸饹為主做了一個總括性的介紹,其實,陜西饸饹還有更豐富的內容。
首先,不獨湯饸饹,涼拌的饸饹也很有特色。所謂涼拌,就是把壓好煮熟的饸饹放涼后,佐以各色調料拌勻。涼饸饹可以當飯吃,特別是油膩吃多后,一碗涼拌饸饹可以清清腸胃、敗敗火,十分清爽宜人;也可以是一盤涼菜,簡單夾取幾筷,也是不錯的味蕾享受。前面說過,陜西涼拌饸饹的特色是那一口芥末,提醒列位吃的時候一定要小口慢吃,不然會有東北小品中吃“辣根”的喜感,呵呵。另一種特色是“炒饸饹”,做法類似于炒面,成品口感更筋韌,爨香撲鼻,也是廣受歡迎的。
其次,前面說過,陜西“饸饹”的食材還有玉米、紅薯等,但現在已經比較少見了,那都是糧食短缺、特別是“細糧”匱乏的年月里的一種思念“面條”的吃法。比如玉米面饸饹,如果不是現壓現吃,放置一陣后再吃,因其質地干硬,必須在上鍋蒸透之后才能重新變軟,但還是會現出剛硬來,于是吃過的人就苦笑曰之“鋼絲饸饹”;紅苕面饸饹曾經也是因為拿紅薯當主糧,所以一度占據過飯桌。這種東西初吃起來有薯香淡甜,但連著吃就受不了了,畢竟是薯類,做面食實在是勉為其難,久吃泛酸水。這兩種“饸饹”基本已經退出餐桌了,時間長了也有人想念這一口的曾經,好不容易找尋到了也會當作美味,但只能是偶一為之。
林林總總、拉拉雜雜,把陜西“饸饹”念叨了一通。其實說白了,“饸饹”畢竟是主打雜糧的,不適合當作頓頓吃的主食。但長期的、大面積的、多樣化的對雜糧的精細加工,讓“饸饹”這個“下里巴人”意味濃厚的食物,現在也成了人們追逐的美味。如此這般,往高里抬點說,能夠把饑饉年代里的無奈之舉,變成在如今可以隨意饕餮的美味,實在是社會的巨大進步。
多姿多彩的陜西“饸饹”,一定要嘗試的一種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