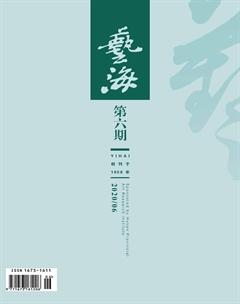會有人看見她的光
郭蔡雪
〔摘 要〕 《呦呦鹿鳴》劇本創作以尊重屠呦呦、尊重事實、尊重科學為前提,突出她身上樸實、淡泊又充滿堅韌力量的“小草”品質。不為增強戲劇性、吸引觀眾眼球去歪曲事實、憑空杜撰。同時,借助民族歌劇自身的特性及優勢完成文本敘事的建構,在關鍵的敘事點上給音樂敘事預留出足夠的空間,用音樂敘事推動、提升文本敘事的力量。
〔關鍵詞〕民族歌劇;現實題材;創作基調;敘事空間
2015年12月10日,當我們在電視新聞報道中看見屠呦呦登上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舞臺,領取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那一刻,心里就涌動著一股抑制不住的創作沖動:就寫她,一個就生活在人們身邊的科學家!沒想到的是,寧波演藝集團董事長,也就是一年后上演的民族歌劇《呦呦鹿鳴》出品人鄒建紅也有為屠呦呦排演一部劇的想法,隨即,一拍即合。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的很難。
在社會各界對屠呦呦高度關注,新聞媒體扎堆宣傳報道,各界圍繞屠呦呦的工作事跡、生活軼事甚至質疑與爭議層出不窮的時候,也正是最需要創作者保持冷靜客觀之時。如何在這樣的一個時間節點,用一個合適的情感角度和表達方式創作一部民族歌劇,向這位平凡而偉大的女性表達崇敬之情,是我們首先要面對和解決的。在查閱大量的資料后,同為女性的我,由衷地欽佩她堅忍不拔、淡泊名利、不懼生死、潛心鉆研的高尚品格。生活中的屠呦呦低調樸素,像一為普通的“鄰家老太太”,如果不是獲得諾貝爾獎,可能沒有太多人會關注到她。對待工作,她又是一個極其嚴謹細致、公而忘私的人。這種生活與工作中巨大的性格反差,恰好給藝術創作留下了可發揮的空間。
青青小草,質樸、寧靜卻有力量
屠呦呦曾經說過:“我喜歡寧靜,蒿葉一樣的寧靜。我追求淡泊,蒿花一樣的淡泊。”
她名字中“呦呦”二字出自《詩經·小雅·鹿鳴》篇,“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在她的人生軌跡中并沒有特別戲劇性的大起大落,即使在她獲得諾獎的高光時刻,她依然保持著從容淡定。怎樣從屠呦呦平實淡然的生活中發掘出她身上的“光”,找到準確的切入點呈現她人格和精神的不凡,同時做到既符合民族歌劇基本創作規律,又符合中國大眾的審美習慣?這些問題于劇本創作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朋友曾在微信中打趣地說,“民族歌劇的創作很難,現實題材的民族歌劇創作更難,真人真事的現實題材民族歌劇是難上加難,你們膽子不小”。誠如他言,這樣的創作是異常艱難甚至是痛苦的。一部成功的作品,尤其是涉及真人真事的現實題材,首先需要做到的便是讓觀眾相信人物和故事的“真”,然后再達到宗白華先生所說的“引人由真入美,引人精神飛越”。因此要盡量避免對人物和事件一味地“歌頌”,避免過多強調偉大和崇高,導致戲劇變得“空洞”、流于“說教”,從而令觀眾難以對劇中人物產生對“真”和“美”的共情。另一方面,編劇的任務是用文字來塑造人物形象、而歌劇主要是以演唱的形式來講述故事并推動情節發展,不把握好文字與音樂之間的分寸感會加大觀眾審美上的疏離感。經過反復斟酌,我們為《呦呦鹿鳴》確定了基調:劇本創作以尊重屠呦呦、尊重事實、尊重科學為前提,突出她身上樸實、淡泊又充滿堅韌力量的“小草”品質。不為增強戲劇性、吸引觀眾眼球去歪曲事實、憑空杜撰。同時,借助民族歌劇自身的特性及優勢完成文本敘事的建構,在關鍵的敘事點上給音樂敘事預留出足夠的空間,用音樂敘事推動、提升文本敘事的力量。細節處理上,重視刻畫其個人生活和心理情感的矛盾和起伏,避免將其人生故事變成寡淡無味的流水賬。整體寫作基調和方向明確了,接下來遇到的難題便是如何選擇素材。講述屠呦呦從兒時到獲得諾貝爾獎時的整個心路歷程,時間跨度大,面面俱到的鋪排,既受到全劇總時長的限制,也不符合創作規律。因此,在攫取屠呦呦的各種素材時,找到最為典型和個性化的關鍵節點,著眼于內在表達,將筆墨更多用在塑造一個有情感、有情懷的藥學家身上,然后再恰當分配力量,形成線條清晰、濃淡適宜的敘事結構,圍繞著這些關鍵點來進行劇本的創作。首先是人物設定,在屠呦呦的父親、丈夫、同學、同事之外,我們選擇通過老、中、幼三個不同年齡段的屠呦呦結構故事。老年屠呦呦作為貫穿全劇的靈魂人物,中年屠呦呦作為全劇的核心人物,幼年的屠呦呦作為色彩人物,三者在各自的時空里即平行也交織,這樣既能有效清晰的推動故事發展,也能藝術化的處理人物的內心獨白及心靈對話。其次,選擇“以身試藥”作為戲眼和高潮,凸顯作為藥學家的屠呦呦為拯救世人不再遭受瘧疾的苦難,舍生忘死的科研精神和人性光輝。“抓主干、去枝蔓”,大的方向和風格一旦確定,創作前期的痛苦、焦灼和迷茫變得快樂、平和和清晰。沉下心,更深入地去揣摩、挖掘屠呦呦的內心世界,技術性的“密針線”,豐滿人物的同時也完善了劇本。雖然創作的過程會有痛苦,但人物在筆下有了生命時,你就能享受到跟隨她前行的快樂。
“青青的小草,山野間悄悄地生,水塘邊默默地長,蘊含生命的美好;青青的小草,任憑那風吹雨打,任憑那獸嚼蟲咬,彰顯生命的驕傲。神奇的小草,千百次霧中尋,千百次夢里找,今天終于把你找到。”當歌劇《呦呦鹿鳴》主題歌響起的時候,我覺得,我已經找到了屠呦呦,已經用心觸摸到了屠呦呦,就像屠呦呦經過191次科學實驗,終于找到了青蒿素。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說到歌劇,人們通常認為是作曲家的藝術。音樂理論家居其宏曾說:“歌劇文學不但是音樂文學的最高形式,更是戲劇文學與音樂文學跨界聯姻和有機結合的產物。因此,歌劇文學中結構設計、場面安排和劇詩創作,還應充分考慮到音樂表現的特點和需要,具有歌劇文學一個必不可少的美學品質——音樂性。”西方歌劇,演唱精湛、旋律動聽就能極大程度地滿足觀眾的需求,我們的民族歌劇則不同,按照中國觀眾的觀劇傳統和審美習慣,一部歌劇在“好聽”的同時還要“好看”。首先是“好聽”,無論是獨唱、對唱、重唱與合唱,歌劇的創作不僅要有抒情性還要具備功能性,在推動劇情發展的同時,要合理、巧妙地留白給作曲家,以便作曲家在二度創作時有足夠的發揮空間。其次是“好看”。“好看”的基礎取決于文本,但也需要依托導演的二度呈現。因為劇中時間跨度大、場景變化多,而舞臺的空間又是有限的,為了避免對導演的二度創作造成困擾,在不影響結構完整和文本流暢性的情況下,對劇中的人物和場景進行了合理的調整和刪減,讓人物性格更鮮明、情節更精煉、節奏更緊湊。作為一度創作,劇本確定了疏朗明晰的結構形態、流暢平和的敘事節奏、真摯樸素的情感基調,克制過多的情感宣泄和泛濫,從文本中的時間與空間上,為作曲家和導演預留足夠的二度創作空間,讓他們在二度創作中能不再為揣摩和呈現劇本的文學性所累、不再被時間與空間所限制。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2017年5月30日,民族歌劇《呦呦鹿鳴》首演,音樂響起的那一瞬間我熱淚盈眶,雖然還不確定是否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可,但至少沒有辜負自己的創作初衷。2019年8月19日,《呦呦鹿鳴》獲得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戲劇)。三年間,《呦呦鹿鳴》演出百余場,讓走進劇場的觀眾享受藝術美好的同時,對屠呦呦和青蒿素也有了更多的了解。2020年的整個春天,受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在居家隔離的日子里,我時常會不由自主地哼唱《呦呦鹿鳴》中“春天是多么美好,可這個春天不屬于我……”這段詠嘆調。病毒讓我們焦慮和恐慌,但也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屠呦呦無懼生死、以身試藥的精神是多么偉大和崇高。作為藝術工作者,我們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講述她的故事,是因為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見她的光芒。
(責任編輯:張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