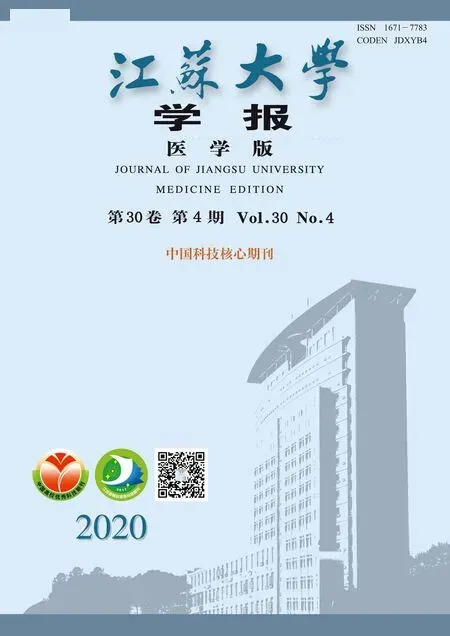外泌體源性長鏈非編碼RNA在消化系統腫瘤中的研究進展
倪修凡, 張尤歷, 徐岷
(1. 江蘇大學醫學院, 江蘇 鎮江 212013; 2. 江蘇大學附屬醫院消化內科, 江蘇 鎮江 212001)
外泌體是一種直徑30~100 nm的小囊泡[1],來自細胞內吞途徑中的多泡體,通過胞膜內陷形成囊泡釋放至細胞外基質中,介導其包裹的蛋白質、核酸、脂質等參與細胞間信息傳遞過程[2]。近來研究顯示,在消化道腫瘤發展中,通過外泌體介導的核酸分子起重要作用,其中,長鏈非編碼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是關鍵的影響因子。LncRNA可通過外泌體的介導,以多種方式調控受體細胞內基因表達,進而發揮生物學效應[3]。本文針對外泌體源性LncRNA在消化道腫瘤中的作用機制,以及其作為消化道腫瘤生物標志物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外泌體與消化道腫瘤
近來研究發現,外泌體作為信息通訊的關鍵物質,通過參與調控腫瘤微環境、影響腫瘤細胞耐藥、調節上皮—間充質轉化以及促腫瘤血管生成等過程對消化道腫瘤的發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例如,Wang等[4]發現缺氧誘導的胰腺癌外泌體富集miR-301a-3p并釋放至受體細胞,激活PI3K信號通路,從而誘導引發巨噬細胞M2極化,促進胰腺癌細胞增殖與遷移。結腸癌SW480細胞分泌的外泌體經HepG2細胞攝取后,促進信號調節激酶ERK1/2磷酸化,激活MAPK信號通路促進結腸癌細胞轉移[5]。同時,作為一個具有穩定性、特異性的囊泡,外泌體還可通過電穿孔方式導入siRNA靶向KRAS治療胰腺癌[6]。
2 LncRNA與消化道腫瘤
LncRNA是轉錄長度200個核苷酸以上的RNA[7],本身不具有編碼蛋白質的功能,是RNA聚合酶Ⅱ轉錄的副產物,所以在研究初期,人們認為其是轉錄過程中的“垃圾”和“噪音”[8]。隨著研究深入,人們逐漸發現LncRNA可從三個方面調控基因表達,即表觀遺傳學調控、轉錄調控和轉錄后調控[9]。雖然參與調控各腫瘤發展的LncRNA不同,但主要通過影響細胞增殖遷移、提升耐藥性、促進血管生成等方式影響腫瘤進展[10]。例如,在胃癌中,LncRNA-UCA1可通過與miR-203相互作用,致靶向轉錄本ZEB2釋放進而促進胃癌細胞增殖轉移[11]。LncRNA-RoR可通過激活Hippo/YAP通路進而促進胰腺癌細胞增殖及侵襲[12]。LncRNA-HOTAIR在肝癌化療的研究中起重要調控作用,敲除LncRNA-HOTAIR后肝癌細胞順鉑化療敏感性得到明顯提升,進一步研究發現其可能通過抑制STAT3/ABCB1信號通路參與腫瘤耐藥的調控[13]。以上研究結果表明,LncRNA可通過多種方式調控消化道腫瘤進展。
3 外泌體源性LncRNA對于消化道腫瘤的影響
外泌體介導的miRNA參與調節腫瘤進展以及作為生物標志物已有較多的研究[12]。研究發現,LncRNA包裹存在于外泌體中[14]。然而對于外泌體介導的LncRNA而言,則不及miRNA研究得廣泛和透徹。LncRNA較miRNA擁有較長核酸片段,包裹進入外泌體的含量約占外泌體總RNA含量3%[15]。實際上,這些經外泌體介導的LncRNA通過促進腫瘤細胞侵襲遷移、促進血管生成、調節腫瘤干細胞特性、促進腫瘤耐藥以及調控腫瘤微環境在消化道腫瘤發生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詳見表1。

表1 外泌體源性LncRNA在消化道腫瘤中的作用
3.1 外泌體源性LncRNA對消化道腫瘤細胞侵襲遷移的影響
TUC339在肝癌細胞中可通過調節趨化因子受體通路及調節巨噬細胞極化促進腫瘤生長,重要的是,TUC339在肝癌細胞外泌體中高度富集,因此擴大了自身作用方式[20]。上皮-間充質轉化是腫瘤遷移侵襲重要因素,其特征表現為E-鈣黏附蛋白表達下降以及N-鈣黏附蛋白、波形蛋白等表達增多[31]。PCAT1在食管癌中高表達,同時其通過外泌體介導,作為miR-326的內源性競爭RNA促進食管鱗癌細胞增殖,血清外泌體中PCAT1作為無創性生物標志物可作為食管癌篩查的指標[16]。LncRNA-ZFAS1在胃癌組織、血清外泌體中呈高表達,且與臨床病理分期相關[19]。進一步研究發現,外泌體介導的LncRNA-ZFAS1通過上調cyclinD1、p-ERK和Bcl-2蛋白表達進而增強胃癌細胞的增殖及遷移能力[19]。此外,LncRNA-HULC亦通過外泌體包裹傳遞,調節上皮-間充質轉化相關蛋白表達增加促進胰腺癌細胞的增殖遷移[25]。LncRNA-NONHSAT105177在胰腺導管腺癌癌組織中呈低表達,通過下調鋅指轉錄因子、波形蛋白、N-鈣黏蛋白等表達從而抑制胰腺導管腺癌細胞增殖和遷移,其可通過外泌體包裹更強地發揮信息傳遞及腫瘤調控作用[24]。由此證實,外泌體也可攜帶抑癌性核酸分子。LncRNA-91H可通過結直腸癌外泌體包裹,上調HNRNPK表達促進結直腸癌細胞增殖及遷移[28]。上述結果表明,外泌體源性LncRNA可通過靶向相關蛋白、激活信號通路進而促進腫瘤細胞侵襲遷移。
3.2 外泌體源性LncRNA對消化道腫瘤干細胞特性調節的影響
腫瘤干細胞是具有自我更新能力且同時產生異質性的腫瘤細胞,腫瘤細胞的干細胞特性調節能力是評判腫瘤惡性程度的關鍵指標[32]。LncRNA-Sox2ot在胰腺導管腺癌細胞的外泌體中高度富集,外泌體介導的LncRNA-Sox2ot可競爭性結合下游分子miR-200調控Sox2表達進而促進胰腺導管腺癌上皮—間充質轉化及腫瘤干細胞特性[26]。同時,血漿外泌體包裹的LncRNA-Sox2ot表達與胰腺導管腺癌患者預后分期及總生存率高度相關[26]。LncRNA-FMR1-AS1差異性高表達于女性食管鱗癌患者,其與TLR7受體結合,進一步激活下游TLR7/NF-κB信號通路,促進c-Myc表達,促進食管鱗癌的增殖遷移;食管鱗癌干細胞可通過外泌體介導LncRNA-FMR1-AS1將干細胞表型轉移到腫瘤微環境中的非干細胞受體[17]。Ren等[29]發現,LncRNA-H19通過外泌體傳遞,激活β-catenin信號通路,促進結直腸癌干細胞特性調控,影響腫瘤進展。由此表明,外泌體源性LncRNA通過調節腫瘤干細胞特性促進腫瘤發生發展。
3.3 外泌體源性LncRNA對消化道腫瘤血管生成的影響
血管生成是腫瘤細胞賴以生長的關鍵因素,癌細胞通過血管汲取養分從而促進自身侵襲和轉移[33]。研究人員通過對比CD90+肝癌細胞與正常肝癌細胞,發現CD90+腫瘤干細胞可釋放富集LncRNA-H19的外泌體,進而作用血管內皮細胞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其受體,調節血管內皮細胞血管生成,進而增強CD90+肝癌細胞對于內皮細胞的黏附,促進肝癌細胞增殖與遷移[21]。此與Ren等[29]研究一致,提示LncRNA-H19可能是外泌體介導的腫瘤相關影響分子。
3.4 外泌體源性LncRNA在消化道腫瘤耐藥中的作用
Takahashi等[22]研究發現,LncRNA-VLDLR在肝細胞癌耐藥株中高表達,可通過外泌體釋放至化療敏感細胞,導致化療敏感細胞對化學耐藥抵抗明顯增強,LncRNA-VLDLR通過上調ABC-G2表達增強肝癌細胞對于索拉菲尼的化療抵抗。類似研究發現,LncRNA-RoR亦參與多柔比星肝癌細胞外泌體的耐藥性傳遞[23]。吉非替尼治療食管癌是目前較為普遍的食管癌化療方案,但依然存在細胞耐藥的問題。研究發現[18],LncRNA-PAPT1在吉非替尼耐藥的食管鱗癌細胞中高表達,其經耐藥細胞株所分泌的外泌體包裹,通過調節Bcl-2/Bax信號通路促進食管鱗癌細胞對于吉非替尼的耐藥。以上研究證實,耐藥細胞株通過外泌體介導的LncRNA致細胞耐藥性增強,該過程顯示出外泌體作為媒介物的重要作用,也表明lncRNA在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
3.5 外泌體源性LncRNA在消化道腫瘤微環境及免疫反應中的作用
近來發現,腫瘤相關巨噬細胞在腫瘤微環境中起重要作用,尤其在發生M2極化之后[34]。外泌體介導的LncRNA亦參與腫瘤相關巨噬細胞M2型極化過程。結直腸癌細胞介導的LncRNA-RPPH1參與巨噬細胞M2型極化過程;此外,結直腸癌患者術前血漿外泌體中LncRNA-RPPH1水平較高,在腫瘤切除后其表達明顯水平下降[30],提示LncRNA-RPPH1不僅可作為治療結直腸癌的重要靶點,還可作為結直腸癌診斷以及術后隨訪的重要指標。腫瘤細胞對于免疫系統監測逃逸為目前造成腫瘤細胞難以被清除及攻克的最大難題[35],LncRNA同樣也參與該過程。最近研究表明[27],經胰腺癌外泌體處理的樹突狀細胞較未處理的樹突狀細胞顯示出較弱激活CD8+及CD4+的能力,進一步通過微陣列及數據庫整合發現胰腺癌外泌體介導的LncRNA-ENST00000560647極可能是促進樹突狀細胞免疫逃逸的最關鍵原因[27]。
4 外泌體源性LncRNA作為消化道腫瘤的生物標志物
目前對于消化道腫瘤仍缺乏特異性較高的生物標志物,外泌體作為一種較為穩定的囊泡,雖然包含有成百上千種不同的LncRNA,但對于特定腫瘤的特異性LncRNA并不多。具體見表2。

表2 外泌體源性LncRNA在各消化道腫瘤中的診斷價值
在結直腸癌研究中,Dong等[36]招募76例結直腸癌患者,篩選出39個與癌癥相關的候選LncRNA,其中,BCAR4的AUC值最高,為0.936,預示其可作為潛在的結直腸癌生物標志物。除此以外,Liu等[37]研究證實外泌體源性的LncRNA-CRNDE-h來源于早期的結直腸癌細胞,通過招募148例結直腸癌患者、80名健康對照者進一步研究發現,LncRNA-CRNDE-h在結直腸癌患者外泌體中顯著升高,其AUC值為0.892。
在導致肝癌的危險因素中,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及飲酒是最常見的三種[42]。Zhang等[38]招募35例慢性丙肝、22例丙肝誘發肝硬化和10例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結合患者基本情況、臨床血清學指標、臨床影像學資料進行調查分析發現,丙肝病毒導致的肝細胞癌患者血清外泌體LncRNA-HEIH顯著增高,提示外泌體源性的 LncRNA-HEIH可作為丙肝病毒相關性的肝癌生物標志物。在另一組關于肝癌的研究中,Xu等[39]通過對60例肝細胞癌患者、85例肝硬化患者、96例慢性乙肝患者、60名健康對照者的血清外泌體中LncRNA分析發現,肝細胞癌組外泌體中兩個LncRNA(ENSG00000258332.1及LINC00635)明顯高于其余組,將兩種LncRNA與甲胎蛋白聯合測定對于肝細胞癌的診斷價值,AUC值為0.894;此外,兩種LncRNA均與淋巴轉移即TNM分期相關,且術后兩種LncRNA水平均顯著降低[39],由此表明血清外泌體來源的兩種LncRNA對肝細胞癌患者臨床分期和治療的預后具有良好的參考價值。
在胃癌研究中,Zhao等[40]招募126例胃癌患者、120名健康對照者,結果顯示胃癌組血清外泌體中LncRNA-HOTTIP表達水平明顯上調,且與浸潤深度、TNM分期顯著相關,同時ROC曲線下AUC值為0.827。由此提示,血清外泌體源性LncRNA-HOTTIP可能是胃癌診斷和預后的潛在生物標志物。在早期胃癌的研究中,Lin等[41]從5名健康者、10例Ⅰ期胃癌患者的血漿分離出外泌體,通過分析發現LncUEGC1在早期胃癌患者中表達顯著上調,同時,其可包裹在外泌體中,LncUEGC1在診斷中區分早期胃癌患者與健康者時AUC值分別為0.876,高于癌胚抗原的診斷準確性。
5 總結
外泌體作為信息傳遞的媒介,使得其內部富集的LncRNA在調控腫瘤的進展中顯示出高效性與準確性。外泌體源性LncRNA可以從多個方面調控腫瘤的進展,同時血清、血漿中的外泌體源性LncRNA可充當生物標志物更好地應用于臨床診斷。但目前的研究仍具有局限性,影響各消化道腫瘤最具特異性的外泌體源性LncRNA尚需進一步明確;同時歸納以及整理影響腫瘤的LncRNA也將有助于數據庫的建立,從而更好地完成從實驗室走向臨床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