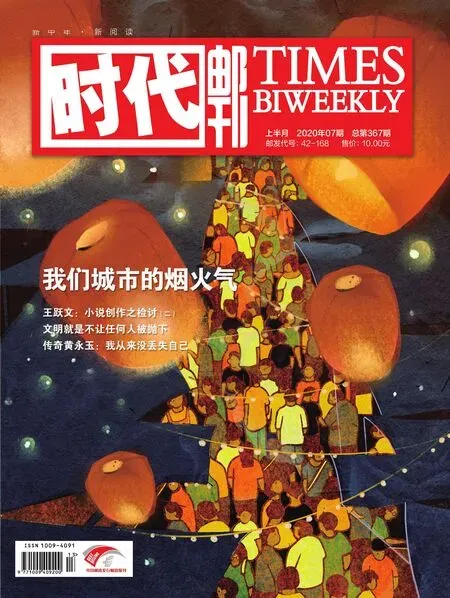英氏家族:從目不識丁到五代傳奇

▲ 1994年英若誠出席人代會時接受媒體采訪
《茶館》是中國話劇最經典的作品,60多年來,上演時幾乎是一票難求。它曾代表中國當代戲劇走出國門,進入歐洲視野。這部劇之所以能走向世界,有一個人起了關鍵性作用,他的名字叫英若誠。
英若誠曾在《茶館》1958年的首演中,飾演販賣人口的劉麻子,將劉麻子的“壞”詮釋得淋漓盡致,但他對《茶館》最大的貢獻還是在翻譯上。戲劇翻譯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茶館》里有60多位人物,從車夫到掌柜到官員,市井方言眾多,根本無法直譯。但英若誠卻能將這樣的作品譯成英文,并讓它在1980年到歐洲各國巡回演出。可以說,他是中國戲劇翻譯史上的“超人”。即便到了今日,《茶館》在國外上演時采用的英文字幕,依然是英若誠當年的譯文。
這位大翻譯家及他背后的家族,堪稱傳奇。這是一個從目不識丁起家到滿門才俊,百余年僅憑幾個人就闖出來的名門望族。
家族崛起的第一塊基石
英家祖上是目不識丁的滿州旗兵家族,本姓赫舍里。1644年,他們隨順治帝入關。英若誠的祖父赫舍里·英華(字斂之)幼時家境貧困,本來只能學一些騎馬摔跤的看家本領,但他有一個不尋常的追求:認字。
這個追求幾乎扭轉了整個家族的命運。英斂之從小就很有想法,為了識字,他到茶館撿包茶葉的廢紙練字,等到他有了一點基礎之后,就到一位教書先生那里當書童。當時剛好有一位落魄的滿洲貴族(雍正皇帝十四弟胤禵的直系后代)請了這位先生到府上當家庭教師,一來二去,府上的格格愛新覺羅·淑仲就看上了先生身旁那個才華橫溢的書童。在先生的竭力撮合下,英斂之與格格成婚了,成了皇族一脈。
雖說一時魚躍龍門,但英斂之能成為英氏崛起的第一塊基石,還要歸功于他憂國憂民的超前理念。他每天勤寫日記磨煉文筆,卻拒絕參加八股文科舉考試。為追求新思想,他參與了改良派的“百日維新”。后來慈禧回鑾下令大赦,法令中他的名字只有“英華”,沒有注明旗姓。這表明英斂之棄了旗姓赫舍里改姓英,從此“英氏家族”出現了。
眼見清廷無能,中國長期閉塞,人民苦不堪言,英斂之決心按照西方的模式創辦一份真正公平、具有正義感的新聞報紙,做人民的喉舌,承擔社會責任。1902年,他避開慈禧手下保守派的反對,在天津創辦了以“敢言”著稱的《大公報》。自己任總經理兼第一任主編,每天寫一篇社論。
《大公報》為中國新聞界樹立了獨立辦報的風氣,也是長江以北唯一一家此類的報紙。可以說,是英斂之和《大公報》為中國報業史寫下了最燦爛的一筆。他在發刊詞上寫道:“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在那樣守舊的年代,從未接受正規教育的英斂之能有這樣的遠見與氣魄,已非常人能企及。
英家二代的家國情懷
英斂之既懂得創辦《大公報》來啟迪同胞智慧,自然更明白“少年強則國強”的道理。他知道,要想振興國家,文化教育是重中之重,于是就創立了輔仁大學和香山孤兒院。
同時,他還將13歲的獨子英千里,托付給莫逆之交雷鳴遠神父,讓雷鳴遠帶英千里到西方去接受正規教育。英家二代英千里25歲學成歸國后,就以輔仁大學秘書長的身份承擔起文化教育的重任,僅用了七八年的時間,就把父親手上書院規模的“輔仁社”,擴大成為文理教育院系完整、頗具學術特色、聞名海內外的大學。
英千里是民國初年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能嫻熟使用英、法、西班牙、拉丁、希臘文等多種語言,并結合歐洲人的傳統習俗、理想和情操來給學生教授西方文學。這對于從未出過國的學生而言,簡直就是一座知識寶庫。凡他手下教出的學生,都被他“一個字一個字地修改”英文,畢業之后,不論在國內從事外語工作,或赴國外進修深造,都能游刃有余。后來連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都慕名邀請他講授“英國文學”的課程。可以說,英千里是外國人公認英語最好的中國人之一。
除此之外,他與父親英斂之一樣,內心都有著家國情懷。七七事變后,北平、天津淪陷。為了救國,英千里力邀年輕有為的知識分子,成立抗日秘密組織“炎武學社”,從事地下抗日工作。英千里因此被日本人逮捕,受盡酷刑。即便如此,英千里仍堅持不屈,保持中國知識分子的凜然正氣。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前夕,英千里才被釋放出獄。
遺憾的是,1949年,英千里因蔣介石的“人才搶救計劃”被架上飛機飛往臺灣,從此離妻別子。在臺灣的日子,他體弱多病,老境凄苦。直至1995年,英千里的兒子英若誠在馬英九的幫助下,才有機會在父親的墳前取一抔黃土帶回大陸,也算是英千里某種意義上的“落葉歸根”吧。
對中國文化貢獻良多的英家三代
真正長期受到英家濃厚文化氣息熏陶的人,是英家三代英若誠。他從小就跟隨父親住在晚清權臣慶親王奕劻的府邸,“在許多無價的古董和珍寶之間玩耍嬉戲”。他享受到父親英千里最完整的“西式”教育理念,家里連立規矩都“很紳士”。在他印象中,父親只打過一次孩子。
英若誠少時調皮搗蛋,僅小學時期,就被三所學校開除過,直到12歲時被父親送到圣路易中學(一所教會寄宿學校)讀書,他才真正用功起來。他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學會了說英語,甚至跟西方孩子吵架都用英語。這個從未出過國的人,對英語中的美國音、澳洲音、黑人音,以及許多地方俚語都能掌握得分毫不差,既能中譯英,也能英譯中。靈活運用程度,令許多長年生活在國外的留學生都自愧不如。就這樣,年僅16歲的英若誠就從圣路易中學畢業,進入清華大學外語系。那年,日本人投降,二戰結束,父親英千里出獄,英家短暫地享受了一段團圓幸福的生活。此后英家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其樂融融的景象。
在中國現代史上最動蕩最具摧毀力的10年,英若誠被捕入獄,妻子也在同一時間被抓了,女兒被送到內蒙古插隊,7歲的兒子英達則沿街乞討。面對這樣的險惡環境,英若誠選擇樂觀面對。他向監牢里的三教九流,請教各行各業的技術,如豆瓣醬制作、釀酒、孵小雞、種葡萄等,幾乎是絞盡腦汁學習周遭難友們的才能與智慧。
撥亂反正后,他全身心投入戲劇文化事業。1981年,他因“倫敦音的英語”被《馬可·波羅》制片人相中出演忽必烈一角,因此名揚天下。《馬可·波羅》先后在各國上映,并獲得美國最佳電視劇艾美獎。英若誠被意大利評為“最佳電視男演員”,榮獲“銀貓獎”。他還演過貝托魯奇導演的《小活佛》中的老活佛,《末代皇帝》中的監獄長。《末代皇帝》中飾演婉容的陳沖嘆道:“他英語真的是太好了,很多非常偏的詞他都知道,就連生活在國外多年的人在這方面也無法跟他相比。”
英若誠流最大的貢獻不是在演藝上,而是在翻譯中西方戲劇文學上。他英譯中的作品有諸如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莎士比亞的《請君入甕》等名作。在翻譯《哈姆雷特》中的“To be or not to be”一句時,他譯成:“是生,還是死?”此譯句成為后世流傳佳句。他中譯英的作品則有老舍的《茶館》、曹禺根據巴金原著改編的《家》等。但凡是英若誠翻譯的劇本臺詞,都十分簡練脆生,演員一開口就能用,不需要做任何轉化,連細微的語氣他都能以戲劇整體情境來參照。
1986年,英若誠調任文化部副部長,病榻上的北京人藝老院長曹禺親撰一聯相贈:大丈夫演好戲當好官,奇君子辦實事做真人。
自由選擇的第四代和第五代
與祖輩相比,英氏家族的第四代、第五代有了更寬松的環境。英若誠之子英達憑借出色的喜劇天賦,成為導演、演員、主持人三位一體的明星,尤其是他因“馬大姐系列”和《東北一家人》出名之后又相繼推出《東北一家人》《相約青春》等系列喜劇,更是在中國情景喜劇領域站穩了腳跟。英達的兩個堂弟英壯、英寧,也都在情景喜劇的編劇、導演方面有不錯的成績。
英氏家族第五代的巴圖成為和英如鏑則分別在各自喜歡的影視、體育領域深耕。
百年間,這個在晚清民國時期崛起的知識精英家庭,為中國與西方的文化、教育、演藝交流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英斂之辦《大公報》,創輔仁大學,引領中國人睜眼看世界;英千里則延續家風,開啟了中國英語教育先河,為國家培養出無數棟梁之材;英若誠把西方的大師之作引進中國,又把中國戲劇傳播到西方,二者被他融合成了人類共同遺產。他們都成為中國近現代史駐足的符號。而新生代英家人,在延續家風的同時,擁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選擇。
曾經目不識丁的祖輩,若看到后來的滿門才俊會作何感想?大概是唏噓又欣慰吧。這個家族用勇敢與倔強,用樂觀與隱忍,承載了中華民族士大夫們幾千年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感與豪邁感。
坦言之,對如此家族,唯有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