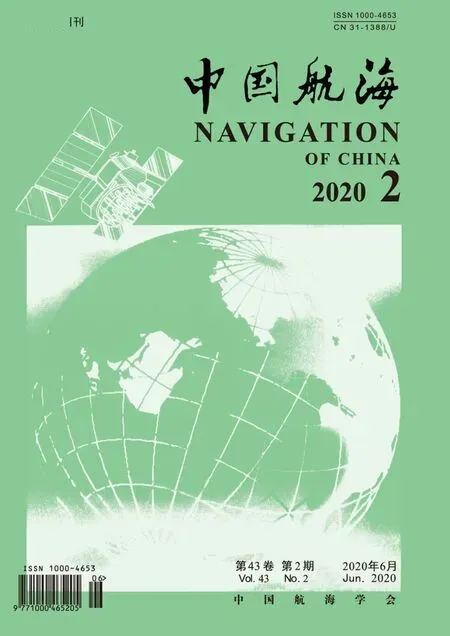貿易沖突對中國出口美國集裝箱影響的區域性差異
包甜甜, 余 慧, 楊忠振
(寧波大學 海運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2018年,美國采取單邊主義措施發起對中貿易戰,先后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價值2 500 億美元的商品加征關稅。2018年7月6日,美國首次公布對34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8月23日,繼續對16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9月24日,再次對2 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10%的關稅。[1]2019年,中美貿易沖突再次升級。2019年5月10日,美國把上述第3批2 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提高至25%。作為當前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密切,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為4 383 億美元,占中國出口總額的19%。加征關稅會提高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價格,降低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導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量減少,進而間接影響中國對美國貿易的運輸市場。[2]航運是國際貨物運輸的主要承載者,中美貿易量減少會打破中美航線運力的供需平衡。由于集裝箱運輸在中美航線上占主導地位,因此有必要研究中美貿易沖突對中美貿易集裝箱運量的影響。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在地理區位和資源稟賦上有著各自的特征,在對外貿易方面也不盡相同,對美國出口的貿易額和商品結構有明顯差異(見圖1)。這些差異使得中美貿易沖突對我國不同地區出口美國集裝箱運量的影響各不相同。

圖1 中國不同地區的對美國出口情況
目前已有研究主要從兩方面分析中美貿易沖突的影響。
1.中美貿易沖突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例如:周政寧等[3]采用動態全球貿易分析項目(Global Trade Aralysis Project,GTAP)模型,分析中美貿易沖突對兩國和世界經濟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結果表明,不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增速、出口和進口的影響均大于美國受到的影響;于紅[4]研究商品出口金額增速與價格增速之間的關系,指出加征關稅后機械和運輸設備、機電和音響設備等價格彈性大的商品對美國出口的增速會出現較大波動;潘家棟等[5]基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構建中國出口貿易模型,認為貿易沖突會增加政策的不確定性,影響中國的出口貿易和經濟發展;陶為群[6]根據消費品主導出口的社會再生產機理,闡明貿易沖突會降低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率。
2.中美貿易沖突對具體行業的影響。例如:陳勇等[7]梳理了中美貿易沖突涉及的主要林產品,指出貿易沖突對中國人造板、木家具等優勢林產品的出口沖擊較大,對中低級技術水平的從業人員影響較大;林濤[8]以紡織業為對象,分析近10 a中美紡織服裝貿易的歷史,發現加征關稅后中國紡織原料、紗線和面料的對美國出口會受到較大影響;孫瀚冰等[9]分析中美貿易商品結構和海運現狀,測算加征關稅后中國直接損失的對美國出口集裝箱量和中國主要港口受到的沖擊程度;童孟達[10]根據中美貿易沖突特點分析港航業受到的沖擊,認為加征關稅使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影響大于進口,對集裝箱運輸的影響大于散貨運輸,對船舶企業的影響大于港口。
綜上所述,不論是從宏觀經濟層面看,還是從具體行業來看,中美貿易沖突必將對中美貿易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導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集裝箱運量減少,但計量貿易沖突對中國出口美國集裝箱運量的影響和區域性差異研究仍有待深入。當前有關貿易沖突對中美兩國經貿的影響研究[5-9]主要是從整體的角度進行分析,文獻[3]、文獻[4]和文獻[10]引入價格彈性等方法分析加征關稅對中國不同產業對美貿易的影響,但由于美國對不同類別的商品采取不同的征稅策略,有必要區分商品類別,結合其價格彈性和美國的征稅方案,研究計算貿易沖突對中國對美國貿易量的影響。雖然有學者[9-10]已分析貿易沖突對航運業的沖擊,初步測算中國對美國貿易集裝箱運輸受到的影響,但未能量化出中國出口美國集裝箱的減少幅度,這需要綜合考慮不同類別商品的價格彈性、美國征稅方案和適箱率等多方面因素。本文基于價格決定市場供需關系的經濟學假設,構建價格彈性模型,分析加征關稅對不同類別商品供需關系的敏感性,研究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量受到的影響。同時,基于適箱率和中國不同地區產業結構的差異,研究貿易沖突對中國對美國貿易集裝箱運量的影響,明確我國集裝箱運輸業受到的影響程度及其區域性差異,為提出具有針對性且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奠定理論基礎。
1 基于價格彈性的中國對美國出口變化分析
1.1 基于商品類別的出口價格彈性估計
加征關稅會使商品在終端市場的價格上升,減少商品的市場需求。不同類別商品有不同的價格彈性,價格變動導致的需求變動程度不同。因此,貿易沖突對中國出口美國的不同類型商品的影響不同。先估計不同類別商品的出口價格彈性,構建不同類別商品出口額與價格變化之間的函數關系。由于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不能完全被美國生產的商品所替代,因此借鑒GOLDSTEIN等[11]的研究,基于不完全替代理論建立一國對另一國的出口額模型為
ln EXi,t=ai+bilnEi,t+ciln FGDPt+
diln EXi,t-1+εi
(1)
式(1)中:EXi,t為t時期第i類商品一國(記為本國)對另一國(記為外國)的出口額;Ei,t為t時期的雙邊實際匯率(直接標價法),可根據“名義匯率×外國CPI(Consumer Price Index, CPI)/本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求得;FGDPt為t時期外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ai為第i類商品的常數項;bi為第i類商品的出口價格彈性;ci為第i類商品的出口收入彈性;di為第i類商品的出口額的一階滯后項系數;εi為第i類商品的隨機誤差項。
通過式(1)可估計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價格彈性,即bi值。美國公布的征稅清單采用《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簡稱HS標準),其將國際貿易商品分為22類98章。由于2 500 億美元征稅清單的HS編碼精確到8位,根據HS編碼規則把這8位碼轉換到22類中,其第19類和第22類中的商品未被列入征稅清單,因此予以忽略。
以1998—2017年為研究對象,從UN Comtrade數據庫中收集到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數據和名義匯率,美國GDP數據來自于世界銀行,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和中國CPI數據分別來自于美國勞工部和中國國家統計局。運用固定效用面板模型[12],經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測算出中國出口美國的各類商品的出口價格彈性見表1。根據回歸方程的相關系數R2、F統計量及其對應P值可知該模型的擬合效果良好。

表1 不同商品類別的出口價格彈性
由表1可知:出口價格彈性大于1的商品類別有第3類(動植物油、脂、蠟,精制食用油脂)、第5類(礦產品)、第11類(紡織原料和紡織制品)、第12類(鞋帽傘等,已加工的羽毛和其制品等)、第14類(珠寶、貴金屬和其制品,仿首飾,硬幣)和第17類(車輛、航空器、船舶和有關運輸設備),其出口價格彈性高,出口美國易受加征關稅的影響,大部分商品類別的出口價格彈性均小于1,如第1類(動物產品)、第2類(植物產品)、第4類(食品,飲料、酒和醋,煙草和制品)和第16類(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附件)等,這些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價格彈性低,受加征關稅的影響小。
1.2 對美國出口額的影響計算
令第i類商品被加征關稅的比例為αi,加征關稅后Ei,t變化為Ei,t(1+αi)。由式(1)可知:Ei,t的變化會導致中國對美國出口額EXi,t相應發生變化。令βi為第i類商品對美國出口額的變化率,加征關稅后第i類商品的對美國出口額表示為EXi,t(1+βi),有
ln EXi,t(1+βi)=ai+bilnEi,t(1+αi)+
ciln FGDPt+diln EXi,t-1+εi
(2)
結合式(1)和式(2),推導出βi的計算式為
βi=(1+αi)bi-1
(3)


(4)
式(4)中:αi=-0.25,為加征25%關稅;ωi為加征25%關稅的中國商品對美國出口額占第i類中國商品對美國出口總額的比。根據式(4)可計算出加征關稅后第i類中國商品對美國出口額的變化率(見圖2)。

圖2 加征關稅后中國的不同類別商品對
由圖2可知:加征關稅后中國對美國出口額變化率較大的商品類別是第5類和第17類,變化率均超過25%。這是因為這兩類中90%以上的商品在2 500 億美元清單的加征范圍內,且其價格彈性大,分別為2.964和1.626,出口額易受加征關稅的影響。部分類別的商品加征關稅后對美國出口額的下降率較小,低于3.5%,如第1類、第8類、第11類、第12類和第14類。第1類和第8類中雖然有超過95%的商品被加征關稅,但由于價格彈性較小(不足0.2),其對美國出口額的變化率較小;第11類、第12類和第14類雖然價格彈性較大(大于1),但其中被加征關稅的占比較小(小于10%),加征關稅后對美國出口額的下降率較小。


(5)
第16類、第17類和第15類商品是中國出口美國的主要商品,計算結果見圖3。由圖3可知:加征關稅后,其對美國的出口額大幅度減少;第16類商品對美國出口額占比最大,這是美國加征關稅的重點,在2 500 億美元清單中第16類商品的對美國出口額約占清單中所有商品的46.29%,因此該類商品受到的影響較大;第20類和第11類商品也是中國出口美國的主要商品,但由于前者的價格彈性小(約為0.07),后者被加征關稅的商品占比較小(約為10%),因此其出口美國的變化量較小,不到第16類商品的6.8%。貿易沖突對中國不同類別商品出口美國的影響程度不同,加征關稅后不同類別的商品對美國出口的變化額不僅受其價格彈性和美國征稅方案的影響,而且與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結構有關。

圖3 加征關稅后中國的不同類別商品對
2 貿易沖突對中國出口美國集裝箱運量的影響
2.1 適箱商品的識別
加征關稅后,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的減少意味著中美航線集裝箱運量的減少。理論上不同商品對集裝箱運輸的適宜程度不同,根據是否適合集裝箱班輪運輸,貿易商品可分為最適合裝箱貨、適合裝箱貨、臨界裝箱貨和不適合裝箱貨等。
本文取前2類可實施集裝箱運輸,取后2類不適合集裝箱運輸。由此,對總共22類98章商品進行歸類,確定適箱與否(見表2),進而根據出口美國商品的類別計算加征關稅后下降的集裝箱運量。
2.2 對美出口集裝箱運量的影響分析
集裝箱運量的預測方法主要有生成系數法[15]、回歸分析法[16]、灰色模型法[17]和遺傳規劃法[18]等,其中被廣為利用的生成系數法主要基于貨物重量計算生成系數,但中美貿易的有些商品類別并非按重量計量,如第11類商品中織物的計量單位是萬米。為此,借鑒文獻[15]的方法,采用基于集裝箱貨值的生成系數法測算不同類別商品的集裝箱運量,有

(6)
式(6)中:Qi為中國出口美國的第i類商品的集裝箱運量;Ri為中國出口美國的第i類商品的適箱率(見表3),通過計算表2中的適箱商品對美國出口額與第i類商品對美出口總額的比值得到;P為出口美國商品的集裝箱箱化率,取90%[15];V為出口美國商品的單箱貨值,取2.33萬美元/TEU。[9]

表3 不同類別商品的適箱率 %
根據式(5)和式(6),結合第i類商品對美國出口額的變化量,計算得到加征關稅后第i類商品對美國出口集裝箱運量的變化,記為ΔQi;對22個商品類別計算并匯總,確定加征關稅后中國出口美國集裝箱運量的總變化,記為ΔQ;最后計算出加征關稅后出口美國集裝箱運量的變化率,記為:
(7)
(8)
(9)
考慮不同類別商品的價格彈性、加征關稅方案和適箱率等,計算得出貿易沖突將使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集裝箱運量減少95.77 萬TEU,約占中國出口美國集裝箱總運量的6.67%。按照之前加征10%的關稅計算,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集裝箱運量將減少52.3萬TEU,占比3.64%。新一輪貿易沖突將導致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集裝箱進一步減少43.47 萬TEU。但是,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集裝箱運量的減少與加征稅率并不同步,總體而言,加征關稅對中國到美國的集裝箱海運量的影響并不顯著,加征關稅對中國到美國的集裝箱海運市場的影響是微弱的。
3 加征關稅后中國出口美國集裝箱運量變化的區域差異
由于產業結構的地區性差異,中國各省份受貿易沖突的影響程度有所差異。以31個省級行政區域(除香港、澳門和臺灣)為空間單元,分析貿易沖突對中國出口美國集裝箱運量影響的區域差異。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商務年鑒》和各省統計年鑒及HS標準,收集整理各省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和不同類別商品對美國的出口額,計算得到加征關稅后各省對美國出口集裝箱數量下降的絕對值和比率(見圖4)。此外,根據各省外貿出口總額,計算加征關稅后各省對美國出口集裝箱的變化量與其外貿出口集裝箱總量的比,得到加征關稅后各省出口集裝箱總運量的下降率見圖4。

圖4 加征關稅后各省出口集裝箱運量的變化情況
由圖4可知,加征關稅后中國不同省份對美國出口的集裝箱運量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絕對值最大的是廣東,預計減少的運量為26.25 萬TEU;浙江、江蘇、山東、上海和福建對美國出口集裝箱下降的絕對值也較高,預計分別為21.70 萬TEU、13.10 萬TEU、8.40 萬TEU、6.98 萬TEU和5.57 萬TEU;而河北、遼寧等其他25個省份預計減少的對美國出口的集裝箱運量的絕對值較小,都不超過2.14 萬TEU,總和約為12.29 萬TEU,不到廣東下降量的1/2。
加征關稅后對美國貿易的集裝箱運量下降率最大的省份是北京,為10.02%。山西、陜西、海南、遼寧和河南出口美國的集裝箱下降率也較高,分別為9.74%、9.36%、9.11%、8.95%和8.79%。相對地,對美國出口集裝箱下降率最低的省份依次為福建、新疆、內蒙古、安徽和湖南,分別為4.86%、5.22%、5.23%、6.61%和6.75%。重慶、四川等其他20個省份的對美國出口集裝箱運量的下降率在6.76%~8.70%。
加征關稅后對美國出口集裝箱總運量下降率最大的省份是河南,為2.46%。四川、重慶、上海、山西和江蘇對美國出口集裝箱總運量的下降率也較大,分別為2.44%、2.09%、2.08%、1.87%和1.69%。相對地,對美國出口的集裝箱總運量下降率較低的省份依次為云南、內蒙古、新疆、黑龍江和甘肅,下降率分別為0.24%、0.34%、0.35%、0.48%和 0.54%。陜西、浙江等其他20個省的對美國出口集裝箱總運量下降率在0.56%~1.63%。
為明晰加征關稅后產生以上區域性差異的原因,從經濟外向性、產業結構特征和對美貿易依賴度等3方面進行分析。
3.1 經濟外向性
東部沿海地區有著發展對外貿易的有利地理條件和政策環境,市場化程度和對外開放度高,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結構,易受國際環境的影響。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山東和上海對美國出口的集裝箱運量分別為375.49 萬TEU、320.81 萬TEU、114.65 萬TEU、117.42 萬TEU、108.73 TEU和82.03 萬TEU,占全中國對美國出口集裝箱總運量的88%。因此,中美貿易沖突必然會導致東部沿海地區對美國出口集裝箱運量大幅度減少。中西部地區的對美貿易規模完全不能與廣東和浙江等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因此加征關稅后其對美國出口集裝箱運量下降的絕對值較小。
3.2 產業結構特征
美國為遏制中國先進制造業的發展,重點打擊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機電產品(主要是第16類商品)。
1) 中西部地區以資源加工型產業為主,如山西、陜西和河南對美國出口的第16類商品分別占各自對美國出口商品總額的86.52%、81.52%和84.7%,由于該類商品適合集裝箱運輸,其貿易量下降直接導致對美國出口集裝箱運量減少,因此在加征關稅后這些省份對美國出口的集裝箱下降率較高。在北京出口美國的商品中,除了第16類以外,第3類商品所占的比例也較大,為21.4%,由于第3類商品的價格彈性較大(為1.09),且適合集裝箱運輸,因此加征關稅后北京對美國出口集裝箱下降率最大。
2) 東部地區以裝備制造業、紡織業、服裝制造業和加工貿易業為主,對美國出口商品中輕工產品比例較高,如福建對美國出口商品中有30%屬于第11類和第12類商品。由于這2類商品不是美國加征關稅的重點,被加征關稅產品的比例較低,因此福建雖然對美國出口集裝箱量下降的絕對值較大,但下降率較小。
3.3 對美貿易依賴度
通過實施“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中西部地區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取得迅猛發展,其中河南、四川和重慶等省份比較依賴美國市場,對美國出口額占其出口總額的比例較高,分別為27.99%、28.6%和24.06%,因此加征關稅后這些省份出口美國集裝箱總運量的下降率最大。云南、內蒙古、黑龍江和新疆等省份因地理位置等因素,與緬甸、越南、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低,其對美國出口額均不到各自外貿出口總額的7%,因此加征關稅后這些省份出口集裝箱總運量下降率較小。
4 總體影響分析
中美貿易戰直接影響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量,進而影響中國對美國貿易的集裝箱運量。本文基于不同類別商品的價格彈性和適箱率,分析美國加征關稅方案和中國不同省份產業結構的差異,計算在中美貿易沖突下中國出口美國集裝箱運量的減少情況及其區域性差異。分析結果表明:
1) 在全國層面,貿易沖突對中國制造業產品的對美國出口的影響較大,加征關稅后第15類、第16類和第17類商品對美國出口量會大幅減少,減少總額為299.035億美元,占中國出口美國產品總額的6.97%。中國對美國貿易集裝箱量受貿易沖突的直接影響總體可控,預計對美國出口集裝箱總運量將減少6.67%。
2) 在各區域層面,中國各省份受貿易沖突的影響程度存在明顯差異。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在加征關稅后,對美貿易的集裝箱運量下降顯著,達到68.03 萬TEU,占全國對美國出口集裝箱運量的5.10%;北京、山西、陜西和海南等省份出口美國以第3類和第16類商品為主,在加征關稅后其對美國貿易的集裝箱運量的下降比例高,均超過9%;河南、四川、重慶和上海等省份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較高,在加征關稅后其出口集裝箱總運量的下降比例較高,均超過2%。
5 結束語
本文的研究結果有助于決策者充分認識貿易沖突對中國出口美國的集裝箱運量的影響及其區域性差異,探討針對性的應對策略。
1) 珠三角地區和長三角地區需密切關注貿易沖突的事態發展,積極應對集裝箱運量的變化。另外,由于這兩個地區的收入水平可比肩部分發達國家,未來一段時期進口貿易額將大幅度增加,減少的出口美國的集裝箱運量完全可能由增加進口的集裝箱運量彌補,需及時調整中美航線的運力布局。
2) 北京、山西、陜西和海南等省份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科學配置外貿商品的構成,以應對中美貿易沖突帶來的影響,未來需密切關注中美貿易的貨種變化情況。
3) 河南、四川、重慶和上海等省份可依托“一帶一路”倡儀等,積極拓展其他國際市場,建立全方位、多元化的全球貿易市場均衡發展戰略,未來需積極開辟東南亞、非洲等“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航線。
此外,本文假定集裝箱箱化率和出口單箱貨值不變,此假設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不成立,未來可在區分商品類別和地區的基礎上細化此假設,以便更加精準地計算在加征關稅后中國對美國出口集裝箱運量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