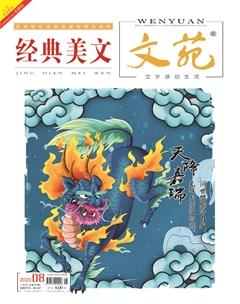抱憾鸛雀樓


提起《語文報》,相信很多讀者都不陌生,可能順手就從書桌里拿出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學生校園文學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邱華棟、段華、洪燭、毛夢溪、江小魚、雷霆、安武林等《語文報》重點中學生作者,因寫作特長未參加高考直接保送上了武大、北大、南開、吉大等中國名牌大學,一時傳為佳話。許多文學大家提起《語文報》,仍一往情深。
本期我們有幸邀請了“校園文學伯樂”任彥鈞老師擔任客座主編。任彥鈞老師是語文報社總編輯,還擔任全國中語會語文名師教研中心主任等職,他心系高考,情懷語文,滿腔熱忱關注語文教學與考試。
本期客座主編:
筆名任悟,1964年出生于山西芮城。語文報社總編輯、編審,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迄今已有百余篇文學作品、新聞作品和學術論文發表于《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 《中國青年報》《中國教育報》《中國新聞出版報》《詩刊》《傳媒》等報刊,出版有個人詩文集《閉目而視》《一任我逍遙——左翼為文,右翼是詩》《論語說文——老編輯的小宇宙》。曾參與主編《朦朧詩名篇鑒賞辭典》《中外微型詩鑒賞》《新世紀語文名師教學智慧研究》《新時代中國高考作文改革檔案(2020:創意制勝)》等數十種圖書。
幼年讀王之渙的唐詩絕唱《登鸛雀樓》,不知道與岳陽樓、黃鶴樓、滕王閣并稱中國四大名樓的鸛雀樓,離我的故鄉并不遠;也沒想到這首短小精悍、淺顯易懂的名詩,居然蘊含著一言難盡的人生哲理。
我的故鄉位于山西省西南端的芮城縣,北有“白日依山盡”中所指的中條山護衛,南有“黃河入海流”中所指的母親河滋養。這一山一水在山西、陜西、河南交界處的風陵渡深情擁抱之后,從東往西蜿蜒而來的中條山,便悄然沉沒于地平線,而從北往南呼嘯而來的黃河,則拐了個浩浩蕩蕩的彎,一路向東,奔騰到海不復回。
駕車從故鄉出發,過了“雞鳴一聲聞三省”的風陵渡,繞中條山望北而行,用不了一個小時即可到達蒲州的鸛雀樓。蒲州現為永濟縣所轄鄉鎮之一,古代其地位卻要高得多。傳說此地就是舜帝的都城蒲坂,從漢朝到清朝,也一直是晉西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甚至有時號稱中都,與西都長安、東都洛陽三足鼎立。
鸛雀樓原本坐落于蒲州城西黃河濕地的一座土丘上,最早是北周大將軍宇文護所建的軍事瞭望臺。北周打敗北齊一統北方后,它的軍事作用消失,于是日趨荒廢,時常有鸛雀棲居其間,便被當地百姓取名鸛雀樓,到了大唐盛世,才成了文人雅士登高望遠、吟詩作賦之所在。金人和元人在蒲州鏖戰之際,鸛雀樓被毀之一炬,明朝隆慶年間,黃河決口倒灌蒲州城,其遺址也被泥沙徹底掩埋。
現在的鸛雀樓,是今人重修的全國最大的仿唐建筑。近年借回鄉探親之便,我曾兩次興沖沖前去造訪,兩次卻都留下深深的遺憾。一次是陪岳母一大家子人上午去的,當時我自告奮勇照顧老人,走到樓下就止步了;另一次是帶新婚的兒子、兒媳下午去的,不料到了大門口售票已叫停,只能遙望、遐想一番作罷,小兩口心里頗為不爽。
按照有關資料介紹,舊貌換新顏的鸛雀樓,是1997至2002年,在古建筑界泰斗鄭孝燮、羅哲文指導,以及著名古建筑專家柴澤俊等主持下,根據清人編纂的《蒲州府志》所附鸛雀樓圖譜復建的,而且采用了失傳已久的唐代彩畫藝術,由古建筑彩繪藝術大師馬瑞田擔綱設計,堪稱古建筑“修舊如舊”的范例。樓體外觀四檐三層,內分六層,總高73.9米,總重量58000噸,景區占地總面積33206平方米。只不過由于黃河改道,原址為水利工程所占,新址自東而西遷移了7華里。
前幾天與朋友無意之中談起鸛雀樓,不由再次悠然神往。試想,如果他日能身臨其境,有了“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切實體驗,對于這首詩,是不是就會有更精妙的感悟呢?
長期以來,關于這首詩的內涵,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人,有著不同的看法。
在家里、在學校,父母和老師講到《登鸛雀樓》,每每都會從直覺出發概括:前兩行寫的是一種景色遼闊、氣勢雄渾的意境,后兩行反映出積極向上的精神,道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遠的人生哲理。
然而據報道,有“中國最后一位‘女先生”之稱的葉嘉瑩教授得知這種講解,曾拍案而起,她說:“如果我們的古典詩歌,再這樣教下去,這個根就要斷了!”在歷盡滄桑的她看來,該詩有三重境界,其大意是:第一重,是寫詩人面對夕陽西下、河水東逝產生了強烈的生命孤獨感,希望通過自我提升,以對抗這種孤獨感;第二重,是寫詩人置身上述特定的蒼茫時空,引發了莫名的人世無常感,希望通過自我超脫抵御這種無常感;第三重,是寫即使你已經處于理想的層次,已經看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這樣的美好場景,卻還須不斷力行、不斷上進,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你的人生才能到達一個更高的平臺,你的生命意義才能更進一步深化和升華。
在政治家心目中,這首詩的意味則又有所拓展。例如,2009年11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訪問埃及時,在傾聽了兩名埃及男青年用中文吟誦《登鸛雀樓》后,曾從國際合作的角度解釋說:“‘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鼓勵人們要有寬闊的視野、高遠的志向,不斷向上,追求更高的目標。我們發展中埃關系,也要站得高、看得遠,不斷加強兩國的戰略合作。”
年過半百的我經過研讀大量文獻,最近對此也有新的體會:1000多年前,在太陽落山、黃河遠遁的那一刻,我們的詩人無疑是感慨萬端的,而最終他或許認識到,世界很大,未來很遠,要成為一個志向高潔的人,只有不斷自我提升、自我超脫,才能在浩瀚的時空中,確立自己生命的最高定位,才能達到中國哲學所謂“天人合一”的最高智慧。
想到這里,我越發期待著再去一趟鸛雀樓,與它面對面、心貼心,以真正領略《登鸛雀樓》的大氣象、大境界,從而彌補自己生命里揮之不去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