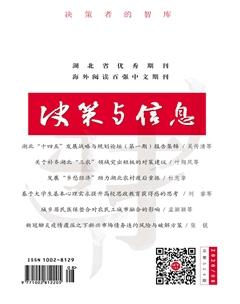疫后時代城市公共服務保障體系思考
魏偉
湖北省作為中國抗疫“第一戰線”,公共服務設施承受了比以往更加巨大的使用壓力。回望疫情,我們需要反思對城市、規劃本身的認知和理解:社區生活圈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否能夠應對極限壓力的考驗?
公共衛生服務設施不僅包含定點醫療機構、應急醫院、方艙醫院、設置發熱門診醫療機構等設施,也包括公共衛生的保障體系,以及各類通道、工具、醫療設備等。基層衛生服務設施和基層管理服務設施主要體現在社區層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服務站等設施發揮了重要的基層檢疫、輕癥治療、穩定群眾等作用;居委會等社區管理設施成為本次疫情中的關鍵環節。線上購物和物流配送等能夠實現無接觸物資供給,在本次疫情中承擔了重要的基礎保障功能。
一、加強社區空間的精準匹配和冗余配置
疫情的發生,讓社區空間的精確匹配和冗余配置變得尤為重要,后者的解決需要引入更多創新型的設施空間設計手段,讓設施本身能夠應對突然變化的需求沖擊;而前者的解決則需要規劃體系的價值轉變,開始重視到不同社區的特異性,在規劃的末端,重視社區的特別需求和空間特質。這種轉變帶來了規劃手段的變化:
1. 設施評估:對原有設施的“點、量、質”進行評估,識別社區現有設施不足,明確改造的典型指標和目標。
2. 需求調查:從兩個方面對居民的需求進行調查,一方面是居民的理性訴求,另一方面是居民“行為”的使用特征。
3. 張力辨識:從使用者、普通居民、設施配給多個角度,辨別要素“點、量、質”配置的上限與下限。
4. 理性共識:由于現實空間的限制,規劃顯然無法滿足所有主體的“上限”需求,因而應以整體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訴求為目標,采取情景判斷、專家研判、公共研討等多種方式,平衡要素與要素、主體與主體利益,在上限與下限中尋求最優解。
5. 規劃匹配:規劃師根據理性共識,將要素“點、量、質”合理安排,在理性中不斷提升理想與現實的匹配度,讓城市基層管理更進一步走向精細化。
二、重視城市空間的安全屬性和空間可達性
當下,現代城市的內涵及實力多以規模效應、密度效應和流通效應來衡量,這也正體現了城市化的本質,即聚集和加快聚集。在這種模式下,我們留給接觸的空間和通道太多了,而留給安全的空間和通道太少了。
因此,應重新審視以要素“集聚”為單一目標的空間規劃與設計導向,在重視規模帶來收益的同時也認識到集聚的潛藏風險,使城市空間回歸居所(殼體)作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的原始概念,以“和諧”為最終目的,以“方便”提效率,以“舒適”促滿意,以“美觀”愉悅群眾。同時,公共服務設施不應被單純視作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空間依托,更應被視作城市核心功能性設施,將公共空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社區服務中心視作居民人身和財產安全的保障設施。
此外,基礎設施的物理空間可達性不是一個孤立的指標,而應與所在人居環境的人口密度、規模和結構內在相關。在規劃和評價時,需要分析、判斷可達性的影響因素,以“綜合滿意度”衡量物理空間可達性。
三、按照層級性布局公共基礎設施
“層級性”體現了公共服務的次序和重要性。
1. 涉及“安全”和“生存”的公共設施,應該具有絕對重要性和優先性,包含:(1)“生命線”設施,如供水、供電、供食、供醫等;(2)“救濟線”設施,如消防、廣電網絡以及救災通道和設備等;(3)“安全線”設施,如基層指揮及警務中心、垃圾收集、污水管線等。
2. 其次為涉及“發展”和“共享”的公共設施,包含:(1)個人發展保障設施,如基礎教育設施、養老設施、殘疾人設施等;(2)群體聚集及保障設施,如開敞空間(含綠化廣場、林蔭步行道等)、社區服務中心等;(3)出行類設施,如公交站點、地鐵站等。
3. 再次為涉及“體驗”“個性化”的公共設施,如文化設施、體育設施、物流點以及非基本需求類的商業設施。
在重視“層級性”的同時,還應體現公共服務行業特征和質量保證的“專業性”,尤其是在涉及具有行業“準入門檻”的公共服務中,需要在精細分工前提下進行社會協作。
(作者系武漢大學中國發展戰略與規劃研究院副院長,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鄒立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