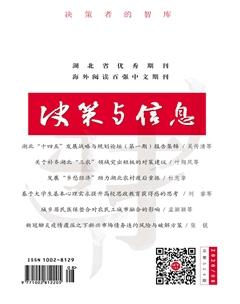準公共物品理論下我國養老服務財政補貼政策的失衡與糾偏
殷俊 段亞男



[摘? ? 要]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盡快建立“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作為補充”的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成為了我國養老服務業改革的重要目標。由于養老服務這一準公共物品的特殊性,其發展需要市場機制和財政補貼政策的雙向支持。當前,我國養老服務的財政補貼政策存在總量不足、區域失衡及結構失衡等問題。對此,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完善我國養老體系:一是加大財政補貼力度,優化資金地區投向結構;二是消除政策障礙,完善和落實吸引民間資本的政策支持體系;三是增強財政資金投入適用性,引領社會養老投資方向。
[關鍵詞] 養老服務;財政補貼政策;準公共物品;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 C91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0)08-0034-09
一、研究背景與理論基礎
21世紀的人類社會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化社會,這對大多數國家而言都將是重大的挑戰,在我國老齡化過程中更是呈現出總量大、增速快與不平衡的鮮明特點。據《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年末,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總量達17603萬人。且聯合國人口署預測,我國將于2020年進入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的深度老齡化社會。隨著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家庭養老觀念的不斷淡化,養老服務事業隨之也迎來了巨大壓力。尤其在我國,未富先老問題突出,美日韓老年人口比重達12.6%時人均GDP均在2.4萬美元以上,而中國僅1萬美元[1],這就意味著中國政府在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中應發揮更加重要的角色。
鄭功成(2011)提出,當老年人領取了養老金后,老年服務便成了老年人的普遍需求[2]。此外,高生活水平帶來的人均預期壽命延長、老年人軀體健康水平的下降,都促使養老服務剛性需求増長迅猛。面對日益增強的養老服務需求,我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仍較滯后,存在供給總量不足與區域發展失衡、錯配的多重問題。據國家發改委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國各類養老服務機構提供的養老床位761.4萬張,平均每千名老年人僅擁有養老床位30張[3]。
根據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對公共物品的定義,公共物品是可以供社會成員共同享用的物品,同時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兩種屬性。然而,純粹的公共物品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基于此,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首次提出了準公共物品這一概念,他認為準公共物品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間,是具有部分競爭性、排他性和外部性的產品[4]。就養老服務而言,首先,養老服務在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它是一項全社會都可享用的物品,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方法享用養老服務;第二,養老服務具有部分競爭性的特點,養老機構每增加一位患者,其所需的服務設施和照料人手也會隨之增加,邊際成本并非為零;第三,養老服務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養老服務不僅可以使老年人在養老機構中得到充分的軀體照料和心理慰藉,利于社會總體福利的提升,還客觀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間接對勞動力市場產生影響。
作為具有非排他性、部分競爭性和外部性的準公共物品,養老服務的發展不僅需要市場的調節以達到產品供需平衡,同時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來實現資源配置優化。楊燕綏等(2014)認為我國在2025年左右會邁入深度老齡化階段,屆時養老服務的需求急劇擴大,要求政府在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中發揮其主導作用,積極利用財政資金、信息和稅收優惠政策等社會資源支持養老服務業發展[5]。
財政政策作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對養老服務業的發展具有關鍵性作用。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16)指出,“十二五”期間,財政在支持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時,存在投入資金規模較小,配套建設補貼不到位等問題[6]。規范政府補貼行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益,推動養老服務業供給側改革,實現養老服務跨越式發展,已成為當下迫切需要破解的政策難題。對此,本文在明確財政政策支持養老服務建設的理論基礎上,從梳理我國財政補貼政策的現狀入手,客觀分析現有養老服務財政補貼政策存在的不足,并結合筆者的思考,提出政策建議,為推進我國養老事業建設提供決策思路。
二、我國養老服務財政補貼政策的現狀
(一)養老服務市場化
我國社會養老服務的最初形式是國家、集體建設運營的社會福利院和敬老院,主要面向城鎮“三無”老人和農村“五保”老人。彼時的養老服務補貼,內化在政府對這些養老機構中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獎金和機構運營經費中,并不存在正式的養老服務財政補貼政策[7]。
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進程,社會辦養老機構逐漸發展起來,政府隨之出臺了越來越多支持養老服務建設的財政政策。養老服務財政補貼政策是與我國養老服務市場化改革進程相輔相成的[8],為了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和養老服務市場化,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加大政策扶持(見表1),鼓勵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投資、興辦養老機構、試圖改變傳統社會公共服務供給中政府大包大攬、既“掌舵”又“劃槳”的做法,支持養老服務建設的財政政策體系也隨之建設起來。
(二)現有養老服務財政補貼政策梳理
目前,養老服務的財政補貼政策有直接投資、財政補貼、政府購買和稅收優惠四種形式,其中以財政補貼為主。
財政補貼政策主要分為補需方和補供方兩種形式。針對需方的財政補貼主要表現為高齡津貼、護理補貼和養老服務補貼這“三大補貼”制度。截至2018年,全國各省均已建立高齡津貼制度,30個省份建立服務補貼制度,29個省份建立護理補貼制度,享受高齡津貼、服務補貼和護理補貼的老年人人數分別達到2680萬、354萬和61萬[9]。
針對供方的財政補貼一般發生在養老服務機構的建設期和運營期兩個階段。在養老服務機構的建設期,按照養老機構的所有制屬性、建設或擴建修繕成本的一定比例給予補貼,并設定補貼標準上限,或給予一次性床位建設補貼。養老服務機構運營期的財政補貼方式較多,包括按人頭數或床位數發放的日常運營補貼、等級評定補助、老年人助餐服務項目補貼、養老機構責任險補貼、商業補充保險補貼以及養老服務人才補助等。
近期,為緩解疫情對養老服務機構運行成本增加的困難,各省市陸續出臺相關政策,階段性減免社會保險稅費,并發放疫情防控補助,以減輕養老機構負擔,助力養老服務行業復工復產。表2梳理了我國2020年部分城市的養老機構財政補貼最新政策。
三、我國養老服務及財政補貼政策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國家財政實力日益壯大,財稅改革不斷深化。面對我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孤寡、失能、貧困、空巢等老年群體擴大,社會養老服務需求日益強烈的現實背景,“十三五”期間,各級政府已出臺了多項政策推動養老服務發展,各級財政的支持力度持續加大。我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由此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中,仍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一)總量不足
當前我國養老機構存在著供給總量不足與財政補貼不足的雙重困境[10]。首先,從養老機構總量上看,截至2019年年末,全國養老服務機構共計3.4萬個,養老服務床位761.4萬張,較2010年增長率達142%。每千名老年人擁有的床位數約為30張,較2010年增長69%,養老服務機構的服務供給能力有了顯著提高(見表3),但這與《“十三五”社會服務兜底工程實施方案》中每千名老人養老床位35-40張的目標仍存在很大差距,養老床位總體不足。
從財政補貼總量上看,根據《2018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民政部門登記和管理的民政服務機構和設施共計187.6萬個,職工總數1470.0萬人,固定資產原價5736.2億元;各類民政服務機構和設施擁有床位755.9萬張,每千人口社會服務床位數5.4張;民政基本建設在建項目建設規模2029.3萬平方米,全年實際完成投資總額188.0億元。2018年,全國民政事業費支出4076.9億元,較上年下降31.3%,占國家財政支出比重為1.8%(見表4)。面對全國老齡化趨勢的不斷推進和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巨大工程而言,財政支出占比僅為1.8%,顯然較低,財政面臨的養老服務支出缺口較大。
(二)區域失衡
首先,我國各省份的養老設施建設和財政補貼差距甚大。據《2017年中國民政統計年鑒》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每千名老年人擁有床位數超過35張的省份有10個,占全國(31個省區市)的32.3%;全國有18個省市的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小于2017年底全國平均水平(31.6張);水平最高的省份每千名老年人擁有58.3張床位,水平最低的僅有14.2張床位,差距顯著。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各地的養老服務財政補貼水平也參差不齊,表2可以看出在總體上東部地區的補貼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區,但地區內的差異仍較大,如同為中部地區的鄭州市和合肥市,前者建設期的補貼標準僅為1000-3000元,后者卻達到2000-10000元,最高水平相差3倍有余。
此外,受我國城鄉二元化體制的制約,城鄉養老服務業發展也呈現出對立、分割和不平衡狀態。農村養老服務“先天不足”,基礎差、起步晚,面臨問題更為突出。在后續培育中,各級政府往往更注重城鎮養老服務設施與機構建設,忽視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服務設施與機構建設。據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9月,城市社區養老服務設施覆蓋率達78.8%,而農村社區養老服務設施覆蓋率僅為45.7%[11]。相比城市地區,農村養老體系建設面臨更多困難,農村集體收入較少,養老標準較低,養老機構后續運轉比較困難等,這就要求各級財政加大對農村地區養老服務補貼的政策規劃和資金投入。
(三)結構失衡
第一,政府對不同所有制養老機構的補貼存在差別化待遇[12]。以天津市為例,在對養老機構的床位建設補貼上,由政府投資新建或購置建設并形成產權的養老機構,每張床位享受一次性3萬元的建設補貼,而由社會力量投資新建或購置建設并形成產權的非營利性養老機構,每張床位僅享受1.5萬元的一次性建設補貼,二者相差一倍。此外,社會力量建成的營利性養老機構不享受任何財政補貼。而從實際建設成本看,據估計我國養老機構每張床位建設成本約為5萬元[13],高成本不免導致民辦養老機構的定價較高。
第二,針對不同所有制養老機構的差異化補貼造成了養老服務市場的不公平競爭,不公平的起點造成了民辦機構實際運營的困難。政府投資興辦的公辦養老機構在土地、資金等方面都更為充足,因此其在環境和設施的建設上要比大部分民辦機構完善,導致老年人搶奪床位資源。而另一邊,據杭州物價局測算,杭州公辦養老機構以第二社會福利院為例,老人每月開銷約為1500元左右,而民辦養老機構以愛康家園為例,老人每月至少花費2000元[14],高昂的收費讓不少老年人望而卻步,“一床難求”和床位空置現象并存。民辦機構的低入住率打擊了社會資本的投資積極性,對民間資本形成了擠出效應。
此外,在養老服務財政補貼的結構中,還存在“重建設輕運營”的傾向[15],往往只強調養老機構的建成數、床位的增加量以及養老從業人員的培訓次數,并不重視床位建成后的入住率、機構建成后的運營情況和從業人員培訓后的效果水平。似乎只是為了單純地完成任務規定的客觀指標,并不在意完成任務的效果和資金使用的效益,直接表現就是對養老服務機構建設期補貼遠遠高于運營期補貼(見表2)。長此以往,將造成養老機構入住率和設施運營率均偏低,導致設施資源的巨大浪費。
四、我國養老服務財政補貼政策的糾偏
(一)加大財政補貼力度,優化資金地區投向結構
考慮到我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以及當前養老體系基礎的薄弱特點,各級政府在制定相關財政補貼政策時,應加大財政補貼力度。用于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資金規模在財政總支出中的占比同樣應逐年提高,其財政支出增長率應明顯高于平均增長率。具體而言,各地財政有必要提高補貼標準并建立補貼標準隨時間推移的自然增長機制,適度降低享受補貼的門檻,放寬外資準入標準,提高補貼標準,并結合市場現狀引入新的財政補貼政策,多角度出發擴大補貼政策的輻射范圍,增加財政投入資金。
此外,在投向結構上,考慮到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差異,當中央政府對東部發達地區的養老服務建設進行補貼時,中央財政投入規模可以適當地小于當地的投入規模,對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增加投資比例,以達到在國家一級保持相對平等的狀態;加快補齊農村養老服務短板,全面構建滿足農村老年人需求的新時代農村養老服務體系,著力實施鄉鎮敬老院改造升級工程,對服務功能較弱、供養人數較少的敬老院進行改造提升,結合實際打造建成區域性養老服務中心。
(二)消除政策歧視,制定并落實促進民辦機構發展的補貼政策
養老服務機構的經營性質劃分與政策扶持不清晰,營利性質與公益性質的關系尚未平衡,補貼差異較大,加之養老產業經營利潤低和投資回報期長的客觀特點,造成民間資本進入該領域時瞻前顧后、顧慮重重。
面對這一困境,在制定養老機構補貼政策和補貼標準時,除了考慮養老機構發展規模外,還應將不同養老機構的地理位置、土地和租金成本等因素納入考量范圍,通過梯度化的方式實現針對性補貼。平衡民辦養老機構營利初衷與公益性質之間的關系。在辦好公辦養老機構的同時,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大對民辦養老機構的資金扶持力度,特別是兌現民辦養老機構應當享受到的土地、稅收、用水、用電等一系列優惠扶持政策。做到公辦與民辦在政策支持上一視同仁,同時加強監管,通過建立起完整的養老機構入住老年人數據統計網絡等方式,對服務硬件、服務態度、服務質量等實施監管,使“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落到實處。
(三)推動新時代養老補貼政策落地,引領社會投資方向
在現有養老補貼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財政投資績效目標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激發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投資的積極性和活力。建議財政資金適度降低固定資產直接投資比例,提升養老服務支出比例,重點加大居家、社區養老補助;支持醫養結合新型養老機構的建設發展,鼓勵養老機構接受失能失智老人。優化財政資金投資的適用性,發揮其對社會投資的風向作用[16]。
此外,應創新財政資金使用方式,積極搭建合作平臺,探索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方式,引導和撬動社會金融資本加大養老服務投資。例如,可嘗試以中央財政資金發起設立養老服務產業發展引導基金,以參股形式設立地方性養老投資基金。并引入市場化運作模式,實現資金滾動使用,提高資金運用效率。
[參考文獻]
[1]? 陳東升.長壽時代的理論與對策[J].管理世界,2020,(4).
[2]? 鄭功成.中國社會福利改革與發展戰略:從照顧弱者到普遍全民[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2).
[3]? 發改委:我國養老服務床位數超761萬張,養老機構逾3.4萬個[EB/OL].中國新聞網,2020-05-12.http://news.china.com.cn/txt/2020-05/12/content_76035919.htm.
[4]? 詹姆斯·M·布坎南,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公共財財政與公共選擇:兩種截然對立的國家觀(第1版)[M].類成曜,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
[5]? 楊燕綏,張弛.開展養老服務立法 推進養老服務體系建設[J].北京人大,2014,(7).
[6]? 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十三五”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投資問題分析與建議[J].宏觀經濟管理,2016,(3).
[7]? 董紅亞.我國養老服務補貼制度的源起和發展路徑[J].中州學刊,2014,(8).
[8]? 陳志勇,張薇.我國養老服務市場化中的財政補貼方式及標準測度[J].求索,2017,(1).
[9]? 民政部:已基本實現老年人高齡津貼、服務補貼和護理補貼制度全國覆蓋[EB/OL].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2019-01-03.http://www.mzzt.mca.gov.cn/article/zt_2019gzhy/mtgz/ 201901/20190100014264.shtml.
[10]? 李萌.支持養老服務體系發展的財稅政策分析[J].中國財政,2014,(4).
[11]? 民政部: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分別達78.8%和45.7%[EB/OL].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2019-09-27. http://mzzt.mca.gov.cn/article/zt_zl70n/fbh/201909/20190900019958. Shtml.
[12]? 梁譽.我國養老服務的現狀、理念與發展路徑[J].老齡科學研究,2014,(5).
[13]? 夏金,李放.江蘇財政支持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問題與對策[J].江蘇社會科學,2017,(1).
[14]? 張慶偉.公辦養老機構定價探討——以杭州為例[J].社會科學家,2015,(8).
[15]? 甘煒,劉向杰,于凌云.養老服務市場化財政補貼與調整機制研究[J].地方財政研究,2017,(11).
[16]? 楊翠迎,魯於,楊慧.我國養老服務發展中的財政政策困境及改進建議——來自上海市的實踐與探索[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5).
[責任編輯:胡? 梁]
Unbalance and Correction of Fiscal Subsidy Policy of Elder Care Service in China
——Based on Quasi-Public Goods Theory
YIN Jun, DUAN Ya-na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zed elder care service system of “home-based, community-supported, and institution-supplemente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oal of Chinas elder care service reform.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quasi-public goods of the elder care service, its development requires two-way market and financial support. With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Chinas elder care service policy, this paper found that,there are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fiscal subsidy policy of elder care service, such as insufficient total amount, regional imbalance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following thre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lder care service system: Firstly, we must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financial subsidies, optimize the regional investment structure of funds; Secondly, we should remove policy obstacles, implement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attracting private capital; Thirdly, we are supposed to enhance the applicability of financial funds investment, and lead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elder care investment.
Keywords: elder care service; fiscal subsidy policy; quasi-public goods; ag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