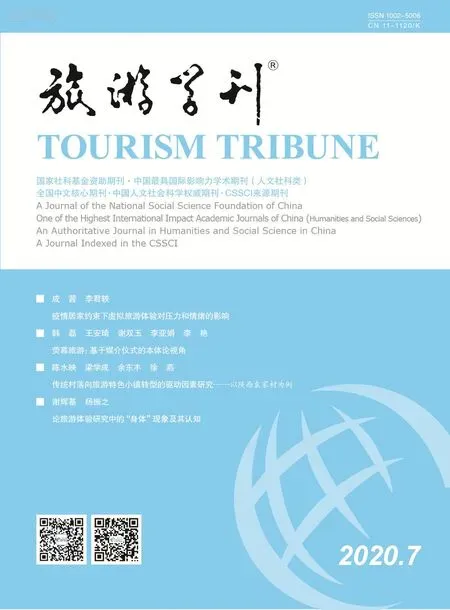“主客關系”視域下“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的融合發展
李勁松 王永琴
1985年“歐洲文化城市”的評選,拉開了世界“文化之都”建設的序幕,并成為人類城市發展史上最為引人矚目的全球性現象。“文化之都”在本質上又是全球化下“人與文化”發展的新理念和新實踐,其必然涉及全球化語境中“人與人”的關系、“文化與文化的關系”兩大核心議題。旅游發展與“東亞文化之都”建設具有天然的耦合關系,旅游觀光和休閑度假是“東亞文化之都”的基本屬性和重要職能。日本學者磯村英一認為文化城市“又多屬于觀光城市”1。國內學者左大康也認為文化城市是“以宗教、藝術、科學、教育、旅游、文物古跡等文化機制為主要職能的城市”2。這決定了作為“東亞文化之都”建設發展主體的“人”必然由東道主和游客共同構成,也決定了作為“東亞文化之都”必然是在東道主代表的本地文化和游客代表的外來文化基礎上再構建的交融共享的新文化。文化人類學尤其關注“文化的人”和“人的文化”。因此,基于人類學主客關系視角對“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融合發展中的東道主與游客這一“人與人”的關系和對東道主本地文化與游客外來文化這一“文化與文化的關系”進行深入探討,對推動以“東亞文化之都”為代表的文化城市相關理論的進一步構建及其實踐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客人到家人”——在“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融合發展中構建東道主與游客融合的新關系
“人”是“東亞文化之都”建設首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戴立然在其關于文化城市的研究中認為“現代城市的核心是市,市的核心是人”1。索艷琳也認為“從內在要求來看,文化即‘人化,文化城市即‘人化城市,它以人為核心”2。具體而言,人的問題就是“東亞文化之都”的主體定位問題,即“東亞文化之都”為誰服務和為誰發展。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具有明顯旅游屬性的“東亞文化之都”的“人”的主體毫無疑問既包括作為“我者”的本地人——東道主,還包括作為“他者”的外來人——游客,所以“東亞文化之都”建設必須服務于這兩大主體,而如何處理好這兩大主體的關系并使其融為“一體”,則成為解決“人”這一核心問題的關鍵。在“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融合發展中,這一和諧關系的關鍵就在于建構“從主客關系到家人關系”,因此,“東亞文化之都”要實現本地人和外來人的“人”的深度融合,打造“家人”之都,構建“家人”關系。
人類學家最早強調了對東道主和游客間的主客關系進行研究的必要性。1963年,人類學家努涅斯(Nunis)在對墨西哥一個村莊周末旅游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在分析研究對象時必須考慮主客交往的因素,而“主客范式自1978年史密斯提出后,日漸成為旅游人類學研究的重要范疇”3,“在所有的旅游人類學研究案例中,研究的中心應該是主客關系。”4在人類學家看來,旅游場域中的主客關系是一種沒有情感而為經濟和政治力量所支配的“異化”關系。努涅茲指出東道主與游客關系在市場經濟下的非感情和工具性特征,他們之間總是有一種社會距離和社會慣例的不同,而這些東西卻不存在于鄰里之間、同事之間和老鄉之間”5。厄里把主客關系置于權利維度中進行探討,認為“作為‘凝視主體的游客和作為‘凝視對象的東道主居民間體現出權利的操控關系,權利使游客成為‘凝視主體,而東道主成為“凝視對象”6。納什更是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旅游者在東道主地區的主導地位這一角度,強調旅游成為了一種帝國主義形式,主客關系成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關系。一些研究也認為,游客也會在主客關系中作為弱勢一方,成為“被劫持者”。因此,旅游中主客形成二元對立成的常態。
“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融合發展中勢必需要突破這一由來已久的藩籬。那么能夠超越“主客”關系而使兩者由“二元二體”對立轉變為“二元一體”融合的更高范疇的概念是什么呢?筆者認為應該是“家人”這一概念。盡管個別學者關于“主客關系”的研究已經開始觸碰到“家”的概念,例如李春霞就談到,“‘家不論是在旅游人類學‘主-客框架里,還是在傳統中國‘主人-客人關系中都是關鍵的節點”③,但可惜未能再前進一步深入聚焦到“家人”這一關鍵概念。從“客人到家人”,將是“東亞文化之都”全面構建東道主與游客的新關系,實現東道主和游客這兩大主體的融合,這才是“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融合發展最為核心的任務。沒有了主人和客人,只有“家人”的時候,“東亞文化之都”才能成為“幸福家園”。涂爾干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為這一融合提供了理論路徑,那就是“當主客之間具有相似的家的信念、參與相似家的活動并且存在互動行為,家的情感凝聚就會形成”,而“有家的情感的人們就是家人,有家的情感的地方就是家園”7。
二、 從“多元到一體”——在“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融合發展中打造基于地方性知識的特色文化與外來全球化文化融合的“文化共同體”
文化是“東亞文化之都”的根基。相關學者對文化城市的概念界定都是圍繞著“文化”這一核心概念展開的,并充分強調了文化對于文化城市的核心意義。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文化》中全面論述了城市發展和文化發展的因果關系8。戴立然指出“‘文化城市是動詞,特指用那些文化因素‘濡化城市。”①劉士林認為,“文化城市核心是一種以文化資源為客觀生產對象,以審美機能為主體勞動條件,以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景觀創造等為中介與過程,以適合人的審美生存與全面發展的社會空間為目標的城市理念與形態。”1文化作為“東亞文化之都”的根基最關鍵體現在文化是“東亞文化之都”的核心資源上,而這一核心資源具體而言既包括本地獨有的地方文化,又包括源于不同客源地以游客為載體的多元外來文化。因而,“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融合發展背景下,如何正確處理“東亞文化之都”地方性文化與外來游客文化所代表的全球文化的關系,使“地方與全球”文化都能更好地服務于“東亞文化之都”建設,是“東亞文化之都”建設必須解決的又一個關鍵問題。
地方性知識是文化人類學分支學科之一的、闡釋人類學的重要概念,由美國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其“既包含有非普遍性、非科學性的知識,也保留那些具有著地方特征于特定條件生成的知識”2。楊庭碩認為,“地方性知識就是本土知識,指各民族在特定自然、社會環境下與之互動并構建的知識體系”3。當前,地方性知識已經成為一種方法論,強調從主位的立場去理解文化,作為對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反思,而強調地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獨特價值和意義。正如李清華指出,“地方性概念試圖表明,每一種文化都具有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存在價值”4。
地方性知識為“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融合發展中如何處理東道主代表的地方本土文化與游客代表的全球化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即要在主位的立場上去理解不同的外來文化,同時更要認識到本土地方性文化的獨特價值,增加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此基礎上以本土地方性文化為根基和特色,積極吸收借鑒外來的全球化多元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終實現從多元到一體,成功打造基于地方性知識特色文化與外來主流文化融合的城市文化共同體。
綜上所述,文旅融合下的“東亞文化之都”建設面臨著如何處理東道主和游客關系、地方性文化和全球化文化關系兩大基本問題,而文化人類學提供的“從客人到家人”和從“多元到一體”的人的融合與文化的融合思路,為“東亞文化之都”與旅游融合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論啟示和積極的實踐借鑒。
(第一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文化與旅游休閑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全國休閑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第二作者系北京聯合大學旅游學院研究生;收稿日期:2020-05-16)